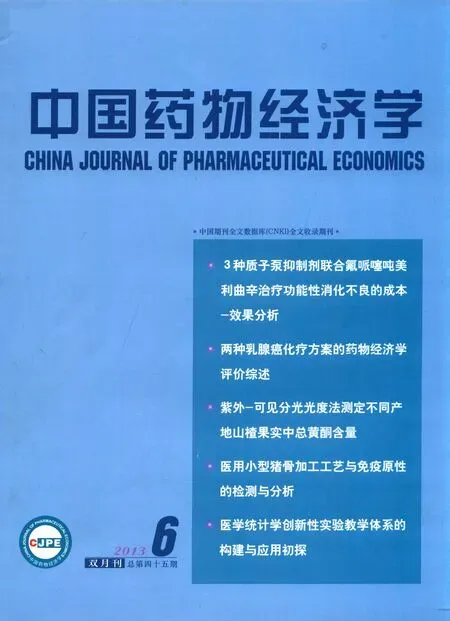中醫思維在中醫藥發展創新過程中的重要作用探析
漆亞學 朱向東
中醫思維在中醫藥發展創新過程中的重要作用探析
漆亞學 朱向東
本文探討了中醫思維在中醫藥發展中的重要性,分析了中醫思維在中醫教育、科研、臨床方面的研究和運用現狀,提出了中醫思維是影響中醫健康發展、創新、生存的重要問題,并針對中醫思維弱化和缺失的問題,提出了中醫思維應該滲透到中醫教育中、中醫科研要以中醫思維為指導、中醫臨床需要多種中醫思維介入的建議,認為中醫思維是中醫藥創新發展的根基,在中醫藥創新發展過程中要高度重視中醫思維研究和運用。借此拋磚引玉,以供同道商榷。
中醫思維;應用;中醫藥;發展創新
1 中醫思維在中醫藥發展中的重要性
思維是人類有別于其它動物最本質、也是最顯著的特征,是決定人類生存狀態和發展走向的關鍵之一。大到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小到一門學科、一門技術,乃至每一個人,其思維方式直接決定著生存狀態和發展[1]。中醫藥要發展,必須要患者接受,才能有生存的空間;中醫藥走向世界,必須讓西方人理解,中醫藥才能真正走出國門。可是,中醫不如西醫容易接受、理解,盡管很多中醫學者對中醫理論的認識十分深刻,認為中醫有巨大優勢,療效顯著,可是,很多百姓、患者真正理解感到困難,甚至一些中醫從業者也不理解。如此,中醫的生存和發展必然要受到挑戰,年輕中醫從業者應該有危機感。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局面,其關鍵問題是中醫思維的傳承與運用問題。比如,中醫學“氣”的概念,是動態的、功能的,受過中國傳統文化熏陶的人們就容易理解,受到西方物質實體尋找思維教育的人,就會說氣是看不見的,無法理解。人和人見面,中國人會說,你的氣色真好,這就是運用了中醫的取象思維,判斷了人體健康狀況。而按照西醫思維,不經過檢查化驗,無法判斷健康狀況。所以,中醫思維是獨特的,是在中國文化背景和哲學基礎上形成的,用獨特的視角去感知和認識生命、世界,并以這種思維方式結合中醫理論認識和診治疾病。這種思維與西醫有著本質的不同。比如,中醫學重視宏觀整體,西醫學重視微觀分析;西醫學以“生物醫學”為主;中醫學則強調“天人合一”;西醫認為微生物的侵襲是病因;而中醫學強調“正氣存內,邪不可干”;西醫學重視局部病變,中醫學重視整體反應;西醫學強調要找物質結構,采取“對抗”、“剿殺”,如抗菌、消炎等;中醫學重視“調和”、“從化”,強調人體自身調節能力等。中醫藥要大發展、創新以及走出國門,首先要普及和傳承中醫思維,中醫思維有很多種,如“辨證思維”、“系統思維”、“直覺思維”、“經驗思維”、“取象思維”、“邏輯思維”、“靈感思維”等,也有很多具體思維方法,諸如“順勢”、“求同”、“求異”、“逆向”等。掌握了中醫獨特的思維方式,理解中醫藥涉及的氣、陰陽、五行、氣化等理論會十分容易。反觀近年來中醫的發展過程中,由于中醫思維的運用重視程度不夠和缺失,導致中醫藥在一些方面的發展失去了固有的特色和優勢,甚至違背了中醫發展規律。近來,受西方文化的沖擊,傳統文化重視不夠,“中醫思維”對于現代中醫界變得生疏,并直接影響到了中醫理論教學、科研和臨床。由于中西醫思維方式上的差異,完全用西醫思維方式詮釋、理解中醫理論體系無疑是行不通的。為什么中醫和西醫思維方式如此不同,是因為中、西醫誕生的文化背景不同,中醫思維是中醫文化的靈魂,深深刻有中國傳統文化的烙印,比如中國傳統美學與傳統藝術主張“中和”為美,“和”體現了中國傳統藝術的辨證思維。要達到“和”,其重要法則是要掌握好“度”,過或不及都不為美。“中和”是一種模糊而崇高及含蓄的美。“和”同樣是中醫治療的最高目標。欣賞字畫要看其意境、看其氣勢,這和中醫望氣色斷病情同出一哲。中醫思維的形成直接影響著中醫從業者的素質修養和成才,是決定其診療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當前一部分中醫大學生和青年中醫,對中醫缺乏信心,中醫思維欠缺,臨床能力不足,其中有少部分中醫畢業生甚至背叛中醫、攻擊中醫,或成為偽中醫、庸醫,這種狀況嚴重影響了中醫藥事業的傳承、發展和生存。
2 中醫思維研究與運用的現狀
中醫的發展離不開中醫的教育、科研和臨床,應該說,中醫藥教育、科研和臨床均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如高等中醫院校發展迅速,培養了大批高級中醫藥人才、中醫科研973項目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諸多領域的資助,取得了豐碩成果;中醫養生知識得到了很好的普及、中醫臨床名家輩出,但是認真分析目前中醫的發展現狀,確實存在中醫思維弱化的問題。
2.1 中醫思維與臨床中醫界的名老中醫、國醫大師都是運用中醫辨證思維的典范,所以臨床療效顯著。但是,中醫臨床也存在中醫思維,特別是中醫辨證思維弱化的問題,例如,治療普通的感冒,患者自行購買速效傷風膠囊退燒,甚至很多中醫師也不辨邪氣之寒熱,必用抗病毒藥物,使用銀翹解毒丸。癌癥就必用抗癌中藥,炎癥則必用清熱解毒中藥,上火就用瀉火藥物,而按照中醫思維方式,如姜湯散寒退燒、扶正固本治癌、引火歸源治火、疏通氣血治療炎癥等方法卻被棄之不用。這說明中醫臨床上存在不運用或不會運用中醫辨證思維的問題。沒有按照中醫辨證思維開方,只能叫做“中藥的處方,西醫的靈魂”,其作用于人體的藥物效應已不能完整地體現中醫的整體辨證論治系統理論的效果,而副作用卻大大彰顯。如“日本小柴胡湯事件”、“英美馬兜鈴事件”、我國的“木通致腎臟損傷事件”,究其原因不外乎是現在的中醫醫師不能完整系統地運用中醫系統思維的方法,不運用辨證論治的原則,而僅憑辨病對癥的方法錯誤地使用中成藥而引起的嚴重后果。
張仲景強調“有是證、用是方”,黃帝內經提出“有故無隕,亦無隕”,都強調中醫臨床首先是辨證,根據證下藥,而不是根據病開方。懂中醫思維,砒霜、烏頭雖然毒性大,但會用其救人,不懂中醫思維,人參、靈芝雖為上等補品,但也能草菅人命。現在臨床上真正具有中醫思維、辨證論治的中醫人才匱乏,造成中醫臨床陣地萎縮,所以中醫思維的問題應該引起有識之士的高度重視。
2.2 中醫思維與科研中醫的科研到底應該怎樣開展,一直是中醫發展的困惑。多年來,中醫藥的科研,多是以現代臨床醫學的觀念、方法和技術,對傳統中醫學進行驗證、詮釋和創新性的研究,尋找中醫藥診斷治病的物質基礎成為主流。而真正能為中醫臨床服務、體現中醫特色和中醫思維的科研成果比較少。比如脾虛、腎虛證的研究,只是證實其與多系統都有關系,經絡的研究,因為非要找出物質實體而最終失敗。雖然這種研究取得一定成果,特別是對于在世界范圍內普及中醫,便于西方人的理解和認識,但同時對中醫學術發展卻帶來了不少負面影響。
有學者說[2]:“傳統中醫學的當務之急并非是去想方設法的求證自己是否合乎現代科學,更不是去采用線性科學的方法找尋驗證自己本身的物質基礎,而是要集中精力、認真細致地去考慮清楚自己本身的優勢在哪里、劣勢在哪里,以及怎樣好好地去發揚、去利用這個優勢來宏揚傳統中醫學,不要處處與現代臨床醫學一爭短長。否則,目標錯誤,精力分散,舍本逐末,很有可能在下個世紀傳統的中醫就再也無法在醫學立足了”。真正的中醫科研應該按照傳統中醫學自身幾千年傳承下來固有的創新體系、思維模式開展,為臨床療效提高服務,而不是盲目的應用現代科技手段闡釋其科學性。
2.3 中醫思維與教育在“中醫科學化”、“中醫西醫化”思想影響下,中醫教育方面因為缺乏中醫思維的教育與傳承,導致學生沒有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比如“肝生于左、肺生于右、腎主生殖”等中醫理論的理解,很多學生會受西醫思維的影響陷入實體器官的誤區。由于高等中醫院校課程設置基本中、西醫各半,其教育結果是造成了學生中醫不精、西醫不通。特別是研究生教育,雖然碩士、博士論文也可見到一些中醫文化、中醫思維的研究,但是精通分子生物學實驗技術的碩士、博士更多,國家師承措施雖然是非常好的導向,但是其傳承面不寬,中醫大部分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依然缺乏中醫思維的根基,一些頗有權威的中醫老專家們說:“中醫研究生教育只是培養了大批為老鼠治病的醫生”。為此,很多老中醫藥專家十分憂慮傳統中醫未來的命運。雖然這種說法有失偏頗,但是終究折射了在中醫教育中存在的巨大危機——中醫文化、中醫思維的弱化,中醫將失去靈魂。
3 中醫思維在中醫健康發展創新中的思考與建議
3.1 中醫思維應該滲透到中醫教育中50年代以來,我國前后在全國各省市陸續成立了數十所高等中醫藥院校,確立了傳統中醫教育的現代科學體制和系統的理論加實踐的課程體系。雖然高等中醫藥院校教材歷經變革,但整體課程體系的基本結構卻并沒有發生明顯的變化,仍然遵循著傳統中醫基礎理論與臨床診治技能相結合的知識教育模式,而對于中醫思維方式、方法的系統訓練非常之缺乏。
中醫思維方式是中國傳統哲學和現代科學思想在醫學領域的闡釋和結晶,呈現為系統整合型的意象思維方式,與現代科學的邏輯思維有著本質的差異[3]。對于學習中國傳統中醫學的學生而言,從小到大接受的均是現代科學體系的邏輯思維方法,再加上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傳承系統基礎非常薄弱,因此導致中醫學學生思維方式上的巨大反差,理論認知上的偏頗非常顯著,一方面使學生對中醫理論和整體辨證論治診療方法在理解、接受上異常艱難,對傳統中醫學的認同性、理解能力明顯降低,專業思想不穩固,難以樹立起充分的信心;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系統完整的中醫理論思維方式訓練,造成中醫藥院校培養出來的中醫醫者不能很好地融會貫通運用傳統的中醫理論系統思維,直接影響了傳統中醫臨床上的辨證論治效果。
同時,由于對傳統中醫與西方醫學、現代臨床醫學及其它現代科學之間思維方式的異同點缺乏明確的認知、系統完善的理解,進而影響了學生的創新思維能力。所以中醫教育中,從本科階段就要設置中醫思維教育和訓練課,碩士研究生、博士階段要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哲學與中醫理論、中醫思維角度,深層次認識中醫思維的重要性,甚至可以開展中醫思維的必修課,就像博士研究生必須學習分子生物學一樣,必須掌握中醫思維方法。當然,中醫教育的真正發展需要多方力量共同努力,如果從小學生開始就加強中醫文化、中國哲學的傳承,必然會為中醫教育增色。
3.2 中醫的科研要以中醫思維為指導
3.2.1 中醫理論研究用西醫理論詮釋中醫理論的先進性、科學性,特別是用系統生物學等具有整體特色的手段研究中醫理論是有價值的。例如臨床上較有影響的“腎陽虛證的研究”、“活血化瘀的研究”、“脾實質的研究”、“肝藏象的研究”、“經絡實質的研究”等。但這些研究項目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問題,大部分研究項目是借用現代臨床醫學的手段與方法來描述、闡釋中醫理論體系的物質實體,從中醫理論體系的主體方面而言,基本上還屬于詮釋學的研究,對中醫理論體系的主體發展根本不具有任何實際意義,有時甚至出現把簡單模仿現代臨床醫學模式當成學術創新的現象,造成傳統中醫學術水平一直徘徊在一個低水平上,一直循環重復,而沒有進一步新進展。傳統中醫學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巨大,與現代醫學的思維方式有根本上的不同,中醫偏重綜合整體,著意功能虛體,目的在于物與人、自然之性,共存共榮。因此,對中醫理論的研究,還必須堅持中醫研究的取向,以中醫思維為指導。張景岳,因為四十歲后飲酒經常腹瀉,提出命門學說,創制右歸丸;李東垣,發展脾胃學說,創立補中益氣湯;清代溫病大家提出溫病學說,都是中醫理論研究創新的典范,這種理論研究的重要價值就是臨床應用,百姓受益,中醫發展。當然,可以吸收運用現代科技成果,如運用系統生物學,網絡藥理學等手段研究中醫的“形神合一”、“整體觀念”、“生克制化”的機制,也是有價值的。但是,完全脫離中醫思維指導的理論研究導向是有問題的。所以,中醫理論的研究、創新,必須堅持中醫思維的系統整體與辨證思維的特點,適當吸納現代科技,重視總結中醫臨床經驗以及理論思維方法,對臨床、實驗以及理論思維的成果進行有機的整合,以建構傳統中醫與現代中醫傳承結合的理論體系,實現中醫學的自主性發展。
3.2.2 中藥、方劑研究不能唯成分論西藥治療疾病的物質基礎、活性成分、作用靶點十分明確,這是西藥治病容易被理解、被接受并迅速發展的原因之一。受該種物質論的思維模式的影響,很多學者開始思考中醫藥為什么能治病、治病的機理是什么、中藥治病的活性成分和物質基礎是什么?于是中藥的活性成分和物質基礎研究百花齊放,從研究的結果看來,確實有很多可喜的結論,比如人參皂甙、枸杞多糖、當歸多糖、芍藥苷等,都是中藥研究中發現的活性成分。但是,這些活性成分是無法代替人參、枸杞、當歸、白芍等整體功效,換句話說,這些物質基礎的運用已經背離了中藥治病的基本原理和辨證思維,已不是中藥。從古至今,中藥都不是以成分作為其治病的依據。雖然現代科技手段研究中藥并發現了很多物質基礎,一定程度上對中藥的認識和功效的拓展是有意義的。但不能因為發現了成分和物質基礎,就以為掌握了中藥治病的規律,偏離中醫藥的理論依據,把精力與錢財花在研究一藥或一方的有效成分上,把中藥與西藥強行接軌,盡量使中藥“西化”的研究創新模式是值得商榷的。
那么中藥到底怎么治病,治病的原理是什么呢?清代名醫徐洄溪的論述:“藥之用,或取其氣,或取其味,或取其色,或取其形,或取其質,或取其性情,或取其所生之時,或取其所成之地。”,這就是說,中醫歷來是從中藥的形、色、氣、味、質、時、地、性等諸方面來研究中藥藥性和功能的,中藥治病的基礎是四氣、五味、升降浮沉,其性能是取天地之精華,本自天成,個別活性成分無法解釋其整體效用的[4]。又如地龍、代赭石、皂角刺等中藥的研究,不能一味找其物質實體,因為古人發現其功效是用取象思維和臨床時間的結合,地龍能通絡,是因為其性善鉆;皂角刺能透膿,是因其勢善通;代赭石降胃氣,乃因其重而勢下行。所以中藥研究者,特別是中青年中醫學科研工作人員與臨床工作者的任務,主要就是去探尋和發現這些中草藥的“理”與“情”,尋找摸索它所最適用的病機,從而運用于臨床。要重視“借方藥之力,觸發機體內在的自我調節能力”,以求達到陰陽自和,其病自愈的目的,這也是傳統中醫治療疾病與現代臨床醫學治病的根本區別。
王孟英說:“用得其宜,硝黃可稱補劑;用失其宜,參術不異砒硇”。所以,研究發展中醫藥,不能一味從藥理研究、化學成分,以及現代科學的角度來闡述分析中醫藥,更加不能作唯成分論者。
3.2.3 中醫臨床需要多種中醫思維的介入現在,國內的很多中醫藥專家都已明確認識到,完全使用現代醫學的檢測、化驗的手段來評價評估中醫藥的治療效果問題,非常的不符合傳統中醫藥自身發展的規律,反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醫藥的發展。那么,如何制定一個符合中國傳統醫學自身發展規律的療效評價體系,就是當前傳統中醫藥發展形勢中所面臨的急需解決的問題。
在遙遠的古代,并沒有現代這些高科技支撐的化驗、檢測儀器和各種的新型手段,那古代的中醫藥學家們到底是在運用什么方式來判斷中醫藥的臨床療效呢?或者說古代中醫療效評價的核心問題到底是什么呢?筆者認為,中醫學是一門綜合的、充滿民族集合智慧的科學,其重要的特征是中醫有自己的獨特思維。中醫學的發展,從理論到臨床,實踐出真理,其本質是思維方式的合理運用。中醫思維應該是中醫臨床療效評價的基石。比如,按照中醫思維,取象思維在中醫臨床療效判定方面應該發揮重要作用。眾所周知,人的生命處于健康狀態,必然有健康的征象,當生命處于病態,必然有病態的征象。那么,哪些是病態的征象,哪些是健康的征象呢?
筆者認為,對于病態征象的把握,既要有醫生自己的客觀感覺和判斷,更要結合患者本身的主觀感受和體會,中醫臨床如能采用征象思維判斷療效,應該是一個較為合理的途徑:如醫患借助征象思維共同體察患者的七種能力。一曰:趨輕能。“輕身延年”是歷史的結論,是氣勝形的表現,是正氣得到補償和恢復,而邪氣消減的表現;因此,可以認為此項治療是產生了趨佳效應,是有效的。二曰:趨柔能。柔者生之途,摶氣可以致柔。“僵”與“脆”都是“器”少“氣”的表現。嬰幼兒富有生生之氣,故柔;老年人則生氣已虧,故肢僵骨脆;動物皆然,植物亦然,病者何其不然?反之正氣得復,邪氣衰退,骨正筋柔,故而其自應被認為是治療趨佳效應之一。其它如趨衡能、趨展能、趨味能、趨趣能、趨便能,也是判斷療效的途徑。
此外,如醫患共同勘對五種生命條件,滋潤德、溫欣德、安定德、出入德、升降德;共同檢驗精、氣、神三寶等,均需要象思維的介入。七能趨佳、五德漸回、三寶來復,自為疾病向愈之象,在此基礎上再以現代醫學的檢查化驗為參考,中醫的臨床療效判定就不會迷失方向了。
[1] 張登本,孫理軍.中醫基礎理論中概念的困惑與思考詮釋[J].中醫藥學刊,2004,22(9):1573-1575.
[2] 邢玉瑞.中醫思維方法[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10.
[3] 邢玉瑞.《黃帝內經》理論與方法論[M].西安:陜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04.
[4] 劉長林.中國系統思維[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1-8.
R2
A
1673-5846(2013)06-0049-04
甘肅中醫學院,甘肅蘭州 73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