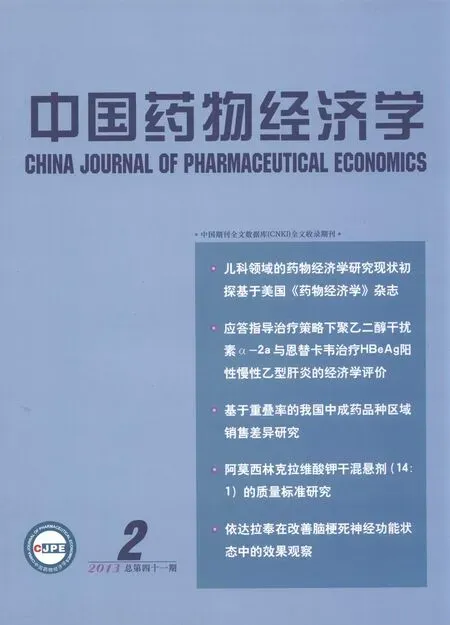試論中醫的養生防病觀
谷雪峰佟子林
試論中醫的養生防病觀
谷雪峰1,2佟子林2
西方醫學模式在應對世界性的醫療危機時越來越顯得蒼白無力,而中醫的養生防病觀,相對于現代醫學的消極醫學觀,是一種更為積極的養生防病觀。
中醫;養生;防病觀
回首20世紀,美國同時實施了人類登月計劃和攻克癌癥計劃,人類登上了月球,癌癥至今還在施虐,可以說,人類對客觀世界的改造所取得的成就是空前的,然而比這更重要的人類健康方面的成就卻微乎其微,不能治愈的疾病越來越多,絕大多數的人不能終其天年,世界性的醫療危機席卷全球造成醫療危機的根源就在于現代西方醫學模式長期統治醫學的結果。不同的醫學模式往往對應或折射出不同的疾病觀、治療觀、健康觀,從而影響著醫學發展的方向,而西方醫學模式錯誤地把治愈疾病視為其首要目標,并且在“努力找病,除惡務盡”的路上越走越遠。重新審視中醫對疾病、健康的看法,對于解決現代醫療危機具有重大的意義。簡而概之,中醫的養生防病觀主要包括如下內容。
1 整體觀
醫學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怎樣去看人體以及用什么去看人體,用顯微鏡看它,人是“一碗細胞”、“一袋基因”、“一兩蛋白質”;如果用心去看它,就會發現人與宇宙萬物原本就有一種深刻的聯系,人們與萬物息息相通,人的生命在時空中,絕不是孤立的,與其共同生成,共興共榮、共侮共毀、同構同律。
與西醫發展向微觀的、分析的進路不同,中醫所一以貫之的是一種宏觀的、整體的進路,這是中醫區別于西醫的顯著特點和優勢。中國人立足于整體,認為整體是生命的基本特征,先人很早就認識到生命與整體、生命內部與外部環境之間以及生命內部各部分之間存在著相存相依、和諧完美的關系。對這些關系的破壞,將意味著疾病甚至生命的完結。
受《周易》整體觀的影響,中醫立足于從整體把握生命、看待健康、治療疾病。《黃帝內經》將《周易》天人整體觀汲取到醫學之中,提出了“人與天地相參”的觀點。《黃帝內經》呈現了一個宏大的整體醫學模式,一種天人相參、人與天同、天人合一的整體觀:天地人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人是處在宇宙大環境和社會大環境下的精神生命。自然的變化一定會影響人體,俗話說:冬日打雷,十欄九空。
中醫在宇宙的大背景下看待生命、研究生命,認為人體與宇宙存在著驚人的相似之處,有著相似的結構特征并遵循著共同的規律,這個規律被稱為道。普利高津在《探索復雜性》中指出:中國文化具有一種遠非消極的整體和諧。中醫的“望、聞、問、切”便是整體觀的應用。根據整體觀念,人本身也是一個整體,身體內部的變化都會從體表上表現出來,身體的外部是身體內部的一個“相”。有了整體觀,中醫治療時不再拘泥于“頭痛醫頭”,而采取“頭痛醫腳”即頭痛從腳上治,治胃病從腿上治等一些內病外治的方法。這是天人整體觀在治療上的應用。
這種天人相參的整體觀是深度的主客體合一,是主客融合的最高層次,與現代生物全息能理論有異曲同工之處。天人整體觀最終是要達成天人合一、主客依存、和諧共處的理想境界,而中醫學的本質正是引領人們向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的生命本質回歸。
2 和諧觀
西方人重事實,中國人重關系,實際上陰陽、五行、八卦都是關系學。陰陽是最基本的關系,五行是相對復雜的關系,八卦是更為復雜的關系。關系雖然看不見,有質無形,但是卻更本質,通過調整這些關系就能夠使事物的結果發生改變。陰陽作為最基本的關系,如果出現了不平衡,就會破壞生命的和諧。生命和諧論認為生命能夠和諧存在,對于出現的不和諧可以通過調節陰陽關系重新達到一種新的和諧。生命的本質是一種和諧存在,也只有和諧才是生命的正常存在。
“和諧”最早出自《周易》,根據《周易》的觀點,世界皆是陰陽。“立天之道,曰陰曰陽。”[2]《周易》以陰陽為符號,從始至終都在論述一個東西:陰陽及陰陽的變化。《莊子?天下篇》曰:“《易》以道陰陽”。陰陽是宇宙中最基本關系,陰陽是指對立的兩個事物或對立的兩個方面,代表了宇宙的兩個組成部分,陰陽互根互用,相互依存,相互轉化,互不分離,獨陰不能生,孤陽不能長。那么,陰和陽在一起是和諧,還是沖突?
作為相互對立的兩個事物,在西方的機械論看來,相互對立的兩個方面,難以調和,非此即彼。如有轉化,也只是一方戰勝了另一方,而在新的條件下又形成新的對立。在《周易》中,任何事物的兩個對立面都是互根的,即互為對方存在的基礎。由于是互為基礎,它們不僅可以相互轉化,還可以共同向其它事物轉化,和諧共存。而和諧是萬事萬物共存的首要條件,陰陽和諧是萬事萬物和諧的根本,若根本不和諧,則任何事物都談不上和諧。故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1],說明世間萬物、人事皆以陰陽和諧為存在的條件。所以說陰陽和諧是根本之道,是客觀規律,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是“和諧”。
生命和諧論影響了中醫對健康的看法,如果人體是和諧的,那就意味著健康。首先,人體有達成和諧的可能,因為人體本身也是一個整體,一個生命系統。根據生命和諧論的觀點,它能通過陰陽的變換和五行的相生相克進行自我調節,而且是一個“高度自治”的系統,即通過人體的自愈能力而達到。其次,陰陽平衡是指一種相對的穩定狀態。中醫以《內經?素問?生氣通天論》中“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來作為判斷人體健康與否的首要條件,就是看陰陽是否處于一種相對平衡和穩定的狀態。陰陽平衡便是陰陽雙方在消長和轉化的過程中,雙方都既不太過也不太衰,呈現出一種和諧的狀態。這是生命存在的一種正常狀態。生命陰陽平衡是一種陰陽和諧,表現為臟腑平衡、寒熱平衡、氣血平衡和虛實平衡。“和乃生,而不和則不生”[3],說明了陰陽和諧的重要性。只有陰陽和諧了,萬物就和諧了。
3 預防觀
“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夫病已成而后藥之,亂已成而后治之,譬猶渴而穿井,斗而鑄錐,不亦晚乎”[4]。意思是說,圣人不等病已經發生再去治療,而是治療在疾病發生之前,不等到亂事已經發生再去治理,而是治理在發生之前,如果疾病已經發生,然后再去治療,亂子已經形成然后再去治理,那就如同渴了才去挖井,戰亂發生了再去制造兵器,豈不是太晚了嗎?它不僅僅告訴人們治療疾病要從預防入手,其實更重要的是它提供的是一種觀念,一種思想,就是要居安思危,要未雨綢繆,從而使生命健康長壽。
“不治己病治未病”站在理性思維的高度,跳出了有病治病對抗性思維的局限,將疾病預防于未萌之先。《素問?八正神明論》說:“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敗”。這里的“上工”是指高明的醫生,意即高明的醫生并不局限于治療己經發生的病癥,更應著眼于人體內外環境之間關系的協調與調理,使其不產生病癥,即保持“平人”狀態。這種思想經過衍生和發展,至唐代就成了“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5]的泛醫學思想,即將人類社會、人(包括人群和人體所患的疾病)都納入了醫學的視野,表現了跳出醫學來認識醫學的勇氣和智慧。
4 生態觀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局限于醫學而探討醫學,視域是狹隘的,無法看到醫學的真面目。而中醫學從誕生時就受到“天人合一”思想的影響,有了樸素的生態醫學觀,把人的生命和健康放在一個更廣闊的背景下,擺脫了“唯人獨尊”和“人之外皆為工具”的思想束縛。
在莊子看來,“以道觀之,物無貴賤”[6],主張尊重自然界的一切生命的價值,敬重生命,厚德載物,普利萬物,使自然界保持正常循環和全面和諧。古人認為,如果人的行為和生產活動“逆天數、違天時”,將自食惡果,所以人的活動要“上律天時”,“不違農時”,主張“谷不可勝食”、“魚鱉不可勝食”、“林木不可勝用”、不麛不卵,不殺胎,不夭夭,不覆巢,即圍獵時要“網開一面”行“三區之禮”,不捕殺幼獸、孵卵之鳥、懷胎母獸,不伐未成材之木,不顛覆鳥巢,強調了對動植物繁殖的保護。
這些思想對于今天的人類仍不失為一種警醒。一個不爭的事實是:醫學在與疾病做斗爭過程中付出了十分慘重的代價。如今用抗生素改變了整個自然界的面貌,其結果是許多常見感染性疾病的控制越來越困難,抗生素的濫用對大多數病原菌造成滅頂之災,同時也濫殺無辜,破壞了菌群間相互制約的平衡,催生了具有超級抗性的抗藥菌株:曾一度得到控制的結核病卷土重來、鼠疫對人類虎視眈眈、霍亂也在一些地區死灰復燃。如果當初能站在生態學的視角,不是把細菌視為危險的敵人而千方百計予以根除,維持“井水不犯河水”的環境條件從而和平共處,那么人類就會避免在這場戰爭中損傷慘重了。
[1] 李存山.老子[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34-57.
[2] 馬恒君.周易全文注釋本[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1:73.
[3] 吳文濤,張善良.管子[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343.
[4] 傅景華,陳心智.黃帝內經素問[M].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 1997:4.
[5] 李俊德,高文柱,沈澍農.中醫必讀百部名著?備急千金要方[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8:24.
[6] (清)王先謙.莊子集解[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7:102.
R212
A
1673-5846(2013)02-0234-03
1齊齊哈爾醫學院,黑龍江齊齊哈爾 161006
2黑龍江中醫藥大學,黑龍江哈爾濱 150040
谷雪峰(1966-),女,黑龍江中醫藥大學2009級中醫醫史文獻專業博士研究生,齊齊哈爾醫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醫學倫理學研究工作。E-mail:gxfdwh@163.com。
佟子林(1951-),男,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東西方醫藥衛生管理政策與規范比較研究。電話:13945695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