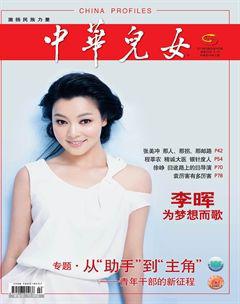誠(chéng)信
劉波
目前發(fā)生在我們社會(huì)上的種種惡劣現(xiàn)象諸如殺熟、宰客、釣魚(yú)執(zhí)法等等,令人每有防不勝防的驚險(xiǎn),這樣的事件,于公于私,不但不會(huì)達(dá)到目的,最終會(huì)損害個(gè)人乃至群體、國(guó)家的信譽(yù),從而導(dǎo)致干脆誰(shuí)都不信任誰(shuí),處處設(shè)防。當(dāng)起碼的信任失去的時(shí)候,要想重建,幾乎無(wú)門,而其他的事情也就萬(wàn)難談起,大家會(huì)為一件小事付出高昂的信任成本。
常常聽(tīng)說(shuō)幼兒園小朋友的父母有一個(gè)困惑:我究竟如何教自己的孩子?是告訴他實(shí)情?教會(huì)他處處設(shè)防以保護(hù)自己?還是叫他凡事講誠(chéng)信?這實(shí)際是被社會(huì)大潮裹挾著根本無(wú)法靜下來(lái)想一想的人群,其實(shí)你不自覺(jué)被逼入或誘入一個(gè)圈套,從而進(jìn)入一個(gè)永難自解的鏈條——不信任別人——得不到別人的信任——更加不信任。其實(shí)你根本不用想別人如何,就根據(jù)自己的心性來(lái)處世,以不變應(yīng)萬(wàn)變。我就誠(chéng)信了,能怎么樣?開(kāi)始,或者會(huì)遇到種種困難、不理解甚至陷阱掉進(jìn)去,但長(zhǎng)此以往,相信在你的周圍,會(huì)形成一個(gè)信任的氛圍。弘一大師講:彼險(xiǎn)仄我以誠(chéng)感之。人非木石,終究會(huì)被感化。一個(gè)長(zhǎng)久的、永不敗壞的良好氛圍就在你的周圍漸漸形成,其他的事情,都瞬間變得簡(jiǎn)單起來(lái)。所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這“道”必然包含著“信”的成分。
常人的邏輯,是總在挑別人的錯(cuò),你怎么不誠(chéng)信?殊不知他人就是自己的一面鏡子,你的不誠(chéng)信會(huì)通過(guò)他人折射回來(lái)。“仁遠(yuǎn)乎我?我欲仁,斯仁至矣。”不必遠(yuǎn)行求道訪仙,大道就在腳下。只要我們真正斷除一切虛妄和狡偽,真正做到一個(gè)“信”字,相信你釋放出來(lái)的善的因子,外界會(huì)攝受得到,從而回饋給你一個(gè)善的、“信”的信號(hào)。從而最終從欺詐與被欺的鏈條解脫。
《論語(yǔ)·為政》:“子曰:“人而無(wú)信,不知其可也。”一個(gè)人獨(dú)處時(shí),思想固然可以天馬行空,但按照佛家的說(shuō)法,應(yīng)該對(duì)起心動(dòng)念有所察覺(jué)和警惕,否則你的一念之間,可能會(huì)得到意想不到的果報(bào)。這種說(shuō)法,我們與其看作迷信,不如從精神變物質(zhì)的角度來(lái)審視:一個(gè)人如果心存惡念,那么首先他的“相”會(huì)表現(xiàn)出來(lái),這種“相”的改變,也會(huì)通過(guò)他的一系列行為而表現(xiàn)出來(lái),從一個(gè)大的概念中講,實(shí)際就是“違天”、“悖理”,則他的行為就會(huì)不自覺(jué)發(fā)生微妙乃至劇烈的變化,從而導(dǎo)致其立身處世遭到敗亡。一個(gè)“不信”的人,必然想盡一切辦法來(lái)掩飾、偽裝自己,甚至還要常常為自己的謊言而尋找說(shuō)辭,他的精神是高度緊張的,在這樣的高度緊張的精神狀態(tài)下,一些本應(yīng)“與天合一”的言行,就會(huì)與之失之交臂,長(zhǎng)此以往,他的面相、骨相和氣象一定會(huì)變化,而這種變化會(huì)通過(guò)他的言、行、舉、止頑強(qiáng)表現(xiàn)出來(lái)而為外界感知,在其周圍形成一個(gè)不信任的氛圍,最終“不知其可”。
我們知道,“仁、義、禮、智、信”為儒家“五常”。這五點(diǎn)概念的提出,雖出儒家,卻幾乎涵蓋了一個(gè)人在社會(huì)、群體中生存所必須具備的幾個(gè)條件。反之,一個(gè)“不仁”、“不義”、“無(wú)禮”、“不智”同時(shí)也“失信”的人,無(wú)論其信仰、所處時(shí)代、社會(huì),終究為人所棄是必然的。儒家提出“三綱”固有其值得商榷、移易處,而“五常”則徑屬大道,應(yīng)該奉行不悖。
《禮記·禮運(yùn)》:“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國(guó)與民之間,“信”是紐帶。商鞅變法,僅僅通過(guò)一個(gè)小小的舉動(dòng),取得了全體民眾的信任,接下來(lái)一切政令的推進(jìn),則勢(shì)如破竹。究其根本,還是應(yīng)該注重實(shí)行。不論法令如何嚴(yán)密、不論說(shuō)辭如何美奐,如果落不到實(shí)處,那民眾的信任則無(wú)從開(kāi)始,也無(wú)由開(kāi)始。作為崛起中的偉大文明,我們有太多需要建立的制度、需要推進(jìn)的事業(yè),而人與人之間、人與國(guó)家之間的“誠(chéng)信”是降低社會(huì)成本、促進(jìn)社會(huì)效率的先決條件和重要法寶。
責(zé)任編輯 張向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