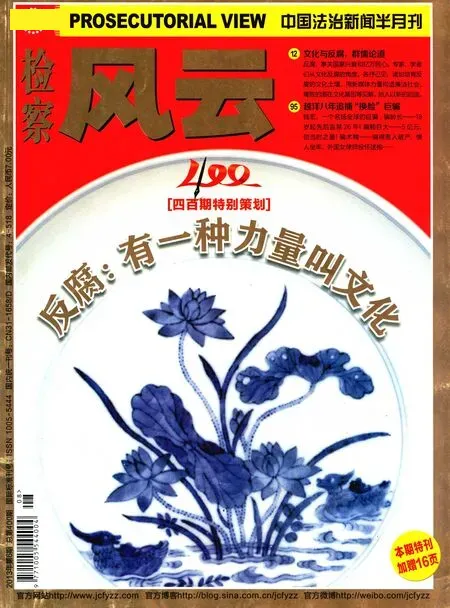堅守法治 春風化雨
文/王琳 《公訴人》(全國版)執行主編
《檢察風云》出刊400期了。中國人有逢十紀念的習俗,400期的堅守更值得紀念與祝賀。紀念是為總結過往,以便更好地走向將來。要為《檢察風云》的過往作出一個全面的總結,并不容易。《檢察風云》400期相伴的這個時代,雖談不上風云變幻,卻也并非云淡風輕。一本法治雜志能做的,也應當做的,并不是對“風云”的追隨,而是對其棲身的這片土壤的不離不棄。這土壤,就是法治。
雜志不是司法機關,不能從事具體案件的查辦或審理。但作為媒體的《檢察風云》,卻是法治文化的載體,負有傳播法治,宣揚法治的使命。在我們這個缺乏法治傳承的國度里,法治文化的培育尤顯重要。
試想想,僅僅30多年前,中國還處于法治虛無主義盛行的時代,一場打著“文化”之名的運動把中國的文化建設完全淹沒在過分擴張了的意識形態之中。到了改革開放時代,有目共睹的不僅是體現在經濟層面的市場轉型,更有社會層面的人心成長以及與之相伴隨的文化轉型。但遺憾的是,與經濟建設的飛速發展相比,我們這30多年的文化建設大大滯后。法治文化不彰,反法治的腐敗文化甚至腐朽文化就迅速填補空白。
文化建設的滯后,還不僅在于它跟不上經濟發展的腳步,更深層的憂患在于它正在逐漸背離正在轉型的中國社會。傳統的中國社會形態,是典型的熟人社會,以血緣、倫理、情感、宗法來維系基本秩序。這種強大的熟人文化一直浸淫在我們的血脈里。而當今30年間的中國社會轉型,卻正在走向一個陌生人社會。這一轉型乃“三千年前所未有之大變局”。陌生人社會需要“陌生人文化”的匹配,這種“陌生人文化”主要就表現為法治文化、契約文化、廉政文化。源自我們心底的對陌生人的不信任,又會強烈地喚起我們的“熟人文化”來抗拒陌生人社會。這就是中國至今仍停留在“關系本位”的內在原因。找“關系”、“熟人好辦事”、“請客吃飯稱兄道弟”等等,這些我們每天都在經歷的日常生活,都能在文化上找到根源。
但這并不表示,我們對法治文化、契約文化、廉政文化是不可預期的。恰恰相反,這正是法治傳媒人的使命所在。基于法治的陌生人關系,也可以建立信任關系。試想想,僅僅30年前,高校中的政法專業還是“絕密”專業,能夠獲得招錄的學生除卻分數要求之外,更需經過嚴格的政審。有關政法的書籍和雜志,都是“國家機密”,尋常人等無緣得見。將“法”與“文化”的割裂,帶來的不僅是法治水平的低下,還有普通民眾法律素養的淡薄。

如今大批法治媒體蓬勃生長,并以各自的影響力努力推動法治建設的深入,從而拉近“法治”與民眾的距離。各家媒體之間雖無日常聯系,卻為著一個共同的理想和目標在努力;那么多優秀的作者、讀者和各界人士共同聚集于《檢察風云》的大旗之下,他們彼此之間可能并不相識,卻都在為營造法治文化攜手共進。這樣的信任關系,不正是法治社會中的常態嗎?
作為法治媒體中的優秀產品,《檢察風云》也承載著宣揚法治的歷史使命走到了第400期——400期雜志鋪往全國各地,多少法治理念在春風化雨間悄然潛入了讀者的腦海,并融入了文化的血脈。借此機會,筆者對《檢察風云》的成績表示由衷的祝賀。期待它能在法治媒體中繼續保持領跑者的姿態,為法治文化的培育作出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