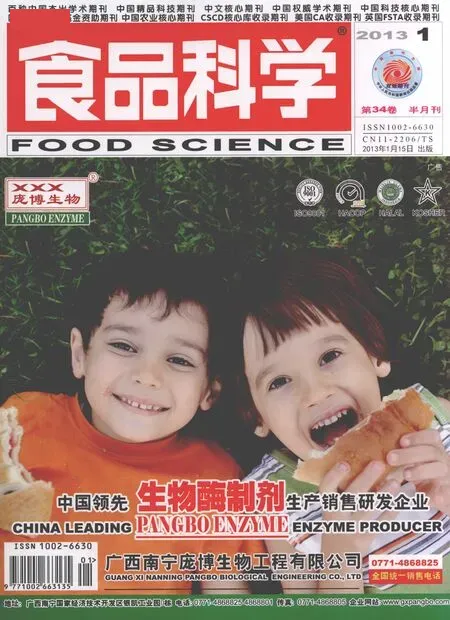冷鮮鵝加工及冷藏過程中的微生物污染分析
張維益,徐幸蓮*,王思丹,周光宏
(南京農(nóng)業(yè)大學(xué) 國家肉品加工與質(zhì)量控制教育部重點(diǎn)實(shí)驗(yàn)室,江蘇 南京 210095)
冷鮮鵝加工及冷藏過程中的微生物污染分析
張維益,徐幸蓮*,王思丹,周光宏
(南京農(nóng)業(yè)大學(xué) 國家肉品加工與質(zhì)量控制教育部重點(diǎn)實(shí)驗(yàn)室,江蘇 南京 210095)
研究商業(yè)屠宰對冷鮮鵝胴體天然菌落的影響。分別對工人手、案板、車間空氣、刀具、預(yù)冷水及屠宰過程中的鵝胴體取樣,進(jìn)行常見腐敗菌及致病菌的微生物傳統(tǒng)培養(yǎng)、計(jì)數(shù);同時(shí)研究冷鮮鵝貯藏過程中的菌落總數(shù)變化。結(jié)果表明:空氣、預(yù)冷水與加工過程中的各類接觸面都是冷鮮鵝潛在的污染源,都對樣品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污染,但總體上,整個(gè)加工過程還是減少了鵝胴體表面各種微生物的污染,加工后鵝胴體表面的各類微生物數(shù)量均顯著低于生產(chǎn)過程中的。凈膛工序使鵝胴體污染程度達(dá)到最大,但是沖洗和預(yù)冷工序都能有效地減少這一過程的污染。預(yù)冷池后段水和包裝是鵝胴體二次污染的主要原因,直接導(dǎo)致冷鮮鵝在冷藏7~9d后的腐敗。
冷鮮鵝;加工;微生物污染;菌相變化
我國消費(fèi)者對畜禽產(chǎn)品的要求將向低脂肪、低膽固醇、高蛋白、營養(yǎng)平衡、安全保健的方向發(fā)展。鵝肉產(chǎn)品的營養(yǎng)特性符合消費(fèi)者的需求,并且鵝肉中無(或低)藥物殘留,屬于天然綠色食品[1]。我國是世界第一鵝業(yè)生產(chǎn)大國,2009年我國肉鵝出欄量6.47億只,占世界的93.5%,鵝肉產(chǎn)量約148t,占全球的94.36%[2]。在我國肉類消費(fèi)中,鵝肉的消費(fèi)比從10年前的1%上升到現(xiàn)在的4%,而且這一比重還在增加。鵝肉產(chǎn)品市場潛力巨大,使得人們開始關(guān)注鵝肉消費(fèi)的安全性,這就要求產(chǎn)品必須在良好的加工、貯藏和銷售環(huán)境中,否則就會被微生物污染,其中以屠宰分割過程微生物污染機(jī)會最大。進(jìn)入商業(yè)屠宰場的禽類羽毛、皮膚、爪子以及消化道都大量攜帶各種天然菌群[3],污染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正確的操作、進(jìn)一步改善肉表面衛(wèi)生進(jìn)而抑制有害微生物的生長,才能延長貨架期,保證產(chǎn)品的安全質(zhì)量[4]。
屠宰過程包括放血、燙毛、凈膛、預(yù)冷等多個(gè)工序,盡管總的來說,屠宰加工過程減少了胴體的微生物污染[5],但是胴體、加工用水和設(shè)備的交叉污染可能會增加胴體的污染水平[6-7]。浸燙和去毛工序去除了活禽羽毛和皮膚上攜帶的大量微生物,然而這些工序可能導(dǎo)致交叉污染,并且使得其他種類的微生物在后續(xù)的凈膛和預(yù)冷工序中有新的附著表面,污染胴體,并且導(dǎo)致產(chǎn)品的腐敗變質(zhì)[6]。生產(chǎn)車間的空氣也會成為污染來源之一,空氣中的微生物可能來源于禽本身、未及時(shí)清理的加工廢棄物以及沒有定期消毒的物體表面[8]。
近年來,傳統(tǒng)的屠宰工藝一直在不斷改進(jìn)以避免細(xì)菌污染,并引用柵欄技術(shù)和HACCP控制體系。宋超[9]在冷卻豬肉生產(chǎn)中引入了無菌柵欄技術(shù),減少了胴體的污染程度,延長了冷卻肉保質(zhì)期。隨著國外先進(jìn)技術(shù)的引進(jìn),我國在冷卻肉和肉雞生產(chǎn)中都建立了完整的HACCP控制體系,但是在鵝屠宰及加工技術(shù)上目前我國甚至全球還無人開展過系統(tǒng)而深入的研究,制約了我國鵝肉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研究冷鮮鵝加工過程中的微生物多樣性和動態(tài)變化,研究加工過程中各工序和生產(chǎn)環(huán)境對產(chǎn)品的污染程度;旨在了解微生物的來源和種群構(gòu)成,為確定科學(xué)的生產(chǎn)車間控菌措施和生產(chǎn)規(guī)范提供理論依據(jù),為建立冷鮮鵝HACCP控制體系提供有用信息。
1 材料與方法
1.1 材料、試劑與儀器
原料鵝肉從大型鵝屠宰加工企業(yè)生產(chǎn)線上隨機(jī)取樣。取各工序后樣品立即冰運(yùn)至實(shí)驗(yàn)室,使用前于(4f1)℃保存不超過1h。
平板計(jì)數(shù)瓊脂(PCA)培養(yǎng)基、MRS培養(yǎng)基、甘露醇氯化鈉瓊脂(MSA)培養(yǎng)基、結(jié)晶紫中性紅膽鹽瓊脂、假單胞分離瓊脂、腸道菌計(jì)數(shù)瓊脂 北京陸橋技術(shù)有限責(zé)任公司。
BCD-208KBS變頻冰箱 青島海爾集團(tuán);SPX-250B-Z 型生化培養(yǎng)箱 上海益恒實(shí)驗(yàn)儀器有限公司;DGG-9240A型電熱恒溫鼓風(fēng)干燥箱 上海柏欣儀器設(shè)備廠;LDZX-50KB立式壓力蒸汽滅菌鍋 上海申安醫(yī)療器械廠;HT-1300-U潔凈工作臺 蘇凈集團(tuán)蘇州安泰公司。
1.2 方法
1.2.1 樣品與處理
1.2.1.1 冷鮮鵝屠宰工序
收鵝→宰殺→瀝血(3~5min)→浸燙(58~65℃、2min)、脫毛→浸蠟(65~70℃,18s)、脫蠟→人工去小毛→開膛、凈膛→噴淋沖洗→預(yù)冷消毒(兩段式螺旋推進(jìn)式預(yù)冷池,0~4℃、40min,80mg/L氯酸鈉)→包裝→冷藏
1.2.1.2 屠宰環(huán)境污染源采樣點(diǎn)
環(huán)境空氣(掛鵝間、放血燙毛間、去小毛間、凈膛間、預(yù)冷間、內(nèi)臟處理間、包裝間);接觸面(包裝案板、凈膛案板、凈膛工人手、去小毛工人手);刀具(放血刀、開膛刀、去翅刀);預(yù)冷水(前段、后段)。
1.2.1.3 屠宰、冷藏過程中胴體污染樣品
生產(chǎn)過程中胴體污染樣品采樣點(diǎn)分別為打毛后、去小毛后、凈膛后、預(yù)冷后。每次在上述4個(gè)工序點(diǎn)各隨即取6個(gè)胴體,20min內(nèi)冰運(yùn)至實(shí)驗(yàn)室,當(dāng)即檢測。
取預(yù)冷后的鵝胴體18只,分別割取鵝胸肉,其中3個(gè)立即檢測,其余15個(gè)樣品真空包裝,(4f1)℃冷藏,分別于1、3、5、7、9d檢測菌落總數(shù)。
1.2.2 取樣及微生物檢測
1.2.2.1 空氣沉降菌落總數(shù)測定
在生產(chǎn)前、生產(chǎn)中和生產(chǎn)后分別取樣。取樣方法參照GB/T 182041ü2000《公共場所空氣微生物檢驗(yàn)方法-細(xì)菌總數(shù)測定》中的自然沉降法。計(jì)數(shù)每塊平板上生長的菌落數(shù),求出全部采樣點(diǎn)的平均菌落數(shù)。以每平皿菌落數(shù)(CFU/皿)報(bào)告結(jié)果。
1.2.2.2 加工工序中接觸處面及刀具
每類接觸面隨即取3個(gè)樣品。采用50cm2專用取樣器,將沾有無菌生理鹽水的滅菌棉棒在取樣器范圍內(nèi)反復(fù)擦拭10次。取樣后迅速將棉棒放入裝有50mL無菌生理鹽水的無菌密閉三角瓶中,立即送至實(shí)驗(yàn)室,搖床(60r/min)30min,然后按要求做10倍梯度稀釋,選擇3個(gè)合適的稀釋度接種后培養(yǎng)計(jì)數(shù)。
1.2.2.3 預(yù)冷水
在生產(chǎn)中期取冷卻水10mL,冰運(yùn)至實(shí)驗(yàn)室,從中取1mL進(jìn)行接種培養(yǎng)。
1.2.2.4 屠宰工序中胴體表面
在鵝胸處取樣,取樣方法同1.2.2.2節(jié)。
1.2.2.5 冷藏過程中鵝胸肉樣品
在無菌環(huán)境下,每個(gè)樣品剪取10g肉樣,剪碎后置于裝有90mL無菌生理鹽水的密閉三角瓶中,搖床(60r/min)30min,靜置5min后取1mL上清液,并由此制備10倍梯度稀釋。
1.2.2.6 微生物培養(yǎng)計(jì)數(shù)
選擇性培養(yǎng)的微生物種類和方法見表1。

表 1 微生物選擇性培養(yǎng)基及培養(yǎng)條件Table 1 Selective media and culture conditions for different bacteria
1.3 數(shù)據(jù)分析
根據(jù)菌落計(jì)數(shù)結(jié)果計(jì)算樣品單位面積(體積)中各種菌的數(shù)量,使用SPSS.16.0對數(shù)據(jù)進(jìn)行單因素方差(One-way ANOVA)分析。
2 結(jié)果與分析
2.1 屠宰環(huán)境污染情況調(diào)查
2.1.1 車間空氣污染情況
由表2可知,生產(chǎn)前,去小毛間和預(yù)冷間空氣沉降菌落總數(shù)分別為0.77(lg(CFU/皿))和0.83(lg(CFU/皿)),空氣污染程度明顯(P<0.05)低于其他房間,其余5個(gè)生產(chǎn)車間細(xì)菌總數(shù)均在1.10(lg(CFU/皿))左右。
生產(chǎn)中,各車間空氣沉降菌落總數(shù)平均上升了1.20(lg(CFU/皿))左右,污染程度均顯著高于生產(chǎn)前(P<0.05)。其中,生產(chǎn)前區(qū)(掛鵝和放血燙毛間)空氣沉降菌落總數(shù)多不可計(jì),污染最嚴(yán)重,而生產(chǎn)后區(qū)空氣污染情況則遠(yuǎn)低于前區(qū),空氣污染嚴(yán)重程度依次為:凈膛間>內(nèi)臟加工間>去小毛間≈預(yù)冷間>包裝間;生產(chǎn)后,掛鵝間空氣沉降菌落總數(shù)依然是多不可計(jì),去小毛間2.20(lg(CFU/皿)),污染最嚴(yán)重,高于生產(chǎn)中(P<0.05),其他車間空氣沉降數(shù)量均顯著低于生產(chǎn)中(P<0.05)。總體上來說,車間空氣污染程度生產(chǎn)中>生產(chǎn)后>生產(chǎn)前。
表 2 不同車間空氣沉降菌落總數(shù)(±s)Table 2 Microbiological examination (aerobic bacterial count) of air samples from different workshops±s)

表 2 不同車間空氣沉降菌落總數(shù)(±s)Table 2 Microbiological examination (aerobic bacterial count) of air samples from different workshops±s)
注: ü表示菌落總數(shù)(CFU)多不可計(jì);同行或同列內(nèi)不同字母表示差異顯著(P<0.05)。
工序掛鵝間放血燙毛間去小毛間凈膛間預(yù)冷間內(nèi)臟加工間包裝間生產(chǎn)前1.08f0.12a1.08f0.19a0.77f0.02b1.16f0.16a0.83f0.05b1.15f0.14a1.21f0.17a生產(chǎn)中üü1.97f0.08c2.41f0.07d1.95f0.03c2.10f0.03b1.80f0.03e生產(chǎn)后ü1.80f0.11b2.20f0.08a1.61f0.11c1.38f0.13d1.67f0.07c1.65f0.09ce
2.1.2 接觸面污染狀況及菌相結(jié)構(gòu)

圖 1 屠宰加工過程中胴體接觸面污染程度及菌相變化Fig.1 Changes in the microf l ora on the surface of chopping boards and workers’hands during processing
由圖1可見,凈膛工人手表面各種細(xì)菌數(shù)量均在3.75(lg(CFU/cm2))左右,明顯高于其他接觸面,其中除了菌落總數(shù)外,金黃色葡萄球菌數(shù)量最多,在4.5(lg (CFU/cm2))左右,假單胞菌最少,為3.3(lg(CFU/cm2))。凈膛案板也是污染較嚴(yán)重的接觸面,菌落總數(shù)最多,為3.1(lg(CFU/cm2)),其他菌數(shù)量均在2.0(lg(CFU/cm2))左右。包裝案板污染相對最小,均在1.5(lg(CFU/cm2))左右,去小毛工人手表面各種細(xì)菌數(shù)量均比包裝案板略高。
2.1.3 加工過程中刀具污染狀況及菌相構(gòu)成
由圖2可見,微生物對刀具的污染程度為:去翅刀>開膛刀>放血刀。去翅刀污染最嚴(yán)重,菌落總數(shù)和腸桿菌科數(shù)量最多,在3.0(lg(CFU/cm2))左右,金黃色葡萄球菌最少;開膛刀上金黃色葡萄球菌略高于去翅刀,其他菌數(shù)量均低于去翅刀;放血刀污染程度最小,除菌落總數(shù)外,金黃色葡萄球菌和乳酸菌最多,為2.3(lg(CFU/cm2)),大腸桿菌和假單胞菌最少,為1.0(lg(CFU/cm2))。

圖 2 加工過程中刀具污染程度及菌相變化Fig.2 Changes in the microf l ora on various cutting tools during processing
2.1.4 預(yù)冷水污染狀況及菌相構(gòu)成
預(yù)冷池分前后兩段,兩段都為流動的冷凝水,換水量保持在每只鵝3L。一般前段預(yù)冷水溫控制在≤10℃,后段≤4℃,前段內(nèi)消毒劑次氯酸鈉質(zhì)量濃度為80mg/L胴體在預(yù)冷池內(nèi)與水流逆向移動,預(yù)冷總時(shí)間不少于40min。

圖 3 預(yù)冷水污染情況及菌相構(gòu)成Fig.3 Bacterial contamination and microf l ora of pre-chilling water
由圖3可見,自來水本身含有一定數(shù)量的大腸桿菌、腸桿菌科,菌落總數(shù)最多,為2.3(lg(CFU/cm2))。預(yù)冷池前段水中各種細(xì)菌均未檢出。預(yù)冷池后段水中菌落總數(shù)為3.2(lg(CFU/cm2)),金黃色葡萄球菌未檢出,其余4種菌數(shù)量都在2.0~2.5(lg(CFU/cm2))之間。
2.2 加工過程中鵝胴體污染狀況及菌相構(gòu)成
圖4反映的是主要加工工序中各種細(xì)菌對胴體表面的污染情況。打毛后鵝屠體表面菌落總數(shù)為3.4(lg(CFU/cm2)),假單胞菌未檢出。去小毛后屠體表面大腸桿菌、腸桿菌科和假單胞菌數(shù)量較打毛后均有顯著增加,其中假單胞菌增長幅度最大,而金黃色葡萄球菌和菌落總數(shù)減少了約30%,乳酸菌變化不大。
凈膛后鵝胴體表面除乳酸菌外各種菌數(shù)量均有顯著增長,菌落總數(shù)最多,達(dá)到4.3(lg(CFU/cm2)),其他種類菌數(shù)量在2.4(lg(CFU/cm2))左右。預(yù)冷后鵝胴體表面大腸桿菌、腸桿菌科、菌落總數(shù)和假單胞菌數(shù)量比凈膛后較少了50%,乳酸菌較少了30%左右,金黃色葡萄球菌沒有檢出。

圖 4 加工過程中鵝胴體污染狀況及菌相構(gòu)成Fig.4 Bacterial contamination and micro fl ora of goose carcasses during processing
2.3 冷藏過程中鮮冷鵝菌落總數(shù)變化情況

圖 5 冷藏過程中冷鮮鵝菌落總數(shù)變化Fig.5 Aerobic bacterial count change of chilled goose during refrigerated storage
由圖5可見,鮮冷鵝的初始菌落總數(shù)為2.0(lg(CFU/g)),在冷藏的第一天就進(jìn)入對數(shù)生長期,迅速繁殖,增長至4.5(lg(CFU/g))。在隨后3~7d的冷藏期間,菌落總數(shù)緩慢增長,到第7天末,菌落總數(shù)為5.2(lg(CFU/g)),此后,細(xì)菌再次加快繁殖速度,到第9天末達(dá)到6.1(lg(CFU/g))。
雖然樣品菌落總數(shù)到第9天還保持在鮮肉標(biāo)準(zhǔn)范圍之內(nèi),但感官品質(zhì)變化明顯,貯藏后期表現(xiàn)出腐敗變質(zhì)特征。樣品冷藏至第7天時(shí)樣品出現(xiàn)肉質(zhì)變軟、肉色變暗、汁液滲出較多的現(xiàn)象,表現(xiàn)出腐敗的特征,到第9天時(shí)開始腐敗,異味加重,肉質(zhì)松軟。
3 討 論
空氣中微生物是禽類生產(chǎn)中不可忽視的污染來源之一。生產(chǎn)過程中,前區(qū)(掛鵝間、放血燙毛間)污染最嚴(yán)重,這些細(xì)菌主要來自鵝本身的皮膚和羽毛,空氣中的高污染程度可能是由于掛鵝時(shí)鵝翅拍打掙扎造成灰塵散布以及鵝糞便未及時(shí)清理,放血燙毛間由于燙毛水造成的霧氣以及打毛機(jī)揚(yáng)起的灰塵和絨毛,并且車間溫濕度較高,這樣的環(huán)境適宜微生物的生長繁殖,使得空氣中菌落總數(shù)較高。生產(chǎn)準(zhǔn)潔凈區(qū)空氣污染程度降低,其中凈膛間和內(nèi)臟加工間污染嚴(yán)重,這可能是由于一些胴體的腸道破損,腸道內(nèi)容物流出,并且沒有及時(shí)清理,使微生物大量繁殖,污染了車間環(huán)境;去小毛車間和預(yù)冷間由于操作都在流動水中進(jìn)行,所以污染相對較低。生產(chǎn)后車間內(nèi)清潔人員的走動及沖洗可能導(dǎo)致一些細(xì)菌揚(yáng)起,并且沒有及時(shí)沉降,使得空氣中仍有較多的細(xì)菌。各車間的污染程度不同,但存在相同的問題,即未采取徹底有效的環(huán)境消毒措施。Cundith等[16]研究表明,靜電沉淀過濾與紫外線對小型肉類加工廠控制空氣中的微生物量有很好的效果。
屠宰加工過程中與產(chǎn)品直接接觸的潛在污染源中,凈膛工人手部污染最嚴(yán)重,這和李虹敏[17]的研究結(jié)果一致,其中金黃色葡萄球菌最多,假單胞菌最少。這是由于在掏膛時(shí)工人手套上會粘有一些血跡和腸道內(nèi)容物,加上沒有及時(shí)清洗,所以微生物大量繁殖,并且污染胴體,同時(shí)這些污染物也污染了凈膛案板。由于燙毛、打毛和去小毛過程中鵝屠體分別經(jīng)過了65℃的水浴和70℃的石蠟,高溫消除了部分污染微生物,所以鵝屠體表面污染程度較輕,并且假單胞菌很少,打毛后鵝屠體表面未檢出假單胞菌。但是經(jīng)過凈膛工序后,各種細(xì)菌數(shù)量均有顯著增加,這是由于凈膛操作不當(dāng)引起的交叉污染。由此可見,凈膛工序是整個(gè)屠宰加工過程的關(guān)鍵控制點(diǎn),必須采取有效措施降低交叉污染。
調(diào)查表明,案板、加工刀具等接觸面也是污染胴體的主要來源。尤其是包裝案板,由于與胴體直接接觸,并且后續(xù)過程沒有減菌措施,直接包裝貯藏,直接影響冷鮮鵝的初始菌數(shù),進(jìn)而限制產(chǎn)品的貨架期和安全性。除乳酸菌外,包裝案板表面各類菌數(shù)量均略高于預(yù)冷后胴體,并檢出金黃色葡萄球菌,可能影響產(chǎn)品的食用安全。由于刀具與胴體直接接觸,刀具上的微生物將會對胴體表面造成交叉污染[18]。有資料表明[19]刀具上的微生物含量在4.0(lg(CFU/cm2)),說明刀具對胴體和鮮肉的污染是非常嚴(yán)重的。文獻(xiàn)[20]報(bào)道對屠宰工序上的刀具進(jìn)行調(diào)查,有的細(xì)菌總數(shù)在4.23~6.26(lg(CFU/cm2))之間,有的在3.5~4.7lg(CFU/cm2)之間[21],還有的達(dá)到9.1h104[22],本實(shí)驗(yàn)調(diào)查結(jié)果中,3類刀具菌落總數(shù)在2.9~3.4(lg(CFU/cm2))之間,其他種類菌也都在較低的水平,說明刀具對胴體的污染較小。這可能是因?yàn)樵谇蓊愅涝准庸み^程中,刀具使用時(shí)接觸面相對較小,并且經(jīng)常清洗,所以污染較小。刀具在使用一段時(shí)間后,表面都會粘滿屠宰過程殘留的污物。這些污物是微生物生長的良好培養(yǎng)基,在外界條件適宜的情況下,短時(shí)間內(nèi)微生物大量繁殖,再與胴體接觸就會造成交叉污染[23]。因此建立良好的刀具防污染控制措施是保證冷鮮鵝生產(chǎn)的重要環(huán)節(jié)。
預(yù)冷過程對消除胴體微生物污染起著重要的作用,通過水的沖洗能沖洗掉胴體表面黏附的大部分細(xì)菌,并且水中一定濃度的消毒劑能抑制絕大多數(shù)嗜溫細(xì)菌的繁殖。經(jīng)過預(yù)冷,胴體表面各種細(xì)菌數(shù)量都顯著下降,金黃色葡萄球菌未檢出。胴體表面與預(yù)冷池后段水中各種菌的數(shù)量和菌相構(gòu)成基本一致,而預(yù)冷池前段水中各類細(xì)菌均未檢出,因此可以看出,前段預(yù)冷水中一定濃度的消毒劑雖然起到了一定的減菌效果,約減少了50%的細(xì)菌,但是仍有一部分細(xì)菌黏附在胴體表面,污染了后段水,并引起交叉污染,成為貯藏過程中的潛在污染菌,這和Hinton等[23]的研究結(jié)果一致。因此在生產(chǎn)過程中,必須經(jīng)常更換預(yù)冷用水,減少預(yù)冷水與胴體的交叉污染;并定時(shí)補(bǔ)充消毒劑濃度,使前段預(yù)冷水保持較高的減菌效率。
冷鮮鵝冷藏過程中菌落總數(shù)顯著增加,這些細(xì)菌主要來自于包裝案板及后段預(yù)冷水。樣品的初始菌落總數(shù)為102CFU/g,從第7天開始有腐敗跡象,第9天達(dá)到106CFU/g,樣品開始腐敗。有資料表明[24],冷卻肉初始菌落總數(shù)為102CFU/g時(shí)貨架期為15d,當(dāng)菌落總數(shù)達(dá)到106CFU/g時(shí)冷卻肉開始腐敗,這和本實(shí)驗(yàn)的結(jié)果基本一致。
4 結(jié) 論
空氣、預(yù)冷水與加工過程中的各類接觸面都是冷鮮鵝潛在的污染源,都對產(chǎn)品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污染。但是總的來說,整個(gè)加工過程還是減少了鵝胴體表面各種微生物的污染,產(chǎn)品表面的各類微生物都顯著低于生產(chǎn)過程中。凈膛工序使胴體污染程度達(dá)到最大,但是后續(xù)的沖洗和預(yù)冷工序都能有效得減少這一過程的污染。預(yù)冷池后段水和包裝過程是鵝胴體二次污染的主要原因,直接導(dǎo)致真空包裝產(chǎn)品在冷藏7~9d后的腐敗。
[1] 曹宏, 蔣云升. 鵝肉食用前景和消費(fèi)市場初探[J]. 安徽農(nóng)業(yè)科學(xué), 2005, 33(12): 2480.
[2] 侯水生. 中國鵝業(yè)發(fā)展面臨的困境及技術(shù)措施建議[C]// 2010全國鵝業(yè)大會. 濟(jì)南: 山東省農(nóng)業(yè)科學(xué)院, 2010: 1-3.
[3] KOTULA K L, PANDYA Y. Bacterial contamination of broiler chickens before scalding[J]. Journal of Food Protection, 1995, 58: 1326-1329.
[4] AHMED S N, CHATTOPADYAY U K, SHERIKAR A T, et al. Chemical sprays as a method for improvement in microbiological quality and shelf-life of fresh sheep and goat meats during refrigeration storage (5ü7 ℃) [J]. Meat Science, 2003, 63: 339-344.
[5] GEORNARAS I, von HOLY A. Bacterial counts associated with poultry processing at different sampling times[J]. Journal of Basic Microbiology, 2000, 40: 343-349.
[6] THOMAS C J, MCMEEKIN T A. Contamination of broiler carcass skin during commercial processing procedures: an electron microscopic study[J]. Applied and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1980, 40: 133-144.
[7] FRIES R, GRAW C. Water and air in two poultry processing plants’chilling facilities: a bacteriological survey[J]. British Poultry Science, 1999, 40: 52-58.
[8] RUSSELL S M, FLETCHER D L, COX N A. Spoilage bacteria of fresh broiler chicken carcasses[J]. Poultry Science, 1996, 75: 2041-2047.
[9] 宋超. 冷卻豬肉生產(chǎn)中無菌柵欄技術(shù)研究[D]. 鄭州: 河南農(nóng)業(yè)大學(xué), 2009.
[10] 中華人民共和國衛(wèi)生部. GB 4789.3ü2010食品微生物學(xué)檢驗(yàn) 大腸菌群計(jì)數(shù)[S].
[1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進(jìn)出口商品檢驗(yàn)局. SN/T 0738ü1997出口食品中腸桿菌科檢驗(yàn)方法[S].
[12] 中華人民共和國衛(wèi)生部. GB 4789.10ü2010食品微生物學(xué)檢驗(yàn)金黃色葡萄球菌檢驗(yàn)[S].
[13] 中華人民共和國衛(wèi)生部. GB 4789.2ü2010食品微生物學(xué)檢驗(yàn)-菌落總數(shù)測定[S].
[14] 中華人民共和國衛(wèi)生部. GB 4789.35ü2010食品微生物學(xué)檢驗(yàn)-乳酸菌檢驗(yàn)[S].
[15] ISO 13720ü2010 Meat and meat products: enumeration of presumptive Pseudomonas spp.[S].
[16] CUNDITH C J, KERTH C R, JONES W R. Air-cleaning system effectiveness for control of airborne microbes in a meat-processing plant[J]. Food Science, 2002, 67: 1170-1173.
[17] 李虹敏. 肉雞屠宰加工及冷藏中的微生物污染來源及菌相分析[J].肉類工業(yè), 2008(6): 33-38.
[18] 李殿鑫. 肉牛屠宰分割生產(chǎn)線HACCP體系的建立[D]. 南京: 南京農(nóng)業(yè)大學(xué), 2005.
[19] 白鳳翎. 生豬屠宰過程中的微生物污染及控制[[J]. 中國獸醫(yī)雜質(zhì), 2004, 40(10): 50-51.
[20] 甘伯中. HACCP 在冷卻分割豬肉生產(chǎn)中的應(yīng)用[J]. 甘肅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bào), 2003(2): 188-193.
[21] 彭梅仙, 黃裕. 肉聯(lián)廠屠宰過程中肉品的致病性細(xì)菌污染分析及關(guān)鍵控制點(diǎn)[J]. 肉品衛(wèi)生, 2002(8): 25-26.
[22] 許益民. 生肉的微生物污染和對策[[J]. 中國動物保健, 2000(9): 26-27.
[23] HINTON A, Jr, CASON J A, INGRAM K D. Enumeration and identif i cation of yeasts associated with commercial poultry processing and spoilage of refrigerated broiler carcasses[J]. Journal of Food Protection, 2002, 65: 993-998.
[24] GILL C O. Extending the storage life of raw chilled meats[J]. Meat Science, 1996, 43(1): 99-109.
Analysis of Bacterial Contamination during Processing and Refrigerated Storage of Chilled Goose
ZHANG Wei-yi,XU Xing-lian*,WANG Si-dan,ZHOU Guang-hong
(Key Laboratory of Meat Processing and Quality Control, Ministry of Education,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The effect of commercial processing on the natural microf l ora of chilled goose was studied. Common spoilage bacteria and pathogenic bacteria from workers’ hands, chopping boards, cutting tools, goose carcasses and workshop air environments and chilling water were cultured by traditional methods and counted. Meanwhile, changes in aerobic plate count during refrigerated storage were explored. Although air, chilling water and various contact surfaces were all potential sources of bacterial contamination for chilled goose, in general, various bacterial contaminants showed a downward trend during the whole processing process. Bacterial contamination of goose carcasses was maximized during the stage of evisceration but effectively reduced by spray rinsing and pre-chilling. The second stage of pre-chilling and packaging were main causes of secondary contamination of goose carcasses and as a result, the shelf life of chilled goose spoiled was only 7ü9 days during refrigerated storage.
chilled goose;processing;microbial contamination;microf l ora changes
Q939.97
A
1002-6630(2013)01-0290-05
2011-10-23
江蘇省科技成果轉(zhuǎn)化專項(xiàng)資金項(xiàng)目(BA2008088)
張維益(1986ü),男,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yàn)槿馄焚|(zhì)量安全控制。E-mail:2009108061@njau.edu.cn
*通信作者:徐幸蓮(1962ü),女,教授,博士,研究方向?yàn)槿馄焚|(zhì)量安全控制。E-mail:xlxu@ nja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