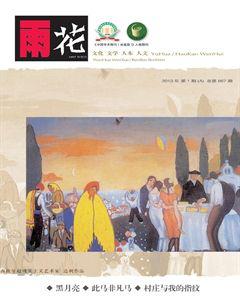岳陽樓頭話悲喜
洞庭湖邊岳陽樓,水光山色眼底收。文學家范仲淹的傳世名篇,寫出了登臨斯樓的悲喜兩重天: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
然而,“以天下為己任”的范仲淹,想要苦苦追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高尚境界。他力圖擺脫“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的兩難,達于“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崇高理想。廣為傳頌的這句范氏名言,有人稱其謂“政治宣言書”。可我以為,它更是一種書生士子情懷,或者,干脆就叫道德烏托邦。
我這樣說,并不是貶低范仲淹。作為北宋出色的政治家,他直言敢諫,銳意革新,又清正廉潔,關愛民生,乃為不可多得的好官、清官。但是,范仲淹推行的慶歷新政,屢屢受挫,他的仕途也起落浮沉,英雄無用武之地。觀其一生,悲情多于喜悅,失敗大于成功。他所秉持的遠大政治抱負,到頭來仍不免是夢幻悲劇。
古代的書生士子,總把忠君愛民,奉為安身立命之本。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其“天下”若解讀為忠君愛民,而重點又在天下蒼生,即平民百姓的話,則這句名言在實際上就蘊含著一個極大的矛盾。這便是,統治者的君主及其官僚集團與被統治的平民百姓,二者的愿望、利益相一致、協調的時候不多,而相對立、沖突的地方卻不少。夾縫中的范仲淹輩士大夫,既要為君分憂,又要解民倒懸,其調和、周旋的余地有多大?多數情況下,他們雖煞費苦心,百般努力,卻調而不和,難以兩全。弄得不好,反會禍及自身。范仲淹,不正是這樣么?
文學家的范仲淹,是浪漫的、理想主義的;而政治家的范仲淹,是務實的、現實主義的。讀《岳陽樓記》,在人們為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博大情懷和高尚操守擊節叫好的時候,許多人忽略了范仲淹名言后面的那句話:“噫,微斯人,吾誰與歸!”環視當世,范仲淹幾乎找不到什么同道之人,只能孤苦伶仃地與古之仁人為伍,為自己的孑立無援、難覓歸宿而悲嘆!每讀至此,我像坐了過山車,剛才還在為他的至理名言歡呼雀躍,瞬間即跌入悲涼的低谷!端的是悲喜交加,五味雜陳。
把“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當作道德教育的座右銘,與后世革命者解放全人類的博大情操,似有共通處。這當然很好,很鼓舞人。但稍加推敲,我又不禁啞然失笑。
因為,從來的朝廷及其官僚集團,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需要維護和擴張。生命個體的官員,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他們作為社會的經濟人,而且還是“人上人”,升官發財的欲望比平民百姓強烈得多!要求他們躬行范氏名言,完全徹底地放棄其特殊利益,不現實,也行不通。古往今來,真正的好官、清官,直如鳳毛麟角,而壞官、貪官卻多如牛毛,治不勝治、殺不勝殺,原由即在于此。所以,看似光鮮的官德教育,每每淪為空洞的說教,甚或只是做戲的宣傳。
又在,天下的平民百姓、蕓蕓蒼生,總是難得安居樂業,存有諸多的民生憂患、難題。即在號稱盛世的當下,我們仍有數以億計的平民百姓面臨著生存之痛,如就業困難、上不起學、看病太貴等等,層出不窮。按照范老先生的名言,咱們的官員、領導者,便難以解脫憂煩、開顏一樂。他們雖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但要始終如一地踐行“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都做道德圣人,就過于理想化了!人生苦短。他們能夠等得及嗎?
不是我鉆牛角尖,也不是要消解高尚的道德操守。道德也好,政治也罷,其實都離不開現實的利益博弈,都是調節、妥協的藝術。太理想化了,后果往往不佳。為政之道,還以少唱高調、多做實事為好。官員們能恪盡職守、先公后私、與民同樂,已屬不易。千萬別像“一代天驕”成吉思汗,“人生最大之樂,即在勝敵、逐敵,奪其所有,見其最親之人以淚洗面,乘其馬,納其妻女也。”那樣,準會出麻煩。
岳陽樓頭話悲喜,樂憂交錯心依依。我為文學家的范仲淹而喜,又為政治家的范仲淹而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