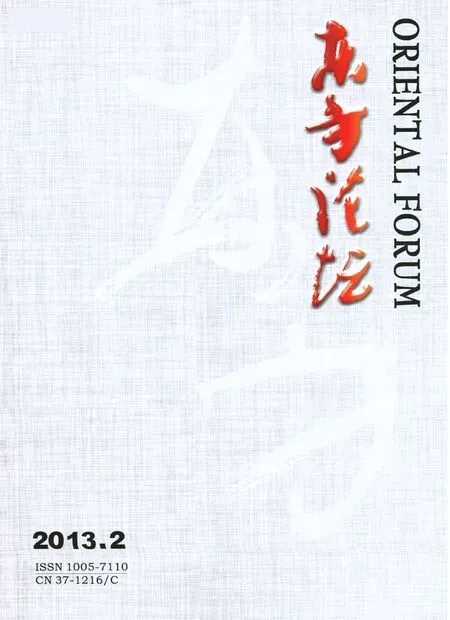論《文心雕龍》與寫作過程中的文體感
趙紅梅
(青島大學 文學院,山東 青島 266071)
寫作活動是一項復雜、綜合性的創造活動,文章是其最終成果的體現,即寫作載體,這個載體又是以一定的體式呈現的,此即我們常說的“文體”,但文體概念在傳統文論中具有更為豐富、多層次的內涵。在寫作教學中,文體是一個不能不涉及的重要方面,如何有效開展并切實提高學生實際寫作中的文體把握能力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教學課題。作為一部研究“為文之用心”的理論專著,《文心雕龍》近年來受到寫作學界的高度重視。“文體”亦是《文心雕龍》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其豐富的文體論思想為今日之寫作教學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參照。通過分析筆者認為,《文心雕龍》中的文體思想是體現于全書的,而尤為可貴的是其寫作活動過程中對文體的動態把握。因而,本文在把握《文心雕龍》之“文體”觀的基礎上,聚焦于寫作過程中的“文體感”,并結合《文心雕龍》之相關篇目進行了更為細化的分析,旨在吸取傳統文論精華,反思并改進高校寫作中的文體教學。
一、《文心雕龍》之多層級、整體性的文體觀
單從字面上來看,據有關學者查考,《文心雕龍》中“文體”一詞出現過8 次,“體”出現190 余次(既是論文,則“體”亦多指“文體”)。①參見楊東林《開放的文體觀——劉勰文體觀念探微》(《文史哲》2008年第4 期第122-129 頁)及王毓紅《中國古代詩學語境中的文體概念——從劉勰〈文心雕龍〉談起》(《固原師專學報》2003年1月第24卷第1 期第5-11 頁)二文。可見,“文體”或“體”是《文心雕龍》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1950年代以來,對劉勰文體觀的研究一度引起關注,并引發一場跨世紀跨海峽的學術論爭。②李建中《龍學的困境——由“文心雕龍文體論”論爭引發的方法論反思》(《文藝研究》2012年第4 期第51 頁)一文說:這場學術論爭,從徐復觀的“主觀情性論”文體觀,到龔鵬程的“客觀規范論”文體觀,再到顏昆陽的“辯證性的文體觀念架構”,以其革命性、批判性和建構性,對《文心雕龍》的文體論研究乃至對整個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產生較大影響。學者們從各自角度,對《文心雕龍》中“文體”的內涵進行了廣泛深入的探討,也有不同的聲音。歸納起來,其共識是“文體”具有多重內涵,不能簡單等同于文章的體裁。其中有代表性的觀點如:上世紀50年代徐復觀先生提出《文心雕龍》之文體有體裁、 體要、體貌三個層次,而以體貌為文體概念之最終依歸;其后龔鵬程先生針對徐文發表不同意見,強調文類,反對做近乎現代風格學上的闡釋;顏昆陽先生在此基礎上提出“辯證性的文體觀念構架”;內地學者中,1960年代陸侃如先生提出文體包含體裁與風格二義;1980年代王運熙先生指出文體包含體裁、體貌;1990年代童慶炳先生提出文體概念的三個層次:體裁、語體、風格等。[1]理論的辨析無疑使我們對“文體”這一術語有了更為深入的理解,這也彰顯出傳統文論批評的特色,往往一字具有豐富之內涵且有時隨文見義,難以用準確的現代術語加以替換。這里,我們取其共識,并對不同的內涵層次做綜合的理解:“文體”是劉勰對待寫作載體——文章的一種整體性看法,既包括體裁之形式特點,也有其他內容風格等方面的附加之義。總之,是一篇文章的整體面貌、有別于其他的質性所在。正如有學者指出的:“不管劉勰從怎樣的角度去把握體概念,而由人體概念引申出的體的整體性和直觀形相性,則是劉勰對文體認識的基礎。”[1]“文體范疇的含義還可進一步表述為具有各種特征和構成的文章整體。”[2]這里,我們亦對“文體”這一概念做整體性理解,并著眼于寫作活動,考查寫作過程中對文章整體的一種多層次的把握。《文心雕龍》中對文體問題的處理與把握值得我們在現今的寫作教學中加以充分借鑒。
一般認為,《文心雕龍》中的文體論即是上篇中的二十篇“論文敘筆”。這部分篇幅之重占全書的近一半,而且下篇的創作論諸篇正是在此基礎上的進一步歸納闡發,可見劉勰對文體問題是非常重視的,是建構其創作理論的基石。與同時期的其他理論著作相比,這部分內容體大慮周,力圖對所處時代的各類文體做出全面之歸納,提供了較為完備的前所未有的文體總結范例。以現在的眼光來看,其分類體系以及各體文的具體闡述對當今之寫作教學仍有較大借鑒意義,尤其在專門文體的教學方面。但文體分類隨時代而變,在內容的借鑒之外,更應吸取其駕馭各類文體的胸襟眼光及方法。《文心雕龍》的文體分類之所以達到時代之最詳備者,正因其開闊的理論視野。縱向上,追根溯源,挖掘探尋各體文的發生發展及變異消長;橫向上,文筆兼收,充分吸納時代之各類文章樣態,涵蓋各種正體變體。在文體探析中,劉勰創造性地運用了“原釋選敷”的研究方法,即“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3](P682)文隨世變而方法可通、原釋選敷的研究思路,對今日之文體研究仍切實有效,尤其“原”、“選”之法在今日之文體教學中亟需加強。
《文心雕龍》對“論文敘筆”部分的極大重視、對各類文章的條分縷析、寬闊的文體視野以及獨特的“原釋選敷”之法,都對今日之文體寫作教學有較大啟發。
詳析“論文敘筆”的這部分內容,側重類的辨析,注意歸納各類文體的特征規范,求同辨異。雖分類較細,但亦有相近文體的歸并,從篇目安排上還可見出有些相近文體應是刻意相鄰而排。《宗經》篇中亦曾說:“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盟、檄,則《春秋》為根。”參照這段話,我們可以看到,劉勰的文體分類呈現出較為嚴謹的系統性。天下文章紛繁龐雜,種類繁多,但本同而末異,從某種角度可以歸并為更為簡約的大類,這樣各依其類、以簡馭繁,可以達到較系統全面的把握。由此,筆者曾提出立足于某些“基本文體”來開展教學與寫作訓練,可以較好解決寫作教學中(尤其基礎寫作教學)文體需廣泛涉獵又難以各個展開的矛盾。這里的基本文體,就是指相近而歸并的文體大類。當然歸并的角度不盡相同,筆者曾嘗試結合表達方式加以歸并,如敘述描寫與敘事文、議論與論辯文等。這樣以基本文體中的典型代表(具體文章)為依托,可以將普適意義的文章之體的要求、類的規范性體現于具體文本,在閱讀與寫作實踐中把握“文體”的創造,并在此基礎上,培養學生對于各種具體文體的自主學習與掌握的能力。[4]實踐證明,這種方法可以較好地打通點與面,使學生在有限的課時內既體會到不同文體之差異,又有較全面的文體把握,從而實現文體教學的鋪展與深入。這應是《文心雕龍》之文體論給我們的又一啟發。
姚愛斌先生曾撰文提出基本文體、文類文體、具體文體的概念,認為文體之創造不是其內部結構層次的逐級升華而是這三種不同層級文體的一個從一般到特殊、由潛在到現實的過程。①姚愛斌《論徐復觀〈文心雕龍〉文體論研究的學理缺失》一文提出基本文體、文類文體、具體文體的概念,認為“文體的生成的確有一個逐層升華的過程,但這個過程不等于文體結構的三個層次,而應該是一個從一般到特殊、由潛在到現實的過程”, 該文中說:從邏輯層面看,文體的生成或升華會經過三個層次和兩個環節。這三個層次分別是作為所有文章范型的基本文體、作為某種文類范型的文類文體和作為現實具體的個別文體。兩個環節分別是:先由基本文體轉化為文類文體,再由文類文體落實為具體個別文體。因此,所謂文體的升華過程,可以理解為包含一般規定和特征的基本文體、文類文體,在實際創作中轉化為包含具體規定和特征的個別文體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遵循的是體用規律。……人們也只能通過種種具體的文類文體(末)來體會、認識文章之“本”,……文類文體又必須通過無數具體的個別文體作為其現實存在。……文體創造應該是文類文體的規范性與個別文體的多樣性結合……《文心雕龍》雖然沒有明確提出文體發展和創造過程中的體用關系,但是其思想方法完全與體用論契合。其“基本文體” 指“所有文章范型”,亦即普適意義的文章之體的要求,與我們所說的出于教學考慮而進行文類歸并的“基本文體”概念指向不同,但其逐層升華論無疑使我們對文體之生成有更為清晰的認識。由此我們也可以歸納:《文心雕龍》中的“文體”,包含了劉勰對普適意義上的文章之體、某類文章之體、具體文章之體等多層級看法,但無論哪個層級,都是將“文體”視為具有多重結構內涵的文章之整體,寫作過程中正是一直秉承這一“整體”觀念而不斷加以矯正(遵守或突破),從而實現文體的實施與創造。
基于這樣多層級的整體的文體觀,劉勰對文體之重視與把握顯然并不僅僅局限于論文敘筆之中,而是貫穿于整個探討“為文之用心”的全過程、貫穿于全書的。從全書綱目看,“文之樞紐”五篇,《序志》中曾概括為:“本乎道,師乎圣,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 無論“本、師”亦或 “酌、變”,其依歸之中心乃是“體乎經”,可見,《宗經》是樞紐論的核心,宗經思想更是籠罩《文心雕龍》全書的主導思想。①關于《宗經》之主導意義亦可參見祖保泉《文心雕龍解說》(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 版)第964、965、976 頁。而宗經實是宗經之體,從《宗經》篇內容可以見出,《文心雕龍》所關注并強調的,是其“稟經制式”的文體意義。[5]
“論文敘筆”部分前已詳述自不贅言。下篇的“剖情析采”之創作論,筆者以為其實更為鮮明地體現了劉勰的多層級整體的文體觀。創作論建立在各體文的歸納之上,力圖通過對各類文體的全面把握,探討普適意義的文章寫作的一般理論,而這些寫作的一般理論又體現于寫作過程中對具體文體的把握,因而,緊密結合實踐的創作論,打通了普適意義上的文章之體、文類文章之體、具體文章之體的多層級界限,在過程中具體體現了文體的生成轉化和一以貫之的整體性。寫作活動中,每一個文本就是一具體“文體”,成功的文本應具備普適意義的文章之要求、文類的規定性,同時又是獨特之創造,自成一體。在這過程中有由隱及顯的文體層級轉化但最終體現為具體文體,有文體內部多層結構的分別把握但以整體之面貌展現,所以就顯像的具體文本而言,創作論中以貫穿寫作活動始終的文之整體觀彰顯其對文體的高度重視。
按照通行之綱目,創作論包括《神思》、《體性》、《風骨》、《通變》、《定勢》、《情采》、《熔裁》、《聲律》、《章句》、《麗辭》、《比興》、《夸飾》、《事類》、《練字》、《隱秀》、《指瑕》、《養氣》、《附會》、《總術》等凡十九篇。②《物色》篇有過爭議,但學者多認為保持原綱目次序為宜,暫不論。從真正論創作的十八篇來看(《總術》篇除外),前五篇無疑是“務先大體”的文章整體之要求,其后十一篇分別涉及了實際寫作過程的諸多方面,最后的《養氣》、《附會》兩篇則又以文章整體之眼光對前面的論述做了有益的補充發揮。行文綱目的“總—分—總”的視角特點,正彰顯了劉勰的文章整體觀:可以分而析之,但一定要有整體之把握,文章的各個不同側面的分析是納入“文章之體”來統一考慮的。綱目中呈現的文之整體觀是一方面,而更為值得重視并挖掘的是創作論內容剖析中時時處處的整體觀念(這將在下文詳細探討)。總之,創作論自始至終體現出對寫作文本的一種整體視角,這種“文之整體感”伴隨著生成過程中的層級轉化,又是對自身多層次結構的綜合把握,尤其值得今日之寫作教學加以借鑒。
綜上,《文心雕龍》之“文體”理論是需要綜合全書加以審視的,并不僅僅局限于“論文敘筆”,劉勰對文體的高度重視幾乎體現于所有章節,而尤其值得我們加以挖掘借鑒的是其貫穿于創作活動始終的文之整體觀。
二、反思:文體感培養的具體思路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文心雕龍》以貫穿全書的文之整體觀念彰顯其對文體的高度重視,并集中體現于創作論諸篇。如果說“論文敘筆” 側重各種既成文類的條分縷析,是靜態之“文體”,那么“剖情析采”的創作論,則是寫作過程中對文體的具體把握,體現出一種動態的“文體感”。實際上這種動態的文體感,左右著寫作的全過程,在寫作實施中通過不斷對文本加以矯正,從而實現文體的由隱及顯的轉化生成,并最終體現為對自身多層結構內涵的整體之把握。
文體感,亦有人提出又稱文體意識,就是寫作或閱讀過程中“對各種各樣的文章體裁的認定和辨析”。[6]本文認同具有多重結構內涵的整體之“文體”概念,因而,文體感并不僅僅針對文章體裁;而“文體感”或與“文體意識”近似,但相較來說,“感”字強調主觀之綜合感覺,更為感性直觀,似更符合“文體”之模糊多義與整體形相性。
至于文體感在寫作中的作用發揮,“認定與辨析”誠然是一方面,但過程中還應有更為細膩的把握。姚愛斌先生曾對文體之生成有一段詳細論述:
在文體創作過程中,創作者一般先有一個關于所有文章的整體觀念,盡管很多作者未必在每次寫作時都能清楚地自覺到這一點,但這是文章寫作的一個基本前提,不能想象一個毫無文章觀念的人能夠進行文章寫作;然后是確定選擇何種文類文體,在這一環節中,作者需要形成一個非常清晰的關于已選文類文體的整體觀念,包括適合這種文類文體的題材內容和語言形式等;最后才是一個現實的、具體的文章整體的完成。當作者完成這一創作過程后,基本文體和文類文體便自然融人了現實存在的直觀的文章整體之中,實現了體與用的合一;也即是說,基本文體層面的文章整體存在、文類文體層面的文章整體存在和具體層面的文章整體存在,在現實中是完全統一的。[2]
文體之生成經歷了這樣一個從一般到特殊、由潛在到現實的過程,文體之層級轉化一目了然。但在實際創作中,層級之界限往往是模糊的,如普適意義的文章觀念常與文類文體之規范合二為一共同制約著文體之走向,具體文體的創造又常常回環往復于其他層級,這一生成過程會通于寫作者的文體感把握。依托于寫作實踐,本部分試結合《文心雕龍》相關篇目從以下四個方面具體審視寫作過程中的文體感:
(一)《宗經》:“論文敘筆”與文體之規范歸屬感
前文說過,《宗經》是樞紐論的核心,亦是貫穿《文心雕龍》全書的指導思想,而“宗經”主要就是宗經之體。篇中說:“勵德樹聲,莫不師圣,而建言修辭,鮮克宗經。”可見劉勰正是要在建言修辭的意義上宗經,并視其為“性靈熔匠,文章奧府”,“義既埏乎性情,辭亦匠于文理,故能開學養正,昭明有融。”這里的“經”具體指易、書、詩、禮、春秋等儒家五經,《文心雕龍》認為其文章典范意義可以燭照寫作之多個方面,并綜合體現為對經典之體的內外多層次的模范與把握,即所謂“稟經以制式,酌雅以富言”。另外,篇中還說到“圣文殊致,表里異體”,五經實際上代表了五種不同的文章大類,并將“論文敘筆”的多種文類做了比附五經的歸納①前已詳引,歸納之合理或牽強不在本文論述范圍,暫不議。。可見,“論文敘筆”部分正是在“宗經”統攝下對各個文類的進一步鋪展,從“經”到各類“文、筆”,體現了文類體系的不同層次。《宗經》篇又指出,圣文異體亦是相通的,它們共同作為文之最高典范,具備普適意義的文之特性:“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貞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這六義,正是劉勰認為的普適意義的文體之規范標準:情深、風清、事信、義貞、體約、文麗。從這里亦可再一次驗證《文心雕龍》中文體涵義的多層次性。
以今日之眼光來看,“經”自然不必再做拘泥之理解,而可以視為某種標準與規范的代稱。前文說普適意義的文章觀念常與文類文體之規范合二為一,共同制約著文體之走向,這正體現于《宗經》及“論文敘筆”的論述中。五經既有文之普適意義,又是某一角度歸并的文體大類之典范,“論文敘筆”的論述亦溯源于五經,規范標準的樹立總是包含著對殊致異體的辨析,普適意義的文體總要依托于某種文類之體。而規范標準又是體現在具體文體中的,“宗經”和在其統攝下進一步鋪展的“論文敘筆”,都是依托于“經”或“文、筆”這些具體之文。我們將這種依托于具體文體而顯現的對普適文體、文類文體規范的認識與把握稱之為文體之規范歸屬感,這正是文體感的初步體現。
文體之規范歸屬感是基于大量閱讀而逐步形成的一種文體感知能力,并在自身之寫作實踐中得到強化,絕非外在的文體知識灌輸所能達到。近年來學生論文寫作中常出現的散文化傾向、缺少思辨的抒情式語言即是缺乏文體之規范歸屬感的典型體現,論文寫作知識可以輕易獲得,但日常閱讀與寫作訓練的缺乏無疑難以形成準確的論文文體感知能力,也就無法有效駕馭論文寫作的各個方面以達到最終成文的整體統一。因而,文體教學應注意依托文本,引導學生多讀多練,在讀文時具備“體”之眼光,對這一具體之文有文類體系上的判斷和比對文體規范的思考。前文提出可以基本文體(文體大類,非姚文所指之普適文體)中的典型代表為切入點,以點帶面。實踐證明這一思路是切實可行的。從各類精選文本的閱讀中,能更鮮明地感受“殊致異體”,從而對文之規范歸屬有較好把握。這里還要注意不是單純的體裁層面,應是建立在對“文體”概念理解之上的多層次把握。如果說文體之規范歸屬感可以在閱讀中有意培養,在寫作過程中則體現為一種潛在力量而左右著寫作行為。執之有度,可以較好地調整寫作走向從而形成最終之成功文本;執之無度,過或不及,則導致兩極:因循套路或文體渙散。這將在下文有所述及。
(二)《體性》與文體之選擇
文體之規范歸屬感其實已隱含一種選擇性判斷,一種確定大方向的文體定位,但著眼在規范歸屬,結合《文心雕龍》之《體性》篇,我們對寫作中的文體選擇當有更清晰認識。寫作中需要有一個文體定位以確定寫作的方向,這個方向會潛在規范著寫作行為。實踐中有指定文體寫作和自選文體寫作之別,而即便是指定文體寫作,基于文類體系的多層次性,亦包含寫作者個人的逐步細化選擇。而且“文體”是有自身多重結構內涵的概念,這種選擇性亦體現在體裁而外多個層面的考慮。寫作行為在文體定位之上,不斷加以調整細化落實,從而實現具體文體的生成,在這轉化過程中,不能忽視個人對文體的個性化選擇。
《體性》篇中說:“才有庸俊,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并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本著“因內而符外”的觀點,其認為文章寫作“各師成心,其異如面”,并歸納出八種文章之體和不同作家的個性文體表現,具體為:典雅、遠奧、精約、顯附、繁縟、壯麗、新奇、輕靡。從用詞看主要就是風格層面的歸納,但結合下文之詳細論述則不難看出,每一體亦包含文辭、體制等多個層面之特性,因而,所謂的八體,即是從風格角度歸納的蘊含多重結構內涵的文體之大類。劉勰認為“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八體”之典范或可學而得,最終之文體創造取決于個體之情性。所謂“表里必符”。《定勢》篇中說的“因情立體”正可以做本篇之恰切注腳:紛繁之文章樣態與作者之主觀情性關系密切,下筆為文無不是個人情性之體現,具體文體的創造是順應情性的選擇。
寫作中個人情性的確影響著作者對文體的選擇,朱自清先生當年就曾慨嘆:“寫小說真不容易。我一輩子都寫不成小說,不知道從哪里下筆。鋪展不開,也組織不起來。不只長篇,連短篇也是。”[7]雖是自謙,亦可見情性之取向,散文詩歌在先生那里則更為得心應手。人之情性有別,對不同文體的駕馭亦各有短長,因情立體,選擇更為契合己之情性的文體發揮所長才是明智之舉。今日之寫作考試中經常面臨的“文體不限”、“文體自定”等題目要求,無疑也是考查作者的文體選擇能力,當然作為應試,還需考慮材料儲備、駕馭難度、時間等其他因素而不單純出于情性之考慮。但作為日常之寫作實踐,情性無疑是影響文體選擇的重要因素,這種選擇也不只在體裁意義上,亦體現于語言、風格等其他層面。
反觀當今,學生在無文體限制的日常寫作中,往往總是選擇寫自己喜歡或自認為較擅長的文體,即主要就是出于一種情性考慮,但應引起重視的現象是:對“不擅長文體”尚缺乏足夠的認識與寫作嘗試卻一味排斥;對“擅長文體”卻在不斷的自我重復中面目雷同難有超越,這便將“因情立體”片面化了,是一種盲目任情的表現。《體性》篇對這一問題有較為辯證的態度,雖標舉性情,但非常重視學之功,即后天的習染,尤其是初學為文,認為“才由天資,學慎始習,斫梓染絲,功在初化,器成采定,難可翻移”,因而提出“童子雕琢,必先雅制”的主張,并進而提出“摹體以定習,因性以練才”的具體訓練方法。
因情立體是有前提的,應對各類文體之規范有較深入了解并通過反復的摸索實踐去揣摩碰撞后才會有清晰之把握。“摹體以定習,因性以練才”正是較好的訓練途徑,要從不斷的摹、練中慢慢確定自己的方向,而不是盲目任情。
(三)《定勢》、《通變》與文體之定與變
文體實施過程中的個性選擇同時引出文體之定與變的問題,文體的細化落實,不是對外在某種固定程式的照搬,而是一種動態的隨機把握。這在《定勢》、《通變》兩篇中有詳細論述。
《定勢》篇中提出的“勢”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概念。篇中說“因情立體,即體成勢”,“勢者,乘利而為制也。”詳析字義,“體”側重靜態之文體呈現,而“勢”側重動態之行文趨勢,二者是緊密關聯的,“勢”的把握體現了文體生成過程中定與變的辯證統一。
《定勢》篇中歸納了四種“即體成勢”的表現:“模經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騷》命篇者,必歸艷逸之華;綜意淺切者,類乏醞藉;斷辭辨約者,率乖繁縟”,從整體文意上看,亦大致呼應了《體性》中提出的“八體”,從中可見“體”之與“勢”的緊密關聯和制約作用,體現出勢之“定”的一面。一旦選擇某種文體,必然在各個層面制約著文之走向,寫作者應因應其自然之勢成文,體不同則勢不同。但“勢”隱含著不確定性,是動態的,并非某種固化之體的再現,“淵乎文者,并總群勢”,必須具備“兼解以俱通”、“隨時而適用”的能力,并且在具體行文中,防止“總一之勢離”,注意文之體勢的統一。因而在文體的創造過程中,既有定,又有變,所謂“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篇中“譬五色之錦,各以本采為地”的比喻形象說明了這一變與不變的道理,行文當“隨勢各配”,亦應遵循體之根本屬性和自身的完整統一。機械因循,必然形成套路而固步自封,失去寫作的創造之義。如學生習以為常的議論文寫作,越來越淪為一種程式化的教學文體,結構固化、材料羅列、論證簡單,呈現為一種一廂情愿地自說自話而沒有真正地“論起來”,即是忽略了對文章之勢的具體分析與靈活把握。而無視規范任意行文,即所謂“隨性文字”,失去了“本采為地”的文體考慮,亦多忽視自身的完整統一,則淪為“失體之文”,或曰“訛體”,亦難以達到真正的文體之創造。《定勢》篇總結應“執正以馭奇”,謹慎“逐奇而失正”,一旦“勢流不反,則文體遂弊”。
亦可結合《通變》篇來進一步辨析。“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可以說文各有體又文無定體,這一問題應辯證對待。文章本同末異,“名理有常,體必資于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于新聲”,這涉及從不同層級來看待文體之義,普適文章之體、文類文體是為“有常”,具體文體則為“無方”之靈活創造。但這一創造是以掌握“有常”之體為前提的,“矯訛翻淺,還宗經誥”,方可“與言通變”。《阿Q 正傳》的序中,魯迅曾對古往今來各種“傳”之特點做了一個總結,雖說有些游戲調侃,但亦可見其對傳統史傳文學、進而章回小說的深厚功底,正是建立在對多種文章舊式的了然于心和融會貫通的基礎之上,魯迅實現了“傳”這一文體的突破,開創了現代小說的新范式。
《通變》篇指出通變之數即為“參伍因革”,有繼承才能有創新,盲目求新,只會成為“訛體”。因而在“規略文統,宜宏大體”的基礎上,寫作者乃“從容按節,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從而造就“穎脫之文”。這正體現了寫作過程中文體之規范歸屬感與個人之情性選擇的綜合作用。
(四)《附會》與文體之整體自圓
具體文體是在對普適文體、文類文體融會貫通基礎上的生成創造,其本身自成一體而完整統一。無論哪個層級,都蘊含著劉勰一以貫之的文之整體觀,而集中體現于顯性的具體文體創造中。通過上述對《文心雕龍》內容的分析我們看到,創作論自始至終體現出對寫作文本的一種整體視角,這種“文之整體感”伴隨著生成過程中的層級轉化,又是對自身多層次結構的綜合把握。前文亦已指出,創作論行文綱目的“總—分—總”的視角特點,正彰顯了劉勰的文章整體觀;而《附會》篇置于創作論之最后,筆者以為在強調具體文體之整體把握方面不無用意。
《附會》篇的內容,有人認為是就附辭會義角度談命意謀篇的,有人認為是講文章結構的,有人認為亦包括文章之修改。總之,本篇之文章整體視角顯而易見,又置于整個創作論之最后,其彰顯的文體論意義不容忽視,寫作過程中文體層級的轉化、文體感的作用發揮最終落實到具體文體的整體自圓。
何為附會?篇中說“總文理,統首尾,定與奪,合涯際,彌綸一篇,使雜而不越者也。”體現出明確的文之整體觀。“附辭會義,務總綱領”,本篇著意強調“體統”之大視角而反對有句無篇。而附會之術又需“表里一體”,這與劉勰的多層次文體觀緊密相聯。篇中提出“必以情志為神明,事義為骨髓,辭采為肌膚,宮商為聲氣”。情志、事義、辭采、宮商正是由內而外多層次的文體之把握。“附會”體現出縱、橫多向度的文之整體觀。變文之術無方,文體之實施創造,應具備超越各種規范之上的獨立把握能力,有效調動多種創作手段,使文章首尾各部、各個層面協調統一以達到自身的整體自圓。篇中說馭文之法“齊其步驟,總轡而已”正是此義,而如果“統緒失宗,辭味必亂;義脈不流,則偏枯文體”。
體之為義,最根本即其整體性。落實到具體文體的創造,在基于文體之規范歸屬、文體之個性選擇的定與變的交錯之上,文體感集中體現為對其自身縱橫各向協調統一的判斷把握。無體不成文,超越范式之后的整體自圓是文體創造之最終把關,倘若沒有這種整體自圓的判斷把握能力,則必定“統緒失宗”,寫作中忽此忽彼,情志、事義、辭采、宮商不能相互協調,文章亦渙散零落,寫成所謂“四不像文體”,這是我們需要警醒的。
有文就有體,文體之于寫作意義重大。現今文體意識的淡薄已成為普遍現象,知識灌輸型的文體教學方式亦應摒棄,培養寫作過程中的“文體感”是提升學生文體把握能力的有效方法。而稟文之整體觀,依托大量的閱讀與寫作實踐,久之必形成強烈的“文體感”(包括規范歸屬感、文體選擇、定與變、整體自圓等多個方面),文體知識也才會真正地內化為自己的能力。這,是《文心雕龍》給我們的重要啟示。
[1] 楊東林.開放的文體觀——劉勰文體觀念探微 [J].文史哲,2008 ,(4).
[2] 姚愛斌.論徐復觀《文心雕龍》文體論研究的學理缺失 [J].文化與詩學,2008,(2).
[3] 周振甫.《文心雕龍》譯注 [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
[4] 趙紅梅.論《文心雕龍》與高校基礎寫作課程的內容體系 [A].文心雕龍研究 (第十輯) [C].北京:北京學苑出版社,2013.
[5] 祖保泉.文心雕龍解說 [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
[6] 李秋萍.不能忽視文體意識的培養 [J].海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8,(4).
[7] 陳孝全.朱自清傳 [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