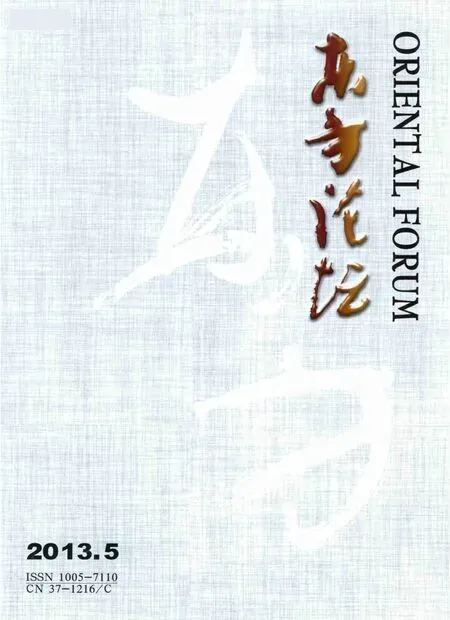現代性與東方文化
石海軍
(中國社會科學院 《外國文學評論》編輯部,北京 100732)
現代性與東方文化
石海軍
(中國社會科學院 《外國文學評論》編輯部,北京 100732)
西方的現代性與東方文化有著復雜的關系,體現在鄉村與城市、殖民主義、資本主義、文化流散、現代社會結構的變遷、“解構”與文化革命等多個方面。對于西方“理論”,我們重要的是要有問題意識、自我意識,在不斷變化的世界里不斷地變化著自我,將我們的經驗借助于外部的刺激而加以融會貫通、并轉化成于自我和現實之中。
現代性;鄉土;城市;鄉愁;解構;第三等級;文化革命
一、西方的現代性與現代城市的出現
“現代”、“現代性”、“現代化”等等詞匯在西方的出現,標志著歐洲中世紀時代的結束,新大陸的發現、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等歷史事件的發生,“構成了現代與中世紀之間的時代分水嶺”。[1](P6)不過,即使從歷史的角度看,“現代”、“現代性”的概念,在學界也是爭議頗多,主要表現為,雖然中世紀結束了,宗教和神學的權威處于逐漸被消解的狀態之中,但理性、絕對理念等等卻變成了新的主體意識,直至19世紀后半葉,我們當下所謂的“現代性”、“現代性”等觀念意識才開始在波德萊爾、福樓拜等作家的作品中出現,這便是與西方工業革命相結合的現代都市生活的體驗:“惡之花”式的現代人的生存狀態。
在工業革命之前,盡管城市早已存在,但人們對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差別和對立并沒有突出的感受,鄉村與城市雖說屬于不同的天地,但在整個英國社會結構中,鄉村一直占據著主要的地位,城市和城市生活對農業社會形態并沒有直接的影響。但工業革命之后,現代大城市的出現,則使英國傳統的農業社會形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早在1911年,喬治·斯圖特(George Sturt)就在《鄉村的變化》(Change in the Village)等書中宣稱:“傳統的英國鄉村現在已經死亡了。”這種觀點在當時及后來一段時間內很有代表性。1932年,利維斯(F.R.Leavis)和湯普森(D.Thompson)在他們合著的《文化與環境》(Culture and Environment)一書中也進一步描述了英國古老鄉村的消失。學界較為普遍的看法是,英國社會的這種變化發生在19世紀上半葉,托馬斯·哈代、喬治·愛略特、理查德·杰弗里斯(Richard Jefferies)的文學創作雖然出現在19世紀下半葉,但反映的卻是19世紀上半葉英國鄉村生活所發生的變化:但伴隨英國工業革命而出現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改變了人們的生活,農業與四季古老而永恒的節奏被擾亂了,它正處于毀滅之中。
雷蒙德·威廉姆斯認為,在英國工業革命后出現的現代大城市不同于傳統英國社會中的城市,工業革命不僅改變了鄉村,同時也改變了傳統的城市,資本主義的歷史是城市對鄉村的逐步勝利。[2](P1)“革命”雖說是“工業”性質的,但實際上它卻是從“農業”資本主義發展而來并使農業從屬于工業的社會轉型過程,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化的過程實際上是使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逐步消失、傳統農業社會的風土人情不再存在的過程,至今英國社會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人從事著農業“勞動”,而且實際上他們也不再是傳統的農民了,因為現代工業技術已經改變了他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他們與城市人口并沒有根本的差別。
當西方工業化的大城市逐步取代星羅棋布的鄉村時,整個社會形態,不僅是經濟領域而且是政治、思想領域,都發生了根本的轉變;而這種轉變,又伴隨著西方的殖民入侵,帶動了整個世界都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從政治和經濟的角度來看,馬克思和恩格斯最早認識到西方現代城市是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果,《共產黨宣言》明確地寫道:“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系都破壞了……資產階級使鄉村屈服于城市的統治。它創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鄉村人口大大增加起來,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脫離了鄉村生活的愚昧狀態。正像它使鄉村從屬于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3](P253-255)
《共產黨宣言》發表于1848年,它對于當時世界的描繪是極其真實的。盡管當時的西方資產階級把共產主義看成是正在歐洲徘徊的“幽靈”,但是他們包括英殖民統治者實際上也是按馬克思對社會歷史的分析來看待東方和西方的。如亨利·薩姆納·梅因(Henry Sumner Maine)1871年發表的《東西方的鄉村社會》(Village Communities in the East and West),巴登—鮑威爾(B.H.Baden—Power)出版于1896年的《印度的村社》(The Indian Village Community),都強調從政治、經濟以及管理的角度對印度村社進行殖民改造,以使印度的社會結構能夠從屬于西方社會的發展。[4](P23-24)
二、鄉愁情緒與東方現代社會的變遷
自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中國逐步淪為殖民與半殖民地,而印度在1849年前后就已經全面淪為英國的殖民地了。與此同時,城市對鄉村的“征服”便在中國和印度開始了,但在將近百年的時間內,人們更多感受到的是西方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上對東方的“征服”,而對現代城市的出現,作家們在文學上的感受并不明顯。
何以如此?這是因為,西方的入侵,并沒有使中國與印度這樣傳統的農業社會一下子便進入與現代城市聯系在一起的現代化工業社會,現代工業與城市雖然出現并快速發展,但人們更多感受到的卻是與傳統農業社會聯系在一起的鄉村的失落。中國現代文學評論家嚴家炎先生曾說:“鄉土文學在鄉下是寫不出來的,它往往是作者來到城市后的產物。”[5](P74)這說明,鄉土文學的產生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廣而言之,它是東方傳統在西方文化的沖擊下產生的,只有當伴隨著城市生活的城市意識或隱或顯、或多或少地出現時,鄉村才能在特殊的環境中凸顯出其現代文化意義來。因此,鄉土文學的出現實際上與東西方之間的文化沖突有著密切的同構關系,在這種同構關系中,鄉村與城市都不再停留于單純的地理意義上的差異,而更多地反映出不同文化之間的接觸與碰撞。
盡管早在戰國時期,中國的城市已經成型,但對于中國古典文學來說,城市與鄉村之間的二元對立并未形成,文學的鄉村覆蓋了城市,文學之中并未出現另一個相異的文化空間。到了20世紀30年代,上海作為一個現代都市出現于在茅盾、張愛玲、丁玲等作家筆下時,盡管這個大都市與現代資本主義發生了密切的關聯,但中國作家對上海的體驗卻完全不同于西方現代作家的城市感受,雖然他們的作品開始涉及鄉村與城市的結構性沖突,雖然對現代城市也有某種“新”的或說是現代的感覺,但“城市經驗”在我國五四以來的文學中,一直沒有占據主導地位,相反,鄉土和鄉村則一直是文學表現的中心,城市常常成為鄉村的陪襯或對立的一面出現,表現城市與鄉村的結構性對立和變化成為我國現代文學的主要形態。
盡管存在著巨大的文化差異,但城市生活給鄉村社會所帶來的結構性沖突,卻是中印兩國現代作家在一定時期內所面臨的共同問題,普列姆昌德等印度作家的小說,正像魯迅、茅盾等作家的小說一樣,也是在城市與鄉村、西方與東方之間不同的文化沖突中自然而然地出現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當英國入侵印度并對印度進行殖民統治時,很長一段時間內,印度的知識分子雖然認識到英國代表的是不同的文明,但他們很少直接從現代城市文明的出現與發展上來認識印度鄉村世界將要發生的巨大變化;當然,在英國的殖民統治下,以加爾各答、孟買等現代大城市為代表的文明已經在印度出現了,但孟買等城市主要是英殖民者的活動中心,相對于印度的廣大鄉村而言,印度的城市化時代遠遠沒有到來,印度的知識分子對城市所帶來的真正信息以及城鄉之間不同的文化意義并沒有多少真實的感受。所以,貫穿20世紀印度文學發展史的基本經驗依舊是“鄉村”,從鄉土文學式的懷舊情緒逐步發展成為“邊區文學”中的破敗感、凋弊感甚至是腐爛感。
東方現代文學中為什么會產生揮之不去的鄉愁情緒,而且這種情緒會逐步演化成為某種頹廢感呢?這實際上與西方文化即現代性問題聯系在一起。一方面,人們懷念傳統的生活方式的寧靜,這就像西方19世紀上半葉,哈代在小說中流露出來的對英國鄉村生活的留戀,在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傳統的鄉村世界注定要失去了;另一方面,與哈代等西方小說家對傳統鄉村的感情不同,印度、中國等東方作家又面臨著不同于哈代等作家當年所面臨的復雜的文化問題,英國社會結構在19世紀上半葉所發生的變化,源于英國文化內部的迫力,而東方國家在20上世紀上半葉的變化,則是在“內外交困”的情形中發生的,從中反映出來的不僅是傳統東方文化的變革問題,同時也是現代性從西方到東方之后所面臨的新的難題。
針對英國對印度的殖民統治,馬克思曾說:“歷史中的資產階級時期負有為新世界創造物質基礎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類互相依賴為基礎的世界交往,以及進行這種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發展人的生產力,把物質生產變成在科學的幫助下對自然力的征服。資產階級的工業和商業正在為新世界創造這些物質條件,正像地質變革為地球創造了表層一樣。”[6](P75)當殖民主義打破了印度等前殖民地國家小農經濟的傳統和社會結構、為這些國家帶來了世界性的交往活動時,東方與西方從此便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在世界擴大的同時,世界秩序的構建問題便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印度等非西方國家本來也有自己的社會秩序,但殖民列強的到來,將它們原有的秩序打破了,它們被拖入到西方現代文明所試圖建立的新秩序之中。在這種新秩序中,它們被迫處于從屬和附庸的地位,而它們又不甘心于此,這樣,英國與印度、西方與非西方常常處于對立的狀態,從而使現代性問題充滿了各種矛盾。隨著西方現代所建立的秩序的不斷擴大,現代性變得越來越混雜、矛盾。西方現代性試圖將現代世界整合為一體,但世界范圍內殖民體系的解體卻促使著現代主義向后現代主義的演變。這種演變一方面證明了西方現代性本身存在著矛盾性和含混性,另一方面也說明西方現代性的對立面即來自西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力量也在不斷地加深了現代性本身的矛盾性和含混性。
麥金泰爾在《德性之后》一書中闡明了現代性導致道德敗壞的根源:由于放棄了舊的道德觀念之后,人們賴以維系生命的價值體系很快就崩潰了,而新的思想觀念又還沒有產生,因此社會生活的混亂就難以避免了,所以他認為“現代道德理論中的問題顯然是啟蒙運動的失敗造成的。”[7](P80)將現代性以及從現代性衍生而來的后現代性的各種問題歸結于與人的理性聯系在一起的啟蒙運動的失敗,是西方學界近些年來形成的看法,這種觀點是對西方文藝復興以來的人文主義傳統的批判與反思,對我們認識現代性問題的思想根源不乏深刻的啟發意義。但無論是文藝復興還是啟蒙運動,對于人文精神和理性的強調并沒有走向極端,啟蒙運動雖然富于反叛精神,但這種反叛恰恰建立在對于人類價值的追求上。理性雖然是啟蒙主義的核心范疇,但并非唯一范疇,更非啟蒙的終極目標。顯然,我們無法將當下西方德性的失落歸究于啟蒙運動的失敗,實際上,啟蒙運動只是西方現代社會發展的一個歷史階段,我們無法以局部代替整體。
在現代性問題產生的根源上,筆者認為馬克思主義依然是我們思考問題的出發點,馬克思深刻認識到資本主義的兩面性,認為它既是一種解放性的力量,也是一種災難性的力量;它既為人類創造了財富,同時也為人類帶來了危機;它既開拓了世界,同時也使世界變得災難重重。這正如馬歇爾·伯曼在《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現代性體驗》一書中評價《共產黨宣言》第一部分時所指出的那樣:“馬克思從兩個對立的方面展開了論述,這兩個方面將塑造和激發未來一個世紀的現代主義文化:一方面是永不滿足的欲望和沖動、不斷的革命、無限的發展、一切生活領域中不斷的創造和更新;另一方面則是虛無主義、永不滿足的破壞、生活的碎裂和吞沒、黑暗的中心、恐怖。”[8](P131)如果說隨著西方對東方的入侵,使東方開始了現代化的歷史進程,那么,與此同時,這種現代化本身既是“革命”的動力,同時也是一種破壞甚至是毀滅性的力量。
可以斷言,目前人類社會文明所遭遇的絕不是東方或西方的問題,更不是人權、民主等某一方面的枝節性問題,而是現代資本主義將世界打成一片但又無法整合世界的危機,是在二元對立的認知“結構”被“解構”之后而發生的價值危機和困境,折射出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世界等各個方面都出現了新的難以解決的問題:在真與假、美與丑、善與惡、身體與靈魂、正義與邪惡等等二元對立的結構被消解之后,世界變得不僅越來越破碎,而且也越來越虛妄、無望了。
三、文化的離散與“鄉愁”的城市化
現代社會的變遷或說是現代化的過程,在20世紀中國和印度作家的筆下更多地表現為鄉村的巨大變化以及這種變化中出現的各種問題。進入21世紀之后,在鄉村城鎮化的快速發展中,在民工潮的強力沖擊下,城鄉之間結構性的矛盾以及這種矛盾的不斷轉化而給社會所帶來的變化,極大地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和生存狀態,雖然我們依舊生活在類似于西方十九世紀上半葉的社會結構之中,但與此同時,西方當下社會的一切又都與我們的生活密切聯系在一起。因此,我們不妨說,與法國作家波德萊爾的城市“惡之花”相比,當下中國、印度等第三世界的文學表現對象更像是鄉村“惡之花”,這種“惡之花”本來是西方的、是大都市的情調,但卻奇特地嫁接于東方“鄉村”世界,在鄉村與城市的界限不再分明、東方與西方相互交錯的文化互動中,文學早已不再是20世紀上半葉的“鄉愁”,隨著鄉村的城鎮化,城市與鄉村兩種“惡之花”也在不斷地靠攏。
2012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了中國作家莫言,10月11日,莫言接受采訪時遇到這樣一個問題:“老師,您好,我是香港無線電視臺的記者,想問一下,因為你很多作品都是以家鄉為主的,但是現在你有不少的時間在北京居住,北京這個城市,有沒有想到未來的作品會以城市為主,或者是香港?有機會到香港嗎?”顯然,作家莫言對鄉村與城市之間的關系問題是深有感觸的,他回答道:“我的小說確實是寫了很多的農村題材,我本人也在農村生活了很多年。實際上我對后來的寫作里面城市對我的影響已經在小說里面有所體現,但是我沒有把它完全放在一個明確的背景里,北京或者香港或者上海。而是寫了很多在一個鄉愁的基礎上成長的城市,也就是說我的鄉愁已經跟30年代的鄉愁有很大的變化,它已經是變化的鄉愁,已經是城鄉化、城鎮化的鄉愁。這樣一個城鎮化的鄉愁跟大城市的生活當然有區別,但已經區別不大。你如果說我一直是一個鄉愁作家,嚴格的說,不太能夠讓我服氣的。”
“城鎮化的鄉愁”,實際上從城市的角度來描寫鄉村,雖然依舊是鄉村,但其中已經浸透了城市的氣息,而且這是一種可怕的、無孔不入但又說不清楚的氣息。如果說20世紀二三十年代發生于中國、印度等東方國家的鄉土文學試圖將喧囂的城市退回于寧靜的鄉村的話,那么,自20世紀下半葉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東方國家正在發生著從鄉村到城市的文明大遷徙;這種遷徙并不是從邊緣向中心的移動,也不是將中心城市文化的價值向邊緣鄉村地區輸送,而是從里到外,從外到里的雙向滲透;再者,這種“滲透”,也不僅僅表現為城市與鄉村的對立或統一,而是有著極其復雜的世界背景,說它是全球化也好,說它是文化的流散也好,由于全球資本的運轉模式,也由于新的信息交流形式,人們的生活、心理和感情不僅不再像以前那樣恒定了,而且一切都被打成了碎片,一切都處于流動之中。因此,莫言認為,雖然他作品中的故事基本上都發生在他的家鄉——山東高密,但與傳統的鄉土文學不同,他的作品并不是以風俗人情見長,而是將高密當成了中國的縮影,他是借高密來描寫他心目中的中國甚至是世界:“西方的小說對我們的文學觀念,產生了巨大的沖擊,使我們從1949年到1979年這30年來形成的文學觀念土崩瓦解,作家的思想真正得到了解放。”實際上,何止是文學觀念,隨著西方“理論”的引進,哲學社會科學各領域都在“解放”,正好應合了整個中國涌動著的“對外開放”潮流,不僅是經濟上的,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
正如改革開放的中國在政治、經濟上要不斷調控一樣,文學創作上,也要在東方和西方之間尋找相應的平衡。馬爾克斯、卡夫卡等作家使當代中國作家眼界大開,但隨之也就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莫言便覺悟到,馬爾克斯、福克納、海明威等作家“就像煉鋼的火爐一樣是灼熱的。如果靠得太近的話,我們就被烤掉了,熔化了,蒸發了。我們必須遠遠地離開他們,必須千方百計地寫出一種跟他們不一樣的小說來。這就需要去民間尋找,在民間故事、口頭傳說、民間文化、民間口語里面尋找,所以說文學豐富的資源還是隱藏在民間。當然這個民間,并不是指偏僻、荒涼的農村,城市也是民間,它是廣義的、另類的民間。”[9]莫言在此所謂的“城市也是民間,它是廣義的、另類的民間”的說法,是頗有見地的,它說明與傳統聯系在一起的“民間”已經變成了一個復雜的文化空間,民間早已不再是一個單純的、特定的文化圈子,而是以某種復雜的社會構成形式存在于我們的生活之中。小說是一種虛構,但與此同時,小說又被認為是真實的;它來源于生活,但又不是生活,這好像是一個悖論。但作家以深刻的洞察力和敏銳的感受化解了這個悖論,這樣,山東高密既是莫言筆下的鄉村世界,同時這個鄉村世界又是城市化了的民間,甚至其中也糅進馬爾克斯或福克納式的文學世界。如此,真實與虛構、城市與鄉村、東方與西方、自我與世界在既有差別又無本質不同的狀態中早已合為一體。
與莫言在文學上對自我生活體驗與西方文學觀念的感知與融化一樣,V.S.奈保爾也有相似的經歷與看法。奈保爾在創作初期曾追隨著英法作家,試圖像西方作家那樣描寫西方世界,但經歷了一段痛苦的摸索之后,他發現自己在創作中走入了死胡同,自己無論如何都無法趕上英法作家,因為他缺乏這些作家賴以生存的歷史環境和知識背景,也沒有與這些作家相似的生活經歷,他實際上無法描寫西方社會,只能回歸于自身在特立尼達的生活經驗之中,而一旦如此,他不僅感到駕輕就熟,而且真實與虛構之間的關系、創作與借鑒等等藝術難題也就迎刃而解了:“當我開始創作并確立創作題材后,通過直覺,有關小說的矛盾認識才算是得到解決。1955年我對伊弗琳·沃有關小說是‘完全轉化了的經驗’(experience totally transformed)的定義有了突破性的認識。在此之前,我是無法認同也無法相信這種說法的。”[10](P23)
奈保爾所謂的“完全轉化了的經驗”,是在打破了時間與空間的束縛之后實現的,既是對自我經驗的回歸,又是對自我經驗的超越。按奈保爾的說法,他自己的生活體驗以及與他類似的印度作家的生活體驗,實際上更接近西方19世紀的文學世界,但他卻生活在“現代”、“后現代”的世界,因此,有某種時間上的斷裂感;與此同時,從前殖民地來到英國,不僅在地理空間,更重要的是在心理空間和文化空間上有某種錯位感。在這種斷裂感和錯位感中,我們常常試圖使自我大踏步似地躍進“新世界”之中,這恰恰是一種錯覺;而意圖回歸于“舊世界”則更是一種錯覺。
在當今“全球化”時代,人人都不再是某種單一文化的產物,無論是生活在西方還是東方、城市或鄉下,“現代性”已滲透到世界的各個角落,我們人人都處于文化“流散”的狀態之中。
四、文化的流散與現代市民社會
文化的“流散”問題,最初主要與寄居西方的東方僑民作家的創作相關,但隨著全球化時代的發展,文化的“流散”問題早已不再是僑民作家所面臨的問題了,而是東西方作家所面臨的共同問題。所謂“流散”,實際上是指傳統文化的穩定性已不復存在,一切都處于風雨飄搖之中,這與資本主義、現代性以及現代城市的出現有密切的關聯。
為什么說與資本主義密切相關的現代城市的出現與發展會使得歷史、傳統以及現實中一切穩固、永恒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呢?我們不妨從日本的明治維新說起,“明治”是日本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歷史時期,“維新”主要是接受西方現代文明而發生的社會變革,首先這是一種價值觀念的轉變:“如果說封建時代的價值觀念是重視出身與教養而恥于言利,那么,明治時期則發展為尊重‘錢神’,認為‘有錢之處即開明之鄉’,‘西洋之文明開化在于錢’,‘國不能富則文明不能進步’……”[11](P99)價值觀念由“義”變成了“利”,隨之而來的便是整個社會結構的改變,身份的高低不再以出身論,而是金錢論,這樣,與傳統的封建等級相關的階級觀念便發生了變化,階級、身份不再是固定的,從而導致整個社會生活在不停地發生著變化,這便是與金錢聯系在一起的資本主義的力量:資產階級的出現必將使一切發生變化,使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在傳統的東方社會中,商人、手工業者等等多屬于社會的第三等級,社會地位本來是不高的,但隨著現代資本主義的到來,第三等級的地位發生了變化,并日益成為社會力量構成的主體,現代社會的結構因此而不斷地發生著變化,因為第三等級的構成從來都不是固定不變的,其價值觀念也完全不同于傳統的仁義道德,一切都受到利益的驅使,從而使現代社會處于不停的變化之中。
馬克思向我們展示了資本主義如何興起以及資本主義給世界帶來的天翻地覆的變化,并從階級分析的角度揭示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及其可能的結局。不過,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馬克思所說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斗爭等等階級分析學說似乎早已過時了,工人階級似乎早已消失了,因此,在冷戰結束后,馬克思主義學說在西方曾經倍受冷落、甚至是責難。但隨著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到來,馬克思作為最早從全球的角度審視資本主義的思想家又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而2008年西方爆發金融危機以來,馬克思主義再度成為西方學界討論的熱點問題。①“據統計,1996年和1997年短短兩年之間,僅在英國就售出將近10萬冊《共產黨宣言》。就連《倫敦書評》、《金融時報》、《紐約客》這樣的‘資產階級’報刊都對馬克思在世界經濟領域的驚人洞察力贊不絕口。”見李春放《在歷史迷霧中探索“馬克思的世界歷史觀》,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2年8月15日。在馬克思生活的時代,工人階級占據了大多數人口,馬克思對工人階級的關注有著特殊的時代背景,如果不是僵化地去理解,我們會發現,馬克思主義有關階級分析的學說側重于社會力量的構成和社會結構的變化,強調的是資產階級的歷史作用。比如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使用的術語“burgerliche gesellschaft”,“在德文中就有‘市民社會’和‘資產階級社會’的雙重含義。日本學者望月清司就據此對馬克思的理論進行了全新的詮釋,在日本形成了‘市民社會派馬克思主義’。”[12]在此,“市民社會”與“資產階級社會”的對應,說明資產階級與市民階層的密切聯系。在我國,“新版《歐洲文學史》法國文學部分基本用‘第三等級’或‘平民’取代了先前文學史中‘資產階級’的說法,《德國文學史》第二卷一以貫之采用了德國學術中通用的‘市民’。”②谷裕《文學流派:啟蒙文學》,此文屬于申丹、王邦維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新中國外國文學研究60年”(批準號:09&ZD071)中“流派研究”的一部分,目前尚未出版(發表)。如果說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無產階級已經“消失”的話,那么無產階級實際上早已轉化于市民階層,而市民階層的構成在當今社會處于極其復雜的狀態,既可以是中產階級,又可以是城市游民,而且由于資本力量的不停運轉,這個階層也處于不斷的分化與重組之中,或上升為資產階級,或跌落為小市民甚至是城市游民;同樣,資產階級也處于不斷的“破產”與“暴發”的變化之中,這便是從資本運轉、資本生成的邏輯中誕生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一對矛盾體所構成的“第三等級”。這一等級與資本的運轉邏輯結合在一起,早已上升為社會發展的主導力量。根據馬克思·韋伯的現代性理論,現代國家成型的標志,便是從以宗教、神學和“明君”魅力治國轉變為以世俗理性治國和以法治國,社會意識也從知識精英轉向市民階層,現代社會實際上便是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
在現代社會結構中,“第三等級”也就是市民占據了主導地位,傳統的宗教統治和君主制讓位于民主制,市民參與政治和經濟的社會意識不斷覺醒,這不僅打破了傳統的等級觀念,而且使現代社會處于不停的動蕩之中。社會的動蕩,根源于“第三等級”本身的不固定性,這種不固定性導致它對任何確定性的東西都產生懷疑,并在懷疑中不斷地進行著“反叛”和“顛覆”。
伴隨著資本化、功利化的社會價值觀念,歷史與傳統中任何永恒的價值都在不斷地被重新加以估量,結果,傳統與歷史不僅變得面目全非,而且被徹底消解了:“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一切都實用化,現實化,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只有當下,而當下則是永遠處于變幻不定的“解構”之中,一切都處于“未完成的”、“開放”的狀態,一切都不定型也無法定型;而且一切試圖定型的東西勢必都將被打破,現實中剛剛確立的看似合理的價值存在很快便會因為新的、更加具有活力的因素所取代。“現代”一詞的含義直指當下,而且是永遠的當下,這意味著文化傳承的斷裂和思想價值的毀滅,雖說“現代”依然強調對傳統的繼承和發展,但由于不是回歸于傳統,而是為了使傳統為當下服務,傳統常常在新的“闡釋”中被加以更新和改造了——“傳統”不再被認為是歷史和文化的積淀,而是被人為地“創造”出來的,因此,從根本上說,“現代”與“傳統”已不再構成相輔相成的思想范疇,“傳統”已被“現代”顛覆、消解了。
在當今全球化的世界交往中,依然是資本的邏輯在發揮著主導作用,快速流動并不斷增值的資本以及與資本密切相關的技術、市場機制依然是推動了現代社會快速發展的根本動力,不僅發達國家而且發展中國家以及欠發達國家的發展,都是在資本的運轉邏輯中進行的:不間斷地進行生產、流動、增值、逐利。與此同時,步入新世紀不久,美國“次貸危機”引發了國際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全球經濟發展狀況呈現出更加復雜的情況,“第三世界”如中國、印度、巴西等發展中的力量,像西方啟蒙時代的“第三等級”一樣,正在迅速地崛起,而發達國家,不僅是歐洲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而且美國、日本等代表當代資本主義力量的國家,也開始出現衰落的跡象。這一變化折射出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東方和西方、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均面臨著能否可持續發展的嚴峻挑戰,發展問題已不再是所謂“第三世界”特有的問題,它已成為全球性的問題。隨著資本的國際化、經濟問題的全球化以及國際金融機制面臨改革等等問題的出現,“現代性”問題在新世紀變得越來越復雜。
五、解構與文化革命問題
數百年來,現代社會的發展和現代性問題一直圍繞著歐美,形成了歐美中心論,而世界經濟形勢的變化以及世界經濟中心的轉移與平衡,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在世界經濟交往的過程中的迅速崛起,也從根本上“顛覆”了歐美在世界經濟的中心地位和價值觀念上的引導角色,勢必將使現代性的問題變得更加撲朔迷離,難以琢磨。
與世界經濟形勢的變化同時發生的,東西方社會也在不斷地發生著“革命”。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不僅在南美和非洲等前殖民地社會爆發了革命、民權運動以及隨之而來的動亂和游擊戰,而且在歐美也出現了“1968年法國學生運動”等風云激蕩的文化革命運動。各種激進的、反傳統思潮的“后”現代理論正是在這種文化背景下產生的,我國的“文化大革命”的出現也正好應合了當時的世界潮流,因此,薩特、波伏娃、羅蘭·巴爾特、克里斯蒂娜等當時歐洲思想界的先鋒人物都先后造訪中國。“文革”不僅是新中國歷史上重大的政治事件,同時也是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上少有的文化現象,這樣一種文化現象產生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到底是外來文化影響還是本土文化滋生的結果,都是頗可深思的。從現代性和后現代性的角度中,當時的整個世界實際上都在進行著“文化大革命”。只不過在西方,這種“革命”更多地表現為文化上的反叛、顛覆與解構。
資本和資本主義既是一種無限的解放力量,同時也是巨大的破壞力量,而且常常是“破壞”的一面推動著歷史向前發展;與資本巨大的破壞力量相呼應,文學和文化理論也特別強調“反叛”與“解構”。對現代社會生存現狀的不斷懷疑和反叛,促成了西方自19世紀中葉以來至今不衰的反叛浪潮,進入21世紀以后,各種“后”理論更是將現代性價值的“顛覆”推向了極至,迫切向往著以“解構”現代的方式使現代性問題土崩瓦解,盡快從“現代性”的迷惘走出來,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但理論終究只是話語,其“反叛”的目的雖然指向政治和經濟,但爭奪的不過是說三道四的話語權,這種話語權與經濟領域實際運行和政治領域實際操作的領導權力還是很不相同的,多表現為富于戰略眼光的“高談闊論”。這里所謂的“高談”,主要是指理論總站在高處,以使自己成為一個清醒的旁觀者;所謂“闊論”,是指理論的出謀劃策總是試圖以戰略的眼光,高屋建瓴,勢如破竹般地對現實中的一切進行具有重要指導意義的“解構”。而理論一旦從高處走下來,進入到現實之中,“高談闊論”常常便成了空談,所以理論總是既“無所不能”又“無能為力”。
在各種“解構”性的“后”理論中,雅克·德里達的“高談闊論”無疑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德里達從現象學和發生學入手對文學創作進行分析,認為文學創作是在“既朦朧又不由自主,既無能無力又獨裁的狀態下”進行的,它不僅穿梭于真實與虛假之間,在“自由批判”與“無能為力”之間做著奇妙的往返運動,總是想要表現那能夠接近和不能接近的所有事物,而且打破了政治、歷史、哲學等等意識形態與文學之間的界限,因此,文學本身具有無限的包容性、開放性和對話性——無限的延異性或說是變異性。德里達的“延異說”打破了文學的反映論和形式論,文學的構成不僅不再是作家、作品、生活、讀者、社會、世界等等外在的因素,而且也不再是語言、意象、反諷等等內在的審美形式,而是各種意識形態要素的差異錯置,表現奇特的“建制的虛構”和“虛構的建制”。[13]在這種建制和虛構中,文學首鼠兩端,一方面是自由的,另一方面又是獨裁的;一方面無所不能,另一方面又無能為力;它可以顛覆一切,同時又什么也沒有顛覆;它擺脫了意識形態的束縛,不再是任何意識形態的附庸,同時又更加自覺地依附于意識形態,特別強調文學對政治的參與性和對日常生活的滲透性。德里達從“延異”的角度對文學的“解構”,一方面使文學在泛文化化的同時具有了無所不能的反叛性和顛覆性,另一方面也使文學在虛無的反叛之中變得少氣無力,這深刻地反映出現代人所面臨的困境,一切都已經變成了虛無的反叛和反叛的虛無。
德里達延異說的高明之處在于,恰恰在于它不停地在旁觀者與當局者之間往返運動,使文化適應于資本運轉的邏輯,并感受其深不可測的奧秘:不停的變化,無限的延異。實際上,各種后現代理論的“反叛”與“顛覆”只是一種說辭,“變化”才是其本質,所以“解構”一詞或許更為接近各種“后”理論的要義和精神:不破不立,具體該“立”什么,誰也無法說清,這正好應合在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名言:“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因為現代性的種種建設性的實踐都以失敗告終,以至于后現代走向了只破不立,追求“變化”,但又無法把握“變化”,這是解構的時代,而不是建構的時代,這是一種文化精神,它可以指向正確,也可以指向錯誤,現代性和后現代性既是一種誘惑,又是一種陷阱,在可為與不可為之間、在能夠接近和不能接近的所有事物之中,解放性與破壞性,差之毫厘,則謬之千里,這其中有著微妙的平衡,而一旦這種平衡被打破,我們一不小心便會落入自設的陷阱之中。在這方面,文化大革命已經給予我們以深刻的教訓。
因此,在我們熱衷于西方理論的同時,如何使我國的外國文學研究既能盡快地與國際接軌,同時又能腳踏實地地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事業做出應有的貢獻,就不單單是一個學術問題了,實際上,西方各種“后”理論早已打破了學術與現實之間的割裂。現實既是我們生活的世界,同時也是我們改變和創造的世界,假如認識不到學術研究也是某種現實的實踐活動,那么這樣的學術研究無論如何純正,也都會使自我逐步異化,被某種外在的、異己的力量所控制,從而失去我們的自我和自我意識。
六、余話
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隨著西方各種“后”理論的引進,我們將西方社會幾百年來的人文思想經歷濃縮在二三十年的感受之中,迅速地與西方保持著“同步發展”,但實際上這其中有很大的差異。西方各種理論的出現有其深刻的社會和文化根源,是西方知識界為了解釋自身所面臨的各種文化困境的產物,他們深究理性、啟蒙與資本生成之間的關系以及由此帶來的后果,深刻感受到現代知識體系中理性的專制和人本的異化,在經歷了“荒誕”和“荒原”意識之后,開始深入剖析主宰自我和世界的話語權力,并由此深化到語言、文本、話語、身份等等問題。而在現代化進程中,我們尚處于發展階段,所謂的理性的專制和人本的異化以及話語權問題等等,對我們來說,多是引進的問題意識,是模仿人家的產物,因此,一定程度上說是某種虛假的存在。后現代問題與中國現實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我們尚無法“荒誕”、也無法“終結”文學,我們當下所提出的“和諧社會”的構想和讓人“體面”地工作等等,實際上都不是“后現代”問題,而是西方人文主義的繼續。我國的外國文學研究是在思想解放的背景下進行的,思想的解放伴隨著人性的解放,但人性的解放也伴隨著“荒誕”意識使人們的思想在打破禁錮之后無所適從。
外國文學研究看似處于學術前沿,對文學研究發揮著引領時代風潮的“先鋒”作用,但因為是外來的,反而更容易跌入錯位感和斷裂感之中而無以自拔,我們生活的世界和我們研究的對象之間似乎有一堵無形的圍墻。筆者這樣說,并不意味著以中國理論或中國文化來主導西方理論和西方文學的研究,也無意強調在外國文學研究中加強本土觀念或比較視野,因為理論或文化的傳播并沒有什么固定的模式,尤其無法人為地加以干涉或引導,而是在自我與外在世界的激烈競爭或交鋒中自然生成的。西方“理論”滲透于我國的外國文學研究領域,無論是我們對之持移植、吸納、嫁接還是改造、更新、創新的態度,實際上都無關緊要,重要的是要有問題意識,要有自我意識,如此,即使是“不求甚解”,也能夠在自我和問題的變異中化解一切。要使我們的研究與國際接軌,并不是趕上或超過、也不是同步發展或同一軌道運行的問題,而是在不斷變化的世界里不斷地變化著自我,只有將我們的經驗借助于外部的刺激而加以融會貫通、并完全轉化成于自我和現實之中,我們的研究才會擺脫基于外部反思的“先驗構造”或是西方理論的改頭換面。隨著我國在政治、經濟上的發展變化,文化、文學自然也會發展變化,我國的外國文學研究隨之也會發展變化。
奈保爾的文學創作曾在對西方文學的“追求”中為自我建造了一道越不過去的高墻,但在回歸“自我”的創作實踐中,這道“高墻”又不推自倒。在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后,陶淵明等中國文人對佛教常常是不求甚解,甚至是囫圇吞棗,即使是王維這樣對佛教極感興趣的作家,也很難說對佛教的義理有什么全面的把握,但這一切都不妨礙他們的詩歌創作富于佛教的意境和禪的韻味,古人所謂的“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正是對這種意境的精妙總結,假如他們究竟于佛教義理和典籍,可能會作繭自縛。同樣,莫言對馬爾克斯和福克納可能并沒有多少研究,但他的創作卻使西方學界從中看出了“百年孤獨”般的魔幻色彩來。只有在莫言所謂的廣義的民間世界或奈保爾“完全轉化了的經驗”中,我們才能找到自我和自我的世界。
[1] 哈貝馬斯.現代性的哲學話語[M].曹衛東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7.
[2] Raymound Williams.The Country and the City.the Hogarth Press,1985.
[3] 馬克思.共產黨宣言[A].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4]Rumina Sethi.Myths of the N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5] 嚴家炎.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
[6]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A].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7] 麥金太爾(A.MacIntyre).德性之后(After Virtue)[M].龔群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8] 馬歇爾·伯曼.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現代性體驗[M].徐大建,張緝編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9]莫言.我怎樣成了小說家[N].北京青年報,2012-10-14.
[10] V.S.Naipaul.Reading&Writing,.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000.
[11] 周啟乾.日本近現代經濟簡史[M].北京:昆侖出版社,2006.
[12] 李春放.在歷史迷霧中探索:馬克思的世界歷史觀[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2-08-15.
[13] 戴登云.“文學是一種奇特的建制”——德里達的文學觀及其啟示[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2-09-21(文學版).
責任編輯:馮濟平
Modernity and Oriental Culture
SHI Hai-jun
( Editorial Board of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Beijing 100732, China )
Western modernity has complicated connections with the Oriental culture,which are embodied in aspects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colonialism,capitalism,cultural loss,transition of modern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deconstruction"and cultural revolution.Facing west"theories",we should have an awareness of problems and our selves,and change along with the constantly changing world.By integrating our experience with outward stimuli,we try to achieve self-perfection and abetter reality.
modernity;rural area;urban area;nostalgia;deconstruction;third class;cultural revolution
G0
A
1005-7110(2013)05-0006-07
2013-06-26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東方文化史”(批準號: 11&ZD082)階段性成果。
石海軍(1962-),男,河南濟源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評論》編審,主要研究印度文學與東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