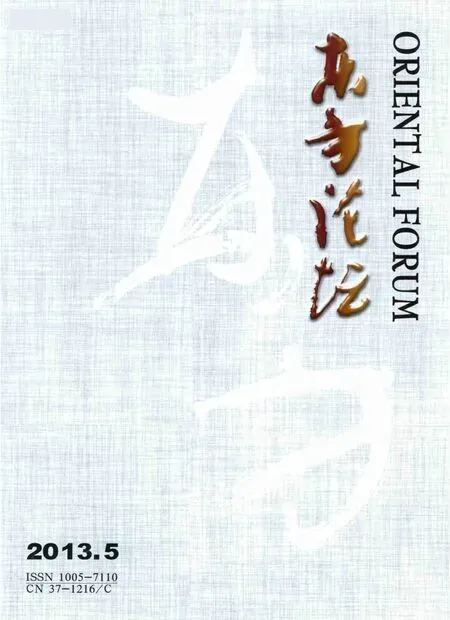稻米之路: 中國(guó)與東南亞稻作業(yè)的起源和發(fā)展
賀圣達(dá)
(云南省社會(huì)科學(xué)院,云南 昆明 650034)
稻米之路: 中國(guó)與東南亞稻作業(yè)的起源和發(fā)展
賀圣達(dá)
(云南省社會(huì)科學(xué)院,云南 昆明 650034)
稻作業(yè)在中國(guó)與東南亞歷史和文化發(fā)展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稻米之路是中國(guó)與東南亞之間最早形成的文化交往之路。由于一些學(xué)者對(duì)1960年代-1970年代東南亞主要是泰國(guó)北部考古新發(fā)現(xiàn)的解讀,產(chǎn)生了栽培稻起源和發(fā)展于東南亞并且從東南亞傳播到中國(guó)的觀點(diǎn),在國(guó)際學(xué)術(shù)界產(chǎn)生了廣泛的影響。但是,對(duì)中國(guó)和東南亞大量農(nóng)業(yè)考古資料的科學(xué)研究充分證實(shí),栽培稻和以栽培稻為基礎(chǔ)的稻作業(yè)在從大約公元前1萬年到公元前6000年在中國(guó)長(zhǎng)江中下游地區(qū)產(chǎn)生并且逐漸得到發(fā)展,此后通過從中國(guó)東南沿海到東南亞的海路、江西湖南經(jīng)廣東廣西進(jìn)入中南半島以及從中國(guó)云南南下這幾條道路逐漸傳入東南亞。公元前4000-3000年間, 中國(guó)到東南亞的稻米之路基本形成。
稻米之路;中國(guó);東南亞
由于中國(guó)與東南亞所處的地理環(huán)境具有適宜于原始農(nóng)業(yè)發(fā)展的特點(diǎn),農(nóng)業(yè)尤其是稻作業(yè)在中國(guó)與東南亞歷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中國(guó)南方與東南亞新石器時(shí)期文化發(fā)展和農(nóng)業(yè)革命的最重要的內(nèi)容,就是稻作業(yè)的發(fā)展。東南亞早期的文明社會(huì)是在稻作業(yè)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起來的。稻作業(yè)對(duì)早期東南亞文明和歷史發(fā)展尤其是古代歷史發(fā)展產(chǎn)生了重大的影響。從史前時(shí)期的后期到19世紀(jì)中葉,東南亞較為發(fā)達(dá)地區(qū)社會(huì)的經(jīng)濟(jì)基礎(chǔ)一直是農(nóng)業(yè),主要是稻作業(yè)。因此,東南亞的稻作業(yè)起源早就引起了包括植物學(xué)家在內(nèi)的學(xué)者注意,而中國(guó)南方也被認(rèn)為是稻作業(yè)的故鄉(xiāng),稻作業(yè)在中國(guó)南方古代農(nóng)業(yè)、古代社會(huì)的發(fā)展中同樣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由于東南亞在地理上、歷史上、民族關(guān)系上與中國(guó)的密切關(guān)系和相互影響,探討稻作業(yè)的起源和發(fā)展,就需要對(duì)東南亞和中國(guó)的稻作業(yè)的起源和發(fā)展聯(lián)系起來,作一個(gè)全面的考察。只有這樣,才能找到稻米之路——稻作業(yè)的起源和發(fā)展之路。
一、東南亞稻作栽培起源問題的探討:從植物學(xué)到考古學(xué)
自20世紀(jì)50年代以來,東南亞農(nóng)業(yè)尤其是稻作業(yè)的起源,一直是學(xué)術(shù)界關(guān)注的問題之一,并且由于對(duì)1960—1970年代泰國(guó)北部考古發(fā)現(xiàn)的不同解說而引起了廣泛的爭(zhēng)議,當(dāng)時(shí)一些考古學(xué)家提出了稻作栽培起源于東南亞尤其是泰國(guó)北部的論斷,此后一些東南亞史、東亞史著作都采納了這一觀點(diǎn)。由于新石器時(shí)代中國(guó)南方與東南亞在地理環(huán)境上的相似性以及族群關(guān)系和文化上的密切聯(lián)系,探討農(nóng)業(yè)尤其是稻作業(yè)的起源,如果不聯(lián)系并充分考慮1960年代以來中國(guó)農(nóng)業(yè)考古取得的大量可信的資料和研究成果,僅就東南亞而言,顯然難以對(duì)這一問題作出合乎歷史實(shí)際的回答。因此,必須把東南亞農(nóng)業(yè)尤其是稻作業(yè)的起源,放在中國(guó)—東南亞早期族群和文化聯(lián)系這樣一個(gè)大的框架中來探討。
正如學(xué)者們所指出,對(duì)于東南亞地區(qū)在人類栽培作物歷史上的重要性,最初是由植物學(xué)家提出的。1951年,蘇聯(lián)植物學(xué)家瓦維洛夫(N.I.Vavilov)將東南亞列入亞洲作物起源的一個(gè)中心,與中國(guó)、印度等并列。但他強(qiáng)調(diào),“在其品種的豐富多樣方面,在其所栽培植物的種類和范圍內(nèi),中國(guó)在種植類型起源的其余中心里是引人注目的”。1952年,美國(guó)地理生物學(xué)家索爾(C.Sauer)在《農(nóng)業(yè)的起源和傳播》一書中則提出了全世界的農(nóng)業(yè)都起源于東南亞,但他所說的東南亞也包括了中國(guó)的華南地區(qū)。1963年,英國(guó)植物學(xué)家達(dá)林頓(C.D.Darlington)對(duì)瓦維洛夫的分類作了修正,將東南亞正式定為全世界九個(gè)栽培作物中心之一。1966年,香港中文大學(xué)生物學(xué)家李惠林將東亞栽培植物的地理分區(qū)分成四個(gè)地帶,自北而南為:北華帶、南華帶、南亞帶(包括自緬甸、泰國(guó)以至中南半島)、南島帶,他認(rèn)為稻等谷物以及芋、海芋、薯蕷、地瓜、荸薺等塊莖作物,均起源于南亞帶。[1](P27-36)
以上這些說法還是基于東南亞的自然地理環(huán)境從植物學(xué)的角度提出的推測(cè),雖然提出了東南亞在栽培作物起源中所處的地位,基本上還屬于一種基于生物學(xué)理論的推測(cè)或假設(shè),并沒有考古學(xué)上的證明。因此,除了在生物學(xué)界,并沒有在學(xué)術(shù)界和社會(huì)上產(chǎn)生多大的影響。
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一些考古學(xué)家對(duì)泰國(guó)北部農(nóng)業(yè)考古的解讀,他們對(duì)東南亞史前農(nóng)業(yè)包括稻作業(yè)起源和發(fā)展及其在亞洲甚至世界農(nóng)業(yè)發(fā)展史上地位提出的新的看法,令舉世矚目。1966年,美國(guó)考古學(xué)家切斯特·戈?duì)柭鼌⒓恿嗽谔﹪?guó)西北部夜豐頌府(Mae Hongson Province)孔河(Khong Stream)西岸的神靈洞(Spirit Cave)的考古發(fā)掘。1973年至1974年,根據(jù)對(duì)出土的一些植物種子的分析,他認(rèn)為神靈洞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原始農(nóng)業(yè),其時(shí)代約在9000年以前。他還認(rèn)為,盡管在神靈洞并沒有發(fā)現(xiàn)稻谷,但某些石器工具卻是與稻谷栽培相聯(lián)系,其時(shí)代在公元前7000年以前。1977年,戈?duì)柭M(jìn)一步提出了有關(guān)東南亞農(nóng)業(yè)發(fā)展三階段的設(shè)想。他認(rèn)為:第一階段開始于14000年前,此時(shí)人們居住在山區(qū),使用的工具是礫石石片石器和竹木器,但已開始了有意識(shí)的照料和栽培野生植物。第二階段始于11000年以前,是一個(gè)由狩獵采集經(jīng)濟(jì)轉(zhuǎn)向農(nóng)耕的階段。大約在距今8000年至7000年以前,出現(xiàn)了定居的村落,開始了稻作栽培。泰國(guó)東北部的儂諾他(Non Nook Tha)和班清(Ban Chiang)均在距今7000—6500年左右,屬于這一范疇。從距今4000年開始到距今2500年前,進(jìn)入了第三階段,人們進(jìn)入沖積平原定居,采用稻作農(nóng)業(yè)和家畜家禽飼養(yǎng)。
戈?duì)柭退鳡柡D返倪@些觀點(diǎn)在美國(guó)等國(guó)的學(xué)術(shù)刊物上發(fā)表后,經(jīng)過媒體的渲染,在1970—1980年代得到廣泛的傳播,迄今一些很有影響的學(xué)術(shù)著作仍采用了他們的看法。例如,美國(guó)學(xué)者墨菲在他2004年出版的那本頗有影響的《亞洲史》中就寫道:“考古證據(jù)表明,穩(wěn)定農(nóng)業(yè)的最早發(fā)源地有兩個(gè),美索不達(dá)米亞……的西南高地,和東南亞大陸沿海部分乃至近海區(qū)。”“雞、豬、水稻和水牛,從它們的東南亞大陸區(qū)發(fā)源地向北進(jìn)入新石器時(shí)代的中國(guó)南部。這一切,直到相當(dāng)晚的時(shí)期,都發(fā)生在一個(gè)單一文化區(qū)的內(nèi)部。總之,缺少來自南方的這些基本要素中的任何一個(gè),中國(guó)的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是難以想象的。”[2](P4,9)其實(shí),即使戈?duì)柭退鳡柡D匪f的“考古材料”可以證實(shí),墨非也作了錯(cuò)誤的解讀,因?yàn)樗麄兯f的泰國(guó)北部較早的農(nóng)業(yè)遺址如“神靈洞”“能諾他”和“班青”等遺址,都不在東南亞沿海而在內(nèi)陸。盡管1980年代以來這些看法都遭到了責(zé)疑甚至否定,但是,在2008年出版的插圖修訂第6版《亞洲史》中,墨菲忽然把他所肯定東南亞農(nóng)業(yè)起源地的“大陸沿海乃至近海”搬到了東南亞內(nèi)陸(也可見墨菲在下結(jié)論時(shí)實(shí)在太輕率了!)。他在2008年版的《亞洲史》中仍寫道,“雞、豬、水稻和水牛,起源于東南亞大陸部分,這一切,直到相當(dāng)晚的時(shí)期,都發(fā)生在一個(gè)單一文化區(qū)內(nèi)部。總之,缺少來自南方的這些基本要素中的任何一個(gè),中國(guó)的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是難以想象的。”[2](P18)中國(guó)學(xué)者汪寧生也引用別的學(xué)者的論述說“新的發(fā)現(xiàn)表明,至少在公元前7000年,泰國(guó)已有明顯的稻谷種植,”[3]這當(dāng)然同樣是缺乏根據(jù)的說法。
正如彼得·貝爾伍德在《劍橋東南亞史》中所指出的:“有人提出泰國(guó)農(nóng)業(yè)和青銅器制造業(yè)開始的時(shí)間相當(dāng)早,可能比世界上其它任何地方都要早的看法,卻造成整體理解上的混亂。近期的研究已經(jīng)將這些發(fā)現(xiàn)放在它們應(yīng)該在的位置,雖然偶爾還可以聽到不同的聲音,但現(xiàn)在已經(jīng)很清楚,早期的一些研究過度夸大了事實(shí)。其中一種看法就是認(rèn)為在泰國(guó)西北神靈洞早在公元前7000年的和平文化地層中找到的植物遺存”。
神靈洞遺址位于泰國(guó)西北部與緬甸邊境城市夜豐頌北郊接壤的海拔600至700米山上的石灰洞遺址。根據(jù)學(xué)者的分析,它由四個(gè)堆積層組成,根據(jù)C14年代測(cè)定,最下部的第四層大約在一萬年前(11,690±560BP)。第二層是距今約八千年(8,142±390BP)的堆積層。第一層距今約7500年(7,622±300BP)。那里出土的文物除石器外,還出土了局部磨制的石斧和石刀及飾有繩紋的陶器,表明這個(gè)地區(qū)曾出現(xiàn)過不同的文化。日本學(xué)者佐佐木高明認(rèn)為,由于仙人洞(神靈洞)發(fā)掘出來的植物殘片很零碎,還缺乏斷定為“栽培種”的證據(jù),特別是關(guān)于植物殘片的識(shí)別和確定尚有很多疑點(diǎn)。[4](P49-51)1977年,美國(guó)夏威夷畢曉普博物館(Bishop Museum)的植物學(xué)家延(D.E.Yen)公布了對(duì)仙人洞植物種籽的研究結(jié)果。他的結(jié)論是:“關(guān)于更早期的和平文化以及其具有超過10000年以前的園圃農(nóng)業(yè)的可能性,現(xiàn)有的證明是非常不足的。我們只能設(shè)想當(dāng)時(shí)的洞穴居民對(duì)于其周圍的環(huán)境已有廣泛的利用。但是卻難以證明這些種籽是出于有目的的種植,從而成為本地以后栽種稻谷的序幕。”進(jìn)一步的實(shí)地考察和相關(guān)的研究證實(shí),實(shí)際上神靈洞或許是在東南亞尋找水稻栽培起源的最不適合的一個(gè)地點(diǎn)。它位于適合于狩獵的地區(qū),而且高居于一個(gè)陡峭的斜坡上,距離最近的流動(dòng)水源都很遠(yuǎn)。這種地勢(shì)非常適合于狩獵者和采集者的生活需求。所以,直到進(jìn)入歷史時(shí)期,都有由狩獵者和采集者結(jié)成的許多小群組在這個(gè)地區(qū)內(nèi)游獵活動(dòng),而且直至20世紀(jì)70年代當(dāng)?shù)厣杏猩贁?shù)人仍然過著這樣的生活。這些學(xué)者的研究結(jié)果表明,以神靈洞為代表的早期和平文化動(dòng)植物遺存代表了一種廣泛的狩獵采集經(jīng)濟(jì),并無栽培農(nóng)業(yè)跡象,更不可能有水稻栽培。這一點(diǎn)已為絕大多數(shù)的學(xué)者所接受。[5](P133-135)
1960—1970年代在發(fā)掘泰國(guó)東北部?jī)z諾他(Non Nok Tha)和班清(Ban Chiang)遺址以后,一些學(xué)者又將注意力轉(zhuǎn)向了泰國(guó)東北部。根據(jù)對(duì)這些發(fā)現(xiàn)的研究,戈?duì)柭⑺鳡柡D返热苏J(rèn)為,從儂諾他遺址的最下層中出土的稻谷看,東南亞應(yīng)該是古代栽培稻的中心。
儂諾他遺址位于泰國(guó)東北部南蓬河流域的低丘陵地帶。美國(guó)和泰國(guó)的考古人員在1966年、1968年發(fā)掘出土了第一到第十一文化層。據(jù)參加考古發(fā)掘的貝阿德的報(bào)告,考古人員從最古老的第一文化層的坑里出土了土器。這種土器的胎土中含有少量的炭化稻殼。日本植物遺傳學(xué)的權(quán)威木原均博士檢驗(yàn)了這種標(biāo)本,確定為稻子,但是還不清楚這一文化層的年代。對(duì)于該遺址出土的水稻種子問題,也有不同的版本。貝阿德起草的該遺址《發(fā)掘報(bào)告書》中說“土器的胎土中含有炭化稻谷”,而索爾海姆教授認(rèn)為那是“稻谷的壓痕”。據(jù)索爾海姆教授說,他把在儂諾他發(fā)掘的稻糠“寄給日本著名的植物遺傳學(xué)家木原均博士,同樣鑒定為人工種植稻”。可是,根據(jù)大冢發(fā)表于木原生物研究所主辦的《Seiken Ziko》(1972年第67、68期)雜志上的報(bào)告,大冢對(duì)儂諾他出土的稻糠的外殼結(jié)構(gòu)作了詳細(xì)研究,認(rèn)為根據(jù)所得到的標(biāo)本判定雖是稻穎,但不能區(qū)別那是種植種還是野生種或雜草。日本京都大學(xué)的渡部忠世教授鑒定了一部分具有谷粒壓痕的土陶片,鑒定結(jié)果是“在幾個(gè)土陶片里明顯有一個(gè)米粒(粗米,不是壓痕)和一個(gè)不清楚的壓痕。”日本學(xué)者佐佐木高明因而認(rèn)為“上述報(bào)告者對(duì)水稻作出不同的鑒定結(jié)果,使我們不知所措。”
班清遺址距儂諾他遺址東北方向約三十公里左右,因出土青銅器和彩陶而聞名。在比出土青銅器和彩陶層更古老的一層地層中,考古人員發(fā)現(xiàn)了石器時(shí)代的稻糠。可是,關(guān)于發(fā)掘的報(bào)告,記載不夠正確,也難以確定其年代,所以詳情不知。據(jù)說青銅器時(shí)代的初期地層和儂諾他的第三文化層的時(shí)間是平行的。所以,如果確定鑒定出了栽培稻,那么不妨可以把兩個(gè)遺址的稻谷看成是時(shí)代大致相同的東西。因此,日木學(xué)者大冢認(rèn)為,還難以對(duì)東南亞北部的稻作起源問題作出結(jié)論。
二、從亞洲視角的考察:稻作業(yè)起源于中國(guó)
除了東南亞,印度和中國(guó)也被一些學(xué)者認(rèn)為是栽培水稻的起源地。因此,顯然不能僅就東南亞,而要從亞洲這一更廣的地理范圍內(nèi)考察栽培稻的起源。
對(duì)于從亞洲的視角考察水稻栽培的出現(xiàn),彼得·貝爾伍德在綜合分析了已有的考古發(fā)掘的研究后提出,盡管印度北部烏塔·普拉答什(Uttar Pradesh)地區(qū)的康爾迪華(Koldihwa)遺址中發(fā)現(xiàn)有稻殼的繩紋陶器,其年代在以前曾被認(rèn)為早到公元前4500年以前(Sharma et al.1890:198),但遺址的碳測(cè)年代并非來自稻谷遺存;而鄰近的馬哈嘎拉(Mahagara)和昆罕(Kunjhun)遺址出土的類似陶器,其年代只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1000年之間。因而就水稻的栽培來說,康爾迪華遺址的年代尚有待證實(shí),也理所當(dāng)然地受到責(zé)疑。
也有學(xué)者主要是日本學(xué)者認(rèn)為(并得到一些中國(guó)學(xué)者肯定和支持),亞洲稻作業(yè)起源于從印度東北部的阿薩姆經(jīng)緬甸、泰國(guó)北部到云南的弧形地帶的“阿薩姆—云南說”[6](P20-22),認(rèn)為起源于阿薩姆,是因?yàn)椤皳?jù)說在印度的十四個(gè)邦中,稻的原始品種數(shù)量合計(jì)為二萬個(gè),而阿薩地區(qū)就占了相當(dāng)?shù)臄?shù)量”,“在阿薩姆復(fù)雜的生態(tài)條件下分布著所有種類的稻種”。但是,“有的人類文化學(xué)者認(rèn)為,阿薩姆的稻作栽培年代并沒有那么古老”,也沒有考古資料可以支持阿薩姆起源說。日本和中國(guó)的一些學(xué)者則認(rèn)為水稻起源于云南的可能性最大,因?yàn)樵颇系闹参锓N類多達(dá)1500余種,約占全國(guó)的一半,素有“植物王國(guó)”之稱;云南稻現(xiàn)有3000個(gè)水稻品種,稻谷種植的垂直分布從海拔100米直到2600米。由于地理、環(huán)境、氣候的特點(diǎn),使云南成為變異中心,因此,云南現(xiàn)代栽培的水稻的祖先很可能就是云南的普通野生稻。東南亞的大河流,都以云南的山地為中心,呈放射狀流向四方。這些大河流的河谷以及夾于河谷之間的隘道,自古以來就是民族遷徙的通道。因此,云南作為稻米的起源地在亞洲稻米往東傳播的過程中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①李昆聲:《亞洲稻作文化的起源》, 《云南文物》, 1984年第15期; 《云南在亞洲栽培稻起源研究中的地位》, 《云南社會(huì)科學(xué)》, 1987年第1期;汪寧生: 《遠(yuǎn)古時(shí)期的云南稻谷栽培》, 《思想戰(zhàn)線》1997年, 第1期。但是,從考古材料看,包括云南在內(nèi)的這一弧形地帶出土的稻谷遺存最早的,是考古工作者2008年在云南大理州劍川海門口遺址發(fā)現(xiàn)的碳化稻,年代為距今約5300—3900年[7](P19-22)。從考古學(xué)的資料和研究看,稻作業(yè)起源于云南這一觀點(diǎn)難以得到證實(shí)。②主張這一觀點(diǎn)的主要是日本學(xué)者渡部忠世, 參閱伊紹亭譯,渡部忠世著: 《稻米之路》,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
彼得·貝爾伍德綜合查爾斯·海厄姆等東南亞史前史研究專家的研究成果,認(rèn)為泰國(guó)北部和越南北部有關(guān)水稻遺存的年代,都不早于公元前3600年。至于東南亞諸島嶼,公元前3000年之后水稻栽培技術(shù)經(jīng)臺(tái)灣和菲律賓向南擴(kuò)展到那里,這可從考古學(xué)和比較南島語言學(xué)兩方面的發(fā)現(xiàn)得到證實(shí)。但是,考古學(xué)還沒有為水稻何時(shí)到達(dá)真正的赤道地區(qū)的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提供明確的依據(jù),但該過程不會(huì)早于公元前2300年。[8]貝爾伍德認(rèn)為,在東南亞(可能除了越南北部沿海地區(qū))的大部分地區(qū),并沒有證據(jù)表明出現(xiàn)過任何原始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當(dāng)?shù)卦嫁r(nóng)業(yè)似乎大多是那些已經(jīng)熟悉了稻谷、粟類和其它亞熱帶作物如番薯、芋根和甘蔗的人引進(jìn)的。現(xiàn)有的證據(jù)表明,進(jìn)入東南亞地區(qū)的農(nóng)業(yè)擴(kuò)張主要開始于中國(guó)南部沿海地區(qū)。而在這種農(nóng)耕體系南向擴(kuò)展的過程中,介入了許多東南亞本土的熱帶水果和塊莖,仍是相當(dāng)重要的。東南亞當(dāng)?shù)氐乃褜な澄锶后w可能在農(nóng)業(yè)植物種類方面提供了十分有用的知識(shí)。[9](P72-73)
貝爾伍德的這一看法符合已有的對(duì)東南亞和中國(guó)農(nóng)業(yè)考古所提供的依據(jù)和所作的研究。1990年代擔(dān)任美國(guó)安多夫考古基金會(huì)主任的著名農(nóng)業(yè)考古學(xué)家R·S·麥克尼什(馬尼士)也認(rèn)為,“東南亞,誠(chéng)然就象非洲一樣,是一批馴化作物的發(fā)源地,如香蕉、甘蔗、芝麻、葡萄、柚、橘子、檸檬等,但我們已有的考古資料只能說明它是一個(gè)非中心區(qū)。這一地區(qū)實(shí)際上就是中國(guó)為核心的遠(yuǎn)東中心區(qū)的外圍”。[10]
稻作業(yè)正是起源于東亞大陸農(nóng)業(yè)中心的中國(guó),并從南部中國(guó)傳播到東南亞的。近幾十年來,中國(guó)的農(nóng)業(yè)考古已有相當(dāng)充分和具有說服力的發(fā)現(xiàn)和相關(guān)的研究證明,中國(guó)大陸在距今1萬年左右開始栽培谷物,出現(xiàn)原始農(nóng)業(yè)。經(jīng)過兩三千年的發(fā)展,到距今七八千年的時(shí)候,中國(guó)大陸的原始農(nóng)業(yè)已經(jīng)較為發(fā)展,并明顯分化出兩大農(nóng)業(yè)系統(tǒng),即南方的稻作農(nóng)業(yè)和北方的粟作農(nóng)業(yè)。與東南亞原始農(nóng)業(yè)起源關(guān)系最為密切的,是中國(guó)長(zhǎng)江中下游的水稻栽培的形成和稻作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著名的東南亞史學(xué)考古學(xué)者、新西蘭奧塔蘭大學(xué)教授查爾斯·海厄姆在2002年出版的《大陸東南亞的早期文化》中也認(rèn)為,廣泛、深入的研究表明,稻谷的馴化經(jīng)歷了一個(gè)長(zhǎng)期的有內(nèi)在的過程,這一過程發(fā)生在公元前10千紀(jì)—公元前8千紀(jì)的長(zhǎng)江中下游地區(qū),東南亞的稻谷栽培技術(shù)從中國(guó)傳入。[11](P351-352)
三、水稻之路的起點(diǎn):中國(guó)長(zhǎng)江中下游地區(qū)
從生物學(xué)、古生物學(xué)的理論上分析,由于中國(guó)南方在自然地理環(huán)境方面與東南亞相似,如果說東南亞有可能是稻作業(yè)的發(fā)源地,那么,中國(guó)南方顯然同樣也有這種可能。因此,破解稻作栽培起源之謎,就不能僅僅從生物學(xué)、古生物學(xué)的理論上分析,還需要考古學(xué)等方面的依據(jù)。
考古學(xué)上的大量資料證實(shí)。距今七八千年前后,中國(guó)長(zhǎng)江中下游地區(qū)已普遍種植水稻。近幾十年來,考古發(fā)現(xiàn)的新石器時(shí)期中國(guó)南方種植水稻的遺址更是層出不窮,其年代遠(yuǎn)遠(yuǎn)在東南亞、南亞之前。20世紀(jì)70年代,考古學(xué)家在距今約7000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發(fā)現(xiàn)了大量的水稻遺存,在當(dāng)時(shí)這已是世界上已發(fā)現(xiàn)的最早的栽培水稻遺存。20世紀(jì)80年代后期,考古學(xué)家在湖南澧縣彭頭山遺址發(fā)現(xiàn)了更早的距今約8000年的栽培稻遺存,把水稻的起源提前了1000年。20世紀(jì)90年代,考古學(xué)家又在江西萬年大源鄉(xiāng)仙人洞和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發(fā)現(xiàn)了距今1萬年的水稻,并找到了從野生稻馴化成栽培稻的證據(jù)。
河姆渡是中國(guó)考古工作者在1970年代發(fā)現(xiàn)的當(dāng)時(shí)世界上最早的大面積種植水稻的考古遺址,距今約7000年。河姆渡遺址稻作遺存豐富,從河姆渡遺址第1期文化上部地層(即4A層),普遍發(fā)現(xiàn)有稻谷、稻稈、稻葉和木片等有機(jī)質(zhì)堆積,一般厚20—50厘米,最厚處超過100厘米,有人曾以平均厚度100厘米計(jì)算,折成稻谷當(dāng)在120噸以上。稻谷遺存之豐富在已發(fā)掘的遺址中是絕無僅有的,在世界上也居首位。而且,還有足夠依據(jù),可以證實(shí)河姆渡遺址北部平原地帶有水田遺跡。從生產(chǎn)工具看,河姆渡遺址出土相當(dāng)數(shù)量的梯形和長(zhǎng)方形石斧,共出土骨器達(dá)2900件之多,其中有作為翻土工具的骨耜約170件。河姆渡先民除使用骨耜外,還使用木耜、用鹿角叉做成的鶴嘴鋤,一種用動(dòng)物肋骨制作的鋸齒狀器,推測(cè)是件收割農(nóng)具——鐮刀。還發(fā)現(xiàn)木杵一件,是河姆渡先民的谷物加工工具。研究者認(rèn)為,在眾多的礪石當(dāng)中,有石磨盤和石磨棒,是當(dāng)時(shí)的糧食加工工具,反映出河姆渡先民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工具已經(jīng)從簡(jiǎn)單走向多樣,已出現(xiàn)專門化的農(nóng)業(yè)工具。遺存中發(fā)現(xiàn)棚欄圈,可能是家畜圈,表明河姆渡先民馴化動(dòng)物已進(jìn)到圈養(yǎng)階段,這是與定居農(nóng)業(yè)相聯(lián)系的。出土的有稻穗紋和豬紋的陶缽,反映了河姆渡先民的種稻和養(yǎng)豬已成為兩項(xiàng)互相依存的重要生產(chǎn)活動(dòng)。這些考古學(xué)上的依據(jù)表明,河姆渡先民從事的耜耕水田農(nóng)業(yè)已離原始農(nóng)業(yè)初創(chuàng)時(shí)期走了好長(zhǎng)一段路程,已有了比較發(fā)達(dá)的水田稻作農(nóng)業(yè)。[12](P40-42)
迄止1970年代,河姆渡遺址可以說是亞洲最早的、數(shù)據(jù)最可靠的栽培稻谷的遺址。聯(lián)系對(duì)河姆渡發(fā)掘和與之相距不遠(yuǎn)、時(shí)代相同的發(fā)現(xiàn)栽培稻的遺址桐鄉(xiāng)縣羅家角遺址的分析,童恩正認(rèn)為“當(dāng)時(shí)杭州灣區(qū)域的栽培稻并不是孤立的現(xiàn)象”。他當(dāng)時(shí)就推測(cè),“從這類遺址稻谷栽培和家畜馴養(yǎng)的規(guī)模及其技術(shù)成熟的程度來看,這并不是中國(guó)南方農(nóng)業(yè)的起點(diǎn)。在此以前,應(yīng)有一個(gè)較長(zhǎng)時(shí)期的發(fā)展階段,這一階段可能不會(huì)短于2000年—3000年”。[5](P132)
此后20年間中國(guó)的農(nóng)業(yè)考古證實(shí)了童恩正教授的這一推測(cè)。從最初馴化水稻到更廣大地域范圍內(nèi)的大規(guī)模的水稻種植,確實(shí)經(jīng)過了二三千年的發(fā)展。農(nóng)業(yè)考古證實(shí),中國(guó)最早的栽培稻演化發(fā)生在長(zhǎng)江中下游地區(qū)。最早的稻屬植硅石遺存的材料來自江西萬年縣大源鄉(xiāng)境內(nèi)的仙人洞和吊桶環(huán)兩處舊石器時(shí)代末期至新石器時(shí)代早中期遺址。仙人洞遺址早在1960年代初期就經(jīng)過兩次較大規(guī)模的發(fā)掘。1993年和1995年秋季,由北京大學(xué)考古學(xué)系、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美國(guó)安德沃考古基金會(huì)(AFAR)組成的聯(lián)合考古隊(duì)再次對(duì)仙人洞遺址進(jìn)行了系統(tǒng)采樣,并在吊桶環(huán)遺址進(jìn)行了小規(guī)模的發(fā)掘。在仙人洞和吊桶環(huán)各層位都采到了木炭,并由中美雙方利用AMS技術(shù)測(cè)定了34個(gè)樣本,所得最晚的一個(gè)數(shù)據(jù)為12430±80BP。在仙人洞和吊桶環(huán)遺址的各個(gè)層位采集的近40個(gè)用于植硅石分析的樣品中,找到了600余個(gè)稻屬植硅石的個(gè)體,鑒別出了一定數(shù)量的野生稻和栽培稻形態(tài)的植硅石。這兩個(gè)層次的年代大約在距今14000年至11000年之間。在仙人洞和吊桶環(huán)遺址舊石器時(shí)代晚期或新石器時(shí)代初期的文化層中,還發(fā)現(xiàn)了12000年前的野生稻植物蛋白石,已具有人工干預(yù)的痕跡,說明當(dāng)時(shí)人們不但已經(jīng)采集野生稻作為食物,而且可能已嘗試人工種植。[13](P55-56)1995年在湖南道縣玉蟾巖發(fā)掘出土的兩枚1萬年前的稻谷,被證明是一種由野生稻向栽培稻演化的古栽培稻類型,其年代參照道縣三角巖C14資料在12060±120BP左右,大體與上述吊桶環(huán)E層和仙人洞3C1a層接近,說明栽培稻在這一時(shí)期長(zhǎng)江中游地區(qū)的出現(xiàn)已非孤例。[14](P43-48)
農(nóng)業(yè)史專家陳文華據(jù)此肯定,栽培稻是從野生稻馴化來的,時(shí)間在1萬多年前。從中國(guó)稻谷遺址的地域分布看,有幾個(gè)特點(diǎn),一是長(zhǎng)江流域明顯可分為下游、中游和上游三個(gè)部分。長(zhǎng)江下游、中游的遺址數(shù)目最多,下游集中在太湖地區(qū),中游集中在湖南、湖北兩省,分布也最密集,因而長(zhǎng)江中、下游近十余年來一直是稻作起源研究的熱點(diǎn),其余地區(qū)被視為擴(kuò)散傳播的結(jié)果。1970年代末最早的遺址是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及桐鄉(xiāng)羅家角遺址,距今7000年;這一記錄被20世紀(jì)80年代發(fā)現(xiàn)的距今8000年的河南舞陽賈湖遺址所打破;進(jìn)入20世紀(jì)90年代后,賈湖的記錄又被距今9000—8000年的湖南澧縣夢(mèng)溪八十垱及澧縣平原彭頭山、安鄉(xiāng)湯家崗等遺址的新發(fā)現(xiàn)所刷新。
同中國(guó)的長(zhǎng)江流域相比,與東南亞比鄰的華南地區(qū)和西南地區(qū)的遺址數(shù)較少,分布也顯得較散。1996年在廣東英德牛欄洞遺址的31個(gè)文化層(年代距今12000—8000年)中發(fā)現(xiàn)7個(gè)樣品有水稻硅酸體,共24粒。研究人員對(duì)遺址的扇形硅酸體進(jìn)行聚類分析,主要結(jié)論認(rèn)為牛欄洞遺址的硅酸體為一種非粳稻的類型,在水稻的演化序列上處于一種原始狀態(tài)。桂北地區(qū)的稻作農(nóng)業(yè)是新石器中期才出現(xiàn)的,重要的證據(jù)是曉錦遺址出土的大量炭化稻谷。曉錦遺址位于廣西北部資源縣曉錦村后龍山上,南距桂林甑皮巖遺址只有百余公里,碳14測(cè)定距今5000—3200年。這里的稻作農(nóng)業(yè)很可能是從鄰近的湖南傳入的,是廣西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最早的史前稻作標(biāo)本。
同樣與東南亞比鄰的長(zhǎng)江上游地區(qū)云南的幾處稻谷栽培遺址在時(shí)間也是比較晚的,距今3000多年前。就迄今已經(jīng)發(fā)掘的材料來看,洱海地區(qū)以賓川白羊村遺址為代表。遺址下層經(jīng)過碳14測(cè)定,年代距今3000多年。元謀大墩子早期碳14測(cè)定年代為距今3000多年。[15](P130-131,178-179)
農(nóng)業(yè)史專家陳文華根據(jù)對(duì)中國(guó)水稻起源和發(fā)展相關(guān)研究總結(jié)道,到了8000年前左右,水稻的種植在長(zhǎng)江流域中游和淮河上游都頗具規(guī)模。“已經(jīng)越過選育、馴化階段,形成了早期稻作農(nóng)業(yè)文化。大約到了7000年前,中國(guó)的稻作農(nóng)業(yè)已進(jìn)入發(fā)展階段。淮河流域下游、長(zhǎng)江中下游都已發(fā)現(xiàn)很多稻作文化遺址,這些遺址的年代距今7300—6800年。說明這一時(shí)期稻作已經(jīng)在長(zhǎng)江中下游地區(qū)得到普及,并且水稻品種也得到了初步的改良,已有稻和粳稻兩個(gè)品種。到了6000年前,中國(guó)的原始稻作開始進(jìn)入發(fā)達(dá)階段,水稻種植的范圍進(jìn)一步擴(kuò)大,稻田的整治已初具規(guī)模。到了5000年前,水稻的種植已經(jīng)遍布長(zhǎng)江流域各地以及華南、閩臺(tái)地區(qū),甚至連黃河流域(如陜西、河南、山東)的一些地區(qū)都已開始種植水稻了。”[13](P55-56)
以考古發(fā)掘出土的實(shí)物資料為依據(jù),結(jié)合生物學(xué)、古生物學(xué)的理論分析,考古學(xué)家認(rèn)為:稻作農(nóng)業(yè)起源于長(zhǎng)江中下游地區(qū)。長(zhǎng)江中下游地區(qū)的稻作農(nóng)業(yè)興起后,不斷地向周邊地區(qū)傳播,向南傳至云南、廣西、廣東;向北傳到河南、陜西、山東等地。[16](P245)
中國(guó)考古學(xué)者的這些研究成果,1980年代以來得到了國(guó)際學(xué)術(shù)界的認(rèn)可、肯定。澳大利亞學(xué)者彼得·貝爾伍德認(rèn)為,“稻谷(稻屬sativa)是首先在中國(guó)培育成功的一年生植物。根據(jù)公認(rèn)的考古證據(jù),稻谷首先是在全新世早期氣候比較溫暖的條件下,在揚(yáng)子江(長(zhǎng)江中下游)低地地區(qū)的某個(gè)地方培育成功。由此證明浙江河姆渡那樣的給人以深刻印象的木構(gòu)村寨的居民,從公元前5000年時(shí)就在當(dāng)?shù)厣睢V袊?guó)中部沿海地區(qū)出土了大量與這些發(fā)展相關(guān)聯(lián)的器物,包括陶器、木工、石斧、木質(zhì)的骨質(zhì)的農(nóng)業(yè)工具,船、槳,用于紡織(棉花?)的紡錘輪、席和繩,伴隨出土的還有動(dòng)物馴化的證據(jù),包括豬、狗、雞,可能還有牛和水牛”。[9](P23)著名的世界史學(xué)者戴維·克里斯蒂也認(rèn)為,大量研究表明,也許在大約9500年到8800年前,那些收獲野生水稻的食物采集的民族就開始在中國(guó)南方長(zhǎng)江一帶栽培水稻了。到距今8000年的時(shí)候,中國(guó)北方以小米為基礎(chǔ)的社會(huì)制度和中國(guó)南方以水稻為基礎(chǔ)的社會(huì)制度都已經(jīng)確立起來了。[17](P120)美國(guó)學(xué)者杰里·本特利等在他們所著的《新全球史》中也明確地肯定,“在東亞長(zhǎng)江流域的居民早在公元前6500年就開始種植稻米。……東亞的人們也許早在公元6000年前,就飼養(yǎng)了豬和雞,后來還把水牛馴養(yǎng)成家畜。”[18](P20)
為什么是中國(guó)的長(zhǎng)江流域,而不是普通野生稻較多的華南或東南亞的某些地區(qū)會(huì)成為稻作農(nóng)業(yè)的起源地呢?中國(guó)考古學(xué)者嚴(yán)文明認(rèn)為,這是因?yàn)殚L(zhǎng)江流域?qū)儆趤啛釒Ъ撅L(fēng)氣候,那里冬季較長(zhǎng),食物比較缺乏,需要某種可以儲(chǔ)存到冬季都可以享用的食物作為補(bǔ)充,稻米正好符合這種需要;長(zhǎng)江流域雖然有普通野生稻,但數(shù)量比中心區(qū)少得多,自然狀態(tài)的產(chǎn)量不可能滿足人們的需要,有必要進(jìn)行人工培植。也只有通過人工培植,稻種才能安全過冬而得以繼續(xù)繁殖。所以,稻作農(nóng)業(yè)的起源首先應(yīng)在野生稻分布北部邊緣的長(zhǎng)江流域。盡管普通野生的分布范圍包括了整個(gè)東南亞及其島嶼,它們的北界在溫帶北緯30o上下、在為期近萬年的歷史長(zhǎng)河中頗多徘徊移動(dòng),但栽培稻的起源為什么偏偏不在這一帶?其重要原因可能就在于“長(zhǎng)年炎熱多雨的熱帶地區(qū),植物終年都能生長(zhǎng),人們隨時(shí)都可以直接從自然界獲取食物,沒有培植谷物的迫切需要,所以谷物農(nóng)業(yè)在那些地方反而發(fā)展得較晚較慢”。[19]生物史和考古學(xué)研究表明,東南亞原始農(nóng)業(yè)是從塊根類芋頭、木薯等開始的。繼芋頭木薯以后種植的是粟、黍、薏苡等,水稻是最后才取代粟類登上主糧地位的。討論水稻起源地既不能沒有野生稻存在這個(gè)大前提,但野生稻又不是唯一的存在前提。“亞洲的包括泰國(guó)在內(nèi)的熱帶季風(fēng)雨林地帶,有著含淀粉的植物糧食和野生的各種果實(shí),魚,貝類,鳥類等豐富的食物。在這樣的自然環(huán)境下,在農(nóng)耕時(shí)代之前,曾經(jīng)歷了非常漫長(zhǎng)的采集、狩獵時(shí)代。”[20](P65-66)東南亞的原始農(nóng)業(yè)首先出現(xiàn)在大陸東南亞北部山區(qū),在相當(dāng)長(zhǎng)的時(shí)期內(nèi)這里的居民仍然要通過狩獵獲得動(dòng)物性食物,而低地的環(huán)境條件并非理想的生活場(chǎng)所。食物來源既然通過林地采集、狩獵和少量種植可以充分滿足,自然沒有必要想到采集野生稻(加工麻煩),栽培水稻[15](P182)。
由此可見,水稻農(nóng)耕的發(fā)生除了需要有適宜的環(huán)境條件之外,還需要有一定的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條件,二者缺一不可。根據(jù)現(xiàn)有材料,在距今10000—7000年前,這些條件也只有中國(guó)長(zhǎng)江中下游的一些地區(qū)才具備,包括野外食物供給季節(jié)的變化無常、環(huán)境變化造成的食物供給數(shù)量減少、甚至是人口數(shù)量的自然增長(zhǎng)等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使得長(zhǎng)江中下游地區(qū)的人類社會(huì)在水稻培植和耕種方面有更大的投入,從而最早利用自然資源發(fā)展了栽培水稻。
四、稻米之路:從中國(guó)長(zhǎng)江中下游經(jīng)華南和西南到東南亞
從對(duì)東南亞史前農(nóng)業(yè)遺存的考古研究看,東南亞的稻作業(yè)最早起源于紅河下游和泰國(guó)北部地區(qū),在時(shí)間上最早在公元前4000多年前,要遠(yuǎn)遠(yuǎn)晚于中國(guó)的長(zhǎng)江中下游地區(qū)。東南亞的稻作業(yè)是從中國(guó)傳入的,這條稻米之路就是從中國(guó)長(zhǎng)江中下游經(jīng)華南和西南到東南亞。1970年代以來的研究表明,越北新石器時(shí)代的物質(zhì)文化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五個(gè)千年以后。如果是那樣,越北地區(qū)可能是東南亞原始農(nóng)業(yè)最早發(fā)展起來的地區(qū)。在越南北方,繼和平文化后出現(xiàn)了北山(Bac-Son)文化,由法國(guó)人曼修于1906年發(fā)現(xiàn)于諒山省的北山,共有45個(gè)遺址。北山文化已明顯屬于新石器早期的文化。較之和平文化,其重要的進(jìn)步是有了手制陶器,出土的石器工具中有磨制的掘土工具,這些都表明當(dāng)時(shí)的居民已從事原始的農(nóng)業(yè),但是,在北山文化遺址還沒有發(fā)現(xiàn)稻谷遺存。晚于北山的新石器文化,有馮原文化(Phung Nguyen)。馮原位于紅河三角洲,在河內(nèi)以北不遠(yuǎn)的地區(qū),由越南考古學(xué)家在1960年代開始發(fā)掘。已發(fā)掘的馮原遺址的面積為3800平方米,文化層堆積達(dá)0.8米,反映出當(dāng)時(shí)居民已長(zhǎng)期定居當(dāng)?shù)亍qT原出土的石器工具有石斧、鋤頭等。一些釜、甕、盆既大且笨,顯然只有定居的居民才制造這樣的器物。在馮原,還發(fā)現(xiàn)了稻谷遺存,和狗、豬、牛、雞等家養(yǎng)動(dòng)物的骸骨。這反映出當(dāng)時(shí)的稻作農(nóng)業(yè)已有一定的發(fā)展。彼得·貝爾伍德認(rèn)為,馮原文化的資料表明,公元前第三個(gè)千年末期或第二個(gè)千年早期,這里已有了稻作及更大范圍的物質(zhì)文化,包括石箭頭和石刀,烘烤過的土紡錘和弓彈丸,以及有鋸齒紋和蓖紋裝飾的陶器。[9](P77)這意味著紅河流域下游在4000多年前已經(jīng)發(fā)展了稻作文化。
較多地提供中南半島北部地區(qū)農(nóng)業(yè)發(fā)展的是泰國(guó)東北部呵叻高原的班清遺址。在呵叻高原西部邊緣的低地山丘地區(qū)。班清遺址的主要發(fā)掘者認(rèn)為,這里在公元前第四個(gè)千年期間已開始有人居住。這個(gè)斷代此后一直受到責(zé)疑,但這些遺址出現(xiàn)于公元前第三個(gè)千年或第二個(gè)千年看來還是可能的。也就是說,在距今4000年前,當(dāng)?shù)氐霓r(nóng)業(yè)社會(huì)已在此建立,這里的居民可能已在河流下游和季節(jié)雨水沖積的土地上種植稻谷。[9](P78)曾參與班清遺址研究工作的考古學(xué)家懷特認(rèn)為,“班清遺址發(fā)掘的最重要的貢獻(xiàn)是考古學(xué)者們找到了今天東南亞到處可見四千年以來以耕作為基礎(chǔ)的低地農(nóng)耕社會(huì)之根。許多泰國(guó)現(xiàn)代社會(huì)生活中十分重要的習(xí)俗——諸如稻作、飼養(yǎng)家蓄、水牛、狗和雞,甚至制陶工藝,在某種形式上在數(shù)千年前的班清文化傳統(tǒng)的遺址中都可以看到。”
雖然儂諾他和班清諸遺址還存在著地層紊亂等問題,但是這兩個(gè)遺址對(duì)于闡明青銅器出現(xiàn)以前時(shí)期東南亞文化的發(fā)展問題具有重要意義。班清仍然是泰國(guó)東北部重要的經(jīng)過發(fā)掘的遺址,最早的居民可能在公元前第四個(gè)千年的后期移入該地區(qū),當(dāng)時(shí)的人口非常稀少。他們帶來了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和新石器的技術(shù)。這些新石器技術(shù)與中國(guó)南部和越南同時(shí)代的石器之間,僅存在一些風(fēng)格和細(xì)節(jié)方面的不同。而在公元前四千紀(jì)之前,中國(guó)南方的新石器技術(shù)和稻作業(yè)已有了相當(dāng)高的發(fā)展水平。因此,泰國(guó)東北部最初的農(nóng)業(yè)居民可能來自越南北部和中國(guó)南部的沿海地區(qū)。[9](P79)
繼班清遺址之后泰國(guó)發(fā)掘的科帕農(nóng)迪和班高遺址,反映出大陸東南亞中部早期農(nóng)業(yè)社會(huì)的更高水平的發(fā)展。科帕農(nóng)迪遺址的直徑達(dá)200米,從公元前2000年到前1400年之間的考古堆積物厚度將近7米,墓坑物品包括成串的貝殼和手鐲、石錛以及做工講究的陶器。在陶器上有稻殼的印痕,稻殼也被摻進(jìn)土中制作陶器,反映出當(dāng)時(shí)的人們已經(jīng)種植稻谷。
從對(duì)現(xiàn)有考古材料的研究看,可以認(rèn)為,如查爾斯·海厄姆所說的,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東南亞大陸一些地區(qū)已經(jīng)種植了水稻。在安南山脈的兩側(cè)所進(jìn)行的考古發(fā)掘證實(shí)了這些發(fā)展。越南的考古工作者在這條山脈東側(cè)的紅河三角洲上游的所謂“中部地區(qū)”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了50多處小型的農(nóng)業(yè)村落遺址。在這條山脈西邊的湄公河中游地區(qū),有泰國(guó)的儂諾他(Non Nok Tha)、班清(Ban Chiang)和斑納迪(Ban Na Di)等遺址的發(fā)掘,揭示了這個(gè)廣大地區(qū)也曾經(jīng)有農(nóng)民開發(fā)耕作和定居過。這批農(nóng)業(yè)先驅(qū)者的村址,都選擇在地勢(shì)稍高的地方,而從泰國(guó)東北部這些村子可以通往地勢(shì)較低的紅河三角洲的內(nèi)河地帶,反之亦然。馮原(Phung Nguyen)遺址就是位于紅河三角洲中部地區(qū)的這類遺址之一。[21]泰國(guó)東北部除了上述三個(gè)主要的遺址以外,還有與馮原文化遺址的分布模式相類似的一些村落遺址,它們也分布在河流小支流的中游地帶。這類村落遺址中,最早的大約始建于公元前2400年前后,村子占地面積大約只有1公頃左右,村民在50到100人左右,其經(jīng)濟(jì)模式也與山脈另一邊的馮原文化遺址十分相似,河谷地帶種植水稻,飼養(yǎng)了牛、豬和狗。
在中南半島其它地區(qū),也發(fā)現(xiàn)了一些新石器時(shí)代的文化遺存。在柬埔寨,東部的三隆盛(Somrongsen)則從19世紀(jì)70年代起就受到考古學(xué)家的注意。法國(guó)學(xué)者A·多凡—默涅認(rèn)為,三隆盛時(shí)代的高棉人已經(jīng)懂得打制斧頭,用石塊制造鑿子,掌握了燒陶技術(shù)。他們懂得了馴養(yǎng)黃牛和水牛,以及養(yǎng)豬和種植水稻。三隆盛文化的年代,為公元前1500年前后。三隆盛文化在時(shí)間上晚于越北馮原文化和泰國(guó)東北部的班清和儂諾他,看來不可能是東南亞最初栽培水稻的地區(qū)。緬甸新石器文化的發(fā)展,以勒班奇波文化和陶馬貢文化為代表。勒班奇波遺址由緬甸考古工作者于1972年發(fā)現(xiàn)于蒲甘附近良吁鎮(zhèn)區(qū)的勒班奇波村,在該地出土的石器達(dá)140多件。陶馬貢新石器遺址位于緬甸中部沙林枝鎮(zhèn)東北5公里處,1982年緬甸考古工作者到該地作了考察,發(fā)現(xiàn)了經(jīng)過磨制石器,其中有石鑿、單刀等,還發(fā)現(xiàn)了陶器碎片和用火的遺跡。此外,還發(fā)現(xiàn)了鹿、牛、馬、豬等動(dòng)物的骨骼化石,但不清楚農(nóng)業(yè)尤其是稻業(yè)是否已有發(fā)展。
海島地區(qū)的水稻種植開始于何時(shí)還有待于深入研究,不能完全排除在7000—4000年前最早一片中國(guó)東南沿海地區(qū)的百越居民南下東南亞海島地區(qū)時(shí)就已經(jīng)把水稻種植帶到當(dāng)?shù)兀牵捎谌狈梢宰C實(shí)史前東南亞海島地區(qū)的水稻種植年代的農(nóng)業(yè)考古資料,這還是一種假設(shè)。現(xiàn)在學(xué)術(shù)界一般認(rèn)為,東南亞海島地區(qū)的水稻種植要晚于東南亞大陸。日本學(xué)者宇野認(rèn)為爪哇在公元前1000年開始種稻,是由中國(guó)南方移居爪哇的族群帶去的。印度尼西亞學(xué)者宇格拉特則認(rèn)為,印度尼西亞在公元前500—200年間種植的還是旱稻。印度尼西亞的水稻種植遠(yuǎn)晚于晚稻,也就是說,在公元前200年后是由中國(guó)南方先民發(fā)明的水利技術(shù)傳入印度尼西亞后,才得以廣泛種植[22](P56)。
因此,從已有的農(nóng)業(yè)考古資料看,泰國(guó)東北部和越南紅河流域是史前東南亞最早開始水稻種植的地區(qū),但是在時(shí)間上要遠(yuǎn)遠(yuǎn)晚于中國(guó)長(zhǎng)江中下游地區(qū)。至少從考古學(xué)的研究看,水稻是從中國(guó)長(zhǎng)江中下游逐漸傳播到東南亞首先是紅河下游和泰國(guó)北部地區(qū)的。
那么,中國(guó)南方的稻作業(yè)與東南亞、南亞稻作業(yè)的發(fā)展是什么樣的一種關(guān)系呢?彼得·貝爾伍德在研究了中國(guó)、印度、泰國(guó)、越南、印度尼西亞等的史前水稻后,認(rèn)為新石器時(shí)代中國(guó)南部沿海地區(qū)稻作文化的大量出現(xiàn),已經(jīng)暗示著他們與浙江省河姆渡遺址之間存在著一定的聯(lián)系,提出了水稻向南傳播的假說。他認(rèn)為水稻起源于中國(guó)長(zhǎng)江中下游地區(qū)后,大約在公元前6000年至前3000年擴(kuò)展到中國(guó)南方和臺(tái)灣以及越南北部,在前2500年之后遠(yuǎn)播至印度北部和泰國(guó)中部,以及赤道以北的東南亞島嶼。很顯然,在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之間,甚至是更早的時(shí)期,整個(gè)中國(guó)南部沿海地區(qū)都居住著使用陶器和耕作稻谷的居民,開始了農(nóng)業(yè)發(fā)展[9](P77)。中國(guó)長(zhǎng)江以南與東南亞新石器時(shí)代后期的自然地理環(huán)境有利于雙方居民之間的直接或間接的交往。因此,栽培稻在中國(guó)長(zhǎng)江中下游地區(qū)起源以后,先傳播到中國(guó)的兩廣(廣東、廣西)、臺(tái)灣島和云南等地區(qū),又通過這些地區(qū)向中南半島和東南亞海島地區(qū)傳播開來。“我們確知水稻栽種的傳播遍及東南亞,可以證明是與中國(guó)南方農(nóng)耕者相聯(lián)系的”。[23](P481)美國(guó)學(xué)者B·M·費(fèi)根在綜合諸多研究成果后得出的這一結(jié)論,完全符合水稻栽種從中國(guó)南方傳播到東南亞的歷史事實(shí)。
從史前東南亞稻作業(yè)發(fā)展看,泰國(guó)東北部和越南紅河流域是史前東南亞最早發(fā)展了稻作業(yè)的兩個(gè)地區(qū)。那么,這兩個(gè)地區(qū)的稻作業(yè)是獨(dú)立地形成和發(fā)展起來的,還是彼此有著交往、聯(lián)系?是哪一方更早一些?首先影響了對(duì)方?從所處的地理位置看,紅河中下游顯然要比地處內(nèi)陸的泰國(guó)東北部更容易受到中國(guó)東南沿海的影響,而現(xiàn)有考古發(fā)現(xiàn)顯示馮原文化的稻作業(yè)的興起要早于泰國(guó)東北部。東南亞大陸地區(qū)最早的農(nóng)業(yè)定居點(diǎn)出現(xiàn)在馮原,而泰國(guó)東北部呵叻高原最早的定居點(diǎn)在大約公元前三千紀(jì)到公元前兩千紀(jì)。彼德·貝爾伍德認(rèn)為,泰國(guó)東北部最初的農(nóng)業(yè)居民來自越南北部和中國(guó)南部的沿海地區(qū)。[9](P77-79)因此,泰國(guó)東北部的稻作栽培可能是從馮原文化時(shí)期的越南北部傳入,而越南馮原文化時(shí)期的稻作業(yè)則是從中國(guó)南方稻作文化地區(qū)傳入的。
也就是說,中國(guó)—東南亞的稻米之路,可能始于中國(guó)長(zhǎng)江中下游—中國(guó)東南沿海或者湖南—兩廣地區(qū)—越南紅河流域進(jìn)入泰國(guó)東北部。經(jīng)海路始于中國(guó)東南沿海到中南半島沿海地區(qū)和東南亞海島地區(qū),陸路則很可能是經(jīng)湖南、江西—兩廣一線首先進(jìn)入中南半島北部。迄今為止的考古發(fā)現(xiàn),距今1.2萬年以前,湘江的主要支流瀟水與流經(jīng)廣西—廣東一線就已有古人類南來北往的。湖南道縣的洞穴遺址和封開縣黃巖洞、羅髻巖有相通的賀江。湖南江華縣、廣西賀州市和富川縣采集到的陶器和陶紋飾,都與廣東封開縣屬于同一的文化類型,這些都證明瀟水一賀江線上的文化交往在新石器時(shí)代已不斷進(jìn)行,進(jìn)入青銅器時(shí)代往更頻繁了。[24]而湖南正是中國(guó)最早的水稻種植發(fā)源地,也可能通過這一古代文化交流通道再南下進(jìn)入紅河流域下游地區(qū)。
由于云南連接著長(zhǎng)江流域,又是流向東南亞的三大河流——紅河、湄公河和伊洛瓦底江的上游(這些河流的河谷地區(qū)也是古代居民遷徙的通道),云南也是中國(guó)農(nóng)業(yè)向南擴(kuò)展運(yùn)動(dòng)的一個(gè)重要地區(qū),稻谷栽培也由可能從云南傳入東南亞大陸北部。但是,從現(xiàn)有的考古數(shù)據(jù)看,云南最早的栽培稻遺存在距今3000多年前①(新西蘭)查爾斯·海厄姆: 《大陸東南亞的早期文化》,曼谷河流出版社,2002年英文版,(Charles· Higham., Early Cultures of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Bangkok: River Books, 2002. ), 第84-85頁。,稻谷栽培從云南傳入東南亞大陸在時(shí)間上要晚于從江西、湖南經(jīng)兩廣進(jìn)入東南亞。至晚到公元前3000年,從中國(guó)南方到東南亞大陸的稻米之路就已經(jīng)基本形成,此后又延伸到東南亞海島地區(qū)。到公元前一千紀(jì),中國(guó)與東南亞之間的稻米之路全面形成。
參考文獻(xiàn):
[1]轉(zhuǎn)引自張光直.考古學(xué)專題六講[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2]羅茲·墨菲.亞洲史[M].黃磷譯,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
[3] E·利普斯.事物的起源[M].汪寧生等譯,甘肅敦煌文藝出版社,2000年增訂版,汪寧生的序言.
[4] 佐佐木高明.照葉樹林文化之路[M].劉愚山譯,昆明:云南大學(xué)出版社,1998.
[5] 轉(zhuǎn)引自童恩正文集·學(xué)術(shù)系列·南方文明[M].重慶出版社,1999.
[6] 渡部世忠.日本稻の源流[A].稻一その源流への道[C].東亞文化交流史研究會(huì),1990年.
[7] 大理州白族學(xué)會(huì)編.中國(guó)劍川海門口遺址[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
[8] 彼得·貝爾伍德.史前亞洲水稻的新年代[J].陳星燦譯,農(nóng)業(yè)考古,1994,(3).
[9] 劍橋東南亞史:第一卷[M].賀圣達(dá)等譯,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10] R.S麥克尼什(馬尼士).農(nóng)業(yè)的三線起源(續(xù))[J].康樂譯.農(nóng)業(yè)考古,1992(3).
[11] 查爾斯·海厄姆.東南亞大陸的早期文化[M].泰國(guó),河流叢書,2002年英文版.
[12] 劉軍,姚仲源.中國(guó)河姆渡文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13]陳文華.中國(guó)古代農(nóng)業(yè)文明史[M].南昌:江西科學(xué)技術(shù)出版社,2005.
[14] 參見張馳.江西萬年早期陶器和稻屬植硅石遺存[A].嚴(yán)文明、安田喜憲主編.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C].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15] 游修齡主編.中國(guó)農(nóng)業(yè)通史·原始社會(huì)卷[M].北京:中國(guó)農(nóng)業(yè)出版社,2008.
[16] 戴維·克里斯蒂安.時(shí)間地圖:大歷史導(dǎo)論[M].上海:上海社會(huì)科學(xué)院出版社,2007.
[17]中國(guó)國(guó)家博物館編.文物史前史[M].北京:中華書局,2009.
[18] 杰里·本特利等著,魏鳳蓮等譯.新全球史[M].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7.
[19]嚴(yán)文明.再論中國(guó)稻作農(nóng)業(yè)的起源[J].農(nóng)業(yè)考古,1989,(2).
[20] 渡部忠世.稻米之路[M].尹紹亭等譯,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
[21] 查爾斯·海厄姆(C.F.W.Higham).東南亞史前的水稻栽培[J].科學(xué)(中文版),1984,(8).
[22] 梁志明等.東南亞文明之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23] B·M·費(fèi)根.地球上的人們:世界史前史導(dǎo)論[M].云南民族學(xué)院民族學(xué)教研室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24] 陳乃良.瀟水和賀江源頭區(qū)先秦古通道[A].封中史話[C].廣州:廣東省地圖出版社,2000年再版.
責(zé)任編輯:侯德彤
The Rice Road: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Rice Cultivation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HE Sheng-da
( Yun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Kunming 650034, China )
Rice growth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The Rice Road is the earliest and oldest cultural exchange road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Because of some scholars'interpretation of th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in Northern Thailand in the1960s and1970s,the view that rice was domesticated and developed originally 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n introduced into China has been widely accepted.But studies on both China's and southeast Asia's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have proved that the rice was domesticated sometime between10000B.C.and6000B.C.in the lower and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Rice cultivation was introduced into Southeast Asia from Southern China's eastern coastal areas,Guangdong,Guangxi and Yunnan.The Rice Road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was established at least between4000-3000B.C.
Rice Road;China;Southeast Asia
K33
A
1005-7110(2013)05-0023-08
2013-06-26
國(guó)家社會(huì)科學(xué)基金重大項(xiàng)目“東方文化史”(批準(zhǔn)號(hào): 11&ZD082)階段性成果。
賀圣達(dá)(1948- ),男,云南省社會(huì)科學(xué)院教授。1982年大學(xué)畢業(yè)后一直從事東南亞研究工作。東南亞研究方面的主要著作有: 專著《東南亞文化發(fā)展史》、《緬甸史》等;在《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亞太研究》、《東南亞研究》等刊物發(fā)表東南亞研究方面的論文百余篇;主持翻譯《劍橋東南亞史》。現(xiàn)為云南省社會(huì)科學(xué)院研究員、中國(guó)東南亞研究會(huì)副會(huì)長(zh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