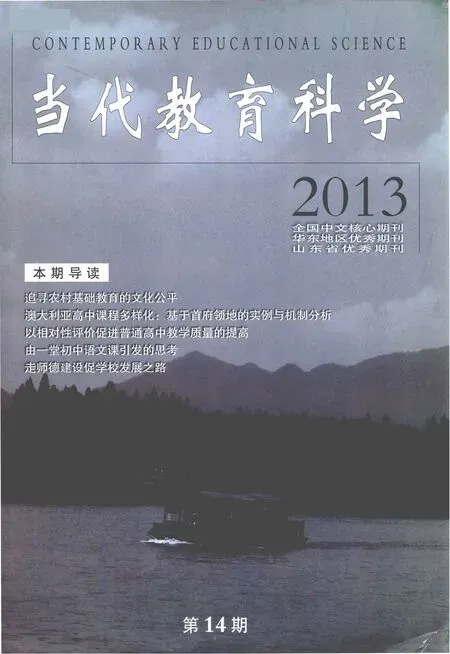全納教育的寬容之維
孫瑞玉
全納教育理念最早由William Stainback和Susan Stainback于1984年提出,旨在倡導特殊教育和普通教育“重新組合、建構、融合為一個統一的教育體系以滿足所有兒童的學習需要”。[1]這個理念從產生之日起,就得到了全球教育學者的極大關注。我國對于全納教育的研究主要涉及對其概念、主要議題、理據、模式、規模、效果等的分析以及對我國“隨班就讀”的全納教育實施情況的調查和分析。在這些研究中,學者一致將自由、民主、平等、合作作為全納教育的價值取向。當然這些價值取向沒有錯,但還缺少了一項非常重要的價值,那就是寬容。長期以來,我國教育實踐中存在對特殊兒童的排斥、歧視現象,[2]這也使得隨班就讀在實際的施行過程中遭遇到很多的問題,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的普通學校、教師和普通學生缺乏對特殊學生的寬容。正因為沒有寬容,“許多普通學校開展的隨班就讀徒有形式,成了‘隨班就坐’或‘隨班混讀’。更為重要的是,在社會上和學校里,依然是用傳統的教育觀來看待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學生,制造了一種不利于全納的氛圍,歧視和排斥弱勢群體的現象時有發生。”[2]
一、缺乏寬容使得全納教育徒具形式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5年發布的 《全納教育指南:確保全民教育的通路》將全納教育定義為:通過增加學習、文化和社區參與,減少教育系統內外的排斥,應對所有學習者的多樣化需求,并對其做出反應的過程。以覆蓋所有適齡兒童為共識,以常規體制負責教育所有兒童為信念,全納教育涉及到教育內容、教育途徑、教育結構和教育戰略的變革和調整。[3]通過這個界定我們可以看到全納教育的一個重要理念是“減少排斥”,想要實現這一點就必須擁有寬容,如果沒有寬容,全納教育只能徒具形式。我國從1989年就已經開始開展特殊兒童隨班就讀的試驗,持續至今已有十幾年的時間。但是隨班就讀的現狀并不樂觀,由于缺乏對特殊學生的寬容,隨班就讀全納教育非但沒有減少排斥,某種意義上還加劇了排斥。
我去H學校聽一節初三數學課,聽課期間我發現教室最后一排靠墻的座位空著,桌斗里和桌面上亂七八糟的堆滿了書和文具。課間我詢問一個學生這個同學怎么沒來上課,學生給了我這樣的回答“老師,她比較特殊,經常不來上學。”“她已經和我們生活快三年了,和她第一次見面就覺得她格外的‘熱情’。那是一次分班考試,她來晚了。一進教室就和她以前的同學打招呼,弄的那個同學很尷尬。后來,我和她分在了一個班。她上課更是格外的‘活躍’,嘴里總是沒完沒了的說個不停,也聽不清楚她到底是在說些什么。”“她不僅上課打擾我們聽課,下課更是能鬧,而且有時還把自己弄的像個大花貓。她有時很愛和班里的同學斗、打架,但總是輸,輸了就哭。”“我們老師讓我們別招惹她,如果她招惹我們,也讓我們別理她,這樣她就鬧不起來了。”聽了這個學生的回答,我感覺到那個沒來的孩子可能是一個特殊兒童,于是就找到班主任想詳細的了解一下情況。班主任說“你怎么關注起她來了?她有多動癥,自己管不住自己,成績不好,還經常把班里搞的烏煙瘴氣的。”“她的父母堅持讓她在我們學校上學,我們也沒有辦法。”“她今天請假了,明天應該會來。”“對了還忘了提醒你,以后你來聽課的話,見了她不用理她,如果她問你喜不喜歡她,千萬不要說喜歡,她會一直粘著你,還會抱著你親你,你受不了的。不用理她就行。”
這就是隨班就讀的特殊學生的實際情況,在教師和其他同學眼中,她是特殊的,不正常的,教師對于班里有這樣一個學生感到無可奈何,學生對于班里有這樣一個同學感到受到打擾。雖然這個學校接收了這個女生,使得她在這個班級中有一個座位,但是她的差異性并沒有獲得寬容,老師和其他同學并沒有從心里接納她。可以想象,她和她的課桌就像教室里的一座孤島,表面看來和同學們在一起,但實際上則與之隔絕。全納教育的本義是取消隔離,減少排斥,但是讓一個特殊學生坐在普通的教室這并不意味著取消了隔離,減少了排斥,因為真正的壁壘存在于師生的心里。缺乏寬容的隨班就讀,只能是隨班就坐,缺乏寬容的全納教育,只能是徒具形式。
二、全納教育的寬容之維不可或缺
“寬容作為一種個人態度,與對人的特定概念密切相關,這種概念可成為一個人如何看待他人的基礎:在他眼中,其他人(每個人都獨一無二,因此‘各不相同’)不管可能有什么差異、個人特征或條件,都是人。寬容者的主要標志是,在具體情況下,即使條件允許,他也不會去損害他人的權利。”[4]“寬容是指一個人雖然具有必要的權力和知識,但是對自己不贊成的行為也不進行阻止、妨礙或干涉的審慎選擇。寬容是個人、機構和社會的共同屬性。所謂不贊同既可以是道義上的,也可以是與道義無關的(即不喜歡)。”[5]客觀的說,特殊兒童確實與正常兒童在生理或心理上存在在差異,正是這些差異導致特殊兒童在生活、學習以及人際交往方面有著和普通兒童不同的方式,這些不同往往招致別人的不喜歡,甚至歧視和排斥。寬容首先是承認每一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其次是即使自己有必要的權利,也“容許別人有行動和判斷的自由,對不同于自己或傳統觀點的見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6]除此之外,更高層次的寬容是“并不滿足于容忍各種差別,反而鼓勵或甚至造成這些差別。”[7]
從某種意義上說,長久以來特殊教育都是基于對特殊兒童和普通兒童的差別不寬容的基礎上的。人們相信“心理—醫學”的研究,認為特殊兒童和普通兒童之間存在差異,并且認為特殊兒童應該在隔離性質的特殊教育學校或機構接受教育,從18世界末特殊教育誕生到20世紀中期這種觀點一直占據統治地位。[8]全納教育基于人權、自由、平等,倡導取消這種長期存在的隔離,這是民主社會的必然要求。但如何在真正的意義上取消隔離關鍵還在于人們對于特殊兒童作為獨一無二的人的承認,對于他們特殊的生活方式的寬容。只有人們從內心真正接納了特殊兒童,只有學校和教師真正把特殊兒童看作學校和班級中的不可缺少的成員,只有同學們真正把他們“看作是自己的弟兄”,[9]長久存在的隔離才可能被取消,全納教育倡導的特殊兒童的自由和平等才能夠實現。從這個意義上說,寬容是全納教育能夠實現的必要保證。
寬容和全納教育的關系并不是單向的,全納教育也為所有學生形成寬容的價值品質提供著良好的契機。全納教育雖然最開始是作為特殊教育領域的一個理念出現的,但全納教育是面向所有兒童的,包括特殊兒童,同時也包括普通兒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全納教育的定義強調的是應對“所有學習者”的多樣化需求,覆蓋“所有適齡兒童”,負責教育“所有兒童”,所以全納教育不僅僅是關注特殊兒童的成長和發展,它所關注的是所有兒童共同的成長和發展。在全納學校和班級中,學生可以更直接地了解每一個人都是不同的,可以學著承認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允許別人以不同的方式生活和學習,可以在潛移默化中形成一種集體認同和歸屬,把集體中的每一個不同的人看作是自己的朋友和兄弟,可以讓彼此的心容在一起,這就是最高層次的寬容。在這個全球化和價值多元的時代,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更加頻繁,人們擁有的接觸其它國家或民族的思想和文化的機會越來越多,如何能適應這樣一個時代,如何能在這樣的一種社會背景中健康有序地形成自己的價值體系這是一個對于青少年來說非常重要的問題。寬容的價值品質的意義在這里就凸顯了出來,只有懂得寬容,能夠寬容的人才能適應這樣的時代,才能更好地成為世界公民。全納教育是實施寬容教育的良好平臺,全納教育對于全體學生成長和發展的促進作用也在這里略見一斑。
三、讓寬容貫通全納教育的策略選擇
寬容是全納教育真正實現的重要保證,缺乏寬容的全納教育只能徒具形式,同時全納教育也為學生養成寬容的價值品質提供著契機。那如何才能讓寬容貫通全納教育,在全納教育中養成學生的寬容品質呢?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努力。
(一)營造一種寬容的全納學校氛圍
基于“心理—醫學”而對特殊兒童采取隔離教育的方式非但不能彌合特殊兒童和普通兒童的差異,反而是加劇和凸顯了這種差異。全納教育旨在取消隔離實現特殊教育和普通教育的融合,由于普通學校的大量存在,其必然成為融合的主要場所。如何實現從普通學校向全納學校的轉變,如何使特殊學生不僅是表面上在班級里有了一個座位而是真正成為班集體的一員,這首先需要營造一種寬容的學校氛圍。從招生方式到學生考核方式,從教師培訓到教師評價體系,從校園文化建設到校園硬件完善,都需體現出對特殊兒童的認可、歡迎和接納,讓所有的教師、學生和家長都感受到這樣一種寬容的學校氛圍。
(二)提升全納教師的寬容意識和寬容教育意識
教師在全納教育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一個特殊學生是否能夠真正被接納,是否能夠容入班級集體,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教師對這個學生的態度。如果教師能在自己日常的言行中傳達對于特殊學生的接納和寬容,其他學生就會效仿,特殊學生也會倍受鼓勵,反之如果教師傳達的是對特殊學生的排斥和冷漠,其他學生就會效尤,特殊學生只能倍感孤立。
教師在言行中傳遞寬容或者不寬容,最終的原因歸結到教師自身是否擁有寬容意識。所謂寬容意識就是容忍差別,鼓勵甚至造成差別的意識。在面對一個情境時,教師需要在瞬間做出反應,在這個反應時間里教師根本來不及去做太多的思考,換句話說,教師并不是事先考慮好了對特殊學生是要寬容還是不寬容,而往往是按照第一反應來行事,本身具有寬容意識的教師會做出寬容的第一反應,不具有寬容意識的教師則會做出不寬容的第一反應,教師就是自然而然的這樣做了。這也就是為什么強調為師要身正,所謂身正就是有良好的價值素養;為什么強調身教,所謂身教就是教師自然而然的行為都傳遞著正向的價值。對于全納教育來說,教師自身具有對于特殊學生的寬容意識是必須的,是最基本的。但這還不夠,作為專業化的教師還要有敏感,強烈的將寬容教給學生,讓學生也擁有寬容意識的教育追求。也就說在日常的學校活動中,教師自己要有對特殊兒童的寬容意識而且還要有用自己的寬容來教會學生寬容的教育意識。
(三)通過行動傳遞寬容,將全納教育落到實處
全納教育不能徒具形式,而是要在日常的學校生活中真真切切的得到實現。這就要求教師通過自己的行動來向學生傳達自己對于特殊兒童的寬容和接納,而不是僅僅停留在口頭上。價值倫理學家舍勒曾經說過 “價值的載體是行為”,[10]一個人是否擁有寬容品質,不是看這個人是否說自己有,而是看在他的行為中是否體現。全納教育不是教師在班會課上不厭其煩的告訴學生應該寬容,也不是嘴上告訴特殊學生他是班級的一員,而是在日常的學校活動中,在教師的言談舉止之間隨風入夜,潤物無聲。學生不是通過達到老師的要求學會寬容,而是在老師的日常行為中體驗到寬容,接收到寬容,心靈被寬容所觸動,久而久之學會了寬容。特殊學生也不是因被告知而體驗到被接納,被寬容,而是在班級生活中,在和教師的交往中體驗到教師和同學對自己的認可,體驗到自己容入到集體之中。對于年紀較小的學生,也許他們不能深刻的理解寬容的意思,但是他們卻能從日常的行為中體驗到寬容和被寬容,并在自己的行為中付諸實現。
[1]Stainback,W.,Stainback,S.A rationale for the merger of special and regular education.Exceptional Children.1984(51):102-111.
[2]黃志成.全納教育展望[J].全球教育展望.2003,(5).
[3]周滿生.全納教育:概念及主要議題[J].教育研究.2008,(7):16.
[4]約安娜·庫茨拉底.論寬容和寬容的限度[J].黃育馥譯.第歐根尼.1998,(12):21.
[5]戴維·米勒,韋農·波格丹諾編.鄧正來等譯.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820.
[6]賀來.寬容意識[M].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1.1.
[7]安托萬·加拉蓬.法律和寬容的新語言[J].馮曄譯.第歐根尼.1998,(12):41.
[8]鄧猛,肖非.全納教育的哲學基礎:批判與反思[J].教育研究與實驗.2008,(5):19.
[9]伏爾泰.論寬容[M].蔡鴻濱譯.廣東:花城出版社,2007.152.
[10]馬克斯·舍勒.倫理學中的形式主義與質料的價值倫理學[M].倪梁康譯.北京:三聯書店,2004.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