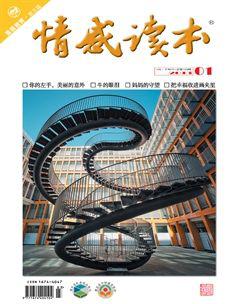十七歲之前
童詩墨
顏麗叫我吃飯的時候,我正在構思一篇為她寫的文。隨著她推門而入,我慌忙將草稿放進了抽屜,轉過身故作自然地擋住了書桌,但我僵硬姿態還是引起了她的疑心。她偏著頭,試圖從我身后有所發現,但是她顯然失敗了,除了攤開的作業再無其他。我強裝淡定“看什么?”顏麗說“沒什么。”然后轉身出去。可她顯然不甘心一無所獲,走到門口又猛然回頭,直到她的狐疑在我的微笑下潰敗,她才悻悻地出去,“快點”她說。
吃飯時,我一直埋著頭,一向被她呵斥“吃飯時不許說話”的我格外安分。透過垂在額前的劉海,我看見顏麗看了我好幾次,每每欲言又止。終于,在我放下碗筷時,她說話了,“最近在學校怎么樣?”我知道這樣平靜卻突兀的開場白意味著什么,不免有些心虛,“還……還好”,“那……和同學的關系呢?”顏麗沒有看我,而是抿了一口湯。這讓我一下輕松了許多,撐在椅靠上,“還行”戰術再迂回也要切題的,正如顏麗現在。“那……就處理好,交什么樣的朋友保持什么樣的距離,有些朋友適不適合,這些你……”“你什么意思?”“這些你應該能處理好,你也不小了,我想說什么你都應該明白”顏麗看著我。“我問你什么意思?”我走上前雙手撐在飯桌上,同樣看著她,“我的意思還用我多說?還有,你這是什么語氣?這是和我說話的態度嗎?”顯然,我們同時被激怒了。
我和顏麗總是這樣,一見面就特親近,不出10分鐘又會吵起來。很多時候我們都是為對方好,可就是誰也不愿服輸,爭得面紅耳赤,在一場唇槍舌戰之后便各自回房間黯然神傷,后悔自己說話太過火。可是現在,我們正處于戰爭狀態,沒有時間計較后果,只是為自己據理力爭,得以舌戰之勝。
我沉默著,我必須思考一個周全的回答才能不被她抓住破綻,“我無非重復我的疑問而已,求知欲的高漲有錯嗎?”我自鳴得意,顏麗沒上過什么學,這種話往往使她敗下陣來,但這一次,我錯了,“求知欲?好啊,我來滿足你所謂的求知欲!同樣,我的求知欲你理應無條件滿足。”我驚愕,但不愿服輸“OK啊!”
“你是不是在學校談戀愛了?前天半夜給你打電話那男孩是誰?你空間那些留言是怎么回事?照片里那上鏡率最高的男生又是誰?……”
“停,你還沒回答我,倒問這么多問題?”我越發心虛,更連漸氣憤。
“這,就是我的意思!”顏麗雙手環抱向后靠著。
我語塞,很難再理直氣壯地和她過招,“那么,顏佳同學,你是不是該滿足我的求知欲了?!”顏麗半瞇著眼。
“清者自清,你別把人都想這么齷齪好嗎?拜托,我們是母女唉,你就對我一點信任感也沒有么?”我做著最后的掙扎。
“信任?是你先讓我失望了”顏麗愈發義正言辭。
“我們沒法溝通了,我對你也很失望!”當我跑回房時,依稀還聽得到這怒吼的回聲,然后被我重重的摔門聲取而代之了。
回房間后,我一直哭,顫抖著給朋友發短信訣別。我是做好了永久沉睡的準備閉上眼的,只是在第二天我仍被鬧鐘叫醒,頂著紅腫的雙眼上學去了。是我太膽怯?不,只是在夢中,我竟夢到和顏麗在一起,過著兒時千百次出現在憧憬中的生活。原來,我還有那么多東西難以割舍,還有那么多東西值得留戀,比如顏麗。
平靜時總是會理智很多,難怪都說沖動是魔鬼,年輕人真不能太沖動。
冷戰的戰果一天天累積,我和顏麗始終僵持不下,誰也不肯低頭,其實彼此心里早已經釋懷了。我平靜地做著自己的事,直到那天,當早上關鬧鐘時看到手機屏幕上赫然印著“3.12”的字樣,我開始慌了,十幾年前的3月12日,是我和顏麗的第一次見面,之后的3月12日,她總是不在我身邊。今年是第一次,可如今關系落到這般田地。
高中生活是太緊迫太充實罷,不然朋友們怎么會記不起我的生日?最失落莫過于生日這天你依然像往日一樣平靜度過,甚至更糟。回到家時顏麗正在看電視,屋內沒有燈,但我卻依舊看見了她冷淡的表情,我徑直回了臥室,隨著燈光充滿整間屋子,一只比我還大的泰迪熊兀地闖入了我眼簾,粉色的彩帶上印著顏麗并不工整的字跡:對不起,親愛的寶貝,生日快樂!我走到床邊將它抱起,淚水潸然,我不知道顏麗是何時進來的,當我已哭得一塌糊涂時她幽幽地說:“這個可洗不了,死丫頭,不知道珍惜”。我回頭正好看到她似笑非笑地站在床邊,立馬過去抱住她,邊蹭邊說“那你可以洗”。
“我不知道你喜歡什么,所以才去你空間看的,沒想到看到那些,我不知道那其實是個女生,現在孩子也真是的,硬是要讓我們做家長的誤會。”顏麗摸著我的頭,好似帶有幾分委屈。
那一夜,我依偎在顏麗的懷里,告別了我的16歲。
作者單位:湖北省宜都市第一高級中學高二十三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