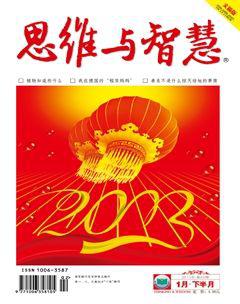母親的織布機
堯山壁
小時候,除去母親之外,最熟悉的是屋里那架織布機。自打落生,家中只有它與我母子朝夕為伴。我愛它又恨它,因為只有它與我爭奪母愛。母親常常撇下我,坐在它面前,“呱噠呱噠”的織布聲淹沒了我的哭聲。但是又不能遷怒于它,因為母親常說,我們娘兒倆是靠它養活的。
這架織布機是母親的陪嫁。結婚時,父親房無一間地無一垅,只有一身好武藝。外祖父是個木匠,早早為母親設計了生路,精心打造了這架織布機。父親臨時搭建的一間地窩子,沒有放織布機的地方,只得暫放鄰居家里。眼看姐姐要降生,萬般無奈,父親鋌而走險,頂替財主家孩子當壯丁,當地叫賣兵,用一個男子漢的身體換回幾間磚房,好把母親的織布機抬進來。行軍路上,父親掙脫繩捆索綁,躥房起脊地消失在夜色里,從此變成了黑人。不久他參加了冀南暴動,兩年后又投奔滏西抗日游擊隊,打了幾個漂亮仗,成了紅人。可惜在我落生十四天時英勇犧牲了。幾畝薄地指望不上,織布機便成為我家唯一的生活來源。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唯聞女嘆息。”那是中國古代織綢緞的機械。我們這一帶,自古以絲織聞名。《西京雜記》上說,漢霍光妻贈朋友淳于衍“蒲桃錦二十匹,散花綾二十五匹。綾出鉅鹿陳寶光,妻傳其法。霍顯召入第,使作之。機用一百二十躡,六十日成一匹,匹直萬錢。又與越珠一斛,綠綾七百端,直錢百萬,黃金百兩。”我們縣向來屬鉅鹿郡,我們村距離現在的巨鹿縣城也不過20公里,所以有著悠久的紡織傳統。
從古代傳授先進棉紡織技術的黃道婆到我母親這一代已經有六百余年歷史了,工藝水平也在循序漸進。外祖父的魏莊是聞名的“棉花窩”,二、七大集,布市占了半條街,母親經常留意布攤的花色品種,織布技術達到了當時農村的最高水平,三里五鄉的女人們常來登門學藝。我從小在織布機旁長大,母親一直當做閨女使喚,所以對一般紡織工藝爛熟于心。后來看到乾隆年間直隸總督方觀承的《棉花圖》,工藝流程大體相似。
我看慣了母親坐在織布機上,手舞足蹈,左右開弓,姿勢優美,節奏明快,呱噠呱噠,如同音樂一般。興致上來,母親也隨著機杼的節奏哼幾句小曲。多是民歌《小白菜》和秧歌《三娘教子》一類的苦戲。
我從小跟著母親搓布節,拐線子,掛橛子,遞線頭,有時幫助把飛出的梭子從地上撿起來。母親是織布能手,表現在快和巧兩字上。織白布,一天能織一塊布,三丈三尺。織花布,功夫在設計圖案和顏色搭配上。母親的三匹綜、四匹綜不斷出新,引領一方布藝的潮流。村里閨女們出嫁,指名要老桃(我的乳名)娘的花色,所以家家新房三鋪四蓋,床單被面,往往是我母親的作品展覽會。我家這架織布機也出名了,越傳越神。
新中國成立前后那幾年,頭年淹、二年旱、三年螞蚱滾了蛋,家家沒了糧食,吃糠咽菜,有人要出三石高粱買這架織布機。母親不肯,忍痛把我送到外祖父家寄養,自己沒日沒夜地紡花織布,率領婦女們用布匹到山西換糧食,然后背著玉茭、豆餅回村來,養活外祖父和我一家人,度過災荒年。我是穿著母親的家織布長大的,直到大學畢業參加工作一直是粗布衣服,粗布被褥,并不覺著土,而是感覺著美,感覺著舒服,以土為榮。這榮就是一位母親的辛苦勞動。
母親辛勞一生,長壽而終。人不在了,那架織布機依然默守在那間屋里——那間父親用生命換來,母親奮斗一生的屋里——等著我回來。每次回家,看到它就看到了母親坐在織布機前節奏明快、手舞足蹈的身影,那就是母親躬織一生不朽的雕像。
這讓我涕淚滿面,長跪不起。
(月月鳥摘自《渤海早報》2012年3月20日)
- 思維與智慧·下半月的其它文章
- 漫畫之頁
- 或許你就在成功的路上
- 善良不是什么驚天動地的事情
- 逼良為優
- 說“錢”
- 書籍本來沒標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