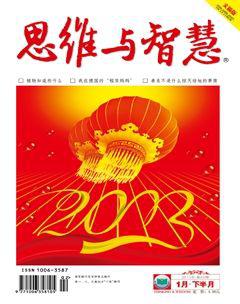我的天堂曾是一部小小的機器
馬家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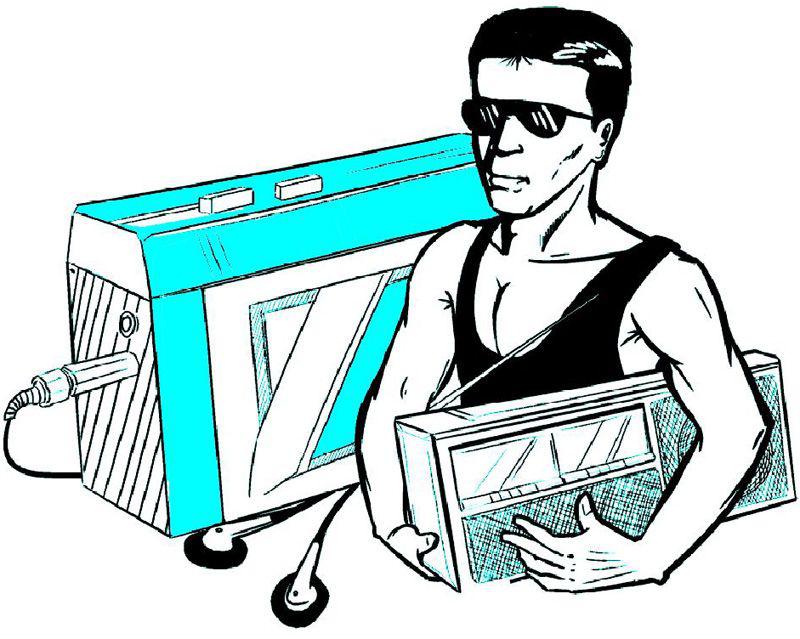
對于此專欄我通常有固定的“寫作儀式”:透過編輯小姐的電郵取得本期關鍵詞,坐下來,面對計算機,閉起眼睛,像招魂一樣召喚我的深層記憶,看看有什么影像從大腦皮層的曲折處浮現。
嗯,來了,第一個影像現身了,立即抓住它,或該說,牽著它,溫柔地牽著這只記憶之手,像跳探戈般跟這記憶影像翩翩共舞,左右旋轉,高低抑揚,耳畔仿佛有樂章響起,很奇妙,過不了多久便有其他影像相繼冒起,像音符般在我眼前飛揚;然后,我便陷入回憶,享受回憶,感慨回憶,隱約似是重新活過生命里的某時某刻,如胡適的詩所說,“有召即重來,若亡而實在”。我似是活了兩遍。
那么對于“錄音機”這詞兒,當我閉目,不消半分鐘,腦海便浮起一幅畫面,那是一片海洋,我站在沙灘岸邊,天氣極熱,我穿著紅色短褲,黑色背心,汗水從額上臉上背上胸前滲出滴出,但我不怕,年輕的我,本就什么都不怕,更何況我的鼻梁上面架著一副上世紀70年代最炫最酷的Ray Ban太陽眼鏡,兩片橢圓形的墨黑鏡片——香港人慣稱之為“蒼蠅鏡”——把我的喜怒哀樂情緒全部掩蓋,藏身鏡后,我昂首挺胸,得意洋洋。
那一年,我17歲。
十七青春好年華,炎炎夏日,跟幾個死黨趁著暑假到沙灘,以曬太陽為名,但其實只是為了泡妞,我所掌握的“武器”,除了一身結實的肌肉,更有提在手里的那部錄音機,黑色,長長的,寬寬的,沉沉的,硬硬的,體積比21世紀流行的筆記本計算機還要大個一兩倍,但我同樣不怕,反因它而感到驕傲,因為我走到哪里它便用聲音替我預先開路張揚到哪里,擾攘之物配上擾攘之人,簡直相得益彰。我還記得那天在沙灘上,我利用這臺錄音機重復播放譚詠麟的《夏日寒風》,剛出爐的新曲,的士高節奏,狂野,勁爆,歌詞淋漓奔放,徹底配合夏天海邊的熱烈情懷:
“擠迫的沙灘里/金啡色的肌膚里/閃爍暑天的汗水/我卻覺冷又寒/縮起雙肩苦笑著/北風仿佛身邊四吹。/只因心中溫暖/都跟她消失去/今天只得一串淚水/說愛我百萬年的她/今愛著誰?/我雖不怪她帶走旭日/卻一生怪她/只帶走癡癡的心/剩低眼淚/狂呼我空虛/空虛/恨極為她心碎/明知結局/何必去做/玩耍器具/狂呼我空虛/空虛/怒罵是她不對/強忍眼淚/從此我愿/獨在痛苦中活下去。”
當然是為了泡妞強唱愁,但這本是少年特權,此時不說,尚待何時?難道等到如今坐四望五才去說?如今生活忙亂到什么是愁什么是樂都經常混淆不清了,無語無言,欲說還休,懶得再談。少年時代則是另一個故事,若能把愁唱得激情動聽,那些躺在沙灘上的女孩子會主動走過來結識我、搭訕我,至少,會把目光從遠處投擲過來,像勾魂一樣,想把我的身子勾引過去。
所以那個17歲的暑假我和死黨幾乎變了“沙灘黨”,三天兩頭有事沒事結伴到沙灘閑坐,出門前,他們總先打個電話來提醒我,別忘了帶錄音機和錄音帶,仿佛戰士到戰場,錄音機和錄音帶是子彈和槍械,沒了它們,便沒我們,它們是我們的命。
又長又寬又沉又硬的錄音機年代終于過去了,換來的是小巧的“隨身聽”,亦即Walkman,盡管相對于今天的iPod,它仍算是龐然怪物。而當我把眼睛張開,沙灘的搖滾記憶消失無形,代之而來的是另一幅陰亮黑暗的影像,那是九龍的廟街,夜市的所在,曖昧的所在。在上世紀80年代,賣淫的吸毒的都在這個地方,我亦在,但不是買春也不是販毒,而是在街頭巷尾的小攤檔處找尋某種口味特殊的錄音帶,那種充滿著呻吟浪叫的錄音帶,大概賣15元港幣,一盒帶子僅有30分鐘聲音片段,其中約有5分鐘對白,由一個女聲一個男聲輪流述說各式幻想情事,最原始的欲望,最犯禁的想象,在字句之中迸發噴射;其余25分鐘,是呼吸和喘氣與哎呀嘩啦的失神叫喊,沒有故事,卻能傳達足以把少年撞擊得天翻地覆的隱密訊息。
我把錄音帶買回家,到了深夜,或把自己蓋在被窩里,或把自己鎖在廁所中,戴上又厚又重的罩式耳機,按下Walkman的播放鍵,把自己推進30分鐘的迷離仙界,沉溺如醉,幾乎不愿回到現實世界。
黑色禁夜,錄音機曾是我的情欲天堂,我的天堂,竟曾是一具小小的機器。我竟然曾是如此的無力卑微。
(莊妃軒摘自《晶報》2012年3月24日)
- 思維與智慧·下半月的其它文章
- 漫畫之頁
- 或許你就在成功的路上
- 善良不是什么驚天動地的事情
- 逼良為優
- 說“錢”
- 書籍本來沒標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