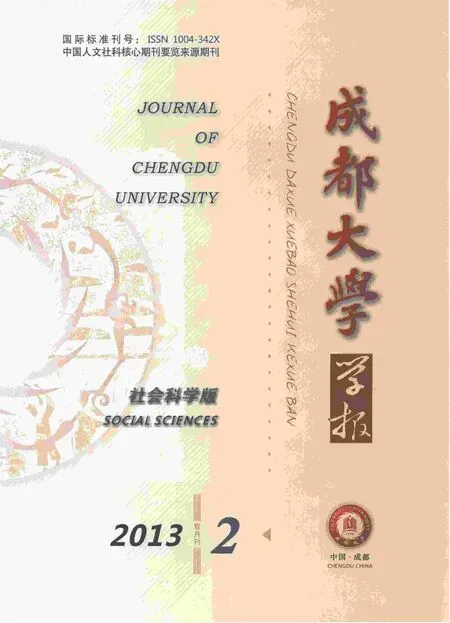江原古城與《山海經》
施權新
(崇州市文物保護管理所,四川崇州611230)
引論
20世紀90年代,川西平原岷江①西岸,亦即秦漢時期的古江原地域,相繼發現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六座城池,從已發掘過的五座來看,當時已初具城邦制國家的雛形,大量精美的石器和具有審美情趣的陶器,反映出相當水平的采集和農耕文化,已有部族議會制度、原始宗教和祭祀;已經形成統治和被統治階層,領導者指揮筑城和部落間的戰爭,有較明確的分工如制陶、捕魚、撈貝等等。城址內出土的文物,經鑒定為距今4500-4000年。碳14測定為4300年,正負50年。
按照文獻推算,距今4300年前后正是我國舜、禹時代。沈起煒編著《中國歷史大事年表》:“公元前二十一世紀,禹死,子啟殺原定繼承人伯益,嗣位。”②那么舜、禹的時代恰在公元前22、23世紀。所以已故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徐南洲先生說成都平原發現的史前遺址“其實已涵蓋了大禹所處的時代”③(以下凡引徐語簡稱徐著》),這是沒錯的。4500年甚至可能早于大禹時代。這個時代正是華夏民族部落大遷徙,炎黃二系各部落斗爭、融合,逐漸形成以中原為中心的部落聯盟,共同譜寫出輝煌燦爛的上古史的時代。
載籍上的黃帝阪泉之戰、大會諸侯、垂衣裳而天下治,堯、舜時的放四兇、與共工的戰爭、禹的征三苗、治水布九州島等便反映聯盟形成至鞏固的過程。如果把考古發現的新石器時期遺址排列起來,不難看出中原以外的部落逐漸向中心集聚的脈絡,從而證實把古籍中的記載完全當成神話傳說是不正確的。即使是看似荒誕的神話,也是“基于現實,可以看到古代的史影。”④魯迅也說過,從某種意義上說,神話是史學的前驅。有一種觀點認為夏朝及此前的記載不能當作信史,但是越來越多的考古資料正把神話傳說還原為正史,如炎黃之戰的涿鹿之野,考古發現不就證明那里曾是龐大而又高等級的部落聚居地嗎?《山海經》(以下凡引自此書只標出方位、經次,如西次三經,大荒北經等)西經中所謂“有國名曰流黃辛氏,其域中方三百里”⑤郭墣注域即城,不就是成都平原史前城址所分布的大致范圍嗎?
江原古城所反映出來的部落繁榮毋庸置疑。有若干部落在這里生活、筑城,但不知什么原因,城里的居民都突然消失了,在整個文化層中缺少商、周這兩代,這里發生了什么情況?這些人到哪去了?他們為什么放棄故土大城?
據載,我國最早的城是禹的父親鯀筑的,《呂氏春秋·君守》:“鯀筑城”。禹是今汶川人,《孟子》:“禹生石紐,西夷人家也。”禹“本汶山郡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⑥“地曰石紐,石紐在西川也。”“禹本汶山廣柔縣人也,生于石紐。”《吳越春秋》也作同樣的記載。“廣柔縣,在汶川縣西72里,漢縣也。屬蜀郡。禹本汶山廣柔人,有石紐邑,禹所生處,今其地名刳兒坪。”⑦也就是說,禹和鯀的部族原住汶川廣柔縣,其地在今崇州西北部郊外,與古江原地域接壤。我們注意到,在《尚書》、《史記》等大量古籍中,禹和后稷的關系都非常好。這兩個名稱在《山海經》中多次出現。在《山海經》成書以前,江原古城早已存在,其規模、數量在全國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中格外引人注目,《山海經》的作者們不可能不注意到它們而不予記載。那么,這些古城在《山海經》中是怎樣出現的,古城和禹、稷等部落或其人又有沒有關系呢?趙俊波、趙小山在《玩·山海》中認為《山海經》中不少記載是歷史,不能僅作巫書來讀。那么,我們能不能從那些點滴的記載中理出一些江原上古史的頭緒來呢?
一 峚山、稷澤的地理位置
(一)峚山在哪里
《西次三經》:
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峚山,其上多丹木,員葉而赤莖,黃華而赤實,其味如飴,食之不饑。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湯湯,黃帝是食是饗。是生玄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歲,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黃帝乃取峚山之榮,而投之鐘山之陽。瑾瑜之玉為良,堅粟精密,濁澤而有光。五色發作,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食是饗;君子服之,以御不祥。自峚山至于鐘山,四百六十里,其間盡澤也。是多奇鳥、怪獸、奇魚,皆異物焉。
這段文字在《山經》所述諸山中是最長的段落之一,它所描寫的丹水、稷澤中的景象和《海經》、《荒經》中也在西經的都廣之野中動植物的美麗景象非常相似,可以互參解讀。文字描寫了峚山、丹水、稷澤中的自然環境,植被物產以及居住在這里黃帝世系部落的祭祀活動、衣食習俗等等,其中不少是古江原地域的信息。
先說峚山。
“峚”,通“密”。郭璞注《穆天子傳》引此經和《文選》李善注《南都賦》、《天臺山賦》引此經俱作“密”,可見古代二字通用。《說文》云:“山如堂者密。”“密”又通“宓”,甲骨文“宓”字作山上之木(甲骨文“宓”作),即“”,前人釋為穹廬下的戈柄,“密”字意為山之上、穹廬之下有軍士執戈,但似乎還有另外的解釋更為貼切。甲骨文中的(木)與此字形極為相似。而(戈)卻與之相去甚遠,故應釋為山上之木在穹廬下,也就是穹廬下山峰多、樹木多。密者,緊鄰而多也,與川西龍門山脈南段的山勢植被情況極為相合。龍門山南段山峰尖細(與其他山脈相對而言),挨鄰很緊,山谷狹深,從下往上望,仿佛山頂蓋著穹廬。西晉時的左思已特別注意到這種情況,他說成都西部“山阜相屬,含溪懷谷,崗巒紛紜,觸石時出。”⑧李善注云:“阜,大山也;巒,山長而狹,一曰山小而銳也。”“紛紜”則是形容山脈上阜巒緊密而多的特點。杜甫《送張十二參軍赴蜀州,因呈楊五侍御》:“兩行秦樹直,萬里蜀山尖。”正指今崇州之山(蜀州即今崇州)。南宋祝穆《方輿勝覽·崇慶府》:“土地肥美,連山特起”,連山特起,山峰密也。據2008年5月汶川地震時成都陸航團搜尋失事飛機的直升機飛行員目測,龍門山南段山峰間的距離最窄處不到200米,這在全國都極為少見。
《山海經》中的地名大體都有出處,不少以地形地貌命名,如《西次一經》中的大、小華山(有研究者認為即今秦嶺)是以其地位于華夏中心、山體大小而命名;《西次三經》中的積石山,山多積石,是因大禹治水積石于此而得名;《南山首經》的成山,山有四方三壇,郭璞注云“成亦重也。”也就是說成山的得名乃山頭重疊,與四方三壇的特征吻合;《北次二經》:“白沙山,廣員三百里盡沙。”《北次三經》:“發鳩山,山上有精衛鳥。”“發鳩”,指精衛飛出。《南山首經》有山“不可以上”,需猨生翼方能上,故名猨翼。《中山首經》之甘栆山,按方位在山西南部,其地多甜棗……由此,可以這樣推斷,峚山的得名是因為它“崗巒紛紜”“長而狹”的山峰,相屬而形成“密”的狀況和植被茂密。
再從具體位置看。
《山海經》中的南經,是“從西南陬至東南陬者。”。⑨《海外南經》第三條:
其為鳥,比翼鳥在其東,青、赤兩鳥比翼。一曰在南山東。
從西南往東南,此條所述之地乃南經與西經交界處往東南的途中。清人吳任臣注云:“比翼鳥即蠻蠻也。”“蠻蠻”見于《西次三經》之首:
崇吾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鳬,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蠻蠻。
“相得乃飛”即《海外南經》之“兩鳥比翼”,否則不能飛也。西晉張華《博物志·異鳥》云:
崇丘山有鳥,名曰蠻。(按,即蠻蠻)
《周書·王會》:
巴人以比翼鳥。
孔晁注云:“巴人,在南者。比翼鳥,不比不飛,名曰鶼鶼。”按“鶼鶼”乃“蠻蠻”的音轉。因此古人以為比翼鳥之東的頭國的“頭”即堯之臣“兜”,被流放到崇山,而《西次三經》之首的崇吾山也有比翼鳥,所以《西經》中的崇吾山就是《南經》中的崇山,也即《尚書·堯典》中“放兜于崇山”的崇山。
很顯然,以鳥來定山名并不準確,因為一種鳥可以在很大范圍活動。按崇山在今湖南澧陽縣,山跨數里,與今重慶涪陵地區相鄰,在《海外南經》所述從西南往東南的途中。涪陵在長江之南,古為巴人活動地區,而澧陽卻是楚人活動的地區,然而涪陵沒有與崇山有關的地情地貌。再者“崇吾山”“在河之南,北望冢隧。”⑩并不在江之南,而是在江北。冢隧即陜西南部嶓冢山谷,其南即巴人之國,地域包括今天的四川東部和重慶北部。崇吾山的具體位置在哪里?前述“巴人,在南者。”換言之,即巴人之國的南方,所以距崇山不遠的崇吾山也有“蠻蠻”。由此可以這樣圈定大致范圍:冢隧之南、長江之北的巴人之國的南方,與澧陽、涪陵相隔不遠的地方,約為今天的重慶合川一帶。合川古屬合州,“合州,春秋時為巴國。”?合州附近璧山縣的重壁山應該就是經文中的崇吾山。
按《西次三經》經文,從崇吾山到川西龍門山南段,方向為西北,距離1090里。《山海經》成書在周初到漢初,按周、秦里小于今市里,一里約合今0.84里,從重壁山至峚山今里約800多,基本和《山海經》所記里程吻合,方向完全一致。如果認為巴人之地所指甚寬,但無論從川東或川東北何地往西北1000里左右均找不到如從峚山發源往東西方向流走的河流,更無如峚山下的稷澤;川東其他地方也沒有如像重壁山的地貌。
峚山,“其上多丹木”,印證甲骨文“密”字穹廬下多樹木的形象。丹木圓葉,應是生于海抜并不太高的闊葉樹,經文描述的情況即今柿樹。柿樹剝開粗皮,莖桿呈紅色,葉片橢圓而闊如手掌,所謂圓葉赤莖;開黃花,果實為漿果,成熟后鮮紅。經云:“其味如飴。”飴,濃粥,正是柿果成熟后的物質形態和味道,確實能充饑,所以“食之不饑”。柿樹在今天的龍門山南段和大邑、崇州交界處的無根山隨處可見,兒歌至今還以謎語的形式唱道:“紅帕帕,包稀飯,又好吃,又好看。”粥,川西人普遍叫稀飯。經文不僅記述了峚山上的物產,同時反映采集野果為生的情況。
峚山之名,還有紀念禹及禹族人發祥地的意義。據徐南洲先生研究,《山海經》中的《山經》是遲于《海經》和《荒經》成書的。按,袁珂先生則認為《山經》早于《海經》、《荒經》?,也就是說《山經》中的材料有可能來至《海經》、《荒經》。《海經》和《荒經》多次提到大禹:
禹所積之山,在其東。河水所入。
禹殺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樹五谷種。禹厥之,三仭三沮,乃以為眾帝之臺。(《海外北經》)
西北海之外……有禹攻共工國山。(《大荒西經》)
禹攻云雨,有赤石焉生欒,黃本、赤枝、青葉,群帝取樂焉。(《大荒南經》)
禹湮洪水,殺相柳……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仭三沮,乃以為池,群帝因是以為臺。(《大荒北經》)
鯀腹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海內經》)
……
禹不僅治水,還攻占地盤以供“群帝取樂”?(按,有學者研究群帝即群巫),功勞很大。《山海經》中以上古英雄命名的地方不少,如堯山、軒轅臺兜國、女媧之腸、稷澤、共工國等等,都是他們居住或活動過的地方,似乎也應該有以禹命名之地。《史記·五帝本紀》正義云:“禹出汶山,字曰文命,名密。”據此推測,龍門山南段之名峚山,除自然形態外,還因禹出生在此地或主要活動在這里而得名。雖然《爾雅》、《說文》均釋“密”為“山如堂者”,但王夫之《潛夫論·姓氏志第35》指出:“前人書堂俱作啟,后人變之,則又作開。”則“堂”在古代又可作“啟”和“開”。“山如堂者”即啟、開也。而禹之子恰恰名“啟”,雖然可能沒有必然聯系,但至少證明載籍所載禹族和峚山有關應該是準確的。峚山為岷山的一部份。岷山,不少學者認為即淖山,據此,則岷山為沼澤旁的山,與峚山下連稷澤相吻合。
(二)丹水即文井江
《山海經》中名丹水者計有六處,分布在不同方位、不同地域,可能上古描述的文字貧乏或無其他特別之處來命名,所以都是因為流水是紅色而得名。《玩·山海》說“《山海經》的作者,略識東南西北,粗知山水走向而已。”“記載錯誤很多,山水之名多為托撰。”?《山海經》原為圖,在晉時其圖尚存,經文是根據圖來描述的,在測量技術有限的情況下,里程不確切,方位不準確是不可避免的。加以各部分并非出自一人一時;各人以各自的起迄座標、中心地域敘述,便出現同一地名、同一地區各經所述差異很大的情況。到劉秀進《山海經》時,更有不少錯訛、錯簡,有的把后來的釋文滲入正文;有的把此經之文編入那經;有的方位顛倒,如《海外北經》:“自東北陬至西北陬者”以下文中諸國的敘述順序實際是從西北到東北;《海外南經》將《北經》之“匈奴在開題之北”錯簡在內;《海外西經》將《北經》的四條內容收在內;甚至在印刷術發明之前傳抄時弄錯字等等。如《西次三經》的經文
昆侖之丘……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丑涂之水。黑水出焉,而西流于大圩。
按,昆侖丘,學者大都認為即今巴顏喀喇山,發源此山向西流較大的河僅今紆爾干河,而黑水如果是《禹貢》中的黑水的話,徐南洲先生考證為今西向東流的洮河?,由此可見《山海經》中的西注、西流可理解為從西往東流。“丹水出焉,西注于稷澤。”應是此例之一。
在崇吾山西北、冢隧之南1090里的地域,方圓上千里找不到一條從東往西流的較大河流,即使從巴國各個地方往西北1000里也找不到,但卻有幾條從西往東流的河流,那就是古江原境內發源于今崇州西北山區,也即龍門山南段的文井江和邛州的火井河、南河?。《西次三經》中“西注于稷澤”的河有兩條,一為發源于峚山的丹水,一為樂游之山的桃水,與今金馬河西岸文井江和火井河為最大的兩條河情況若合。文井江在龍門山里從西往東流數十公里,出山后稍折向東南,至新津與岷江匯。火井河則基本上是一直往東流至岷江。因此經文的“西注”應理解為從西往東流。
文井江之名始自《史記·河渠書》及《西南夷列傳》:李“冰又通笮道文井。”是說李冰疏通笮道縣的文井江。峚山下的丹水便是此江。
(三)稷澤粗識
古江原地域沼澤的遺跡歷有記述,到20世紀中葉尚未完全消失。左思《蜀都賦》:
昔者王孫之屬、邵公之流……玄黃異校,結駟紛紜,西越金堤,東越玉津。
漢賦中狩獵多在澤中,說卓王孫結駟連騎獵于田澤,西邊越過金堤。金堤即今都江堰,從臨邛到都江堰必須經過江原,江原為田澤。而卓王孫之所以從河北遷川西,是因為
岷山之陽,有蹲鴟,民至死不饑。(《史記·貨殖列傳》)
蹲鴟,即芋頭,澤瀉科水生植物,野生栽培均可食用。既說明那時仍多沼澤,也說明史前人可采集其作為食物,所以這里人們聚居。
《水經注》記汶川廣柔縣下137里為濕阪,137里到達的正是龍門山下的江原。《爾雅·釋名》:“山旁曰阪”,“阪”通“坂”。《說文》:“坡也。”《爾雅》:“下原為濕。”《詩·王風》:“隰則有泮。”“隰”通“濕”。《傳》:“泮,坡也。”據此,濕阪即山旁的坡,且為濕地,正是江原地域從西北向東南的地勢地情。南宋范成大詩“曲沼擎荷蓋,新畦藝綠針”?。詩人在沿途看到很多曲沼。公元20世紀四五十年代,崇州、大邑、新津、都江堰等古江原地域還有不少常年積水的成片冬水田,殘留著沼澤的明顯痕跡。由于丹水出山后沒有主河道,水流散漫,所以毎逢下雨漲水,必然形成“其原沸沸湯湯”,人們才在原上筑城防水,故爾留存多座古城至今。這些城地勢低的一方不是無城墻?就是有缺口?,三面阻水,一面排洪。后來李冰疏出主河道,減少洪澇災害,百姓安居,接受秦人統治,這是通笮道文井的另一政治目的。
經文“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湯湯。”“玉膏所出,以灌丹木。”徐南洲、趙俊波等均以為石油涌漫之貌?。如果玉膏是石油,石油怎能灌丹木?而且丹木被灌以后還長得鮮亮,果子味道很好,所謂“五色乃清、五味乃馨”。用石油澆灌丹木,只會使其枯死,這是常識。所以應按原文解釋為白色玉石和蘊藏白色石的河流流水。川西都廣之野那時有大量玉石,廣漢三星堆出土大量玉器,必是就地取材。“黃帝是食是饗”是黃帝族人、子孫以柿子為食,用玉祭祀,后文黃帝取好玉以祭“天地鬼神”并“服(佩戴)之以御不祥”和三星堆以玉為祭物和佩戴物是同樣的禮俗文化。黃帝族曾在古江原活動,據《崇慶府圖經》杜光庭《青城山記》等道教典籍中的中皇上人寧封?,早期活動在天國山?,山里至遲在漢時就有他的觀宇,唐開元十八年(759)才由蜀州刺史楊勵遷往青城的。這說明寧封是在這一帶發明燒制陶器的,也與雙河古城中的陶器類別與川西以外地方不同吻合,這里是燒陶誕生的源頭之一,這也與雙河等川西史前古城出土的陶器發展情況吻合。黃帝就寧封問三一道,寧封贈其《龍蹻經》等傳說,可以推斷黃帝族人在這里的活動。峚山下自古有玉,原屬江原地域的灌縣,與江原緊鄰的寶興,以及古江原的核心地大邑、崇州山中至今還有漢白玉,那時水流中有白玉是肯定的。“玉膏”,《文選·蜀都賦》:“坂坻巀薛而成甗,溪壑錯繆而盤紆;芝房菌蠢生其隈,玉膏密溢流其隅。”溪壑玉膏,盤紆流隅,正指流水。同書《天臺山賦》:“挹以玄玉之膏,漱以華池之泉。”難道是捧石油洗漱?結合“其原沸沸湯湯”,從左思的賦里可以理解為膏液即流水沸沸湯湯。李善注膏液引蔡邕:“凝雨為陸,《洪范》:‘月失道而入畢,則多雨。’《詩經》:‘月離于畢,卑滂也。’”意思是膏液為“多雨而卑滂。”沸沸湯湯的情狀。《蜀都賦》這段記述的是成都以西,大部分為古江原地域雨澇淫溢之貌。《南山經》:“堂庭之山,多掞木、多白猿、多水玉。”蕭綺錄《拾遺記》:“按山海經云:常帝之山,出浮水玉;巫閭之地,其木多文。”與今本相較多后句,可見今本有遺。郭璞注水玉為水晶,與蕭綺的浮水玉有別,但可證玉在水中,故水名玉膏。至于玄玉,三星堆出土也不少。
澤在古代是寶盆,有陸有水,植被豐茂,故“多奇鳥、怪獸、奇魚,皆異物焉。”既便于采集,又便于狩獵農耕,是古人首選的居住之地。據《左傳》等先秦典籍及漢賦記載,直到商周戰國時期的許多政治、軍事活動都在澤中進行。但遇雨季又不堪其苦,為趨利避害,在澤中筑城,現存的江原史前古城正是這種特定自然環璄的產物。
《西次三經》中“峚山條”所描述的生態和生活,在《海經》、《荒經》中的西經也有描述:
此諸沃之野,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鳳凰卵,民食之;甘露,民飲之,所欲自眾也。百獸相與群居。(《海外西經》)
有沃之國……凡其所欲,其味盡存。(《海內西經》)
沃之國,沃民是處。沃之野,鳳鳥之卵是食,甘露是飲。凡其所欲,其味盡存。爰有甘華、甘柤、白柳、視肉、三騅、璇瑰、瑤碧、白木、瑯玕、白丹……爰有百獸,相群是處。(《大荒西經》)
開明西有鳳凰、鸞鳥……北有視樹、珠樹、文玉樹、玗琪樹、不死樹。鳳凰、鸞鳥皆戴瞂。
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靈壽實花,草木所聚。爰有百獸,相群爰處。此草也冬夏不死。(《海內經》)
按《呂覽》中亦有如上記述,這與峚山下的美玉、丹木“多奇鳥、怪獸、奇魚、皆異物”的情況何其相似!而且都在西經!除此之外,僅《大荒南經》中的巫臷民有這種生活環境。這個環境包括沃民之國、都廣之野、峚山下的稷澤。按沃民之國經文所述方位在建木西,《淮南子·墜形訓》:
建木在都廣,眾帝所自上下,日中無影,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矣。
有木青葉、紫莖、玄花黃實,名曰建木,百仞無枝。(《海內經》)
據胡太玉先生《眾神之國——三星堆》云:“專家考證,(建木)為三星堆青銅神樹。”以上述座標,沃民之野在成都平原西部,大致方位是不錯的,經文所描述的生態環境和成都西部也較吻合,直到漢初川西仍叫沃野,所謂“岷山之下,沃野。”?而江原附近還有廣都?。又:
后稷垅在建木西。
建木西還有個氐國:
其為人,人面而魚身。無足。(《海外南經》)
流黃沃民在其北,(其城)方三百里。(《淮南子·墜形訓》)
袁珂先生認為“民”字乃“氐”字之偽。“氐”,楊樹達《中國文字學概要》:“蜀名山岸脅之旁箸欲落堶者曰氐。”是蜀地產生的字。那么“沃民”和“氐”是同一族屬,同在一地。“氐”,低地之羌。《大荒西經》中有云:
有魚偏枯,名曰魚婦,顓頊死即復蘇。
不少學者研究認為魚婦即巴蜀先王魚鳧,或為顓頊。那么,與沃民或叫氐相鄰的后稷垅又在哪里呢?
前面說過,《山經》是遲于《海經》、《荒經》的,因此后稷垅、稷澤之名很可能源于《海內西經》:
后稷之葬,山水環之,在氐國西。
另據《海內經》:
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蓋天地之中,素女所出矣。?
垅者,葬地也。以后稷族聚居、生活、安葬之地名澤,非常合理。很可能沃民或氐是發明并善于種植而被尊稱作后稷。而在“后稷葬西”有
流黃豐氏之國,中方三百里,有涂四方,中有山。(《海內西經》)
郭璞注“涂”為道路,甚是。四方都有道路,可見三百里地勢都較平坦,而在平坦中有山,這地情地貌與今龍門山南段南麓大邑、崇州一二百里的平疇中聳出一座無根山極為吻合。“豐氏之國”袁珂先生注即氐國,也即沃民之國。雖然各經所名不同,但沃、氐、豐以及后稷之葬均在都廣之野、建木之西是不錯的。
上引經文后稷所葬之地,除“天地之中”任何地方均可指、無確定性外,必須同時有“山水環之”“其城方三百里”“素女所出”“都廣之野”這幾個基本條件,后人研究曾付出不小努力。郭璞注“都廣”即“廣都”,甚是。“都”,居也、全也,也指較大的區劃,“都廣”,可居的區域很大,與金馬河東西岸情況相符。楊慎《山海經補注》:“黑水廣都,今之成都。”“素女在青城天谷,今名玉女洞。”但今成都、廣都二地沒有山水環之的地貌,青城沒有天谷地名。但青城山南麓今三郎、西山等山區古名天國山,天谷天國音同而形訛,天國在都廣之野的西邊。山水環之的地貌只有江原,其東為岷江、羊馬河,南有天社山、邛崍山,西有天國、鶴鳴,北有青城、玉壘。公元20世紀末,在江原地域,文井江流域相繼發現的六座史前古城,分布在上起都江堰,下至新津,西達大邑,東到文井江東岸,占地面積也就在三百平方里左右,基本符合“其城方三百里”的記述?。后稷垅、后稷之葬,無論從方位和局部地貌來看,都在古江原境內,以后稷命名的稷澤符合古江原的地理環境。
“五味乃馨”應是說稷澤居民好馨香。馨者,香味濃烈。《華陽國志·蜀志》說川人“尚滋味,好辛香”,陳柏清先生在《常璩川味斷語崇州來》?里分析易經八卦方位,結合崇州濕熱的地理環境氣候,認為常璩的記述來自他的家鄉:江原。好辛香,因辛香除濕。雙河遺址考古試掘也證實“當時這里的氣候比較濕熱。”?而“奇鳥、怪獸、奇魚”等也可在20世紀出土的臘瑪象化石、鹿一類動物的遺骨以及大熊貓、梆梆魚這些并不常見的動物中得到證明。唐、宋時期大量的鹿類,明代尚多的虎、豹,現在雞冠山的牛羚、紅腹角雉,各種野禽組成當時的“異物”世界。至于“至其間盡澤”的鐘山,雖不能肯定是否在邛崍山脈今蘆山、寶興一帶(說詳后文),但從都江堰岷江西岸南下至蒲江、名山,距離300多里盡是山下坡地濕原,大抵與420里的古里相符了。
《玩·山海》里說:“《山海經》對巴蜀的記載很詳細。”當然不會遺漏占蜀地很大一部份且地情優越的古江原地域,而峚山、丹水、稷澤便是古今異名的這一地域。從以西經為主的描述中,約略可以看到沃氐之國、后稷、大禹等各部落在這里和自然作斗爭、生存、繁衍……譜寫一段段生動的歷史。
二 姜嫄、后稷與江原
(一)姜嫄之原
公元前318年,秦取巴蜀,設蜀郡,領縣15,今存九處縣名,未見江原。《漢書·地理志》始錄江原縣:“(壽阝)水首受江,南至武陽入江。”轄地在大江(金馬河)以西至龍門、邛崍山,還包括今蘆山、雙流部分地區。
江原,歷來大多數人釋為古人誤以岷江為長江之源,所以將地處岷江中上游的今崇州、大邑、都江堰、新津等地稱為江原。宋人不知究里,索性把江原改為江源。然而,先秦時人們已認為江水源于岷山,或稱瀆山、汶山、窮山、獨山、淖山,在今四川松潘。如:
江出岷山。(《山海經》)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尚書·禹貢》)
豈能以數百里之下江邊的原野為江水之源?胡太玉在《眾神之國——三星堆》和《破譯“山海經”》里說:“我們以為,后稷母姜原,實是姜原氏。姜原為地名,就是江原。”江原即姜原,是以后稷之母姜原氏得名,但沒有舉證,缺乏說服力。按,原者“廣平。”?江原實是江邊平坦廣闊之地。此地貌岷江出山后兩岸都是,為何獨稱西岸呢?因“姜”源于“羌”,姜原為牧羊女之原,和該江西岸上古活躍著羌族牧羊女有關。
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沃生炎居……祝融降處江水……生術器……以處江水。
——《海內經》(按,祝融亦神農世系。)
有氐人之國炎帝之孫……,太原神釜岡中,有神農嘗藥之鼎存焉。成陽山中,有神農鞭藥處,一名神農原。(《述異記·卷下》)
南方火也,其帝炎帝。(《淮南子·天文訓》)
南方祝融,獸身人面,乘兩龍。(《山海經·海外南經》)
名曰靈恝,靈恝生氐人,是能上下于天。(《山海經·大荒西經》)
江水、氐人?上面已討論過,在江原;源于炎帝族的姜原也出在江原。龍門山歷史上姜姓甚多,佐禹治水的江瀆神姓姜,漢代姜氏出龍門山下等等。載籍以為姜嫄乃有邰氏女,臺即臺國,在今陜西扶風,這也可能源于后稷封邰之后臺人建立姜嫄祠而誕生的傳說。關于“臺”,《玩·山海》說是指部落居住之地,并非部落名稱。《史記正義》:“臺,炎帝之后,姜姓,封臺。周棄外子。”司馬遷在《史記》中記為有邰氏。按《正義》所說應該是姜姓封于臺后,地名才改為臺國,也就是說有邰氏并非土著,而是遷來,這與姜嫄出川西不矛盾。《史記集解》:“或曰姜嫄,謚號也。”贊同者寡,姑備考。《詩經·生民》中并沒有說姜嫄生在何處,僅說其子后稷“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隘巷,小巷道;小于街的屋間道,應在較大的聚落中,極有可能指城中房屋之間的小道。這種聚落,迄今周原上未發現大于江原古城者。江原古城在畜牧中可能還扮演著圈欄的角色,當雞犬豕馬牛羊變為家養后必須要圈欄;“牛羊腓字之”也證明姜嫄乃牧羊女,牛羊與其有感情也。同時也可推測城中養殖業已很發達。
姜嫄為西戎牧羊女,西戎之地甚寬,今陜西西南、四川西部、西北及青海、甘肅均是其活動范圍。成都西部平原與山區交接處自古為西戎羌人之地,(參見本文關于禹出生地)所謂“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羌人支屬部落甚多,直至唐宋仍有許多部落活動,今天龍門山脈仍有羌族。姜嫄是否是這些部落之一呢?
袁珂先生《山海經校注》注經文:
大比赤陰,是始為國。
引郝懿行云:“大比赤陰即赤國郪氏,是也;然謂當是地名則非,疑當是人名。大比或即“大妣”之壞文,赤陰或即后稷之母姜原,以與姜原音近也。”
上引經文乃是后稷及其子孫在某處發明農耕和禹、鯀布土定九州島之事,同時談及叔均始作牛耕。同樣的記述《大荒西經》里也有:
有西周之國,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有赤國郪氏,有雙山。
這個大比赤陰或赤國郪氏與后稷族相鄰,有密切的關系。大比的“比”可通“妣”。但比的含義并不是母而是“密”。《說文》:“比,密也。”《左傳·文公十八年》:“是與比周。”注“比,近也。周,密也。”據此,大比可訓為大密,大比赤陰,即大密姜原,大峚山之姜嫄,兼有地名和人名,和周人始祖后稷族發祥地峚山下的稷澤有關(說詳后文)。
前面說過“沃民之國”、“氐人國”,同在江原,與居于近水低地相合;“流黃豐氏”據袁珂先生說“豐”可通“沃”,流黃豐氏即流黃沃民,也指江原部落。江原上古為羌氐各族屬活動的地域。前述流黃豐氏所處的無根山全是頁巖黃土。關于流黃,《說文》:“火在壟山,黃地色也。”即色似燒過之山,地質學上叫丹霞地貌,正是無根山顏色。徐中舒引《禮記》以證郭沫若《金文叢考·釋黃》:“象人佩環,遂以為佩玉之稱。”這是今人的解釋。兩千多年前的古人也這樣解釋,《淮南子·本經訓》:“流黃出而朱草生。”高繡注:“流黃,玉也。”左思《吳都賦》:“紫貝流黃,縹碧素玉。”古今一辭,流黃肯定是佩玉之俗。而《山海經》中有佩玉習俗的僅在《西次三經》中的稷澤:“佩之(玉)以御不祥”,這足以說明稷澤中住著記述名稱稍異的同一族屬,流黃豐氏,也即姜原氏。
即使今人有把流和黃拆開解,認為“流”即《禮記·王制》:“千里之外曰采、曰流。”是指荒服;黃則為土色或佩玉,也和無根山情況吻合。“流黃豐氏”即經中的“流黃辛氏”,也即“赤國郪氏”,辛、郪同為西韻,音同可通。黃色深則赤,赤,從大從火,古文從炎從土,火燒之土,與黃一義。“是始為國”,“國”通“郭”,訓為城,實指今無根山周邊的江原史前古城。而出現辛、郪等音同字不同的原因,也與《山海經》為多人記述有關,各人對發音的記述不同,所以出現同一地物而稱謂之字不同的情況。
無根山東麓,公元2000年在六城之外又發現一座古城,中科院考古所與成都市考古所聯合進行地面調查,僅拾得漢代陶片,但城墻的壘筑形制和雙河城垣一樣,不排除漢代人使用新石器時期遺址的可能。關于城,《山海經》記載僅一處,已見前?。《呂覽·君守》:“鯀筑城”,鯀為禹之父,西戎羌人,與江原緊鄰;與稷之母同時代。稷之母“大比赤陰”“始為國”,“國”通“廓”訓城,即始筑城,時代與鯀相合,可見江原諸城是西羌所屬各部落共同創造壘筑的,而城邦制為一城一國,所以史籍出現名稱的小有差異。
公元2005年,在無根山里發現許多石核,也為新石器時期的遺物。此山海拔不到千米,各山頭似座座土臺,溝坡遍布,谷中土地濕潤,古代水草豐茂?,宜于放牧。這個地區放牧的羌民部落也有可能叫有邰氏。有邰氏的牧羊女在山下后稷族人晚上祭祀時,跟隨神尸?的腳跡野合于夜色中,生下后稷,反映了上古江原地域各部落間通婚的情況,這種情況后來又重現在關于杜宇和朱利的傳說中。唐李冗《獨異志》:“有娥簡狄氏,呑鳥卵而生后稷。”與稷澤中民食鳳凰卵?相合,這是因濕地宜留下腳跡和食鳳凰卵產生的兩種傳說版本,且至今川中孕、產婦尚以雞蛋為營養品而大量食用,似也與姜嫄履大人跡而孕有某種聯系。
(二)農耕族的發祥地
稷澤是因后稷族的生活之地和葬所得名,江原的地貌和地情與之相合。后稷是農業的始祖,載籍中比比皆是。
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谷。(《尚書·舜典》)
暨益稷,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尚書·益稷》)
自禹以后,歷朝歷代都祭稷,周代以后配祀天地,“蓋稷出于社”?,是因為姜嫄“踐帝之跡于畎畝之中而欣喜。”?可見原始社會農業和婚姻的關系。姜嫄為游牧而后稷為農耕,他們的結合反映游牧向農耕的過渡,就像后來杜宇和朱利聯姻是鋤耕向牛耕過渡一樣(詳后文)。
稷,《說文》:“離也,五谷之長。”《大荒西經》:
叔均代其父及稷播百谷。
稷是個世代業農的部落。稷,又可作百谷解。稷,《甲骨文字典》作,象一人戴寬邊物(或為帽),手伸向前,跪蹲于地,在田中刈割的形象。古文,作田下之人面對禾苗,更為形象。稷為周人之祖,周,密也,其發祥地可能與密山相關;《甲骨文》作、,徐中舒先生釋為“象界劃分明之農田,其中小點象禾稼之形。”有一定道理。但此字更象水田;周是水與田的結合,即(水)在(田)中,由此可以推斷,周人是發祥于水田中的農業部落。周字的象形為水從上面流來,漫串于梯田中,正是江原濕坂的地勢水情,非常生動準確的表現。周人發祥于沼澤水田中還可以從《詩·鳧鹥》中得到證明(詳后文)。
江原的環境符合后稷,即周人的生存繁衍,而地處秦嶺之北的歧山周原?,那時已是旱地環境。中國南澇北旱的情況在新石器時期已出現:
應龍蓄水……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大荒北經》)
黃帝與蚩尤在翼州大戰時下魃止雨后不上,故北方不雨而旱。這是用神話詮釋旱象。
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海外北經》)
不足者,水少也,少水故渴,少水故旱。
應龍已殺蚩尤,又殺夸父,乃去南方處之,故南方多雨。(《大荒北經》)
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為應龍之狀,乃得大雨。(《大荒東經》)
旱魃在北方;應龍在南方,北旱而南澇。據此,依靠水田的部落怎能在歧山發祥?涉及渭水流域的《山海經》經文大約在《西次首經》《西次二經》《西次四經》,除《西次四經》外,前二經所有地方祭祀均不用糈或稻,說明此二經所歷之處不產水稻,《四經》祭祀雖用稻米,但僅記渭水受此經之水而不是渭水流經之地。《禹貢》、《史記》記大禹曾經治理過渭水,沒有言及開稻田,即使歧山下渭水河灘有少量稻田,也是后來“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之水以溉田”?乃是后來修渠引水而不是自由散漫的狀況。說不定正是后稷遷歧后開始的引水工程,因為他們畢竟長于水田耕作。但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如周字所形象記錄的自流漫灌梯田的情況。且“春夏干燥,少水時也。”?正在水稻生長時缺水。且歧之稷族“陟則在巘,復降在原”?在漆、杜時是生活在山上,后來下周原的(也許正是這個民族不習慣山居才下的周原)。余冠英先生釋此詩“乃埸乃疆”為田的界畔,而非攔水、貯水的田埂。埸疆為大界小界的劃分,與平疇水田以道路、田埂劃分有所不同。《詩經》中記錄周人歷史的篇章《生民》、《公劉》、《綿》等沒有見到有關水田勞作的形象,所以周人應該如《山海經》記載發祥于稷澤,后來遷往北方的。
江原地域今黑石河、文井江、出阝江沿岸,土地的耕熟程度大大高于其他地區,土壤呈黑褐色,腐植質相當多。《華陽國志·蜀志·江原縣》:“安漢上下、朱邑出好麻,黃潤細布,有羌筒盛。小亭有好稻田。”羌筒即當地羌人所制竹筒,用以盛布,今四川榮昌一帶猶有此俗。好稻田除緊鄰江原的廣都“江西有好稻田”(按廣都之江西原亦為江原地)。其他屬于成都平原蜀郡范圍內僅繁縣“有泉水稻田”。成都縣“新開稻田”。好稻田當然是耕熟程度高,作物產量高的水田,這說明江原的稻田開墾時間最早。秦取巴蜀“司馬錯率巴蜀眾十萬,大舶船萬艘,米六百萬斛,浮江伐楚。”“蕭何發蜀漢米萬船而給助軍糧。”?證明歷來蜀米產量之盛。沿江而下為沿岷江而下,因江原、廣都均在岷江邊,便于裝運。江原人有豐富的水稻栽培技術,加以土質好、自流灌溉,故產量高。其土壤非上千年耕作豈能達到這種程度?
《史記·周本紀》:后稷
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好種樹麻,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農耕,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焉。
按產麻之地《山海經》中只有一處,《漢書》云山東、廣東產麻,未及江原。而《華陽國志》記江原出好麻,織成的黃潤細布遠銷西亞,揚雄《蜀都賦》也說成都西部的麻布很不錯,這說明漢初江原的麻種植很發達。從周成王時“西戎貢火浣布”?,即用硫黃熏麻布始,直到20世紀中葉江原猶是如此,可以看到繼承后稷種麻的脈絡。
江原古城的考古發掘證明,4500年前已進入父系社會,邦國制初具雛形。出土的細石器、磨制石器不能用于狩獵,只能用于食品加工;小型陶器方便貯存和炊煮蹲鴟、稻米等植物性食物和飲水、飲酒……稻字的甲骨文、,“象米在器中”?,這個器是一支尖底、盤口或敞口、喇叭口的罐,尖底器成都十二橋遺址出土較多;現在的稻字,除開形意的禾字旁,應該是一支有蓋的小平底罐裝著米粒。這種盤口或敞口、平底的罐江原古城出土很多?,直到西漢仍是江原人的主要盛器,是此地當時稻作文明已較發達的有力證物。當前考古界公認陶器和磨制石器是農業生活的重要標識,江原那時除采集外已有較發達的畜牧養殖和出現作物栽培,筑城便是原始種、養殖業的一種重要設施。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比寶墩文化早一千多年,尚已成片栽種水稻,何況同在北緯30度線稍北的江原;能筑如此大城的居民!
再來看看后稷、沃民、大比、郪氏所在地域的情況,不妨詳細引用上面已提到過的《山海經》文:
帝俊生三身,三身生義均,義均是始為巧陲,是始作下民百巧。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孫始作牛耕,大比赤陰是始為國。禹、鯀是始布土,均定九州島。(《海內經》)
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靈壽實花,草木所聚。爰有百獸,相群爰處。此草也,冬夏不死。(《海內經》)
有沃民之國,沃民是處。沃之野,鳳鳥之卵是食,甘露是飲。凡其所欲,其味盡存。爰有甘華、甘柤、白柳、視肉、三騅、璇碧、瑤碧、白木、瑯玕、白丹、青丹、多銀鐵。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群是處,是謂沃之野。(《大荒西經》)
有西周之國,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帝降以百谷。稷之弟曰臺璽,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有赤國郪氏,有雙山。(《大荒西經》)
窮山在其北。此諸沃之野,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鳳凰卵,民食之,甘露,民飲之,所欲自從也。百獸相與群居。(《海外西經》)
(峚山)其上多丹木……黃花而赤實,其味如飴,食之不饑……丹木五歲,五色乃清,五味乃馨。(《西次三經》)
各條所述景象大致相同,俱在西經,所指地域前已討論過為江原。窮山即岷山已為各家認同,“窮山在其北”再次坐實描述的是江原。這里有姬姓西周之國,“國,人物之黨也。”?也就是姬姓姬族黨聚之地,當指后稷族所葬之地的江原古城。這里是一幅農業生活的和諧景象:食鳳凰卵者食雞蛋也,雞,民間戲稱鳳凰,今崇州、大邑猶是;雞蛋是此地居民喜尚的食物。百獸相與群處,狀家畜養殖發達;冬夏播琴?,草木所聚,靈壽實花,即可種植兩季,且植被蔥籠,果實豐熟,與今天金馬河西岸的種植時令、植被情況完全相同。此草也,冬夏不死,正是四季皆綠。其他前面已討論過,茲不贅述。值得注意的是“后稷葬焉”之地“爰有膏稻”等,再次證實周人起源于水田的觀點。而江原至今幾乎所有糧食作物均可在此生長,所以“后稷降以百谷”。
江原是我國農業起源地之一,《山海經》以后的文獻也能證實。
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務農(此與后稷發明農業似有矛盾,下面將予以討論),一號杜主。時朱提梁氏女游江原,宇悅之,納以為妃。(《華陽國志·蜀志》)
揚雄《蜀王本紀》略同:
望帝者,杜宇也,從天下。女子朱利,自江原井中出,為宇妻,遂王于蜀。(《水經注》引來敏《本蜀論》)
井者,市井也。朱利是市井里的居民;井,《周禮》中為千田,則朱利乃從事農田作業的女子,江原農業先于杜宇而存在。杜宇和蜀王開明一樣為氏族名,開明傳12世,如果杜宇也傳十余世,以最先稱王的杜宇推算,約生活在古城筑成后數百年,“教民務農”不是“播時百谷”,應該是繼承和發展江原農耕。朱利,大多數研究者認為是江原的農耕女神,可能是牧羊女的后裔?,從事鋤耕農業的女性。后稷族人的農耕以后不斷進化,所以有叔均代父輩播種百谷、始作牛耕的記載。叔均和杜宇一音之轉,會不會叔均即是杜宇呢?所謂代者,是原屬后稷、臺璽之事,后來一度停止,被其后裔重新開始呢?這些問題將在下面討論。
(三)江原的周人習俗
常璩根據《詩經·漢廣》及《毛詩注》,在《華陽國志·蜀志》的開篇便說:“在詩,文王之化被乎江漢之域;秦豳同詠,故有夏聲也。”無異于說蜀地包括江原在內周人影響甚大,并且有夏聲。由此可知在魏晉以前此地夏、周習俗之盛。時至今日江原尚有許多周人習俗,從中可以看到并非僅是文王之化,而是源于公劉之前的后稷族時代。
《詩經·公劉》:
止基乃基,爰眾爰有。
夾其皇澗,溯其過澗。
余冠英先生釋為夾澗而居和面澗而居。?這種擇居習慣一直在江原傳承。《文選·蜀都賦》:
于西則右挾岷江……爾乃邑居隱賑,夾江傍山。
成都之西、岷江之右,正是江原。南宋范成大《吳船錄·卷上》記蜀州:
人家悉有流渠修竹。
直到20世紀70年代,人們依然是傍水擇居。而在公劉時已“夾其皇澗”,可見此俗早已形成,應始于公劉之前,或即后稷時代。
民國時期,江原農村在農歷五、六月間,毎日巳到午時,婦女們給田間勞作的男人送酒食、烙餅(俗稱軟粑子),一路調笑。這種情景始見于《詩經·載芟》:
有嗿其馌,思媚其婦。
有依其士,有略其耜。
公元1987年在今崇州公議鄉境內發現的大型隋唐窯址中有大量用于給田間送酒飯的四系或雙系盤口罐,說明這種習俗數千年未曾中斷。到20世紀50年代前仍是如此。
江原農村筑土墻,用木板夾筑,場面、過程和《詩經·綿》里一模一樣。
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
筑之登登,削屨馮馮。
百堵皆興,鼛鼓弗勝。
江原地域喊父親為“伯伯”,不僅是血緣的含意,還包括《周禮》、《禮記》中“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男子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有年長、職能、為首等諸多含意,與喊爹、爸、父親略有不同。
江原人叫巨大的不知時代的山包、土墩、大墳冢為“生姬”,一說為“生基”,意為生命的根源、基礎。來源于靈魂不死的觀念,產生在秦漢以后。如果是這個含義,那么所有墳塋無論大小都應該叫“生基”而不僅是大墳,應該有另外的意義。聞一多先生《神話與詩·姜嫄履大人跡考》:“姬者,猶言足跡所生。”引《廣雅·釋言》:“姬,基也。”生基也即生姬。因此,所謂生姬,是說傳衍下來足跡所生的部落,指后稷之葬,即《山海經》中的“西周之國,姬姓。”《山海經》大部分成文于周初,時周天子統率各諸侯國,這里如果不是公劉以前的姬姓國,作者當不會如此記述。姬姓的后人不知“先王之所思,惟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故先王之葬,以葬于山林則合于山林;葬于阪濕則合于阪濕。此之謂愛人。”“堯葬于谷林,通樹之。舜葬于紀市,不復其肆。禹葬于會稽,不變人徒。”害怕被發掘受辱,所以“不封不樹”。這些先王的葬地沒有任何標記,今天的考古調查也未發現。其實這是原始社會的葬俗,并且所謂誰葬那里,很有可能是指其領導的部落的葬地。秦漢以后的百姓們以當時富貴人家的葬俗,來揣度史籍記載的后稷這樣的祖先應該有高墳大冢,但又不知具體位置,所以把大土墩、土臺、小山都叫生姬了。
如果說上述習俗其他地方偶爾還有一、二種,并非江原特有的話,那么過年包粽子、十月蒸醪糟就是江原獨有的源于公劉以前的習俗。
吃粽子,歷來被認為是紀念屈原,端午節投粽于水以免蛟龍吃掉愛國詩人的香軀,江原周邊的成都、眉山、雅安等地都在端午食粽,顯然是緣于楚地的風俗。而在今崇州、大邑、都江堰、新津等地,人們至今沿習在農歷歲末和春節吃粽子,這是源于《詩經·生民》里記述的以米飯作祭品的習俗。
誕我祀如何?
或舂或揄,或簸或揉。
釋之溲溲,蒸之浮浮。
載詩載帷,取蕭祭脂,取羝以軷。
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
后稷肇祀。
舂出米,淘米蒸成飯,盛在豆里,發出香味作為祭品……與江原人歲末淘米包成粽子、煮熟供于神龕或餐桌,向祖先跪拜后方食用一模一樣。詩中的“以興嗣歲”分明就是說從頭年開始到第二年,和今天江原歲末包粽子吃到次年春節完全一致。粽,與宗字同源,有“宗”的含意,“宗周”,即繼承后稷開始的這種祭祀,即“后稷肇祀”。不說古公亶父、不說公劉,標明此習俗源于發明水稻栽培的后稷,而非文王之化。粽葉包裹煮出的米飯有一種特別的香味,“其香始升”說不定那時包裹的正是江原周邊低山丘陵、澤中陸地大量生長的粽葉。用米飯祭祖先平時也是,筆者幼年每天早晨將兩個小酒杯合成的米飯團,敬置于堂屋神龕上給祖先神位燒香磕頭,和《西次三經》:“其祠之禮,用一吉玉瘞,糈用稷米。”以及《淮南子·泛論訓》:“周人祭于日出以朝”是完全吻合的。民國時期,即使并不十分富裕的人家,安葬親人同時瘞玉,也是繼承那時的習俗。
周人尚醴,《詩經·載芟》、《周禮·酒正》、《儀禮·士喪禮》、《禮記·郊特牲·王制》等記載,周人祭祀進獻醴。醴是用秫米釀的甜酒。秫米即糯米,江原人稱為酒米,專用于釀醴,發酵后濾渣叫甜酒;不濾渣即煮食叫醪醩,也在每年冬初釀造。
享廟之際,冬曰烝。(《禮記·王制》)
是月也,大飲烝。(《禮記·月令》)
十月醪醩子。(江原諺語)
十月是釀醴祭祀之月,按周歷十月為歲末;今江原于十月蒸醪醩,吃到過年,時令古今不悖。烝,進獻。江原此俗有傳承脈絡。《劍南詩稿》中《野飯》、《湖上晚歸》:“時能喚鄰里,小甕酒新漉。”“碩果畦丁獻,芳醪稚子斟。”新漉,剛濾出的。寫上二詩時陸游正在蜀州任上。清代乾隆時,《崇慶州志》載知州林良銓詩《蜀州》:“庭多圍綠竹,家盡釀春醅。”春醅,備吃至春天的醪醩。……
江原還有不少周人風俗,如“既種既戒,去其螟螣,去其蟊賊,無害我田稚……秉畀炎火。”,其實就是上世紀初農民還在使用的燒雜草和稻谷樁頭以消滅害蟲;“文王嗜菖蒲菹。”即今崇州人用菖蒲草漚豆豉;以及過年殺年豬祭社及祖先等等……
為什么江原流傳這么多周人風俗,且有不少為江原獨傳,難道全是周朝的統治者提倡和推行?如果是,其他周人直接管轄的地區為何反少這些習俗?而蜀國僅和周朝關系較好而已。風俗是約定俗成,需經過較長時間蘊釀和積淀。原始祭祀產生于生產、生活;產生于與自然的斗爭中,而不是某某人強制推行,況在夏、商時蜀乃獨立國家,即在周時也非直接從屬于周,自有其生活、生產習俗,文王之化怕也不能達到此地。江原的這些風俗乃產生于后稷族人栽培稻谷的生產活動中,從后稷時一代代傳下來,所謂“后稷肇祀”。
東漢應邵《風俗通義·祀典第八》:
未之神為稷,故以癸未日祠稷于西南。
先秦時西南一帶的人們每祭祀總是朝祖先發祥的方向,三星堆的祭祀坑朝向西北龍門山,就是他們的祖先從龍門山下到川西平原之故。西南是江原人尚滋味的方位,也是后稷發祥的稷澤所在方位,祠稷于西南者不忘故土也。這說明至遲在東漢,還有人依稀記得后稷族的誕生處。而在江原,至遲在清代還有人知道此地遺存周人習俗。乾隆時桐江人顧堯峰任崇慶州知州,修《州志》時在《風俗》章中說:“州民以農為務,勤勞隴畔,不稍懈惰,有豳、岐遺風”可證。
三 “舍潛于歧”
(一)“舍潛于歧”解
雅安博物館陳列蘆山東漢《樊敏碑》:
肇祖伏羲,遺苗后稷,為堯種樹,舍潛于歧。天顧亶父,乃萌昌、發……君贊其緒,華南西畺。濱近圣禹,飲汶茹(氵防)。
按樊敏(119—203)為雅安蘆山人,曾任巴郡太守。蘆山與古江原縣接壤。據碑文記述是濱近圣禹,飲汶茹(氵防)的后稷后人。這就是說后稷族后裔鄰禹出生地,飲汶江,即岷江水,是后稷族在江原的另一佐證。姑且不論后稷是否為伏羲的后代(其母為伏羲族,見前述),不過該碑言后稷“為堯種樹,舍潛于歧。”卻頗值得玩味。
后稷為堯、舜、禹時的農官名,載諸先秦典籍:
稷隆播谷,農殖嘉谷。之后成功,維假于民。(《墨子·尚賢》)
得后稷,五谷殖。(《荀子·成相》)
秦以后的典籍中更多: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谷。(《尚書·舜典》)
暨稷播,奏庶鮮食。(《尚書·益稷》)
堯舉棄為農師。(《史記·五帝本紀》)
而稷也沒有辜負對他的信任:
相地之宜,宜種谷者稼穡焉。
天下得其利。(《史記·五帝本紀》)
據司馬遷記載,后稷“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是說后稷一族的首領自堯始相繼為農官且有功德,若是一人何能歷數代?這一族人善于農耕,有豐富的栽培經驗和技術,所以歷有“令德”,到帝舜時才“封棄于邰”。馬骕《繹史》:“35世以后為稷,佐堯有功,被封為稷。”是因為這一族有播百谷的特長到35世以后才封為主管農業栽培的。這族人的特長如何形成,在被封之前35世之久在何處活動,雖然史籍語焉不詳,而我們已討論過應在江原。先讓我們來研究“舍潛于歧”,歧即歧山,在渭水北岸的周原,即邰。被舍之“潛”在何處呢?
按,潛,即潛水。《禹貢》記有兩處,一在荊及衡陽:“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一在華陽黑水之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績”。具體位置諸說不一。《爾雅·釋水》鄭注:“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孔穎達《尚書正義》:“此則解荊州之沱潛發源于此州。”和梁州沱潛了不相干。周秉鈞注《尚書》采鄭說,也失梁州之潛。《史記·索隱》認為“潛出漢中安陽縣西,北入漢。”《正義》引《括地志》云:“潛水一名復水,今名龍門水,源出利州綿谷縣東龍門山大石穴下也。”《史記·集解》引孔安國疏則把禹貢荊、梁二州之沱、潛合為一,認為均“源于此州,入荊州。”《漢書·地理志》云:“今蜀郡郫縣江沱、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于此出。江原有壽阝江,首出江,南至犍為武陽入江,豈沱之類。”說壽阝江與《禹貢》沱水相類,言外之意即潛水或江原亦有水類潛。而孔穎達認為孔安國為武帝博士,不容不知《漢書·地理志》的內容,所說“沱出于江、潛出于漢”“入于荊州”是正確的。孔穎達是孔安國后裔,姑不說是否有維護祖先之嫌,二水既源于梁州均南流入江經巴郡入湖北,是江入荊州而非沱潛入荊州。孔穎達又疏《禹貢》荊州“浮于江、沱、潛、漢”云“浮此四水乃得至洛。”顯然與梁州無涉。對于《禹貢》二州皆有沱、潛,如何解決方位上的矛盾?孔穎達對源于梁、入于荊之說也不滿意,所以他又說:“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這樣名沱潛的江河更多,具體在何處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反而更混亂了。按,枝江、潛江在今湖北中部,荊州市東面,長江中游,與岷、嶓了不相涉。梁州之沱、潛應“濱近圣禹,飲汶茹(氵防)。”胡太玉《破譯《山海經》認為(氵防)即今什邡,姑備考。但與岷山(汶山)岷江(汶江)相近是明白的。就《尚書》所記應在岷、嶓山下,與蔡山(今雅安周公山)蒙山(今雅安蒙頂山)同一地域,可以肯定這個潛水在岷江附近,《地理志》所說壽阝江,近似,蓋壽阝江出于湔江,至武陽又入于湔江,湔、潛一音之轉,湔、灒同音;灒、潛同音。《集韻》:灒,財仙切,音潛。”潛為灒的壞文。許慎《說文》:“潛,涉水也、游也。”《揚子方言》:“灒,污陷也;一曰水中人。”二字同義,所以《康熙字典》又說“灒,亦作淺、湔、濺。”潛和湔乃同音義,潛水即湔江,否則《禹貢》何以同名迭出而不同地域。再則,與沱水并舉,梁州之沱在今四川綿陽,北往南流,與荊州之沱西北往東南流方向差很多。梁州與沱相鄰之潛也北往南流,故潛為湔江或其支流壽阝江,指江水(即岷江)都江堰到新津這一段,即今天的金馬河,與“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合。按岷江源出龍門山北之松潘,《說文》:“湔水出蜀郡綿虒玉壘山。”玉壘山在都江堰。《漢書·地理志》:“蜀郡有湔道,岷山在西郊外,江水所出矣。”《華陽國志·蜀志》記岷江上的都江堰叫湔埝。《水經注》:“江水歷氐道縣北,湔水入焉。”按《說文》和《水經注》似應為岷江支流壽阝江。無論支流正流,湔堰以下都指岷江西岸,正是后稷族人所居之稷澤,這就符合該族人的“舍潛于歧”,從岷江西岸遷往北方,去“為堯種樹”了。樊敏東漢時住蘆山,則可能是稷族留居者或又從北方遷回蜀地了。據雅安博物館《漢故領校巴郡太守樊府君碑記》:“楚漢之際,或居于楚、或集于梁,君贊其緒,華南西疆。”稷的后人散居楚、梁,而樊敏則“贊”祖先之“緒”,住在江原緊鄰之“華南西疆”的蘆山。華南西疆即華山之南面的西部,應指蘆山。這就是說東漢時后稷族的后裔還在江原附近“贊”后稷之“緒”。
那么,除了稷族“為堯種樹”而北遷以外,文獻中有沒有關于北遷比較直接的記述呢?我們注意到《史記·周本紀》有引穆王時祭公謀父說稷之子不窋自竄戎狄之間的記述,而朱熹《詩集傳·豳風》中有比較詳細的轉述:
虞夏之際,棄為后稷而封于邰。乃夏之衰,棄稷不務,棄子不窋失其官守,而自竄于戎狄之間,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復修后稷之業……
這里有幾點需要指出:
1.自竄于戎狄之間分明是遷徙,雖然沒有說從何處竄走。
2.遷徙時間在后稷封邰之后,遷徙后幾代才出公劉。
3.遷徙的原因是失其官守,但不知是何官又為何棄(這里作放棄解而非人名)稷(這里作稼穡解)不務。
4.不窋自竄之前并不住在北方,住在何處?
這里的戎狄當然包括峚山的羌氐等西戎在內。這里的夏之衰,《史記集解》韋昭注“夏之衰”為“太康失國,廢稷之官。”如果是太康廢農官,何以不窋反而遷往稷之封地至后代復修其業?而稷族與夏之關系密切,怎能棄稷不務?這種解釋是有問題的。如果不窋或稷族因其他原因在稷澤站不住腳(失其官守,或夏人失國)而從岷江西岸往北方(他們的首領所封之地)沿龍門山東西麓,經西戎的地域到達或接近北狄所住的地方,這似乎更加合理。
沿這條路線遷徙的不僅后稷族人,姜嫄族也一同北遷。他們先是遷至渭水南岸,今姜水上游(可能在那里定居后才名姜水)。后又沿渭河南岸,再越渭水進入周原。而后稷族也經歷了從漆到杜的過程。郭沫若先生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曾說:“《詩經·大雅·綿》和《生民》把傳說的原始性保存得很濃厚……還可以看出一個原始社會的遠景。”這遠景可能遠在后稷前。郭沫若先生還說周人是善于遷徙、不斷遷徙的民族,所以后稷被禹任命負責遷徙:“食少,調有余補不足,徙居。”把相對密集的人口遷徙到生活資源豐富或未被開發的地方。
后稷族人北遷后的一系列行為也說明他們是從岷江西岸遷來的。
前引《風俗通義》周人祠后稷于西南就像三星堆人祭祀坑朝向西北一樣,是懷念祖先的發祥地,同時也反映兩地同一風俗,方向不同但指向一致,同風俗也可能是同族源。
《詩·大雅·鳧鹥》編在“生民之什”,此“什”均為周人祭祀祖先的祭詩。《鳧鹥》是祭祀后稷的。前面說過《山海經》最早的篇章寫成之前,我國南澇北旱的情況已經形成,已演變為“應龍”、“旱魃”的神話。而《鳧鹥》的背景卻儼然是江南水鄉:“鳧鹥在涇”“在沙”“在渚”“在潨”“在亹”,不能籠統地釋為在山邊,何況“亹”也不是山。
涇,《莊子·秋水》:“流之大。”注云:“通也,謂通流也。”《集韻》:“泉也,挺直流也。”
沙,《說文》:“水散石也,水少沙見。”《爾雅·釋水》:“穎為沙。”注云:“大水溢出,別為小水。”
渚,《爾雅》:“小洲曰渚。水中可居曰洲。”《釋名》:“遮也,能遮水使旁回。”“聚也,人及鳥物所聚之所。”《詩集傳》:“小歧曰渚。”《韓詩外傳》:“一溢一否曰渚。”
潨,《說文》:“小水入大水。”《詩集傳》:“水匯也。”
亹,《詩集傳》:“水流峽中,兩岸對出入門也。”
綜合上述水情地貌,大小水分分合合,水流散漫,有洲有沙,有水從兩山間流出,完全是文井江出山后,稷澤的地貌。可以肯定《鳧鹥》詩的背景是沸沸湯湯的沼澤。鳧翳是捕食魚類的鳥,應該就是蜀人魚鳧族的圖騰,魚鳧的時代大致在夏中期到商中期,三星堆出土有大量魚鷹嘴的銅器,蜀民早在新石器時期就以捕魚鳥為圖騰。《鳧鹥》中說明周人的生活與魚有密切的關系,這不由想到秦漢時江原“民食稻魚。”。可以從詩里看到,在祭祀的舞蹈中有裝扮成鳧鹥的巫(神尸),而詩是一首祝辭,活動是他們記憶中西南故鄉的場景。
1975年,陜西省寶雞市茹家莊發現魚國墓葬,出土敞口尖底器和握圈小銅人。葬俗和陶器與四川新繁、金堂墓葬相同;青銅人和三星堆青銅人相同。地處江原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寶墩文化中喇叭口、侈口器占絕大部份,有許多尖底。寶雞市博物館羅連成先生推測,魚國人早年翻越秦嶺來到渭水南岸的清江河邊,后來成為西周的諸侯國。早年到什么時候,從陶器分析應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為什么周人會分封?魚國應該是姬姓或姜姓,為后稷或姜嫄的后裔,或是江原某一隨后稷、姜嫄“舍潛于歧”的部落。
大量材料表明,周人和蜀的關系至為密切,“武王伐紂,蜀與焉。”《逸周書》、《繹史·年表》等記西蜀羌人在周建立王朝以后多次主動入貢,并非僅僅因為殷人曾經歧視和打壓蜀人,還有深沉的族屬淵源在內。
后稷族人除北遷外,有一部分是南遷了的,也有少數人留下來或移居巴地,前引《樊敏碑》有“君贊其緒,華南西疆。”“或居于楚,或集于梁。”便是他們祖先原來飲于岷江,后遷徙各處的證明。而留在稷澤的少數人與新占領該地的炎帝族融合、同化,很可能便是朱利族的祖先。
(二)南方去來
南遷的人們沿著他們長期以來非常熟悉的橫斷山脈雅礱江河谷到達今西昌、云南一帶成為淑士國或淑士族。徐南洲先生認為淑士族的杜宇是從南遷來江原的,與一般學者認為杜宇族是從岷江上游山區下來的氐羌支裔不同。我認為兩者并不矛盾,因為下山和南遷在時間上有先后,實際情況是從岷山下來的羌和氐的支裔——后稷族在南遷后又回到故土。
前面引用過的《山海經》中有關牛耕的叔均即杜宇,其證有五:
1.叔與杜同為雙聲疊韻,同在魚部,都為定母,音近可通。宇,大也,王力《同源字典》:“宇、芋、竽,曉匣旁紐。”同為大的意思。《廣雅·釋詁》及《方言十二》均謂:“宇,大也。”《爾雅·釋詁》:“宇,大也。”《呂氏春秋》注:“竽,笙之大者。”均,《說文》:“平,徧也。”徧,即遍。可作大解。“徧,幣也,周也,周盛貌。”均可訓為周。江原地勢較平坦寬闊,大量出產蹲鴟,即芋。《說文》:“芋,大葉實根駭人。”與杜宇生活、活動在江原的環境若合,宇、均(周)二字同與生活環境有關。
2.叔均為稷的后人,一作孫或曾孫,《大荒西經》作侄,我認為孫和侄都不一定是具體的輩份,應理解為其族后代。周人的圖騰為杜鵑,《說文》:“嶲,周燕也,從佳,屮象其冠也,冏聲。一曰蜀王望帝淫其相妻,慚,亡去,為子嶲鳥。故蜀人聞子嶲,皆起曰是望帝也。”子嶲即杜鵑。人死怎能化為杜鵑?杜鵑實為杜宇族的圖騰,與周人之燕同為一鳥。杜宇、后稷皆在江原發明、發展農業,故江原人至今認為杜鵑叫聲為“割麥插禾”。無論杜鵑、周燕都是農耕族的圖騰鳥。叔均與杜宇是同圖騰的周人后裔
3.《大荒西經》:
有國名淑士……顓頊之子。有神十人,名曰女媧之腸,化為神,處栗廣之野,橫道而處。有人名曰石夷……
淑士與后稷均出黃帝、顓頊。徐南洲先生認為淑士即朱提,王文才先生認為朱提即朱亭,在今崇州;朱提即朱堤,丹水邊的城,即江原史前古城。徐先生還說栗廣之野在今涼山州,石夷即杜宇族。叔均疑即淑士族的首領,只有這樣才能解疑兩個朱提的聯系。也有不少學者認為栗廣之野即都廣之野,若此,更能證明叔均即杜宇,為后稷族人。淑士即叔均,士可訓為君,君均同音;士、君同為對男子的尊稱。
4.叔均和杜宇同為發展后稷之“播百谷”者。降或播百谷,是變野生為人工栽培。二人同是將鋤耕農業改革為牛耕者,叔均之事具載經中,杜宇“教民務農”則應該是變鋤耕為牛耕。因后稷早已發明種植,江原古城的出土文物也證明4300年前已有農業,為何遲到公元前1000年上下的杜宇時代才教民務農?因江原原住民仍為鋤耕。朱利的利字,甲骨文象一女子用耒翻土,象征鋤耕農業,而杜宇“以汶山為畜牧,南中為園苑。”說明畜牧業已相當發達,只有在畜牧業高度發達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出現牛耕。叔均的“始作牛耕”也就是“以汶山為畜牧”的成果。“牧”,管理、驅使,包含“牛耕”的內容。杜宇也即是“始作牛耕”的叔均,否則他來“教民務農”便多此一舉。正因為他變鋤耕為牛耕,大大節省人工,提高了生產力,所以被原住朱利族人接受,進而通婚,這是《蜀王本紀》等關于江原杜宇和朱利的歷史情況。
5.叔均代后稷播百谷當在稷澤,否則不應叫代而應名創,至少隔數代以后又才在這里恢復其柤上的事業;杜宇的主要活動也在江原,揚雄《蜀王本紀》:
梁氏女名利,從江原井中出,帝悅之,納以為妃。
井者,千畝田也;或指市井,可能為某座古城。無論大片農田還是某座城,足見江原農業發展,需要牛耕。
各種版本的《山海經》都記叔均“代”臺璽和后稷播百谷,換言之,播百谷本來是其先人的事。為什么由叔均代呢?應該是先人因為什么原因不再播了、中斷放棄了。繼而說代,其間可能存在一個沒有播的時段,那就是后稷族遷走以后,叔均(杜宇)返鄉之前。
關于蜀人南遷的記載還有文獻佐證。《史記正義》引《譜記》:“蠶叢國破,子孫居姚嶲等處。”四川歷史上的蠶叢國破時代約在禹末至夏代前期,是否就是古城居民南遷到姚州(今云南姚安)、嶲州(今四川西昌)呢?有可能,因為時代基本吻合。而徐南洲之說更可以證明蜀人南遷后又返回川西。今天殘存的彝文古文獻中不少關于蜀和與蜀交流的記載也可從中獲得蜀人遷徙和返回的信息。
杜宇族為什么又回到稷澤呢?
我們知道,農耕和自然氣候、天文地理關系密切,農耕往往伴隨對自然認識的發展,從而出現原始的天文知識和傳奇性的天文人物。后稷之父帝俊,也即帝嚳的妻子常羲“生十二月”;羲和“生十日”。常羲和羲和,據《破譯“山海經”》考證:“帝俊妻其實就是赤國郪氏。”也就是前文分析的江原姜嫄。現在比較一致的說法“生十二月”就是發明以十二月為太陽周期的歷法;掌握春夏秋冬四時季節。江原地域的居民有當時先進的天文知識,姜嫄族是掌握不少天文知識的部族,而后稷族的農業活動須由天文知識輔佐,這可能是后稷和姜嫄通婚,后來同時遷徙,關系很好的重要原因之一。《破譯“山海經”》認為當時有不少天文“觀察站”。徐南洲先生在《古巴蜀與“山海經”》中考證,都江堰的天彭闕、什邡的土門子等就是杜宇族使用過的觀象站。且不說都江堰有一大部分屬古江原,今大邑、崇州也有類似的觀象站。清《嘉慶崇慶州志》:“百家門在州西八十里,旁兩山峙立,上闔下開,門內二里有天生橋。”這個“百”字疑為“白”字之訛,因為這里自古住著羌人,白為羌人崇尙的顏色。天彭闕也為“兩山相對,古謂之天彭門。”徐先生認為:“應該是古蜀國社會農業、牧業生產發展到要求準確地測定四時,蠶叢部落用來觀測季節的一種工具。是后世‘土圭’的原型。”“如門、如闕,相互對立,都有山與地面相交成直角的涵義。”“土圭形制的每一個條件,莫不具備。”土圭是古代用以定方位、測日影、定季節的天文設施。《民國崇慶縣志》把這種土門的作用說得更明白:“懷遠楓香嘴,由崇達大邑之孔道也,舊志兩山夾峙,上有古楓高數十丈,古根盤屈似斗魁之象。”兩山夾峙為土圭;根似斗魁是巧合還是人為?如果是人為,那么后人曾在這里建造天文設施觀測并記錄天象;據考古調查,這個孔道有明顯的開鑿痕跡,是上古先人有意建造的“土圭”。周代,靈王用蜀人萇弘“執周室之數”,漢代,閬中落下閎在長安制定歷法,蜀人有天文氣象的優秀傳統。后稷族的后人知道故鄉的天文水平、有較完善的天文氣象觀測設施,而這些在云南、西昌的淑士國是不具備的。
后稷族后裔南遷后大概感到許多不便,首先是沒有農業生產非常便利的濕阪;沒有僅靠野生便能生活的植物資源,如使“民至死不饑”的蹲鴟及魚蚌等,從而無法抗拒自然災害使農業欠收帶來的饑荒;也缺乏觀察天象掌握季節的土門、土臺、山峰、垣口;再就是離開故土念念不忘祖先的發祥地。他們把杜鵑鳥的叫聲“催歸”諧為“不如歸去”便是這種感情的反映。因此,當稷澤社會安定、環境適宜生存后,他們又沿著熟悉的路線回到江原,重新在后稷族播百谷的土地上從事耕種,所以經文稱為“代”。并且由于畜牧業的發展;水田和無根山丘陵地的開墾,促使耕作技術產生變革,以牛耕代替鋤耕,這應該就是從播百谷到始作牛耕的大概過程。
但是,當時文井江等沒有主河道,淫雨之際,低洼處形成大片冬水田,當牛耕越來越廣泛應用時這種環境便嚴重制約了耕田的擴大,杜宇族不能不考慮,所以他們便向岷江東岸發展,這從史籍中可以看到。《華陽國志·蜀志》:“時朱提梁氏女游江原,宇悅之,納以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劉琳注謂郫邑在今郫縣城北二里;瞿上,劉注引羅蘋注《路史·前紀》:“在今雙流縣南十八里”。新津縣文化館李澄波考證在今新津與雙流交界處之牧馬山蠶叢祠九倒拐一帶。《華陽國志》又云:“江原縣……小亭有好稻田。”“廣都縣……江西有好稻田。”“繁縣……有泉水稻田。”繁縣即今新都新繁。好稻田者,耕熟程度很高之謂。泉水稻田者將就泉水凼草創之田也。后二處稻田未著開于何時,到漢代成都縣還“開稻田百頃”,可見前述之稻田開墾于漢以前。“移治郫邑”“或瞿上”可能是去“教民務農”“治農業”,或那里有待開發的資源,否則江原這么好的條件為什么要移去?這里,常志的記載有一個明顯的傳播脈絡,杜宇族的稻作農業由江西、江原發展到成都之北及成都本治,其原因是牛耕以后,江原的可耕地已無法滿足高度發展的生產力。
杜宇族從南方遷回以后,不知什么原因大多數人沒有住在古城里,而是選擇了無根山麓的坡地和文井江岸的臺地和土墩,“從井中出”也可說明居民不住古城可能是因為耕地增加,集中居住不便至較遠的田里耕作,因此就近住在耕地附近的高處,才有朱利出于千田之說。按《晉書·地理志》“畝三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八百八十畝”,“井”是一個小聚落或小村子。城里的居民因此大大減少,所以沒有留下什么遺物遺跡。而進入廣漢、繁縣一帶的杜宇族和那里原住居民一同創造了燦爛的三星堆文化。
南遷的后稷族人有部分留在當地,所以他們的墓葬與岷江上游有相同的文化內容;據徐南洲先生對景頗族的研究,該族說他們的祖先發源于蜀,其傳說的農業生產情況與古蜀相同,既然是源于,當先在蜀而后至云南。從上面的分析可知徐先生所說杜宇來自云南或應為自云南返鄉。
(三)遷徙原因試說
在新石器時代晚期,人們為追逐、占有、掠奪生活資源和優越的自然環境而主動遷徙,因洪澇、干旱、地震、戰爭而被動遷徙。江原古城的人們是否可能因洪水往北遷至相對干旱的漆、杜呢?
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為田祖。魃時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決通溝瀆。(《大荒北經》)
這段經文似乎也說叔均逐旱魃、通溝洫,有抗旱防澇的意思,但無洪水泛濫之說;對江原數座古城的考古試掘也沒有發現足以使居民放棄優越環境的洪水跡象;從《山海經》中對這片地域的描述,更不存在環境惡化的問題。但是,優越的環境和豐富的資源卻會招致旨在掠奪、占領的戰爭,或許這正是古城居民大規模遷徙的主要原因。那么,這里是否發生過戰爭,能不能考察出戰爭的一些情形呢?
晁福林在《天玄地黃》中說:“我國西南地區可能是人類發祥地之一。”“黃帝、炎帝、堯、舜等都是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人物。作為部落酋長,他們在歷史舞臺上縱橫馳騁,創造了光輝史冊的豐功偉績。”恩格斯說過,在新石器時代后期,人的惡欲,包括權勢欲,就已經登上舞臺。因此引發戰爭的因素還包括爭奪部落或部落聯盟的統治地位。除了族屬之間,還有族屬內部的部落之間的斗爭。在江原古城的時期,除了炎黃之爭,還有各自內部之爭。四川,尤其是川西是上古民族活動的主要地區,《山海經》中無論以今河南、湖北為中心座標的《山經》;以荊楚、巴蜀為中心座標的《海內經》,以及海外、大荒二經中都記西部的內容為多,有許多人們在成都平原及川西北活動的記錄,當然應該包含有戰爭情況。我們來看:
祝融降處江水,生共工,共工生術器,術器首方顛,是復土壤,以處江水。(《海內經》)
值得注意的是祝融降處江水的時代、世系與不窋自竄北方竟是那樣吻合。前引《史記·周本紀》、《索隱》引《國語》及祭公謀父語均認為不窋乃后稷之子,正因其不任農官所以在最后一代后稷之后不名稷而改稱不窋。按馬骕《繹史》世系圖,神農和黃帝同出于少典氏,是同時代的兩大部落聯盟。祝融為神農后裔,從神農歷八代而至祝融;而不窋為黃帝后裔,至不窋歷七代。相差一代可能與稷族首領任農官是數代而只計后稷為一世有關,或傳衍年代不相等而差一代。即使按《繹史》的說法不窋為孫輩,其上一世為叔均,而叔均的部落也是遷徙了的,且世序也和祝融、共工降處江水的時代大致吻合。由此有理由得出結論:在祝融族的武力壓迫下,后稷族的子孫不窋、叔均的部落分別南北遷徙了的。
爭奪川西的戰爭并非始于后稷時,處在若水的顓頊“與共工爭為帝”其戰場可能延及江原。
有池名孟翼攻顓頊之池。(《大荒西經》)
根據諸家注釋和近世研究,都認為戰場約在今茂、汶至雅安之間,中途為江原地域、稷澤池沼。前引“降”字同樣含從上到下的意思,和今天對該字多種釋義一致,即共工族從茂汶山上下來與顓頊之子孫后稷族人在江原作戰,這是另一證據。共工與顓頊之爭歷來認為是炎黃之爭;一說共工出于少,而少皞是后稷父帝嚳之祖,這樣,則祝融、共工“降處江水”乃黃帝系的兩個部落爭奪江原。
共工族占領江原后,禹族曾經發動過驅趕共工的戰爭。禹族和后稷族有地緣上的親密關系,據先秦大量史料來看,兩個族屬的友好程度非比尋常。禹族不僅長于治水,也善于征伐,其討三苗、伐共工是史籍保存的兩大戰爭,其中伐共工便與江原有關。
有山而不合,名不周負子。有禹攻共工國山。(《大荒西經》)
西北方曰不周山,曰幽都之門。(《淮南子·地形訓》)
又西北370里,曰不周山。(《西次三經》按,此條之下即是“峚山”。)
這樣,由荊楚為座標,可以確定共工頭撞之不周山在西北,與峚山相鄰。如以淮南子所說幽都之門為座標,則今江原附近之山近似(詳后文)。禹攻共工國山,徐南洲先生認為攻乃伐木,但不能包含攻伐的全意,應仍以征討解釋,因其山在共工國,共工國以占領者命名,如不征服其國,怎能去砍伐其國的樹木?禹和共工的戰爭是在峚山附近進行的“反侵略”戰爭。
川西南的雅安從古流傳許多女媧、大禹的傳說。周公山原名蔡山,即《禹貢》“蔡蒙旅平”之蔡山,“旅平”不僅為修治道路,也指用軍旅平復。周公山是否即不周山之訛,不能臆測。但雅安自古稱天漏,李泰《括地志》說雅州有漏天;祝穆《方輿勝覽》引《梁益記》:“大、小漏天在雅州西北,山高谷深,沉晦多雨。”雅安至今叫雨城。而“名山有蓋天寺,女媧補天續缺之處。”這與共工與顓頊之戰戰敗撞不周山、天缺漏雨、女媧煉石補續的神話完全是巧合嗎?聞一多先生及許多學者認為女媧這個人物其實是各個民族都有的,她代表母系社會的部落首領,是婦女為生活、生產的主力的反映。有的學者認為其用蘆灰湮水、煉石補天,其實是用堵塞和疏導(炸開巖石)的方法治水。從《山海經》經文看,應該是禹與共工戰爭后的災后重建。
有鐘山者,有女子衣青衣,名赤水女子獻。(《大荒北經》)
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黃帝……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大荒北經》)
吳承志認為赤水女子獻即黃帝女魃,袁珂先生從此說。鐘山,《西次三經》也有,緊接峚山之后,按地望在今雅安蘆山一帶。女魃是戰勝澇災的英雄,衣青衣。雅安青衣江上游在三千年前就住著青衣羌,女魃疑即青衣羌人的部落首領帶領人民與淫雨澇災作斗爭者,女魃是她們的女媧。而“振滔洪水”的共工戰敗后留下的創傷是由她們的女媧來補的,這應該是撞不周山和補天的歷史影子。
這里還有一則經文值得注意。
有氐人之國……有魚偏枯,名曰魚婦,顓頊死即復蘇。風道北來,天乃大水泉,蛇乃化為魚,是為魚婦。顓頊死即復蘇。(《大荒西經》)
根據經文,顓頊處在若水,為黃帝的嫡裔。這里的“風道北來,天乃大水泉”和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一致。水泉怎么會使名叫魚婦的、由蛇化成的魚偏枯呢,偏枯者是指部分萎死、部分被破壞,應是指戰爭創傷;死即復蘇,即災后重建。蛇是黃帝族的圖騰,也即后來夏民族的龍。結合雅安關于黃帝下女魃止雨、女媧補天,以及氐人國在岷江西岸、禹和顓頊同出黃帝等諸多材料,可以推測在夏代初年江原曾經歷過一段黃帝族和共工族爭戰的歲月,是古城居民遷徙的主要原因,也就是不窋棄稷不務的原因。禹族攻下共工以后,可能有的人留居下來,留下諸如祭器和葬具內紅外黑、用竹編籠紐石等等夏人習俗,直到公元20世紀前半葉還流行,所以《華陽國志》說“兼有夏聲”也。
結語
新石器時代后期是一個巨大的歷史舞臺,在這個舞臺上上演著各種活劇、進行著各種斗爭。以六座古城為座標的江原地域是這個舞臺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從考古發現和《山海經》等一系列材料的研究,可以清淅地看到,在4500年前上下,這里水草豐沛、動植物繁盛。人們在這里捕魚采芋、筑城防水,創造了長江上游的稻作文明,發明、發展了畜牧業。這里住著炎、黃兩個世系的民族,部落間相互通婚。姜嫄族以擅長的天文知識和畜牧,后稷族人以他們豐富的種植技術,禹族人以他們高明的治水經驗等發祥在稷澤、峚山,并在加入中原部落聯盟后發揮著各自的特長,接受封地后部分北遷,居住于邰和姜水。人口不多的周人由公劉等幾經遷徙,發展到文王時的數百人,仍然懷念西南故土。后稷族的子孫在祝融族的武力壓迫下繼續北遷、部分南遷。南遷的人有的停留于今雅安一帶,后來成為青衣羌或融入當地青衣羌。在禹族攻伐共工族后,南遷的后稷族人返回稷澤并開始牛耕,逐漸使江原成為富庶的魚米之鄉,并由此拉開了有文字記述的歷史序幕。而和南方的交流一直傳承下來,后來這個地區相對獨立的另一族屬笮人,仍然沿襲著這種交流。留在雅安的與惡劣的自然氣候作斗爭,很快復蘇了深受戰爭創傷的部族,至今留下動人的傳說。
注釋:
①即金馬河《山海經》中所說的江水上游。
②上海辭書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第6頁。
③徐南洲著《古巴蜀與山海經·鯀何所營,禹何所成。》四川出版集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第102頁。
④袁珂:《復馮天瑜的來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上古神話縱橫談》第3頁。
⑤⑨⑩袁珂:《山海經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月第1版第454頁;184頁;38頁。
⑥《史記·六國年表》。中華書局1982年11月第2版第49頁。
⑦《吳越春秋》卷6,岳麓書社1998年8月第1版,第120頁;《元和郡縣圖志·劍南道(中)》中華書局,2005年1月第2版第812頁。
⑧《文選·蜀都賦》,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11月電子版《文淵閣四庫全書》。
??《元和郡縣圖志·劍南道(中)》,中華書局2005年1月第2版第855頁。
?二人之說分別參見2004年6月版《古巴蜀與“山海經”》;1980年7月版《山海經校注》。
?按,不少學者研究群帝即群巫,也即神尸。如聞一多《神話與詩》中的《伏羲考》、《姜嫄履大人跡考》等。
?廣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第48-49頁。
?一說為瀾滄江。
?二河在馬湖合水后仍稱南河。
?《范石湖集》卷18。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第252頁。
?如雙河古城西面無墻。見《考古》2002年第11期《崇州市雙河遺址試掘報告》。
?如紫竹古城東面。見2000年第4期《成都文物·成都考古研究所2000年考古調查紀要》。
?參見上引《古巴蜀與山海經》、《玩·山海》等書。
?今青城山丈人觀中的主神。關于寧封事跡參見《列仙傳》等道教典籍中。
?天國山在今崇州懷遠、街子一帶山區。《崇慶府圖經》語轉引自王文才《青城山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版第19頁。按,《崇慶府圖經》已佚,南宋王象之《輿地紀勝》曾引此書。
?《史記·貨殖列傳》,中華書局1982年11月第2版第3277頁。
?今雙流,舊時該縣部分地域屬江原。按成都古籍書店1983年9月第1版龔煦春《四川郡縣志》第5頁注:“廣都,漢元朔二年置。今華陽、雙流、仁壽等縣地。”
?引按,后三句今在郭璞注中,袁珂先生《山海經校注》認為原在正文,后被誤入郭注。按,王逸注此經時仍在正文中。
?當時不可能一座城就方三百里。
?《百年崇州》,中國文史出版社2012年6月第1版第42頁。
?《考古》,2002年第11期。
?《爾雅·釋地》。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2月第1版第42頁。
?近年不少學者認為乃是商以后從高原下至低地的羌族分支。
?參見本文關于禹出生地,《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中華書局1982年11月第2版第2992頁。
?按,《海內東經》有“入江州城下”語,按江州乃漢初建置,此處顯系后人滲入之文。
?最遲至唐代以前還是這種情況。近年在山腳發掘大型隋唐窯,所用柴薪均來自此山,可見那時樹木甚多。
?巫或部落首領——史籍中稱帝嚳。參見聞一多《神話與詩·姜嫄履大人跡考》等。
?即雞卵,詳后文。
??聞一多:《伏羲考·姜嫄履大人跡考》,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9年7月第1版第109頁。
?今武功、扶風一帶。
??《漢書·溝洫志》,團結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第314頁
?《詩經·公劉》,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第255頁。
?以上均引自《華陽國志·蜀志》,時代文藝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第28、30、34等頁。
?參見《逸周書》、《博物志》等,時代文藝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諸子百家集成·博物志》第237頁。
?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四川辭書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第780頁。
?參見2000、2002年《考古》,《新津縣寶墩遺址發掘報告》、《崇州雙河遺址試掘報告》等。
?王充:《論衡·訂鬼》,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9月第1版第344頁。
?琴,郭璞、畢沅均訓為種植。見袁珂《山海經校注》引文。
?參見《朱利文化研究》光明日報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中有關討論。。
?參見《詩經選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10月第2版第26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