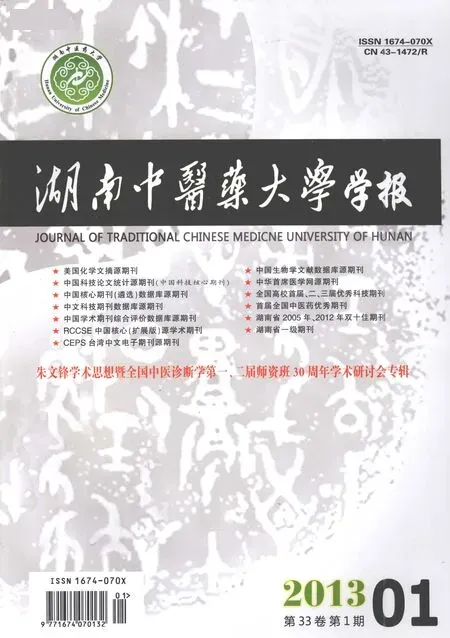基于臟腑經絡理論及證素辨證學統一中醫外感病辨證方法的思考
曾逸笛,朱文雄,周小青
(1.湖南中醫藥大學研究生教育學院,湖南 長沙410208;2.湖南中醫藥大學中醫診斷研究所,湖南 長沙410208)
辨證論治和整體觀念并稱為中醫學理論體系的主要特點[1],也是中醫學的特色與精華。千百年來,眾多醫家在與疾病的斗爭中總結、衍生了多種辨證方法,如八綱辨證、病性辨證、臟腑辨證、經絡辨證、方劑辨證……中醫學歷來將疾病劃分為外感、內傷兩大類,內傷雜病的辨證方法較為統一,其核心和共性在病性辨證、臟腑辨證。然而對外感疾病的認識素有寒溫之爭,派生出了六經、三焦、衛氣營血等多種辨證方法。寒溫雖然異氣,病因、病理乃至治法理當不可混同,然而面對寒溫之異所采用的不同辨證方法之間有無內在共同基礎,能否統一,成為解決爭議的關鍵。正如姜建國教授指出[2]:“寒溫統一究竟如何‘統’? 以什么‘統’? 實質就是如何處理六經辨證與衛氣營血辨證(包括三焦辨證)的關系問題,這是關鍵所在。”
1 中醫外感病辨證方法述評
漢代張仲景在《傷寒論》一書中首創六經辨證,他是依據《素問·熱論》的六經分證,根據傷寒病的證候特點和傳變規律而總結出來的一種辨證方法。所謂六經辨證,就是以六經所系的臟腑經絡、氣血津液的生理功能與病理變化為基礎,結合人體抗病力的強弱、病因的屬性、病勢的進退、緩急等因素,對外感疾病發生、發展過程中的各種癥狀進行分析、綜合、歸納,借以判斷病變的部位、證候的性質與特點、邪正消長的趨向,并以此為前提決定立法處方等問題的基本法則[3]。清代葉天士在《溫熱論》中首創衛氣營血辨證,將外感溫熱病發展過程中,不同病理階段所反映的證候,分為衛分證、氣分證、營分證、血分證4 類,用以說明病位的淺深、病情的輕重和傳變的規律,并指導臨床治療[4]。三焦辨證為清代溫病學家吳鞠通所倡導。吳氏以三焦為綱,病名為目,將溫邪作用于三焦所屬臟腑導致功能失調,以及實質損害所產生的復雜紛繁的臨床癥狀,歸納為證候類型,從而確定病變部位及其淺深層次,確定病變類型及證候性質,為確定治療原則提供依據[5]。
外感病邪即為風、寒、暑、濕、燥、火六淫,其中風、暑、火為陽邪,寒、濕、燥為陰邪,傷于寒的外感病多用六經辨證,傷于溫的外感病多用三焦、衛氣營血辨證。“三焦”主要反映溫邪阻滯氣機的病變,多用于濕熱類溫病的辨證;“衛氣營血” 主要反映溫邪傷陰程度的淺深層次分布,多用于溫熱類溫病的辨證。上述3 種辨證方法讓中醫對外感病的認識趨于全面,每種辨證方法下證、法、方齊備,幾千年來用于臨床行之有效,是中醫寶貴的財富,值得繼承和發揚光大。
2 中醫外感病辨證方法的實質
我們認為中醫外感辨證方法的實質是統一的。關于六經辨證的實質,古今醫家之說不下20 種[6]。六經辨證的稱謂源于宋代朱肱所著的 《類證活人書》,他以“太陽經”、“陽明經”、“少陽經”、“太陰經”、“少陰經”、“厥陰經”立論,清代汪琥積極響應此說,謂“仲景書止分六經,不言手足,其實則合乎經而皆病”[7]。其實張仲景《傷寒論》六經病提綱條文只言“太陽之為病”、“陽明之為病”、“少陽之為病”、“太陰之為病”、“少陰之為病”、“厥陰之為病”,并未言及“經”字。六經若套以臟腑經絡學說,則有足太陽膀胱腑、手太陽小腸腑、足陽明胃腑、手陽明大腸腑、足少陽膽腑、手少陽三焦腑、足太陰脾臟、手太陰肺臟、足少陰腎臟、手少陰心臟、足厥陰肝臟、手厥陰心包臟,而傷寒中的太陽病主要講表證,陽明病主要講里實熱證,少陽病主要講半表半里證,太陰病主要講里虛寒證,少陰病主要講真陽虛衰證,厥陰病主要講寒熱錯雜證,且六經病證實質是臟腑、經絡病變的具體反映。由此,我們認為仲景把傷寒病歸為三陰三陽其實質是對機體傷于寒邪之后疾病淺深層次的劃分及傳變規律的認識。
葉天士針對外感溫熱病提出:“衛之后方言氣,營之后方言血。在衛汗之可也,到氣才可清氣,入營猶可透熱轉氣……入血就恐耗血動血,直須涼血散血”[8],這是“橫”的規律。吳鞠通也提出:“治上焦如羽,非輕不舉;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權,非重不沉”[9],這是“縱”的規律。一“縱”一“橫”依然是機體傷于溫邪之后疾病淺深層次的劃分及傳變規律的認識。上焦心肺、中焦脾胃、下焦肝腎這已經提示臟腑經絡才是三焦、衛氣營血的實質。如果基于臟腑經絡來審視這三種外感疾病的辨證方法,會發現太陽證和衛分證即是表證,陽明證和氣分證即是里實熱證,少陽證和膜原證即是半表半里證,同屬氣分證的范疇。太陰病證亦屬氣分證,不過太陰病證以脾虛寒濕為特征;氣分證之病位在脾者,則以濕熱蘊脾為主。少陰病證和厥陰病證屬營分證、血分證,少陰病證重點言心腎陽虛寒化的表現,營血分證重點指陰血虧損所致證候,與少陰熱化證相類似。厥陰病證由于寒熱錯雜、陰陽氣不相順接常見肢厥與煩躁昏厥,營血分證亦常見昏譫痙厥之象,說明二者的病位均在肝或心包絡。傷寒是傷于陰邪,故后期多為陽虛;溫病是傷于陽邪,故后期多為陰虛。所以針對外感寒邪的六經辨證也好,針對溫熱病邪的衛氣營血辨證也好,針對濕熱病邪的三焦辨證也好,均離不開臟腑、經絡、氣血津液。臟腑經絡理論不僅能應用于內傷雜病的辨證,同樣可以用來詮釋外感疾病的規律。
3 統一中醫外感病辨證方法的思考
其實,關于外邪傷人的傳變模式《內經》中早有論述,如《靈樞·百病始生》等篇,虛邪之中人,無非始于皮膚、口鼻,再由淺入深地傳變。《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有云:“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膚,其次治筋脈,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臟,治五臟者,半死半生也”[10],皮毛→肌膚→筋脈→六腑→五臟即是外感病發生發展的一般規律。自張仲景的《金匱要略》奠定了臟腑辨證的基礎,千百年來臟腑辨證作為一種完善的辨證理論體系一直用于內傷雜病的診療[11]。然而,經過上述分析,發現六經、三焦、衛氣營血三種外感病辨證方法的內核離不開臟腑經絡理論,運用臟腑經絡學說來給外邪傷人淺深層次定位,即可概括幾乎所有外感病發生發展的規律。同時,“證素辨證”正是朱文鋒教授有感于中醫學的辨證方法多端紛繁,缺乏統一標準,而潛心探討中醫辨證思維,結合現代數學模型[12],建立在八綱、臟腑、六經辨證等實質內容的基礎上所創立的,根據證候辨別證素、組成證名的一種新的系統的綜合辨證方法,對臟腑經絡辨證是一種完善和量化,所以統一中醫外感病辨證方法也可結合證素辨證對其進行判斷和量化,甚至可歸向證素辨證,以證素辨證不同計量值為基礎鑒別證型。臨床運用時,將外感病患者的每一癥狀、體征等病情資料,按提示的證素分別進行加權求和(含減負值),其中小括號內為簡化計量權值,小括號后為計算機計量權值,通過“加權求和浮動閾值運算”以確定各證素的總權值,從而對證素做出判斷。然后取權值超過閾值(或較高)的證素進行有機組合,根據臟腑經絡辨證,從而構成完整的證名診斷。
概括地說,結合證素辨證,太陽經證即風寒表證,又可分為中風表虛證和傷寒表實證,臨床表現為新起惡寒[計量權值為(6)30]、頭項強痛[計量權值為(4)22]、脈浮[計量權值為(4)20][13],法用辛溫解表,方如麻黃湯、桂枝湯等;衛分證即風熱表證,亦可兼挾濕邪,臨床表現多為發熱重惡寒輕[計量權值為(6)30]、頭痛[計量權值為(4)22]、口微渴[計量權值為(4)20]、咽喉痛[計量權值為(4)19]、舌邊尖紅[計量權值為(5)26]、舌苔薄白[計量權值為(4)20]、脈浮數[計量權值為(4)20],法用辛涼解表,方如銀翹散、桑菊飲等;太陽腑證即邪傳膀胱、小腸所表現出來的證候,又可分為蓄水、蓄血兩證,分別投以五苓散和桃核承氣湯;氣分證即里實熱證,邪熱可侵犯肺、胸膈、胃腸、膽等臟腑形成不同的證候,陽明經證是邪熱亢盛,充斥陽明,臨床表現為大熱[計量權值為(6)32]、大汗[計量權值為(6)28]、大渴[計量權值為(4)20]、脈洪[計量權值為(4)20],法用辛寒清熱,方如白虎湯,陽明腑證即腸熱腑實證,臨床表現為潮熱汗出[計量權值為(6)28]、腹硬滿[計量權值為(5)26]、腹痛[計量權值為(4)20]、便秘[計量權值為(10)50]等,法用清熱攻下,方如承氣湯;邪留半表半里可分為少陽證和邪阻膜原證,病位在膽腑、三焦、膜原,臨床常見寒熱往來等證,方用小柴胡湯、達原飲;根據心主血脈、神明的理論,且營血分證和少陰證均有神志上的改變甚至障礙,故營血分證和少陰證均可歸于心的證候。營血分證即邪入血脈,傷損營陰,耗血動血,心主血脈,熱邪易內陷心包,并伴神昏譫語[計量權值為(9)46]等癥,類似于毒入心營證、邪犯心包證,法用清營涼血,方如清營湯、犀角地黃湯;太陰病證即脾胃虛寒證,臨床表現為腹滿時痛[計量權值為(2)11]、腹瀉[計量權值為(8)40],法用溫中散寒,方用理中湯、小建中湯;少陰病證的病位主要在心腎,有寒化、熱化之分,心腎陽虛者臨床表現為畏寒肢厥[計量權值為(6)30]、下利清谷[計量權值為(10)52]、脈微[計量權值為(5)26],法用回陽救逆,方如四逆湯一類方;心腎陰虛者主要表現為心煩不得眠[計量權值為(8)40],法用交通心腎,方如阿膠雞子黃湯;厥陰病證基本病機為上熱下寒,臨床表現為消渴[計量權值為(4)18]、心中疼熱[計量權值為(4)20]、饑而不欲食[計量權值為(4)20],方用烏梅丸。溫病后期為余熱未清、諸臟陰傷之表現,法用滋陰清熱,方可隨證選用。以上就是外感病辨證方法統一的初步綱領,考慮到中醫診斷歷來是“辨病為先,辨證為主”,在證素辨證的基礎上,還可加入病素加權的相關內容,明辨證候表現上的寒溫之別,更能切合病機,洞察精詳。
綜上所述,外感疾病的多種辨證方法臨床運用時容易混淆甚至相互沖突。我們認為運用臟腑經絡理論可概括外感病各階段發生發展的規律,進一步結合、甚至歸向證素辨證,不僅有利于中醫學人明晰外感病對機體的影響過程,掌握疾病預后,明確疾病辨證,在充分吸取已有診斷標準制定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統一規劃,整體科學設計[14],更有利于在臨床運用過程中建立統一、標準化的認識,規范臨證處方用藥,有助于中醫辨證方法的統一和客觀化。然而,六經、三焦、衛氣營血等辨證方法各有所側重,基于大量的臨床實踐,不能完全地等同于臟腑及經絡辨證或證素辨證,況且沿用已久,有其臨床實用價值。我們認為基于臟腑經絡理論和證素辨證統一中醫外感病辨證方法是完全可能的,目前關鍵的問題在于這種“大而全”的臟腑經絡辨證結合證素辨證還能不能繼續延續六經、三焦、衛氣營血對外感疾病認識的深刻性,保持各自的優勢與特性。這種統一的嘗試也需要大量的臨床實踐來補充完善。總之,統一中醫外感病辨證方法是一個值得進一步挖掘和深究的大課題、大工程,可能需要幾代中醫人的不懈努力。
[1]孫廣仁.中醫基礎理論[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7:10.
[2]姜建國.論六經辨證與寒溫統一[J].山東中醫藥大學學報,2000,24(1):513-515.
[3]熊曼琪.傷寒學[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9:7.
[4]朱文鋒.中醫診斷學[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7:212.
[5]林培政.溫病學[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8:23.
[6]袁肇凱,王天芳.中醫診斷學(研究生教材)[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7:261-264.
[7]朱文鋒,袁肇凱.中醫診斷學(第2 版)[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11:800.
[8]張志斌.溫熱論/濕熱論[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9:2.
[9]吳 瑭.溫病條辨[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9:174.
[10]田代華.黃帝內經素問[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9:93.
[11]朱文鋒.證素證候學[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8:24.
[12]路志正.讀《證素辨證學》有感[J].湖南中醫藥大學學報,2009,29(1):封三.
[13]郝萬山,錢超塵.傷寒論[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9:32.
[14]朱文鋒.制定常見證診斷標準的思路[J].湖南中醫藥大學學報,2008,28(2):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