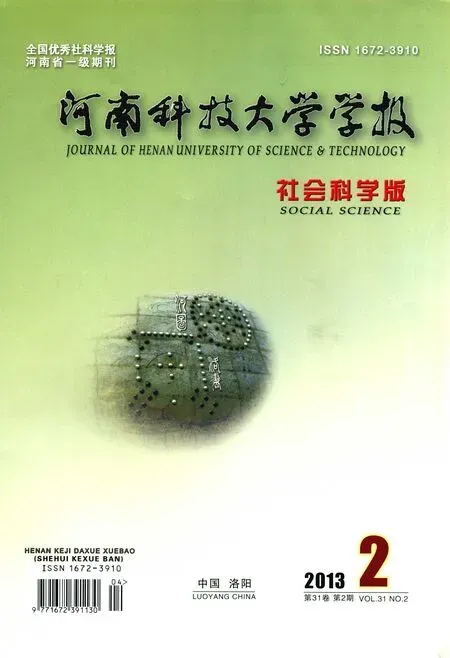行賄罪探析
熊明明,趙 東
(1.昆明市檢察院,昆明650000;2.重慶郵電大學移通學院,重慶401520)
一、行賄罪的構成要件分析
我國刑法第389條明確對行賄罪分兩種情況分別予以規定,即一般的行賄罪和以行賄論處。依據該條文的規定,行賄罪的客觀行為主要表現為以下幾種情況:一是主動行賄,即為了謀取不正當利益,主動給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二是被動行賄,被國家工作人員索要財物后,謀取了不正當的利益;三是在經濟往來中的行賄,主要表現為在國家機關采購等經濟活動中違反規定,給予國家工作人員數額較大財物或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以上這三種行賄方式都要求行賄的對象具有特殊的主體身份,即行賄對象必須是國家工作人員,若對象不是國家工作人員,則不能構成行賄罪。
行賄罪侵犯的法益是什么?筆者認為,基于行賄罪與受賄罪的特殊關系,其侵犯的法益應與受賄罪侵犯的法益相同,即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至于“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的內涵,筆者贊同有些論者的觀點:“不可收買性至少具有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本身,二是國民對職務行為不可收買性的信賴。”[1]874這些可以從行賄罪的要件解剖中得到體現。行賄罪通常可以解剖為兩個部分:為謀取不正當利益和給國家工作人員財物,前者意味著行為人違反正常的行業規則和公平公正的競爭秩序,這間接體現了行賄行為侵犯國民對職務行為公平公正的信賴;后者則侵犯了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本身的不可收買性。
行賄罪的主觀要件要求行為人明知自己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的行為侵害了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并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的發生。在認識層面,不同的行為方式對行賄人的認識內容有著不同的要求:第一,就主動行賄而言,要求行為人認識到自己的行為動機(為了謀取不正當利益)、對方的國家工作人員身份以及給予財物行為的違法性。在實踐中,要求行為人認識自己行為的動機應從整體角度來講,而不是將行為人的一系列行為割裂開來談。例如,行為人在前幾次送給國家工作人員財物時只是出于聯絡感情,并沒有具體的請托事由,只是為今后“辦事”做感情鋪墊,事實上通過前期的“投資”,行為人很順利地與國家工作人員進行了后期的“權”“錢”交易,那么這時其前期的行為就具有了謀取不正當的利益的動機。另外,行為人對給予國家工作人員財物的違法性認識,只要具有意識到這種行為的不當性即可,不需要知道具體違反了什么法律法規,也就是說此時的違法性認識是一種抽象的違法性認識。第二,就被動行賄而言,要求行為人認識到對方的國家工作人員身份和給予國家工作人員財物的違法性,以及行為人獲取了不正當利益的事實。因為被勒索給予財物,故不存在行為人“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動機。根據最高檢的司法解釋,被動行賄的行為人構成行賄罪還要認識到已經獲得了不正當利益的客觀事實,如果沒有實際獲取不正當利益,也就失去了構成此種行賄犯罪的要件。第三,在經濟往來中的行賄,要求行賄人認識到對方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以及自己行為的違法性。這里的違法性同樣只是抽象違法,不需要行為人知道違反具體的法律名稱。另外,這種情況下也不需要行為人認識自己的行為動機或者獲得不正當利益的客觀事實。在意志層面,行為人明知自己給予國家工作人員財物的行為侵害了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仍然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發生。
行賄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凡年滿16周歲、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人,均可以成為本罪的主體。行賄罪的對象要求是國家工作人員。
二、行賄罪與相似罪名的比較
與行賄罪相近的罪名有:單位行賄罪、對單位行賄罪以及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其中,單位行賄罪、對單位行賄罪與行賄罪同屬于我國刑法第8章貪污賄賂犯罪的罪名,單位行賄罪和行賄罪都要求行賄的對象是國家工作人員,而對單位行賄罪則要求行賄的對象是“國”字單位,即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事業單位、人民團體;而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則是刑法第3章第3節妨害對公司、企業的管理秩序罪的罪名,該罪名與其他幾個罪名的不同,主要是行賄的對象不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
行賄罪與單位行賄罪的比較:第一,主體不同,個人行賄罪的主體是自然人,而單位行賄罪的犯罪主體必須是單位。這里所講的單位,根據《刑法》第30條的規定,應指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的規定:“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既包括國有、集體所有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也包括依法設立的合資經營、合作經營企業和具有法人資格的獨資、私營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個人為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而設立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實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業、事業單位設立后,以實施犯罪為主要活動的,不以單位犯罪論處。第二,違法所得歸屬不同,單位行賄罪行賄行為的違法所得必須歸單位所有。刑法第393條明確規定,因行賄取得的違法所得歸個人所有的,依照個人行賄罪的規定定罪處罰。最高人民法院有關的司法解釋也規定,盜用單位名義實施犯罪,違法所得由實施犯罪的個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關自然人犯罪的規定定罪處罰。第三,情節標準不同。“情節嚴重”是構成單位行賄罪的必要條件之一,也是與個人行賄罪相區別的一個重要標志。
行賄罪與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的主要區別就是行賄對象身份不同,行賄罪行賄的對象必須是國家工作人員,而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則要求行賄對象不是國家工作人員。因此,區分行賄對象是否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關系重大。根據我國刑法第93條的規定,國家工作人員主要有兩個特征:第一,必須是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中的人員或者上述機關、單位委派到其他單位的人員。第二,必須是依照法律從事公務或者受委托從事公務。實踐中,基層組織人員、集體性質的單位以及國家出資企業中的相關人員是否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比較難以認定。
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93條第2款的解釋》以及其他相關司法解釋、兩高的答復,村基層組織人員協助人民政府從事行政管理工作時應以國家工作人員論;經過政府或者主管行政機關任命的集體性質單位的人員從事本區域的相關事務管理與業務技術指導等公務活動時,以國家工作人員論。如何認定國家出資企業中受委派從事公務的國家工作人員身份?根據兩高的《關于辦理國家出資企業中職務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6條的規定,我們不難看出:委派具有兩個方面的特征,第一,委派形式不拘一格,任命、指派、提名、推薦、認可、同意、批準等均可;第二,委派的實質即被委派者具有國有單位意志的直接代表性,需代表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事業單位在非國有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中從事組織、領導、監督、管理等公務活動。委派不限次數,只要被委派者的管理職位與相關國有單位的意志行為具有關聯性和延續性即可。
三、實踐中的疑難與困惑
(一)如何處理行受賄關系中的認識偏差
在實踐中,對行賄罪名影響最大的就是當出現事實認識錯誤時的處理。關于事實認識錯誤,我國刑法理論上通常指的是狹義上的認識錯誤,即與構成要件相關的事實認識錯誤,既包括行為人對受托主體、對象、行為的要素認識錯誤,又包括對客體、主觀罪過方面的要素認識錯誤。就行賄罪而言,通常會發生對象上的一系列認識錯誤。
行賄人與受賄人處于簡單的一一對應關系時通常是不存在對象認識錯誤的,但在實踐中,在有其他因素介入的情況下行受賄關系變得復雜,尤其是在第三者介入進行介紹、幫助請托事項時。身份的認識錯誤,可細分為兩種:具體職位的認識錯誤,即將受托人的此職位誤認為彼職位,但對受托人的國家工作人員身份沒有認識錯誤。另一種是行為人對受托人的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發生認識錯誤,即受托人不是國家工作人員,行為人(請托人)卻誤認為其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第一種情況在實踐中不會影響對行為人行賄罪的認定,因為認識對方的國家工作人員身份屬于概括的認識,不以對國家工作人員具體的職責范圍有明確的認識為條件,否則會不當縮小行賄罪的范圍。對于第二種情況,因對方不具有行賄罪要求的對象條件,故行為人不成立行賄罪,而可能構成向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或其他罪名。實踐中之所以出現對象的認識錯誤,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間人的出現。大多數情況下,行賄人通過第三人認識最后利用職權的國家工作人員,這個過程中的第三人既可能是普通人員也可能是沒能利用自己職權的國家工作人員,既可能僅僅是一人,也可能是許多人。因此,行為人沒法查明核實受托人的真實身份和其職權情況。更有甚者,還會出現詐騙或招搖撞騙的事情。
在行受賄過程中,可能會出現對財物數額的認識錯誤、財物性質的認識錯誤、行為主體的認識錯誤。針對主體認識錯誤,諸如對行賄人是個人還是單位的界定屬于司法機關查證的事實。因此,如果當事人對這樣的事實發生錯誤時也不影響對其行為本身的評價。對財物性質的認識錯誤同樣也屬于司法機關查證的事實,對該事實的認識錯誤也不影響對行為人的評價。例如,行為人誤以為送購物卡等不屬于送財物,此情況為法律認識錯誤,不影響定罪。對行賄數額的認識錯誤通常發生在第三方介入的時候,此時對行賄人數額的判斷應依據其主觀認識程度做出符合客觀事實的判斷。例如,請托人找受托人甲(國家工作人員)給自己“辦事”,并給受托人甲20萬元作為酬謝,受托人甲在收下這20萬元后,覺得自己能力有限,又找國家工作人員乙將此事辦成,并給國家工作人員乙10萬元,此時請托人與甲、乙的犯罪數額怎樣確定取決于請托人對事件的認知程度。如果請托人對受托人甲給乙錢物辦事不知情,則請托人只向甲行賄數額為20萬元,受托人甲給乙的10萬元又另行構成一個行、受賄關系;若請托人對后續事項知情又該如何確定行賄數額呢?是否推定請托人有與甲的共同行賄故意,按照請托人和甲共同向乙行賄20萬元計算?還是行賄數額分別評價:即單獨對國家工作人員甲行賄10萬元,以及請托人與甲共同行賄乙10萬元呢?筆者認為后者觀點更為合理,首先,請托人知曉受托人甲的后續事項,沒有做出任何反對的表示,而乙又不知請托人與甲的商定內容,也就是說乙與請托人、受托人甲之間不存在共同故意的共謀。由此我們推定請托人與受托人甲有共同行賄的故意,即請托人與受托人甲共同向乙行賄10萬元,而不是請托人向甲、乙行賄,甲乙之間不存在共同受賄的主觀故意;其次,至于請托人之前送給受托人甲的20萬元,甲從中拿出10萬交給乙的部分,由于請托人沒有追加數額,故可以認為甲從中拿出10萬元的行為被請托人默認,即請托人給甲只行賄10萬元,而非20萬元。
(二)如何理解“不正當利益”
關于不正當利益的界定,雖然兩高出臺的《關于辦理商業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9條已經提供了更為具體的標準,但是“不正當利益”是一個規范的構成要件要素,是需要就具體事實關系進行判斷與評價才能確定的要素,因此,在實踐中如何理解和認定“不正當利益”始終是一個難題。我們認為,如何理解和解釋需要和刑事政策聯系起來,在目前反腐形勢嚴峻的情況下,司法實踐中應該予以擴大解釋。正如有些學者的觀點:“國外刑法以及舊中國刑法均未要求行賄罪出于‘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目的,現行刑法的規定本來就縮小了行賄罪的處罰范圍,如果再對‘謀取不正當利益’作限制解釋,則不當縮小了處罰范圍。”[1]888另外,為謀取不正當利益,既包括為自己謀取,也包括為他人謀取,只要行為人在行為時認識到了其行為動機即可。
(三)現有法律條文應對的不足
我國刑法第390條規定了行賄罪的量刑與處罰,其中該條第3款明確了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單位行賄罪則無類似規定。也就是說,單位行賄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在被追訴前主動交代單位行賄行為的不能得到個人行賄罪中減輕或者免除處罰的待遇,而只能以自首的情節論處。但是,筆者認為,通常情況下,單位犯罪的意志都是由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管理人員做出,犯意的源頭來自單位管理層的直接責任人,對個人行賄人的特別處遇應適用于具有類似性質的單位行賄的直接責任人員身上,否則,不利于類似法條之間刑罰處罰的平衡。
《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8章增加了一個新的罪名——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明確了在國家工作人員不知曉的情況下,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或者其他與該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人收受他人賄賂后的處罰。但是,當這些國家工作人員近親屬或者關系密切人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后,給國家工作人員近親屬或關系密切人行賄的人構成何罪呢?以目前刑法條文的規定來看,因為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或關系密切人不是國家工作人員,只能以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追究行賄人。但是,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侵害的客體是妨害對公司、企業的管理秩序,而利用影響力受賄罪侵害的是國家工作人員公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很顯然,行賄方與受賄方此時侵害的法益有沖突,這種處理不利于刑法體系的合理化,極有可能造成刑罰的不公。
四、結語
基于實踐中存在的困難,筆者認為,應采取以下措施處理行賄罪。
首先,應擴大對“不正當利益”的解讀。任何方式或結果不正當獲取的利益皆為不正當利益。我們贊同有的學者提出的觀點:“有必要在條件成熟的時候修訂立法,把賄賂的范圍擴大到財產性利益甚至非財產性的不正當利益。”[2]不正當利益不僅包括財物(貨物及實物),還包括可以用貨幣計算的財產性利益,以及其他非財產性的不正當利益,如提供指標、安置親屬就業、升學、提升職務、遷移戶口等,只有這樣擴大解釋“不正當利益”,才不會縮小行賄罪的打擊范圍,才有利于同腐敗行為作斗爭,切實維護國家的廉政制度。同時,對行賄人主觀目的的擴大解釋,也不會不當擴大對行賄人的打擊面,因為法律條文在規定了行賄人的主觀目的是“為了謀取不正當利益”之后,明確規定了送給國家工作人員“財物”這一限制性條件。
其次,擴大行賄罪的行賄對象范圍以適應《刑法修正案(七)》,將行賄對象擴大為國家工作人員及其近親屬或關系密切人。因為給國家工作人員近親屬或關系密切人行賄最終侵犯的是國家工作人員公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而非是公司、企業的社會秩序。
[1]張明楷.刑法學[M].第3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2]王作富.刑法分則實務研究:下[M].第3版.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7:17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