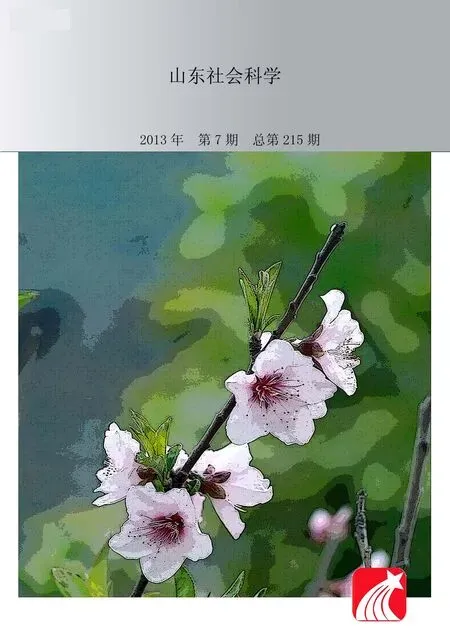留學背景與新文學的標志性創作
鄭 春
(山東大學 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山東 濟南 250100)
20世紀40年代,當作家楊絳的劇作《弄真成假》引起轟動的時候,著名文藝評論家李健吾說過這樣一句話:“假如中國有喜劇,真正的風俗喜劇,我不想夸張地說,但是我堅持地說,在現代中國文學里面,《弄真成假》將是第二道紀程碑。有人一定嫌我過甚其辭,我們不妨過些年回頭來看,是否我的偏見有些正確的預感。第一道紀程碑屬諸丁西林,人所共知,第二道我將歡歡喜喜地指出,乃是楊絳女士。”注孟度:《關于楊絳的話》,載《錢鐘書楊絳研究資料集》,華中師大出版社1997年版,第661頁。丁西林是早年留英的學生,雖是物理學教授,但他卻是以我國現代喜劇的開拓者而聞名于世。楊絳則在20世紀30年代后期剛剛從國外回來,有意味的是,將具有留學背景的現代作家當作某一文學領域的紀程碑,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是屢見不鮮的。學者舒蕪在談到周作人時也指出:“他是北京大學第一個講授歐洲文學史的教授。他還寫了大量介紹外國作家作品,輸入外國文學理論與知識的文章。接著他又作為文藝理論家出名。他的名文《人的文學》,第一次給中國新文學運動制定了一個民主的人道的思想綱領,啟發了一代兩代的文學青年。接著他第一個提出了‘思想革命’的口號,為文學革命提出了進一步的目標。他呼吁人的發現,女性的發現,兒童的發現,他提倡寬容和自由,反對束縛和統制。他又是最初的新詩人之一,他的長詩《小河》,被推為中國新詩運動史上一個新的里程碑。周作人后來把寫作的重點轉向小品文,他對中國新文學新文化史的最重要的貢獻就在這一方面,他的沖淡雋永、苦澀回甘的小品文,極盡‘陰柔’之美,與魯迅極盡陽剛之美的雜文,兩峰對峙,雙水分流,代表中國新文學的最高成就。”注舒蕪:《串味讀書》,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2頁。舒蕪這段話較為全面地評價了周作人在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歷史成就,從那一系列的“第一個”、“第一次”和“最初”、“最高”中,我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周作人突出貢獻和獨特價值。
其實不止周作人如此,所有具有留學背景的現代作家,都以自己的不同創作成就,在新文學的發展過程中起到了各自不同的關鍵作用。他們不僅以極大的理論勇氣開創了中國文學發展的嶄新局面,更重要的是,以自己各具特色的創作實踐為這一局面的鞏固和發展奠定了極具意義的作品基礎。這一點當時人們就有所認識,陳源在《新文學運動十部著作》一文中,特意選出郭沫若的《女神》、徐志摩的《志摩的詩》、楊振聲的《玉君》、郁達夫的《沉淪》和魯迅的《吶喊》等作品,進行了有針對性的評論。他認為這些作品共同的價值,就在于它們都具有“開創”的意義。這種開創表現在各個方面:郁達夫的小說以“單調”為特點,開創了描寫“現代的青年”的先河;魯迅的小說,特別是他所奉獻的阿Q形象,“不僅是一個tape”,而且將會是“不朽的”;郭沫若《女神》的意義,在于它一反傳統詩詞的束縛,“自己創造一種新的語句”,而且聲調和諧;徐志摩詩的開創意義表現在“他的文字是把中國文字、西洋文字,融化在一個洪爐里,煉成的一種特殊的而又曲折如意的工具”;楊振聲《玉君》的開創意義,則在于他塑造了“中國小說中不曾有過的人物”。[注]陳源:《西瀅閑話》,新月書店1931年版,第206-214頁。陳源的分析自有他獨特的視角和觀點,當然其中也不無偏頗之處,但他對以上作品開創意義的把握還是十分敏銳的,并且是有道理的。從總體上看,具有留學背景的現代作家確實對新文學的發生和發展具有奠基性的重要貢獻,其標志性的創作主要有三種表現形式:其一,首創但不成熟;其二,首創同時達到頂峰;其三,非首創但成為成熟的標志。
一
早在“文學革命”發難之始,新文學創作也隨之產生,但這些萌芽作品無疑是極為稚嫩和粗疏的。最初的新文學創作主要是一些白話新詩和白話體的議論散文,是真正意義上的白話文學實驗。而且這些實驗者幾乎都是發起“文學革命”的旗手和主將,大多是剛從國外返回的留學人員,如胡適、周作人、沈尹默等人。他們從事創作主要不是為了當文學家,而是為了實踐他們的白話文學主張,或者說是想用創作推動他們所致力的國語運動;他們的作品主要不是為新文學摸索藝術規律和經驗,而是為新的文學觀念補充可操作的佐證。正因為如此,早期的新文學創作大多是粗淺的嘗試性作品,藝術質量和藝術水準普遍不高,往往表現出首創但是很不成熟的特點。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首推胡適。
胡適是滿懷一腔熱血返回祖國的,他渴望以學報國,下定決心用自己的知識和學問使祖國發生某種積極的變化。他要為祖國的新文化建筑起一個全面更新的基礎,要為祖國邁向全面現代化、世界化捧出自己全部的熱忱。回國后,他迅即投入了極為緊張的工作之中。在理論倡導方面,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的基礎上又發表了《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一文,將“新文學要點”之“八事”,簡約成四句話:“一、要有話說,方才說話。二、有什么話,說什么話。話怎么說,就怎么說。三、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四、是什么時代的人,說什么時代的話。”[注]《新青年》第4卷第4號(1918年4月15日)。
隨后,他又把這四句話進一步提煉和概括為十個字:“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并解釋道:現代的人,應說現代的話,即國語;現代的人,應做現代的文學,即國語的文學。他認為,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才可以有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我們的國語才可以算真正的國語。正因為如此,他進一步明確標示出要以“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作為“文學革命”的宗旨,努力造就言文一致的統一的“國語”,作為實現思想啟蒙和建立統一的現代民主國家的必要條件。這就把白話文運動提高到了一個新的理論層次,由單一的文學改革的范圍向整個社會全方位推進,這也是文學革命在短時期內大獲全勝的原因之一。更為重要的是,胡適不僅是一個積極的白話文運動倡導者,而且是一個恪盡全力的實踐者和先行者。盡管他對自己有著清醒的認識,深知文學創作非己所長,也曾多次說過自己缺乏創造的靈感,但還是愿意身體力行、率先示范,并且努力走出了蓽路藍縷的第一步。他在很短的時間內,先后寫出了一部獨幕劇、一部翻譯小說集,以及幾篇嚴格意義上的白話散文作品,還結集出版了自己獨具特色的新詩集《嘗試集》。胡適文學創作的開創嘗試是十分明顯的:1919年3月,胡適推出了中國現代話劇劇本的開山之作《終身大事》。劇本把老少兩代人在婚姻問題上的矛盾安排在一個半新半舊、中西合璧的家庭里,使戲劇沖突的內涵超出了五四時期常見的,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主題范圍。作品在形式上顯然是深受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影響,但內容上切中五四時期青年最為關注的時代問題,因而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反響。若就戲劇藝術而論,這部獨幕劇實在是頗為粗糙,缺乏戲劇特有的審美力量,然而若從中國話劇文學史的角度看,它卻首先宣告了中國人自己創作的話劇劇本的誕生,從而具有特別的歷史地位和經典意義。胡適還最早推出了用白話文翻譯的外國文學作品集《短篇小說一集》,這在當時也是頗具影響力的外國文學翻譯作品。一般論者認定,“五四”時期的新文學創作成績以短篇小說和新詩兩種體裁為最大,胡適的《論短篇小說》、《談新詩》在當時幾乎是指導短篇小說和新詩創作的金科玉律。
另外,胡適還是現代文學史上用白話創作新詩的第一人。早在美國留學期間,他便開始思考中國詩歌的改革問題,并從翻譯外國詩歌入手,嘗試著用白話寫詩。回國以后,在倡導“文學革命”的同時,他渴望能有一種“樣品”,來證明其理論的“正確”與“可行”。他在《〈嘗試集〉自序》中說:“因為這一年來白話散文雖然傳播的很快很遠,但是大多數人對于白話詩仍舊很懷疑;還有許多人不但懷疑,簡直持反對態度。因此我覺得這個時候有一兩種白話韻文的集子出來,也許可以引起一般人的注意,也許可以供贊成和反對的人作一種參考的材料。”于是,他便開始“暫不與君辯,且著《嘗試集》”。他不僅努力倡導以白話寫詩﹐主張新詩文體的自由和不拘格律﹐而且以自己的親身實踐努力印證這一點。他的努力對新詩的創立具有積極意義﹐并直接導致了新詩自由詩派的形成。1920年,他的《嘗試集》出版,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新詩集。這部詩集的開拓性貢獻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對白話語言的充分運用;二是對自然音節的大膽講求;三是提倡并實踐著“詩體的大解放”。盡管胡適的白話詩一向被論者詬病,但客觀地說,其中有一些篇章還是達到了相當的水準,例如《夢與詩》:
都是平常經驗,/都是平常形象,/偶然涌到夢中來,/變換出多少新奇花樣!//都是平常情感,/都是平常言語,/偶然碰著個詩人,/變換出多少新奇詩句!//醉過方知酒濃/愛過方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詩,/正如我不能做你的夢。
再如《回向》:
他從大風雨里過來,/爬向最高峰去了。/山上只有和平,只有美;/沒有風和雨了。//他回頭望著山腳下,/想起了風雨中的同伴,/在那密云遮著的村子里,/忍受那風雨中的沉暗。//他舍不得他們,/但他又怕那山下的風雨。/“也許還下雹呢?”/他在山上自言自語。//他終于下山來了,/向著那密云遮處走。/“管他下雨下雹!/他們受得,我也能受!”
這兩首小詩比較明顯地代表著胡適詩歌的特色,其長處是時時閃爍著理念、感悟和思辨的光澤,既有哲理的力量,又有文理的色彩,詩句中滲透著濃郁的人生況味,很能潛入人心;不足則是過于淺顯直白,而且過度口語化,有些就好像是分段的散文,詩情詩味和詩的韻律都是欠缺的。概括地說,胡適的詩歌成就是有限的,從審美的角度來看《嘗試集》,其藝術價值遠遠低于他的文學史價值。究其原因,才氣不足是一個重要原因,另外就性情而言,胡適似乎更適宜成為一名學者,而很難成為一位詩人,因為大多時候他太平和、太理智,或者換句話說,平和理智是其性格的底色,他從根本上缺乏那種激情澎湃、超越一切的詩人氣質,這就注定了他的藝術創作只能流于一般。從總體來看,胡適的文學素養,在其人才輩出、云蒸霞蔚的同代人中,并不特別突出,甚至說不上突出,他的小說、散文、劇本、詩歌都寫得平平,好在胡適的意義并不在于此。胡適的意義不在于寫得好,而在于寫得早;不在于會寫,而在于敢寫,也就是敢于“嘗試”。在紀念百年校慶時,北大出了本紀念文集,名為《北大校長與中國文化》,介紹胡適的一章題目是《他沒有完成什么,卻幾乎開創了一切》,說“一切”似乎大了些,但在文學領域,他確實有諸多首創之功。對此,李澤厚的評價還是頗為中肯的,他說:“胡適當然不止于提出‘八不’,而且也在一片嘲諷譏笑中努力提倡了白話文的創作。他自己率先‘嘗試’,不顧成敗,盡管作品的確很不成功,卻畢竟帶了頭。接著便涌現了康白情、沈尹默、俞平伯、冰心、郭沫若等第一批新詩作者。所以,胡適是開風氣者。開風氣者經常自己并不成功,膚淺浮泛,卻具有思想史上的意義。”[注]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東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頁。
二
限于種種條件,首開風氣者往往創作成就并不太高,這在文學史上是正常的也是較為普遍的現象。但也有例外,那就是在首創的同時又是這一文學領域成熟的標志,魯迅的小說創作就是這樣一個特例。
1918年5月,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了《狂人日記》,這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具有現代形式和現代精神的白話短篇小說,它“以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內容和形式的現代化特征,成為中國現代小說的偉大開端,同時它開辟了中國文學發展史上一個嶄新的時代。繼《狂人日記》之后,魯迅的文學創造力便“一發而不可收拾”,在隨后幾年中,他陸續創作了20多篇小說作品,先后結集為《吶喊》、《彷徨》。而這兩部小說集則是中國現代小說的成熟之作,這就是說,“中國現代小說在魯迅手中開始,又在魯迅手中成熟,這在歷史上是一種并不多見的現象”。[注]嚴家炎:《世紀的足音》,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64頁。
應當指出的是,魯迅最初對新文化運動并不是十分熱情,更談不上積極,正如周作人所言:“那時《新青年》還是用文言文,雖然漸漸你吹我唱地在談文學革命,其中有一篇文章還是用文言所寫,在那里罵封建的、貴族的古文。總結的說一句,對《新青年》總是態度很冷淡的。”[注]周作人:《關于魯迅》,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2頁。周作人認為魯迅對于簡單的文學革命并不太感興趣,他贊成文學革命,但覺得文學革命如果不與思想革命相結合,便無多大意義。魯迅自己也說:“我那時對于‘文學革命’,其實并沒有怎樣的熱情。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于是失望,頹唐得很了。”[注]魯迅:《〈自選集〉自序》,載《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455頁。后來,是在朋友們的勸說下,魯迅的認識和思想才逐漸發生了一些改變。在《吶喊·自序》中,他這樣描述錢玄同動員他為《新青年》投稿時,自己的心理變化過程: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們正辦《新青年》,然而那時仿佛不特沒有人來贊同,并且也沒有人來反對,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說: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嗎?”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絕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于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于是我終于答應他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注]魯迅:《〈吶喊〉自序》,載《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419頁。
魯迅是帶著對人情世故的深刻體察,對中國和世界歷史文化長期深入的思考,加入新文化陣營,開始文學創作的。正是從這層意義上,李鷗梵說過,五四時期的作者大多是年輕人,只有魯迅是中年人,這話意味深長。日本學者伊藤虎丸也關注到這一點,他一再提請人們注意,魯迅是到了37歲才開始小說創作,他把37歲當作研究魯迅的一個契入點,甚至是一個包含了許多內容的秘密。他說:“到了1918年,37歲時,才寫處女作《狂人日記》,這也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近代小說。魯迅為什么到了這個年齡才做起小說來呢?為什么又能做出小說來呢?此后,魯迅又接二連三地一直寫小說和戰斗性評論,其背后的秘密,可看做就隱藏在他37歲時寫出的這篇處女作當中。我通過讀解這篇作品,來探討魯迅為什么成為‘小說家’,并且把魯迅當中確立近代現實主義的內面過程,作為‘個人主義’即‘個的自覺’問題來予以對待。”[注]伊藤虎丸:《魯迅與日本人:亞洲的近代與“個”的思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頁。伊藤在其卓有成效的研究中,努力探討魯迅小說創作獨特的動機和態度,他特別強調:“有兩點可以指出:第一,他在辛亥革命以來的經驗中,懷抱著深深的‘寂寞’,這‘寂寞’成了‘失望’,也成了‘絕望’,使他對文學革命運動也‘懷疑’起來。然而,盡管如此,出于‘對于熱情者們的同感’,還是決定為他們去‘助威’,添上幾聲‘吶喊’(這種態度在魯迅一生當中是一貫的)。第二,不過,這‘絕望’和‘寂寞的悲哀’,又同時是他不能不‘吶喊’的來由(然而,因為他的‘絕望’過于黑暗,所以才不恤用‘曲筆’來調和)。”[注]伊藤虎丸:《魯迅與日本人:亞洲的近代與“個”的思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頁。我們以為,這些分析都是具有相當的力度和深度的,這些海外學者的獨特視角和感受尤其值得重視。的確,中年人自有中年人的目光和不凡,37歲的作品也有這個年齡段創作的長處和短處。魯迅多次說過,自己之所以創作,是為了“揭出痛苦,引起療救的注意”,又說,他的小說是個人回憶的產物:“所謂回憶者,雖說可以使人歡欣,有時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絲縷還牽著已逝的寂寞的時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卻,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現在便成了《吶喊》的來由。”[注]魯迅:《〈吶喊〉自序》,載《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415頁。魯迅創作的意義恰恰體現在這里,“他努力把個人對往事的回憶同對民眾的知識啟蒙那種關切之情藝術地結合在一起,他試圖把對個人經歷的回憶重新加以整理,使他進入中華民族歷程這幅更廣闊的圖景中,這樣就能夠使它不像五四文學初期的絕大多數作品那樣以自我為中心,使作品對讀者產生更重大的意義。”[注]李歐梵:《現代性的追求》,三聯書店2000年版,第216頁。7年的留日生活使魯迅的視野和思想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通過留學了解到西歐近代新的人的觀念的魯迅,由此獲得了對舊中國社會展開根本性批判的視角”[注]伊藤虎丸:《魯迅與日本人:亞洲的近代與“個”的思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頁。,回國以后,他又目睹或親歷了晚清崩潰和民國初建過程中政局的持續動蕩,對社會現實的復雜性有了更為清醒的認識,更深切地感受到中國改革之難,留學期間開始的關于國民性的思考愈益邃密,用文學來表達這種思考的沖動也不斷增強,而多年埋首古書,對社會史和文學史作了長期不懈的精細研究,積累了豐富的思想材料和深厚的文學修養,所以他一出手就突發大聲,一改“文學革命”初期頗為沉寂的局面。
與其說新文學選擇了魯迅來顯示創作成績,不如說魯迅選擇了“文學革命”這塊陣地,在更大的社會語境中陳述積累已久的思想。作為卓越文學家的魯迅同時是位卓越的思想家,而他的思想家的特點往往是通過文學作品來展現的,所以從今天的歷史高度回望,魯迅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貢獻也許比任何人都更豐富和深刻。魯迅對他的作品寄予了深切的期望,正如茅盾在《魯迅論》中所指出的,《吶喊》里的小說最突出的特點就是作者的思想不是用喉嚨喊出來的,而是用人人都熟悉但又有點兒陌生的人物形象表現出來的。茅盾用極為形象化的語言說,魯迅的確沒有什么主義要宣傳,也不想發起什么運動,他從不擺出“我是青年導師”的面孔,然而他卻實實在在地為青年們指引著一個大的方針:應該怎樣生活著。我們深深地贊同茅盾的觀點,并且認為魯迅筆下的人物的確具有長久的生命力,在幾十年后的今天,我們通讀魯迅作品,依然能夠感受到一種異樣的情懷。魯迅的出現,給中國文化氣質帶來了極大的改變,他的作品則給中國文學帶來一種充滿生機和活力的新氣息。
德國哲學家阿多諾說:“對藝術的正當有效的主體反應是一種驚愕。驚愕由偉大作品所激發。驚愕不是接受者的某種受到壓抑并由于藝術的作用而浮到表面上來的情緒,而是片刻的窘迫感,更確切地說,是一種震動。在這一片刻中,他凝神于作品,心曠神怡,感到審美意象中顯現的人生真諦不再是虛無縹緲的,而是伸手可及。”[注]周憲編:《當代西方藝術文化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77頁。我們以為,這種驚愕和震撼恰恰是魯迅作品問世以后社會影響的真實寫照。《狂人日記》一經發表,立刻引起巨大反響,青年學生傅斯年熱情洋溢地向人們介紹,這“誠然是中國第一篇好小說”,并用象征性的語言宣告:“瘋子是我們的老師”,“我們帶著孩子,跟著瘋子走——走向光明去”。[注]孟真(傅斯年):《一段瘋話》,《新潮》第1卷第4號(1919年4月)。更能表達這種驚愕和震撼的是張定璜的《魯迅先生》,這是1925年1月《現代評論》連載的一篇全面評價魯迅的長文,其最有意義之處在于首次準確描述了魯迅出世前后中國精神文化界所發生的質變,他把魯迅的小說放在新舊文學分離的典型背景下,通過具體的事實,說明魯迅小說對中國文學所具有的開創性質。作者以極為形象和動情的文字寫道:“我若把《雙枰記》和《狂人日記》擺在一塊兒了,那是因為第一,我覺得前者是親切而有味的一點小東西;第二,這樣可以使我更加了解《吶喊》的地位。《雙枰記》等載在《甲寅》上是1914年的事情,《新青年》發表《狂人日記》在1918年,中間不過四年的光陰,然而他們彼此相去多么遠。兩種的語言,兩樣的感情,兩個不同的世界!在《雙枰記》、《絳紗記》和《焚劍記》里面我們保持著我們最后的舊體作風,最后的文言小說,最后的才子佳人的幻影,最后的浪漫的情波,最后的中國人祖先傳來的人生觀。讀了他們再讀《狂人日記》時,我們就譬如從薄暗的古廟的燈明底下驟然間走到夏日炎光里來,我們由中世紀跨進了現代。”隨即,他用形象生動的語言描繪道:“魯迅先生站在路旁邊,看見我們男男女女在大街上來去,高的矮的,老的小的,肥的瘦的,笑的哭的,一大群在那里蠢動。從我們的眼睛,面貌,舉動上,從我們的全身上,他看出我們的冥頑,卑劣,丑惡和饑餓。饑餓!”[注]張定璜:《魯迅先生》,載雷達編:《百年經典文學評論》,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極為敏銳地感悟到魯迅作品的特殊意義,并將這種對精神文化的感覺形象準確地描述出來,從而確定魯迅及其第一本小說集《吶喊》的歷史地位,張定璜的目光和判斷都是難能可貴的。魯迅確實是中國精神文化從中世紀跨進現代轉型期的代表作家,他把近現代知識分子對風起云涌的大時代的獨特體驗,轉化成了嶄新的藝術樣式,創作出一批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小說,他用文學的樣式,表達了這個時期先進知識分子所能達到的思想高度和認識深度。正因為如此,他的小說創作不僅開風氣之先,而且成為一座難以逾越的高峰。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帥和當年的同事、戰友,晚年的陳獨秀在獄中曾經對魯迅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作了總體評價,他說,首先必須承認,他在中國現代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他的中短篇小說,無論在內容、形式、結構、表達各方面,都超上乘,比其他作家要深刻得多,因而也沉重得多。[注]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載陳木辛編:《陳獨秀印象》,學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50頁。
三
還有一種情況較為普遍,即雖然不是首創者,但卻是真正的奠基者。也就是說,雖然新的創作風氣不是由他而開,但這一風氣卻是經過他的努力而真正走向成熟。這方面的突出代表是郭沫若的詩歌創作。
眾所周知,“五四”文學革命在創作實踐上是以新詩的創作為突破口的,新文化最重要的實績之一,就是以口語入詩,完成“吾手寫吾口”的任務。于是,現代文壇一時間風起云涌、詩潮澎湃。1917年2月1日,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陣地《新青年》在其2卷6號上率先刊出胡適的8首白話詩,這是中國現代詩歌運動中出現的第一批白話詩,1918年正月《新青年》4卷 1號又集中刊出胡適﹑劉半農﹑沈尹默等人的9首白話新詩。隨后《新潮》、《星期評論》等刊物也紛紛推波助瀾,而新文化運動的骨干如胡適、劉半農、周作人、沈尹默則成了聲名遠揚的第一批白話詩人,就連李大釗、陳獨秀、魯迅等對新詩并不多么感興趣的人也都寫過新詩。總之,這個時期嘗試新詩創作的人不少,但綜觀其創作成就卻不能過高評價。初期白話詩作的共同特點是:說理有余,抒情不足;注重真情實感的流露,缺少詩歌的升華和想象;強調新詩語言的更新,忽視了言詞的錘煉及其符號化功能;提倡詩體的破壞和解放,而對新詩詩學的建設則嚴重欠缺等等。總之,最初一批白話詩人的歷史貢獻和歷史局限是同位一體的,他們強調了“白話”,卻忽略了“詩”,正如我們對胡適詩作的評價,這些詩歌中有些作品幾乎就是分行排列的散文,還有的詩作則難以跳出舊詩的窠臼,成了一些所謂的“半放腳”體的過渡性的“未成品”。
真正完成這一過渡的是郭沫若,真正開辟了中國現代詩歌全新天地的是他的《女神》。《女神》雖然不是中國第一部白話新詩集,卻是中國舊詩與新詩分野的真正界碑,它徹底沖破了中國傳統詩歌的束縛,無論從內容上、形式上、觀念上、語言上,都表現出一種與傳統詩歌乃至近代詩歌創作形成鮮明差別的現代意識和現代形式。它以全新的精神和形式為“五四”時期的白話新詩取得了強力的突破,無論在境界和情趣上都躍上一個嶄新的臺階,從而有力地結束了新詩初創階段的稚嫩徘徊狀態,并成為中國新詩真正的奠基之作。正因為如此,《女神》出版后不久,聞一多就大聲疾呼:“若講新詩,郭沫若君的詩才配稱新呢!不獨藝術上他的作品與舊詩相去最遠,最要緊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時代的精神——二十世紀的時代精神。有人講文藝作品是時代底產兒,《女神》真不愧是一個時代的肖子。”[注]聞一多:《他的精神完全是時代的精神》,《創造周報》第4號(1923年6月3日)。
郭沫若在日本留學期間一項重要的活動便是大量閱讀外國文學名著。他曾一再說過,自己在高等學校學習期間,便不期而然地與歐美文學發生了關系,接近了泰戈爾、雪萊、莎士比亞、海涅、歌德、席勒以及北歐文學、法國文學、俄國文學等,這些優秀的作家作品無疑有效地滋潤了他,培育了他,賦予他獨特的精神氣質,并成為其文學創作最重要的基礎和背景。《女神》便鮮明地顯示出這一點,這部詩作具有濃郁的浪漫主義色彩,它從中外思想家和文學家——屈原、莊子、泰戈爾、釋迦牟尼、羅素、尼采、海涅、斯賓諾莎等人的著作中廣泛地吸取營養,其中斯賓諾莎的泛神論思想和惠特曼的詩風對《女神》的影響最為明顯。在《女神》中,熱情奔放的詩人完全按照自己的主觀想象去謳歌生活、描繪未來,對理想的熱烈追求與激情贊頌遠遠多于對黑暗現實的冷靜剖析和批判。但這種詩情畫意的浪漫主義并不脫離現實,而是深深植根于現實土壤之中。它那種毀壞一切、創造一切的狂飆突進精神,正是“五四”時期廣大民眾,特別是初步覺醒起來的青年知識分子的熱切愿望和強烈要求。
《女神》分為三輯,其中第二輯是詩作的主體部分,《天狗》、《爐中煤》、《地球,我的母親》、《立在地球邊上放號》等都是郭沫若詩歌中的名篇,是“五四”精神的詩化,也標志著“五四”詩歌所能企及的歷史高度,其中《鳳凰涅磐》是《女神》中的代表作,也是現代詩歌史上具有重要歷史地位的詩篇。《女神》對于祖國的頌揚,對于自我的肯定與贊美以及對反抗、叛逆與創造精神的歌唱,充分代表了當時青年知識分子的理想和追求,洋溢著濃郁的革命理想主義精神。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女神》眾多篇章中所表現出來那種囊括天地、氣吞寰宇、與整個人類和世界融為一體的氣魄和胸懷,那種試圖展現人類共同精神和共同情感的強烈渴望和追求,都是中國文學史上從未有過的文學意識,這也是《女神》屹立于現代文學史中具有獨特價值的地方。在表現手法上,與奔放流動的情感相一致,基本上采取了自由詩體,主要詩篇構思宏偉博大,運用了大量想象、夸張、反復等藝術手法,構成了濃烈的色彩。大膽的想象、形象的比喻、極度的夸張等浪漫主義手法,激昂的音調與急促的旋律,具有狂放的風格,開辟了自由體新詩空前的境界。在詩歌的形式上,詩人也進行了大膽的引進和創新,不僅成功地創造了不拘一格的自由詩體,還創造了把抒情與敘事巧妙結合在一起的詩劇形式,進而開創和拓展了詩歌創作的新領域。《女神》中50余首詩作,幾乎每一首都有自己的形式,少有重復;另一方面,郭沫若注重詩歌內在的情緒的節奏和每一首詩自身的韻律,因此每一首詩又都給人以齊整、和諧的統一感。從這個意義上說,五四時期能與《女神》相媲美的只有魯迅的《吶喊》,因此文學史家把這兩部作品稱為照耀那個時代的“雙星”。如果說,魯迅用他深邃的小說冷靜地解剖和展現著黑暗的現實,希望引起療救的注意;那么,郭沫若便是用他激情的詩歌熱烈地呼喚著希望的明天,希望導致光明的到來:
我們更生了。/我們更生了。/一切的一,更生了。/一的一切,更生了。/我們便是他,他們便是我。/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我便是你。/你便是我。 /火便是鳳。/ 鳳便是火。/翱翔!翱翔!/歡唱!歡唱!//我們光明,我們新鮮,/我們華美,我們芬芳,/一切的一,芬芳。/一的一切,芬芳。/芬芳便是你,芬芳便是我。/芬芳便是他,芬芳便是火。/火便是你。/火便是我。/火便是他。/火便是火。/翱翔!翱翔!/ 歡唱!歡唱![注]郭沫若:《鳳凰涅磐》,載《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選》,山東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65頁。
這是一個理想的夢境,這是一個青春的理想:舊的世界被毀滅了,鳳凰在灰燼中奮然更生,一個充滿新鮮、凈朗、華美、芬芳、熱誠、摯愛、歡樂、和諧、光明、生動、自由、雄渾、悠久的新天地終將到來,而這正是詩人最最渴望、期盼并熱切呼喚的,郭沫若曾經說過,《鳳凰涅磐》“是在象征著中國再生”。這種朝氣蓬勃、熱血沸騰、充滿著青春活力的美麗詩句,這種燃燒著對一切舊秩序、舊傳統、舊禮教的大膽否定和無情詛咒,這種山呼海嘯般禮贊創造與光明、民主與進步的理念和情懷,激動、振奮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奔向新中國的青年。
《女神》以其出色的成就成為中國現代詩歌史上最重要的詩集之一,它的嶄新的自由體形式、恢弘的想象力和強大的創造力,都標志著白話新詩已完全掙脫了舊體詩的藩籬,開始進入創造自己經典化成熟作品的歷史階段。郭沫若多次說過,《女神》之后他就不再是詩人了,確實他再也沒能寫出像《女神》一樣的詩歌,當然,別人也未能做到,從這個意義上說,《女神》成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絕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