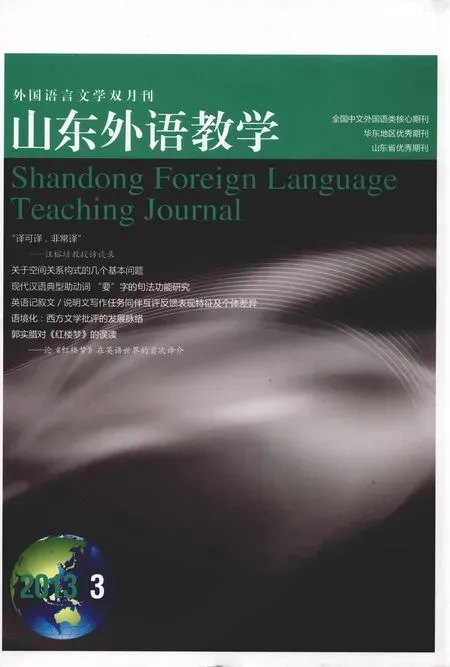婦女主義視角下的新現實主義
——透視艾麗斯·沃克的小說批評尤蕾
(南京郵電大學外國語學院,江蘇南京 210046)
婦女主義視角下的新現實主義
——透視艾麗斯·沃克的小說批評尤蕾
(南京郵電大學外國語學院,江蘇南京 210046)
艾麗斯·沃克的小說批評多見于其散文集,尤其是批評文集《尋找我們母親的花園:婦女主義散文》中,涵蓋了藝術與生活、小說的人物、小說的視角、小說的功能、小說的語言等重要方面。本文對沃克的小說批評進行了梳理和歸納,認為沃克的小說充分體現了社會意識和審美意識的結合,屬于美國新現實主義一派,同時,其獨特的婦女主義視角決定了沃克對題材和素材的取舍,也影響了她對小說形式結構的選擇。
艾麗斯·沃克的小說批評;婦女主義;新現實主義
1.0 引言
艾麗斯·沃克的小說批評多見于其散文集,尤其是批評文集《尋找我們母親的花園:婦女主義散文》中。這本集子的副標題首次明確提出“婦女主義”(womanism)一詞——其作品解讀的重要索引。但僅用“婦女主義”來概括沃克的小說創作,是否過于簡單化?在《非洲裔美國黑人小說及其傳統》一書中,伯納德·貝爾對沃克小說創作的評述,在筆者看來,是十分中肯的:
通過探索南方黑人妻子、母親、女兒所受的壓迫和頌揚她們的勝利(因為她們彼此十分相關,勝于同工人階級男人的關系),沃克裁剪了批判現實主義的傳統,使之適用于民間傳奇,并加強了非洲裔美國黑人小說中黑人女權主義的主題。(貝爾,2000: 325)
這段話為沃克的小說創作勾勒出了一個清晰的脈絡。首先,批判現實主義是沃克小說創作的基礎。沃克的作品關注現實,尤其是黑人婦女的生存境況,帶有濃厚的社會批判意識。其次,沃克突破了傳統現實主義的界限,在作品中糅合了現代主義、浪漫主義、甚至魔幻主義等成分,不僅豐富了作品的表現手段,還借此傳達了沃克對黑人族群的期許。正是這樣的突破使她成為新現實主義的代表作家。最后,則是貫穿其作品始終的婦女主義。沃克的婦女主義文集《尋找我們母親的花園:婦女主義散文》如今已成為黑人女性主義的經典。與巴巴拉·史密斯的《邁向黑人女性主義批評》、芭芭拉·克里斯汀的《黑人女性主義批評:黑人女性作家評論》、貝爾·胡克斯的《女權主義理論:從邊緣到中心》以及德波拉·麥克道威爾《黑人女性主義批評的新方向》等一起,共同建構了黑人女性主義批評傳統。沃克的作品則是其婦女主義理論的形象載體。可以說,婦女主義決定了沃克對題材和素材的取舍,也影響了她對小說形式結構的選擇。
2.0 藝術是生活的真實再現
沃克認為,藝術可能是“唯一一面可以讓我們看見自己真實的集體面容的鏡子”。(凌建娥,2005)這句話讓人聯想起莎士比亞著名的“鏡子論”,以及始于亞里士多德、且在西方文論界綿延數千年的“摹仿說”。沃克延續了現實主義的傳統,其作品基于現實,筆觸深入人物內心,是作者生活體驗的結晶。
“真實的集體面容”涉及小說諸要素之一的人物。藝術的真實離不開人物的真實。沃克十分欣賞美國南方女作家弗萊納里·奧康納的小說藝術,尤其稱道她作品中對南方人的逼真再現。“……這些沒有木蘭香氣的白人(他們對這種樹的存在毫不關心),和這些沒有西瓜也沒有極好的種族忍耐力的黑人,這些人像足了我所認識的南方人。”(Walker,1983:52)奧康納的小說中沒有刻板形象,“她用即將來臨的死亡來觀照人物——就像她也是如此觀照自己一樣——無論他們有著怎樣的膚色和社會地位”。(同上:54)她捕捉的是人性,呈現的也是這一最本質的東西,既不受成見和偏見的影響,也不回避人性的缺陷。同樣,沃克在創作中也力求表現人物的真實性和復雜性。“很少能用一個詞來概括一個人的生活;即使那個詞是黑或白。藝術家的職責在于如實展現那個人……盡可能逼真地重新塑造那些處于至善和至惡之間廣闊地帶的人們。”(同上: 137)真實在沃克是第一位的,更勝于意識形態,這也是她的作品備受爭議的原因之一。沃克的第二部長篇小說《梅麗迪安》再現了20世紀60年代的黑人民權運動,并將其批評的焦點指向書中的某些黑人活動家。這些人和很多白人男性一樣,也充滿了種族偏見,不同之處在于他們將所有黑人等同于善,將所有白人等同于惡。沃克抨擊的正是這種基于意識形態的偏見。她塑造的一些負面的黑人男性形象,如《格蘭奇·科普蘭德的第三生》中的布朗斯菲爾德,《紫顏色》中的繼父和某某先生,取材于真人真事。黑人婦女在自己的族群中飽受性別歧視和壓迫,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任何掩飾和美化都有違沃克的創作原則。《擁有快樂的秘密》是一部揭露非洲女性割禮的小說。黑人美學運動和民權運動中人們喊出的口號“黑的就是美的”,無疑將非洲理想化了。但沃克的故事卻將非洲傳統文化愚昧落后的一面暴露在世人面前,這一大膽的去魅引來一片指責。作為有著深切人文關懷的藝術家,沃克對真相的追問遠遠超出了對禁忌的規避。正如她在創作中敢于直面黑人內部的性別歧視問題,她也敢于正視古老非洲沿襲下來的陋習。支撐著她的正是她對“真實”的藝術原則的恪守和堅持。
人物的真實更多地體現在沃克對黑人女性的再現上。長期以來,美國文學作品中的黑人女性局限于妓女、生育機器、保姆,或凄慘的白黑混血兒這幾種符號化的形象。因此,黑人女作家不得不投入到“一種修正性的使命中,其目標在于以現實來代替刻板形象”。(Thomas,2007)實際上,早在20世紀20年代的哈萊姆文藝復興時期,阿蘭·洛克(Alain Locke)就已提出“新黑人”一說,這一時期的黑人作家,包括圖默(Jean Toomer)、休斯(Langston Hughes)、赫斯頓(Zora Neale Hurston)在內,都致力于重新闡釋和塑造黑人自我形象。沃克筆下的黑人女性,如同前者的一樣,是“一種更為貼近自我的再現”。(王曉路,2005)第一部短篇小說集《愛情與煩惱:黑人婦女故事集》中,沃克就已“下意識真誠地探索黑人婦女生活的面貌和恐懼”。(凌建娥,2005)沃克筆下的女性形象鮮明,性格各異,充滿生活氣息。為了反映她們的真實面貌,沃克在體裁的選擇上也頗具匠心。《紫顏色》刻畫了20世紀初掙扎在社會最底層的美國黑人婦女的生活原貌和心路歷程。全書采用書信體,以樸素的文字、真摯的情感和生動的黑人土語記錄了黑人婦女們當下的生活,記錄了她們“所受的壓迫、瘋狂、忠誠和勝利”。(Walker,1983:250)書信體常帶有紀實性,往往是社會文獻和歷史書寫的寶貴資源;同時它也是一種特殊的文體,常給人帶來時間上的錯覺,讀者感到敘事人講述的不是已發生,而是正在發生的事,流露的是最本能、最真實的情感和思想。
3.0 日常生活美學
然而,沃克筆下的真實超越了鏡像式的真實。她曾對比美國黑人和白人的作品,指出白人作家傾向于以人物的死亡作為故事結局,留給讀者的是一個失敗者的沮喪形象;而黑人作家卻很少會讓人物終止奮斗,故事的終場常常跳動著希望的音符。因此沃克將希臘神話中的西緒福斯視為黑人的象征。正是這種在逆境中永不放棄的堅強和勇敢,被沃克視為種族健康、完整和幸存的基石,這也是她在赫斯頓的作品中體會到的最典型的品質:“種族健康,一種將黑人視為完整的、復雜的和不被貶損的人類的認知,一種在黑人創作和黑人文學里面缺乏的認知。”(Walker,1983:85)沃克尤其欣賞赫斯頓民間故事集《騾子和人》,故事中的黑人總是革新者和創造者,身上沒有一絲失敗者的影子。而這樣的似乎只會在神話和史詩中出現的“英雄”,又出自哪里?
在“講述一個至關重要的故事:艾麗斯·沃克的《尋找我們母親的花園》”一文中,勞瑞·麥克米蘭指出沃克的這部文集中3篇文章的題目,“超越虛榮”、“尋找佐拉”,以及“尋找我們母親的花園”全都暗含著探尋這一主題,暗示了作者對美國文學現狀的不滿。(McMillan,2004)為了挖掘和書寫隱藏在黑人現實和歷史深處的東西,沃克將其視線投向了黑人的日常生活,“向低處看”是沃克的一條重要美學原則:“她講述普通生命的簡簡單單的故事,但這些故事卻是為了集體幸存而寫的。”(同上)沃克的小說中沒有建功立言的宏大敘事,有的是點點滴滴普通人的生活片段,在充滿著“房子、母親、花園”這類看似庸常的意象的作品中,漸漸凸顯的是“一幅重新描畫過的社會地圖”。(同上)這幅地圖下涌動的正是黑人民族精神的激流——逆境下抗爭的勇氣、智慧、寬容和關愛,是種族幸存不可缺少的力量。沃克曾經這樣來批評以賴特(Richard Wright)為代表的“抗議文學”:表面的東西——一度成了——最深邃的現實,取代了集體潛意識的靜靜的水域。(Walker,1983:262)“最深邃的現實”觸及的是黑人民族的靈魂,是黑人想象和文化所體現的持久的精神力量。白人文化以書面形式傳播,黑人文化則以口耳相傳的方式流傳,他們的創造力在普通黑人的日常生活中,尤其是黑人婦女講故事、縫制百衲被、做園藝、烹飪等日常活動中得到體現。
收于短篇小說集《愛情與煩惱》中的《漢娜·肯赫夫報仇》,其故事靈感來源于沃克自己母親——一名普通黑人鄉村婦女——的親身經歷:“我不但已經吸收了這些故事本身,而且吸收了她(母親)講述故事的方法,那種認識到她的故事——如同她的一生一樣——必須記錄下來的緊迫感。”(Walker,1983:240)
沃克記錄的正是普通黑人婦女的歷史。與傳統現實主義創作不同的是,沃克著意表現了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美、優雅和尊嚴”,人物的身上多了悲劇和史詩的崇高,多了幾分傳奇色彩。在《梅麗迪安》、《寵靈的殿堂》、《擁有快樂的秘密》中,沃克將女性主人公置于傳統男性英雄的位置上。神話中的男性英雄讓位于女性,是一個“重要的原型事件”。通過重新界定英雄這個角色,沃克改變了社會對女性的觀感,而作家自己則成為那些鼓勵婦女潛力的神話的仲裁者。(Campbell,1998:IV)沃克對歷史也有著獨到的理解。她把《紫顏色》稱為一部歷史小說,但這部歷史又與眾不同,是從一個再普通不過的日常場景寫起:一個女人向另一個女人索要內衣。這個特別的形象“是在進行一種分享,是在開啟一種交流,是在將家庭主題中最樸實無華的事物化為一個震撼世界的時刻”。(伯科維奇,2005:531)這種升華性的瞬間在沃克作品中比比皆是。那些被稱為“世間的騾子”的黑人婦女,例如短篇小說《外婆的日用家當》中的母親,當她從大女兒手中奪過祖傳的被子,放在小女兒的懷中時,讀者看到的是她粗陋的外表下那顆睿智的心靈,就像是黑人的苦難歷史織就的一幅動人的畫卷。沃克的眾多作品,無論是結局洋溢著理想主義色彩的《紫顏色》,還是被沃克自己稱為“羅曼史”的《寵靈的殿堂》,都是對傳統現實主義的超越。它們跨出了社會學、解釋性寫作和統計數據的小圈子,邁入了神秘、詩意和預言。(Walker,1983:8)沃克擅于賦形式于想象,去傳達本質的和永恒的東西。其實這在黑人作家群中并不罕見,戴維斯和萊丁在《行列: 1760年至今的美國黑人寫作》一書中指出,“美國黑人作家在其作品中,將布道與禱告相結合,現實與夢想相結合,現狀與期盼相結合”。(Fryar,1990)長久以來,美國黑人作家肩負著對藝術和對種族的雙重責任,社會意識深深融入了審美意識之中。
4.0 婦女主義
沃克認為,作家應該“寫自己想讀的那種書”。“當托尼·莫里森說她寫的是自己想讀的那種書,她是在承認著這樣一個事實:在我們社會里,所謂‘被大眾接受的文學’常常是性別主義的,種族主義的,要不就是對眾多生命而言毫不相關甚或是冒犯的,因此她必須身兼二職——作為關注、創造、學習和實現這種模式(即她自己)的藝術家,同時她必須是她自己的模式。”(Walker,1983:8)
如果說“自己的模式”需要從黑人女性的現實生活中提取,那么應該“關注、創造、學習和實現”的那種模式又從何而來?顯然,沃克在白人的文學傳統中很難找到共鳴。在她看來,黑人不可能完全認同白人的藝術創作,后者作品中或隱或顯的無論是向外還是向內的殖民主義(指種族主義)都會影響黑人的閱讀愉悅。其次,沃克對眾多的黑人男性作家同樣無法認同:“很多‘主要’作家——常常是男性的作品——很少寫到黑人的文化、歷史,或者未來、想象、幻想等等,卻對一個非特定的白人世界里的、孤立的往往未必確定的、范圍有限的沖突寫得很多。”(范革新,1995)不滿于白人作品中的種族偏見和黑人男性作家對黑人世界的回避,更不滿于大批文學作品對黑人社會和文化的病理性解讀(即將其視為貧窮、愚昧、政治和文化地位上低人一等的代名詞),沃克將目光轉向過去,轉向有待發掘的黑人女性文學,并試圖建立一個黑人女性的文學傳統。沃克認為,黑人女作家“不僅僅要去贏得新世界,還須找回被遺忘的舊世界。無數個已消失和被遺忘的女性渴望著對她說話——從弗朗西斯·哈珀、安·斯賓塞到多蘿西·韋斯特——但她必須努力去找到她們,把她們從被忽略被噤聲的境地(由于她們既是黑人又是女性的身份)中解放出來”。(Walker,1983:36)沃克在這一文化考古過程中,發現了一個煥發著精神力量的母系傳統,無論對族群身份的認同,還是對種族自尊的樹立,它都是不可或缺的。
正是在這幅被重新發掘的版圖上,沃克找到了她的模式——佐拉·尼爾·赫斯頓的模式。“讀她的(赫斯頓的)作品時,我才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化,認出它是那個樣子,它的幽默總是努力地試圖與痛苦保持平衡,我覺得似乎,的確,它給了我一張指向我文學之國的地圖……”(轉引自王曉英,2008: 70)
哈萊姆文藝復興時期,赫斯頓就和休斯、喬治·舒勒(George Schuyler)等人一起,撰文表現理想化的文學主題、文化身份和心理重建等問題。他們的創作成為后來的文學理論家創建理論賴以依存的經典話語。(李權文,2009)赫斯頓的作品再現了美國黑人的民俗文化,追溯其非洲文化之根,傳遞種族健康的品質,正因為它們體現了黑人民族精神的精華,而成為沃克文學創作的坐標。挖掘某個族群的文化和文學傳統,既是一名作家建立個人創作模式的需要,更是一個族群精神生存的需要。赫斯頓的小說,特別是代表作《他們眼望上蒼》以其濃厚的南方黑人文化和黑人女性特有的語言、形象和象征深深影響了沃克。沃克的作品,無論從主題和形式上,都是對這位她稱之為“精神向導”的文學先輩的致敬。當代美國黑人批評家小蓋茨(Henry Louis Gates Jr.)就曾明確指出:沃克的代表作《紫顏色》是對《他們眼望上蒼》的“認祖歸宗”之作。如今,《紫顏色》已成為“黑人婦女小說的一種格式”。(伯科維奇,2005:531)可以說,沃克的“婦女主義”模式,正是將赫斯頓的作品作為黑人女性寫作的范本,建構出來的現代黑人婦女文學的經典模式。
上世紀80年代,黑人女性主義美學逐漸取代了以男性為主導的黑人民族主義美學。沃克的婦女主義是黑人女性主義理論構建過程中的里程碑。在《尋找我們母親的花園:婦女主義散文》一書中,沃克對婦女主義者的定義是激進的:她們“蠻橫、剛毅、勇敢或倔強”,她們“熱愛其他婦女,不論是否有性含義”,她們“力求包括男性和女性在內全民族的生存和精神完整”……(Walker,1983:xii)顯然,沃克致力于塑造那些經歷了女性意識和族群意識的雙重覺醒,自立自強、互相關愛的黑人婦女形象,致力于建構一個黑人民族兩性和諧的理想社會。換句話說,婦女主義體現了女性主義的多元性,提供了一種“既看中心也看邊緣”(胡克斯,2001:9)的視角。它既從種族的視角去審視女性主義研究,又從性屬的視角去審視黑人研究,以差異性的表述——即匯合了種族、性屬、階級的多聲話語——拓展了二者,是黑人婦女獨特的文化經歷在美學上的表述。這樣的表述是以何種形式呈現在沃克的作品中的呢?
首先是敘事的碎片化。少數族裔身份、后現代思潮的影響、非洲價值觀的滲入,都在推動著沃克的實驗性寫作。“去中心”是她常用的寫作策略,這使她的作品常常以碎片的形式呈現。如何讓這些碎片綴成一幅有意義的圖景?沃克的靈感來自于女性、尤其是黑人女性的日常用品——百衲被。
百衲被的歷史見證了一部發展中的婦女文化史,作為女性美學的象征,它對女性文學,尤其是女性小說的形式和結構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對黑人婦女而言,縫被子既是她們的生存策略,又反映了她們為孤立的黑人女性尋求整體性和為離散的黑人同胞建立和諧的整體做出的努力。(李靜,2008)縫被子的場景出現在《紫顏色》中,成為黑人姐妹情誼的粘合劑;《外婆的日用家當》中的兩床百衲被是故事的中心意象,連綴著黑人的歷史和現實,也連綴著幾代黑人婦女的情感經歷;《尋找我們母親的花園》中,承載著母親們的創造力的百衲被成為黑人女性精神傳統的象征。
除了在情節上借百衲被來書寫黑人女性的生活,沃克在其小說結構上也借鑒了百衲被的結構。小說結構的碎片化處理是沃克常用的寫作策略。美國當代黑人文論家休斯頓·A·貝克指出,百衲被上的“一塊補丁就是一塊碎布片。它是一件完整物品的遺骸,既是破損的標志,又對新的創造設計提出挑戰。作為殘留物或幸存者,碎片可以象征破裂和消亡,也可以代表已經逝去的榮耀,同時,它還富有可待探尋的潛在意義”。(轉引自王曉英,2008: 156)這段話體現了兩層意思:一是百衲被結構反映了沃克的哲學觀——整體觀;二是它體現了沃克的創作特色——對話性和開放性。
縫被子這個活動跨越了種族、地域和階級的界限,暗合了婦女主義提倡的多元文化理念。美國黑人文化、非洲傳統文化、美國白人文化就像那些質地、圖案和顏色迥然各異的碎布片一樣,組合成為多種族、多民族和諧共存的畫面。同時,百衲被是由看似毫無價值的歷史碎片組成的有機整體,象征著創作者對歷史記憶的挖掘、整理和組合,是非洲移民作為散落民族的整體形態的表征。正因為此,加之它以碎片形式呈現完整藝術效果的功能,“百衲被式”的敘事藝術常常受到非裔美國女作家的青睞。沃克的多部作品都采用了多元敘述視角、多聲部敘述聲音和拼貼的敘事結構:如《梅麗迪安》、《父親的微笑之光》、《寵靈的殿堂》等。
百衲被上碎片與碎片之間是一種平等對話的關系,而非主客對立關系。沃克的小說常常呈現出一種內在的對話關系,如不同時空、不同意識形態、不同聲音、不同文類之間的對話。她的大多作品具有“復調”特點,它們吸收了非洲口頭傳統的對話模式,在作者、敘事者和讀者之間,在不同文類之間,甚至在不同作品之間形成一種召喚應答式的互動。芭芭拉·克里斯汀認為:“沃克的作品是一個持續的整體,對她來說,寫作是與各種各樣的觀眾交流,人類和非人類,現在的和過去的,同時也是一種療傷的過程。她常常在各種文類中探索顯然是相似的思想、情感、意象;她對某種形式的運用,比方說隨筆,有時候會與她以前寫的一首詩或一則短故事互為補充,形成對話。”(Christian,1989)除了橫向的聯系之外,沃克的作品也體現了縱向的延續性,即傳統與個人的對話。蘇珊·威利斯認為,當代黑人女作家的小說在多種層次上抵制了資產階級小說中孤獨個體的傾向(轉引自王曉英,2008:123),它們重視紐帶關系,反對個人主義導致的情感萎縮。對美國黑人而言,傳統不僅僅指黑人文化和文學傳統,也包括白人傳統。《我父親的微笑之光》包含了多種傳統西方文類,如羅曼史、社會風尚小說、神話、甚至是敘事詩。創作于2004年的長篇小說《打開你的心靈》,互文色彩強烈,那條伴隨女主人公精神成長的科羅拉多河讓人想起馬克·吐溫《哈克貝利·芬歷險記》里的密西西比河,主人公人到中年的迷惘和探尋延續了但丁的《神曲》主題,同時遵循了西方探尋故事傳統。
除了碎片化的敘事手段,沃克對語言的選擇同樣獨具匠心。文學不僅是對現實的反映,同時也是語言的建構。文學作品說到底是一種語言藝術。小蓋茨就將非裔美國文學視為一種語言行為。(Fryar,1990)作為對標準英語語言的置換,黑人土語在沃克的創作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基于共同現實和心理意識的黑人語言,“是組成我們的身份和我們無論好壞的經歷的固有的成分。而且,令人稱奇的是,它支撐著我們,比天使的臂膀還要安全”。( Roden,1999:464)
黑人土語具有豐富的美學價值。在“來自一次訪談”一文中,沃克再一次提到了赫斯頓,“佐拉不辭辛苦地捕捉鄉村黑人表述的美。在其他作家只看到學習英語的失敗(指黑人的非標準英語)時,她看到了詩意”。(Walker,1983:261)有評論者認為,赫斯頓之后的作家鮮有象沃克在《紫顏色》中那樣如此成功地表達了民間語言的精髓。(Richardson,1999:8)小說中大量使用黑人方言,充分表達了黑人語言的美和生動。
更為重要的是,黑人土語也是包括沃克在內的黑人作家用來消解主流話語的重要工具。它以一種差異性的重復,改寫了白人的標準英語及其內含的價值觀。負載著黑人文化及其價值觀的語言,就像黑人的布魯斯音樂一樣,是“一種差異性的文本形式,并由此證實了黑人文化的社會性存在”。(程錫麟、王曉路,2001:212)
黑人傳統抗爭式的文學語言突出體現在其“表意”(signifyin(g))性上。源于非洲神話傳統,并融合了黑人民俗特點的黑人表意,指向無止境的闡釋行為。小蓋茨是這樣來定義它的:表意對于過去構成一種闡釋、一種變化、一種修正、一種擴展,它是“我對文學史的隱喻”。(轉引自王莉婭,1997)
除了借用黑人音樂——爵士樂,特別是布魯斯富于重復與變化的形式與結構——之外,隱喻性的語言成為非裔美國作家主要的表意性實踐。例如,《紫顏色》常常給人留下這樣的閱讀體驗,即:這個特別的書名始終象一個問號似地浮在讀者的腦海中。作為全書最重要的象征,“紫顏色”有著多重寓意。《紫顏色》發表后僅一年,《尋找我們母親的花園》問世了。在這本集子的扉頁,沃克詳細地定義了婦女主義者一詞,其中最后一條是這樣的:婦女主義者之于女性主義者,就像是紫色之于淡紫色。(Walker,1983:xii)與白人女性主義同源而異質,紫色,既蘊含著生命禮贊的情感迸發,又閃耀著黑人女性主義理論的理性之光。它將“黑人體驗的詩一般的美、奇跡和痛苦”(孫薇、程錫麟,2004)提煉成雋永的意象,穿梭在沃克的多部作品之中。“紫顏色”這個能指對應著無限的所指,是跳動在黑人男性和白人女性主義美學表述之間的變奏曲。
這種象征性的語言尤其適用于呼吁社會變革的寫作。南希·米勒認為,“應該十分認真地把隱喻看作是一種經濟的方法,它跳出了種種單一的體系去建構理論,同時又借助語言來想象那些尚未成為社會存在的事物”。(Miller,1991:xiii)一方面,這樣的語言挑戰了主流思想,具有潛在的顛覆性;另一方面,作者帶有理想主義精神的文學介入,使故事平添了預見性的色彩。社會大同的理想貫穿在沃克的寫作中,貫穿在她激進的行動主義中,既是她標志性的理論符碼,又是她身體力行、尋求消除統治和改變社會的勇氣源泉。因此沃克的作品又有著道德上的訴求,從形式到內容上都滲透著她本人的道德理想。無論是前期作品對社會問題、尤其是對黑人婦女生存狀況的揭露,還是后期作品對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的關注,沃克始終以一種強烈的責任感,聚焦于人類真實的道德狀況。其作品常帶有深切的社會批判意識。沃克的婦女主義思想核心是“愛”,正是在對人類對自然的愛的驅動下,沃克將其行動主義精神灌注在藝術創作之中,鑄成了以“反性別主義、反種族主義、非洲中心主義、人道主義”(劉戈、韓子滿,2004)為中心的婦女主義理想。
沃克通過其小說批評及實踐,建構了婦女主義文學傳統和模式,豐富了文學創作的表現手段,為美國文學的經典重構提供了重要參照。其文學批評思想是美國黑人批評中的重要一環,也是美國文學批評研究者們不可錯過的篇章。
[1]Campbell,N.Alice Walker:Redefining the Hero[D].Floria Atlantic University,1998.
[2]Christian,B.Conversations with the universe[J].The Women’s Review of Books,1989,6(5):9-10.
[3]Fryar,I.B.Literary Aesthetics and the Black Woman Writer[J].Journal of Black Studies,1990,20(4):443-466.
[4]McMillan,L.Telling a critical story:Alice Walker’s In Search of Our Mothers’Gardens[J].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2004,28(1):107-123.
[5]Miller,N.Getting Personal:Feminist Occasions and Other Autobiographical Acts[M].New York:Routledge,1991.
[6]Richardson,C.M.Zora Neale Hurston and Alice Walker: Intertextualites[D]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1999.
[7]Roden,M.Alice Walker[A].In E.S.Nelson(ed.).Contemporary African American Novelists:A Bio-Bibilographical Critical Sourcebook[C].Westport:Greenwood Press,1999.459-467.
[8]Thomas,G.D.Spirituality,Transmi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by Octavia Butler’s Kindred,Phillis Alesia Perry’s Stigmata,and Alice Walker’s The Temple of My Familiar[D].Temple University,2007.
[9]Walker,A.In Search of Our Mother’s Gardens:Womanist Prose[M].Orlando:Harcourt Inc.,1983.
[10]貝爾·胡克斯.女權主義理論:從邊緣到中心[M].曉征、平林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
[11]伯納德·貝爾.非洲裔美國黑人小說及其傳統[M].劉捷等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12]程錫麟,王曉路.當代美國小說理論[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1.
[13]孫薇,程錫麟.解讀艾麗斯·沃克的“婦女主義”——從《他們的眼睛望著上帝》和《紫色》看黑人女性主義文學傳統[J].當代外國文學,2004,(2):60-66.
[14]范革新.又一次“黑色的”浪潮——托妮·莫里森、艾麗斯·沃克及其作品初探[J].外國文學評論,1995,(3):69-74.
[15]李靜.“被子”在艾麗絲·沃克作品中的意義[J].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8,24(1):27-30.
[16]李權文.從邊緣到中心:非裔美國文學理論的經典化歷程論略[J].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4):85-91.
[17]凌建娥.愛與拯救:艾麗斯·沃克婦女主義的靈魂[J].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2005,(1):110-113.
[18]劉戈,韓子滿.艾麗斯·沃克與婦女主義[J].鄭州大學學報(哲社版),2004,37(3):111-114.
[19]薩克文·伯科維奇.劍橋美國文學史(第七卷)[M].孫宏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
[20]王莉婭.黑人文學的美學特征[J].北方論叢,1997,(5):96-97.
[21]王曉路.表征理論與美國少數族裔書寫[J].南開學報(哲社版),2005,(4):33-38.
[22]王曉英.走向完整生存的追尋——艾麗絲·沃克婦女主義文學創作研究[M].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8.
Neorealism with a Womanist Perspective:Alice Walker on the Novel
YOU L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Nanjing 210046,China)
Alice Walker’s views on the novel are mostly available in her collections of essays,especially in her critical collection In Search of Our Mothers’Gardens:Womenist Prose,covering such vital aspects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 and life,th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as well as the perspective,the function,and the language of the novel.This paper attempts to sort out and summarizes Walker’s views on the novel.The argument here is that Walker’s novels fuse social consciousness with aesthetic consciousness,falling into the school of American Neorealism,while her unique womanist perspective determines not only her selection of subjects and materials,but also her choice of forms and structures.
Alice Walker’s views on the novel;Womanism;Neorealism
I106
A
1002-2643(2013)03-0094-06
2012-07-09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20世紀非裔美國文學批評研究”(項目編號:11BWW056)的階段性成果。
尤蕾(1971-),女,漢族,江蘇吳江人,副教授,碩士。研究方向:美國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