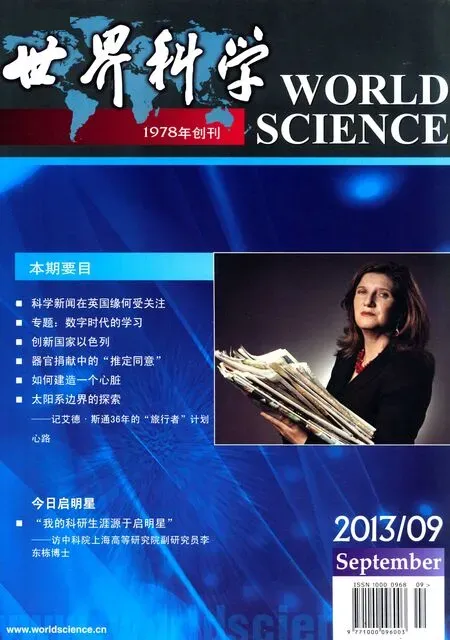創新國家以色列
方陵生/編譯
創新國家以色列
方陵生/編譯
● 在高科技創業方面,以色列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如今,在生物技術領域,以色列正在向一個強大而先進的生物技術產業群邁進。
2010年,前葛蘭素史克公司和諾華公司行政主管丹尼爾·特佩爾(DanielTeper)來到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與該校制藥學院院長西蒙·貝妮塔(Simon Benita)見面。特佩爾對后者的給藥技術商業化非常感興趣,之前,他倆有過一次成功的合作——在法國創辦了眼科生物技術公司Novagali——這次,特佩爾決定將新創辦的企業建立在以色列。
作為一個曾與以色列許多公司有過密切合作的美國人,特佩爾說道:“我對以色列的創新環境和創業精神非常熟悉。”他知道,與美國或歐洲相比,以色列的創業啟動成本低很多,并且擁有一批熱心的投資者。“以色列人均風險投資資本非常可觀,他們以前是這么做的,如今更有意再投資于其他的產業。”
僅在幾個月時間里,特佩爾就在特拉維夫北部建立起了IMMUNE制藥公司,500萬美元啟動資金主要來自以色列的投資者,并獲得了貝妮塔公司的技術許可。如今,IMMUNE公司擁有單克隆抗體的藥物傳遞技術和進入臨床二期的炎癥性腸病的世界領先候選藥物。“在以色列做研究更有效率,投入的每一美元,都會為我們賺回更多的錢。”特佩爾說道。
事實上,特佩爾并不是唯一感受到以色列生物技術巨大推力的人。據以色列工業部稱,以色列生命科學公司的數量已從 1996的186家猛增到2012年的1100多家。相對于以色列的700萬人口,這是一個相當龐大的數字。在與生命科學領域相關的公司中,以色列醫療設備公司幾乎占了其中的50%,人均醫療設備專利為全球第一,人均生物制藥專利也僅次于美國。
過去15年是以色列生物技術的孵化期,在此期間,企業家們致力力學習如何駕馭生命科學這一新生事物,以色列先進技術產業組織(IATI)聯合主席本尼·澤維(BennyZeevi)說道。如今,有60家以上公司的產品已進入臨床二期或三期,澤維認為,這已遠遠超過以色列以往歷史記錄,“以色列的生物技術發展正處于突破性邊緣的十年。”
傳統與自主創新相結合
以色列的生物技術淵源可以追溯到1901年成立的Teva制藥公司,當時Teva只是一家以進口藥物為主的企業。如今,Teva不僅是以色列最大的制藥公司,也是全球十大制藥公司之一。雖然Teva以生產非專利藥物而聞名,但它致力于將以色列本國研制的新藥推向市場,包括治療多發性硬化癥藥物Copaxone,以及治療帕金森氏癥藥物Azilect等。
Teva的成功給以色列生物技術的發展帶來了深遠的影響,例如,保護和維護本國生物技術于它的羽翼下,培養本國的管理人才等。希伯來大學伊薩姆技術轉讓公司總裁亞科伊·米切林(Yaacov Michlin)認為,以色列生物技術成功的關鍵先是開辦小公司,然后引起大型制藥公司的關注。
“在我與同事們的交流中,幾乎每個人都有創新熱情,每個人都想創造出一些新的東西,”特拉維夫癌癥診斷公司首席技術官阿迪·艾爾凱勒斯(Adi Elkeles)說道,“以色列小公司數量之多非常驚人。”以Pluristem公司為例,其擁有員工140人,幾種胎盤細胞療法已進入臨床二期,其中包括兩種用來治療罕見疾病的藥物,可望在不久之后進入三期臨床。而BioLineRx,公司只有50個員工,但已有6種藥物進入了臨床試驗階段。
業內人士一致認為,為這些公司提供創新源泉的是以色列的一些醫學中心和七所大學,其中包括希伯來大學、魏茨曼科學研究所和特拉維夫大學等,而且由這些機構開發的7種重要藥物都已投放市場。
學術界的創新,同樣離不開精明的商人,這一點以色列并不缺乏。據以色列2009年出版的一本暢銷書中記載,以色列在高科技行業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創辦了成千上百家軟件公司和通信企業。“如果你經常看報紙,你就會發現,幾乎每個星期都會出現某個新的公司,由此創造了一種特別的氛圍,讓你產生一種也想加入其中的激情。”Oramed制藥公司首席執行官納達維·基德隆 (NadavKidron)說道。
在創辦這家公司之前,基德隆是一名沒有任何生物技術經驗的律師。對于自己成為生物科技公司的高管,基德隆認為,包括自己在內的許多人將目光投向科技公司,緣于以色列發展空間和將商品出售給周邊國家的能力有限,而高科技產品可較為容易地轉讓或銷售到其他國家。
最重要的是,以色列生物技術部門有政府研發基金的注入,每年有3億美元的預算,分配給500家公司提出的約1000個項目。例如,一個聯邦孵化器計劃給志在創業的企業家,甚至只是一個創新想法的人提供42.5萬~68萬美元的啟動基金(這筆資金可在公司成功后償還)。其中,Protalix就是一個常被引用成功故事的典型。
這就是政府、學術界和產業界聯合鑄就的一個讓許多創新理念得以實施的微環境,以色列正在向一個強大而先進的生物技術產業邁進。
尋求合作志在相得益彰
基德隆的母親是耶路撒冷哈達薩大學醫療中心從事口服胰島素開發的高級研究員。在一次與母親的閑聊中,基德隆得知這一項目有了突破性進展,可以進入商業化操作階段時,他馬上與哈達薩大學談判并獲得了這項技術,隨后便成立了Oramed公司,著手準備將這一產品推向市場。其間,公司從政府研發基金中獲得100萬美元啟動資金和向市場融資2000萬美元。
如今,Oramed已完成了該藥物的第一和第二階段臨床試驗,第一階段在以色列進行,5月獲得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批準,在美國進行第二階段試驗。
像大多數以色列生物科技公司總裁一樣,基德隆并不打算由自己來完成將藥物推向市場的終端。“到了最終階段,我們會尋找比我們擁有更好營銷能力的合作者,我們就在幕后潛心搞研發。”類似Oramed這樣的情況在以色列生物技術領域內很普遍,這些小企業創新能力強,但缺乏將候選藥物通過第三階段臨床并最終推向市場的資金和專業能力。
Protalix的故事則充分體現了這一趨勢。去年,FDA批準了Protalix的高雪氏癥酶治療方案 (高雪氏癥是溶酶體糖脂貯積癥中較常見的一種染色體隱性遺傳性疾病——譯注),最終由Protalix與輝瑞公司合作進行藥物開發和商品化,目前已贏利近1000萬美元。
“以色列是一個出連續企業家的地方 (連續企業家是指接二連三創立新公司的企業家——譯注),”特佩爾說道,“以色列人擅長創建新公司,但對于壯大公司他們或許缺乏耐心。”對于一家互聯網公司來說,可以在短短幾年時間里從一個車庫走到國際市場,但生物技術的開發則需要更多時間和龐大的資金支撐。盡管以色列擁有大量的風險資本群體,但投資者通常傾向于投資短期或中期項目。“我們擅長于藥物前期的第一和第二階段的臨床開發,僅此而已,”米切林說道,“我們目前沒有能力、資金和管理經驗進行第三階段試驗,也沒有將新研發藥物推向全球市場的實力。”
對于如何進一步發展以色列的生物科技產業,也是一些生物技術企業高管關注的問題。以色列擁有世界級科技公司的一些大型研究中心,如谷歌、英特爾、通用汽車等。蘋果設在以色列荷茲利亞的研發中心是該公司在美國之外的唯一研究機構,但生物技術領域還沒有類似的模式, 至少目前沒有。
如果大型制藥公司在以色列建立類似的國際研究中心,對于以色列的科學發展將產生很大的影響。“我們確實需要大型制藥公司在以色列建立研發中心,而國內生物科學領域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應全盤學習這些大公司的做法。”澤維說道。作為IATI的聯合主席,澤維正與同事們和以色列政府一起,準備設立一些項目吸引大公司來以色列,他說,“經驗和知識,是以色列生命科學產業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以色列擁有受過良好教育和有經驗的勞動者,或許大型制藥公司因地理位置,或政治環境等原因一時不愿落戶以色列,特佩爾說道。如果以色列企業家可以吸引大型藥企來以色列進行訪問,一些誤解也許可以迅速消散。
大型制藥公司正在表示出一些興趣。四年前,羅氏集團與以色列生命科學風險投資基金Pontifax基金合作,在以色列物色一些符合羅氏研發投資實力的企業和技術。去年,默克公司旗下的一個部門,在以色列投資1300萬美元,建立了Inter-Lab生物技術實驗室,雖然它不一定是澤維所期待的研發中心,但Inter-Lab實驗室擁有足以支持五六家公司的實驗設施和業務能力。
“雖然我們只是一個小國家,我們的地理位置既不在歐洲,也不與美國鄰近,但我們仍出現在所有大型制藥公司的地圖上,”米切林說道,“只要我們出現一項好的產品或技術,我們就能夠找到將創新技術推向市場的合作伙伴。”
[資料來源:TheScientist][責任編輯:則 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