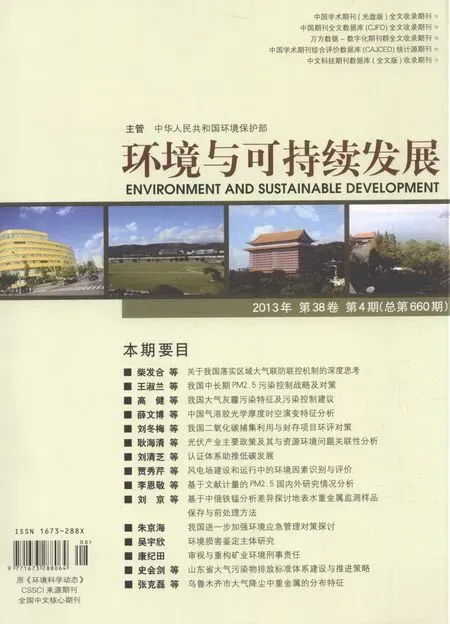環境NGO與公眾的關系初探
張密生
(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資源與環境學院,武漢 430072)
環境NGO,是指那些以環境保護和環境治理為目標的非政府組織。環境NGO與其它各類非政府組織相比,環境NGO的歷史使命就是解決環境污染問題和生態破壞問題,它是由公眾自發組織和自愿參與,成為繼政府、企業之后的又一環境治理主體,被稱為環境治理的“第三力量”。
環境的公共性、環境問題的公害性和環境保護的公益性決定了環境保護需要公眾的參與,而且環境保護正是在公眾的推動下成長與發展起來的。中共十七大提出建設生態文明的新理念、新目標,生態文明建設離不開公眾的積極參與,環境問題公眾參與發展的程度,直接體現著一個國家生態文明的發展程度。公眾參與環境保護的方式與參與的程度,將決定我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實現的進程。重視培養和提高公眾的環境保護意識,積極引導公眾有組織地參加環境保護行動,是實現可持續發展和環境善治,建設生態文明的有效途徑。環境NGO是公眾參與環境保護的重要組織形式,探討環境NGO與公眾的關系,對于實現我國環境保護的合力和生態文明建設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環境NGO與公眾(公民)的關系是既對立又統一,二者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互依賴、相互制約。
1 環境NGO與公眾的統一
環境NGO與公民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環境NGO的發展與公眾的認可程度和參與程度呈正比關系,環境NGO來源于民,取信于民,服務于民,這正是環境NGO在行動社會得以迅猛發展的力量之所在,環境NGO與公眾的聯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環境NGO以公民社會和為公民服務為目的。市場、企業以追求利潤為其目的,不會無緣無故地、主觀能動地位公民服務。在“市場失靈”的情況下,市場、企業還會損害公民的利益、至少是損害部分公民的利益。政府在正常情況下以多數人的整體利益為目的,因而難免損害少數公民的利益。在“政府失靈”時甚至會損害多數公民的利益。環境NGO以保護公民環境權益為其活動宗旨,是公民環境權益的代表。
第二,環境NGO為公民社會提供了合適而又生命力的組織化形式。從世界環境保護的歷史過程來看,環境NGO是伴隨著公眾參與環境保護的不斷深入而發展壯大的,它是公眾參與環保運動的組織保證和重要社會形式。世界環保事業的最初推動力量來自于公眾,沒有公眾參與就沒有環境運動,也就沒有環境非政府組織。公眾參與環境保護,必須是有秩序的、有效率的,最佳途徑之一便是組織建立環境NGO或非政府群眾組織,通過這類組織參與環境管理,開展環境保護活動。
環境NGO是實現公眾參與的一種新興的、有效的、不可或缺的組織形式和組織制度,他們為解決“市場失靈”、“政府失靈”問題,建立公眾參與的環境保護機制提供了新的可能。個人力量畢竟是十分有限的,通過NGO的制度安排可以凝聚多個公民個體的力量,以組織的形式參與國家或市場中的利益博弈,以實現公民利益的最大化,憑借NGO實現一定范圍內或是普遍的互惠。這也是將外部成本內部化,從而實現帕累托的改進的過程。組織形式可以是自上而下的的環境NGO,也可以是自下而上的環境NGO。環境NGO作為新生事物具有最廣泛的社會基礎和民眾根基,是公眾參與最活躍、最有效和最具生命力的組織形式。
第三,環境NGO加強了公民之間的平等互動關系。環境NGO在建立組織和組織活動過程中為公民提供了溝通、交流的場所,這種溝通和交流促進了公民間新的人際紐帶的形成和良性互動,產生了新的公共空間。環境NGO往往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一方面大量動員社區居民、在校學生和普通百姓積極參與各種形式的環境保護活動,形成廣泛的社會參與、平等互動;另一方面往往能夠匯集相當數量的專家資源,吸納社會各界的人士,包括媒體記者、大學教授、法律工作者、社會名流等,從而形成專業化的支持體系與良好的社會公信基礎。
第四,環境NGO培養了公民自我管理和社會管理的能力與熱情。環境的公共性、環境問題的公害性和環境保護的公益性決定了環境保護需要公眾的參與,公民在環境非政府組織內的活動、服務與管理也培養了公民的自我管理和參與社會管理的積極性、主動性、熱情和能力。環境NGO組織的環境保護活動具有形式多樣、喜聞樂見等特點,為公眾參與環境保護提供了各種機會和手段,提高了公眾自我管理和社會管理的能力和水平。公眾在參與制止云南怒江建壩方案、南京紫金山建觀光建筑、都江堰修建水庫大壩等事件中都發揮了巨大作用,體現了公民自我管理和社會管理的能力與熱情。
環境問題公眾參與發展的程度,直接體現著一個國家生態文明的發展程度。我國的公眾參與還只是剛剛起步,大多數公眾沒有環境參與的主動性,公眾參與到與自己環境利益相關的公共管理渠道也非常有限。環境NGO在環境信息的提供、環境參與的渠道、環境決策民主化,保障公眾的環境權益等方面,具有組織化的優勢。環境NGO推動了公眾參與的主動性、積極性,提高了公眾參與環境管理的水平和能力。
2 環境NGO與公眾的對立
第一,公信力是環境NGO生存和發展的生命線。環境NGO產生和發展的最重要基礎就是公眾的支持與信任,NGO具有公益使命,同時又依賴公眾的支持進行組織運作,公信力是社會對它的認可及信任程度,體現了一個NGO存在的權威性、在社會中的信譽度以及在公眾中的影響力。NGO的公信力基本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社會相信NGO將資源按照其宗旨使用,不會濫用到其它地方,二是社會相信NGO能夠很好地利用資源提供公益服務。NGO能否嚴格遵循使命承諾,高效合理地利用公益資產,能否公開、透明財務管理狀況,能否接受社會公眾的監督就成了NGO是否具有公信力的根本要求。
NGO通過對社會的服務和奉獻,得到政府、企業和公眾的信任支持,獲得高度的社會認知和社會認可,進而獲得社會影響力和號召力以及重要的公益資源,公信力成為NGO生存的生命線。一個沒有信譽的NGO無法獲得公眾的信任,也難以獲得組織生存或發展所需要的資源。沒有公信力的NGO終將失去生命力,被社會公眾所拋棄。
第二,NGO失靈會使環境NGO失去廣泛的社會基礎和深厚的民眾根基。市場失靈、政府失靈理論為NGO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相當有說服力的解釋,但這些理論都有一個基本假設前提,就是認為NGO是獨立于市場與政府之外的,是政府和市場失靈后的輔助性衍生物,政府、市場之短正是NGO之長。但是任何組織都存在著功能失靈,正如政府和市場不是萬能的,NGO也同樣不是萬能的。NGO因其內在的天生局限性,也會產生NGO失靈(志愿失靈),導致慈善不足、管理失策、非專業舉措失誤等問題。
公眾對環境NGO的期待往往高于對政府和企業,當NGO慈善精神、志愿精神、公益精神弱化或公益資金使用不當而出現公益腐敗、公益異化、公益私化時,公眾的反映會非常迅速,他們就會產生對立感,環境NGO的公信力會嚴重受損。特別是當環境NGO嚴重偏離其價值目標時,必將影響到NGO的公信力和影響力,使其失去廣泛的社會基礎和深厚的民眾根基。
環境NGO與公眾是我國環境保護的多元合作治理主體力量之一,環境NGO與公眾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和諧互動關系直接影響社會環境治理目標的實現,二者只有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聯系、相互依賴,開展多種契約性、制度性的聯合,建立良性、友好的伙伴關系,才能實現環境善治和生態文明建設。
[1]若弘:中國NGO——非政府組織在中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7頁.
[2]曾寶強,曾麗瓏.香港環境NGO的工作對推進內地公眾參與環境保護的借鑒.環境保護,2005(6):75-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