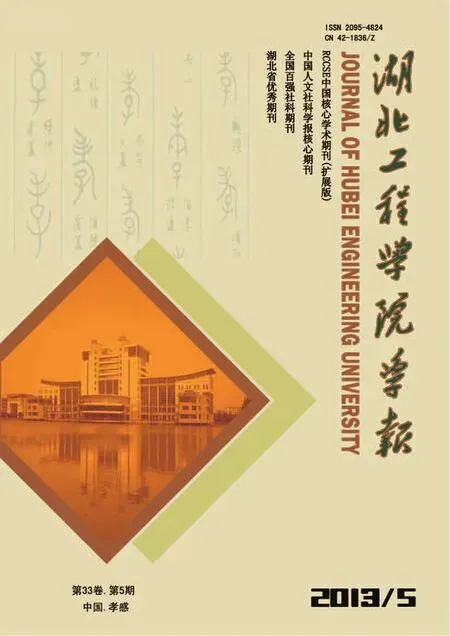蔡元培的廣告活動及其意義
楊家友,王俊超
(武漢紡織大學(xué) 傳媒學(xué)院,湖北 武漢 430073)
蔡元培的廣告活動及其意義
楊家友,王俊超
(武漢紡織大學(xué) 傳媒學(xué)院,湖北 武漢 430073)
蔡元培一生中從事了很多的廣告活動,主要包括“序跋”廣告和報(bào)刊廣告。其廣告活動的主要特征就是現(xiàn)代廣告學(xué)中的名人效應(yīng),其廣告服務(wù)的對象大多是學(xué)會、學(xué)人、藝術(shù)家和革命報(bào)刊,廣告活動的目的是推薦相關(guān)優(yōu)秀人才,推薦的基本準(zhǔn)則是對國家有利,并有助于宣揚(yáng)民主革命。蔡元培提出“正確”、“純潔”、“博大”原則應(yīng)該成為新聞和廣告行業(yè)注重培養(yǎng)的品格,對當(dāng)代日益虛假的名人廣告則不失為一劑良藥。
蔡元培;廣告活動;名人效應(yīng)
蔡元培是近代中國最重要的教育家,被毛澤東稱譽(yù)為“學(xué)界泰斗,人世楷模”。他一生都致力于發(fā)展中華民族的教育和科學(xué)事業(yè),爭取國家獨(dú)立和民主解放。作為近代中國最有影響力的文化名人,蔡元培的廣告活動及其效應(yīng)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論價(jià)值和實(shí)踐價(jià)值。
一、蔡元培的廣告活動
蔡元培以北大校長的身份招攬了不同派別,不同意見的老師到北京大學(xué)教書,他甚至讓當(dāng)時(shí)的反動軍閥也認(rèn)可了他的先進(jìn)的教育理念。在推廣和實(shí)踐自己的教育理念期間,蔡元培先生從事了一系列的廣告活動,主要包括他的“序跋”廣告活動和報(bào)刊廣告活動。
蔡元培一生所做的“序跋”大約有150篇,這些“序跋”廣告之中活動內(nèi)容非常豐富,其涉及的人數(shù)之廣,影響的中國學(xué)科行業(yè)之深,都是其他人的廣告難以比擬的。徐寶璜是中國新聞學(xué)的開山者,他在新聞教育史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在北京大學(xué)工作期間取得的,而這都是在蔡元培先生的支持和幫助下才得以完成的。蔡元培與徐寶璜的父親徐秀均是摯友,在徐寶璜少年時(shí)期就給予他指導(dǎo)。而后蔡元培任北大校長,就將徐寶璜聘為北大教授。“1918-1919年間,徐寶璜撰寫了中國最早的一本新聞學(xué)理論著作《新聞學(xué)》,蔡元培曾先后兩次(1918年夏季和1919年冬季)為該書寫作序言, 并盛贊這本著作為破天荒之作,對徐寶璜的成長和他所開創(chuàng)的新聞學(xué)術(shù)研究事業(yè)取得的成就極力贊賞。”[1]蔡元培十分支持中國新聞學(xué)的發(fā)展,所以才會率先聘請徐寶璜在北大成立新聞學(xué)科。作為長輩的蔡元培,希望藉由自己作序的廣告活動掀起新聞教育的浪潮,而事實(shí)上徐寶璜也由此開創(chuàng)了中國新聞教育和學(xué)術(shù)研究的輝煌。魯迅作為蔡元培的紹興同鄉(xiāng),也是在蔡元培的提攜下得到成長和成名的。“作為概括魯迅其人與文學(xué),蔡元培寫在《魯迅全集》卷頭的序言是最為出色的。”[2]蔡元培之所以能夠如此了解魯迅,是因?yàn)樗麄兊纳砩瞎餐哂械牡疵⒅R分子極強(qiáng)的自覺性這些東西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作為教育家蔡元培戰(zhàn)斗的改革氣質(zhì),和被作為中國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魯迅息息相通。蔡元培在序中說道:“綜觀魯迅先生全集,雖亦有幾種工作,與越縵先生相類似的;但方面較多,蹊徑獨(dú)辟,為后學(xué)開示無數(shù)法門,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學(xué)開山目之。然歟否歟,質(zhì)諸讀者。”[3]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思想一直貫穿他整個教育生涯,對于文學(xué)革命,他一直全力捍衛(wèi)思想表達(dá)的自由。而魯迅在他一生的文學(xué)革命中作出了最實(shí)質(zhì)性貢獻(xiàn),在這個角度上可以說,魯迅在蔡元培的直接庇護(hù)下開始了他的新文學(xué)創(chuàng)作。因此,他對于魯迅“新文學(xué)開山”的評價(jià),也表現(xiàn)了他對新文學(xué)的一種推廣。蔡元培先生是1917年1月4日正式踐履北京大學(xué)校長一職的,而這位校長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聘請陳獨(dú)秀統(tǒng)領(lǐng)北大文科,極力推薦他為文科學(xué)長,為此他給當(dāng)時(shí)的北洋軍閥政府教育部寫信。由此可見蔡元培對人才的重視程度。1933年4月,當(dāng)亞東圖書館準(zhǔn)備再次出版陳獨(dú)秀的《獨(dú)秀文存》時(shí),蔡元培置陳獨(dú)秀共黨嫌疑的政治囚犯身份于不顧,毅然決然地為陳獨(dú)秀《獨(dú)秀文存》寫序:“這部文存所存的,都是陳君在《新青年》上發(fā)表的文,大抵取推翻舊習(xí)慣、創(chuàng)造新生命的態(tài)度;而文筆廉悍, 足藥拖沓含糊等病;即到今日,仍沒有失掉青年模范文的資格。我所以寫幾句話,替他介紹。”[4]在那個年代,蔡元培先生作序跋等廣告活動的意義,不僅僅在于宣傳書籍,更重要的意義在于表明他對陳獨(dú)秀的支持。在實(shí)踐中,蔡元培也是十分積極地營救陳獨(dú)秀,動員一切可能動員的國內(nèi)外進(jìn)步人士,來共同營救和保護(hù)政治犯,以保障人民的民主權(quán)和自由利。清陶方琦、姚振宗整理并補(bǔ)輯,徐友蘭、孟晉齋抄錄的《埤蒼》、《廣倉》抄本有蔡元培先生跋文一則,這篇跋文是蔡元培在徐友蘭家中伴讀校勘時(shí)期所作。校勘不僅只是簡單的文字語法校對,它需要非常淵博的學(xué)識為基礎(chǔ),體現(xiàn)了校者的思考和認(rèn)識。“蔡先生在徐氏家中不僅僅是伴讀、校書,更多的還是一種學(xué)術(shù)上的交流與活動,而且是其中的積極分子。跋文既是蔡先生為徐氏校勘書籍的見證,也是這種學(xué)術(shù)交流與學(xué)術(shù)活動的見證。”[5]蔡元培的序跋廣告活動的內(nèi)容十分廣泛,有自然科學(xué),包括農(nóng)業(yè)、氣象、水利、植物學(xué)、數(shù)學(xué)、醫(yī)學(xué);也有人文科學(xué),如文學(xué)、藝術(shù)、美術(shù),還有社會科學(xué),如政治、經(jīng)濟(jì)、法律、軍事、哲學(xué)、語言文字、歷史考古、社會學(xué)、倫理學(xué)、人口學(xué)諸多方面。這些活動有力地推動了各學(xué)科的成長和發(fā)展。
蔡元培先生除了為學(xué)術(shù)著作撰寫“序跋”等廣告活動外,還十分熱衷于報(bào)刊的廣告宣傳活動,他參與創(chuàng)辦的《蘇報(bào)》、《俄事警聞》等報(bào),都是在中國近代史上產(chǎn)生過主流影響的報(bào)刊。后來在任北京大學(xué)校長期間也不忘報(bào)人使命,促成了《新潮》、《國民》、《新青年》等雜志的發(fā)行。發(fā)刊詞的發(fā)表除了是為報(bào)紙本身,更是為報(bào)刊新聞思想做廣告宣傳。那時(shí)的發(fā)刊詞都是表明報(bào)紙的一個辦報(bào)主旨,定位非常明確,也可以看出辦報(bào)人的新聞思想。由張?jiān)獫?jì)任董事兼總經(jīng)理、蔡元培負(fù)責(zé)撰述并翻譯日文稿件的《外交報(bào)》于1902 年1 月4日在上海順利開辦,該刊是當(dāng)時(shí)中國最早翻譯的外事資料,總共出版300期,直到1911年1月15日被迫停刊,最大的特色是,每期都用大量的篇幅翻譯和刊載三四十種外刊時(shí)文與評論。此外,該刊還輯錄和出版了相關(guān)文章的單行本《外交匯編》共30冊。蔡元培在他所撰的發(fā)刊詞中表明了他對報(bào)紙功能的定義:“夫思想頑鈍,賴言論以破之”,報(bào)紙“以言論轉(zhuǎn)移思想,抉摘弊習(xí),有摧陷廓清之功”,從而“將以定言論之界,而樹思想之的。”[6]《申報(bào)》作為中國近代報(bào)紙的典范,學(xué)習(xí)西方先進(jìn)技術(shù),無論是報(bào)紙格局,版面欄目安排還是標(biāo)題制作新聞報(bào)道,都已經(jīng)十分接近現(xiàn)代報(bào)刊。因此,《申報(bào)》擁有獨(dú)立的廣告欄,是非常進(jìn)步的一個標(biāo)志。蔡元培時(shí)任北京大學(xué)校長。他領(lǐng)銜與蔣維喬等6 人在《申報(bào)》上為惲鐵樵的《群經(jīng)見智錄》做廣告,這則廣告的宣傳手法很豐富,不僅說明書的學(xué)術(shù)價(jià)值,還從“定價(jià)洋十二元,預(yù)約期內(nèi)只收洋六元”,“紙張印刷裝訂之精美”等方面全力推薦。蔡元培為各種新的研究會在報(bào)刊上發(fā)表過啟事,借由報(bào)刊的廣告宣傳,吸引各界知識分子和學(xué)生參與進(jìn)來,為研究會壯大人才隊(duì)伍,優(yōu)化人事配置,比如新聞學(xué)研究會成立之時(shí),蔡元培就發(fā)表過啟事。在《北京大學(xué)日刊》第208、209、211、212、214號上又連續(xù)五次以“校長布告”形式刊載招生消息:“本校為增進(jìn)新聞智識起見將設(shè)立一新聞研究會,凡愿入會者于本月內(nèi)向日刊處報(bào)名可也。”[7]北京大學(xué)新聞學(xué)研究會后來果然培養(yǎng)了一批應(yīng)時(shí)的人才,為新聞學(xué)教學(xué)內(nèi)容和方法樹立了良好的開端,這些急需人才形成了優(yōu)良的學(xué)風(fēng),理論聯(lián)系實(shí)際,結(jié)合中國報(bào)業(yè)自身的特點(diǎn),制定適合學(xué)生學(xué)習(xí)新聞學(xué)的教材。“蔡元培辦報(bào)時(shí)最焦急的并不是報(bào)館中的各種繁難瑣事,卻是這報(bào)紙的銷路,為了擴(kuò)大銷路,他曾雇用一名紹興工人背一面旗,上面寫著全國人注意日俄戰(zhàn)爭的標(biāo)語或畫,手里敲著一面小鑼,帶著報(bào)紙到南市叫賣。如此做去,居然每天可以多賣出一二百份報(bào)。但不久就有人出來干涉,于是不能再繼續(xù)叫賣。”[8]蔡元培的叫賣廣告結(jié)合旗幟廣告,綜合運(yùn)用了多種廣告宣傳手法,對擴(kuò)大銷路有著十分明顯的效果。蔡元培先生畢生倡導(dǎo)審美教育,因此對廣大藝術(shù)家們的美學(xué)創(chuàng)作給予了大力推崇和力所能及的支持,曾為十多位書畫家代訂潤例,并且全心全意地予以推薦和介紹。所謂“潤例”就是指書畫家賣書賣畫的廣告文字。潤例又分自訂和代訂兩類。代訂者多為社會名流、書畫名家, 多表現(xiàn)為老師為弟子定潤例,前輩為后生定潤例,有的潤例刊于報(bào)紙雜志,有的潤例印成單葉散發(fā)。蔡元培曾經(jīng)為劉海粟寫過《介紹畫家劉海粟》、《題〈海粟近作〉》、《歡迎劉海粟由歐展覽回國參會上演說詞》等推廣的文字和演講。二人在藝術(shù)教育主張上的一致性,是他們攜手打造上海美術(shù)專科學(xué)校的理論基礎(chǔ)。蔡元培愿意為這些藝術(shù)家們無償?shù)刈鰪V告宣傳,是因?yàn)樗诶砟钌蠈@些藝術(shù)家們的認(rèn)同,而這些被支持的人也會受到蔡元培的影響。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治校方略和人才政策也促使劉海粟以海納百川的胸懷來吸納人才,當(dāng)時(shí)的上海美專集中了當(dāng)時(shí)中國最優(yōu)秀的藝術(shù)家、最龐大最雄厚的師資隊(duì)伍。蔡元培還為羅鈍翁撰寫了兩篇潤例,羅鈍翁善書善墨梅,但是在近現(xiàn)代美術(shù)史并不是很有名氣,可是蔡元培依然表示了對他的支持和欣賞,兩次為其撰寫潤例。從這里可以看出,蔡元培做廣告宣傳看重的并不是一個人的名氣,而是他的才能。
二、蔡元培廣告活動的特征:名人效應(yīng)
從以上蔡元培廣告活動可以看出,蔡元培的廣告活動的主要特征就是現(xiàn)代廣告學(xué)中的名人效應(yīng)。名人效應(yīng)廣告是現(xiàn)代商家最偏愛的廣告形式之一,它具有獨(dú)特的文化表現(xiàn)手法,影響著我們?nèi)粘I畹拿恳惶臁2淘嘞壬鳛橹袊弦晃恢匾臍v史人物,他利用自己的名人效應(yīng)所從事的廣告活動,則有著其特殊的廣告對象和宣傳原因。
蔡元培先生的廣告活動服務(wù)對象大多是各種學(xué)會、學(xué)人、藝術(shù)家和革命報(bào)刊。蔡元培先生曾為很多學(xué)會寫過啟事,除了前文提到的北大新聞學(xué)會,還有中國歷史學(xué)會。1930前后到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之間是中國城市相對穩(wěn)定的時(shí)候,各種學(xué)會都有過一段“黃金時(shí)期”,官方、半官方乃至民間主辦負(fù)責(zé)的各種學(xué)術(shù)團(tuán)體紛紛成立,因此報(bào)紙上經(jīng)常出現(xiàn)各種學(xué)會的啟事或廣告。1933年11月11日《申報(bào)》所刊《發(fā)起中國歷史學(xué)會啟事》即為其中之一。發(fā)起人吳稚暉、蔡元培、李煜瀛等21人都是當(dāng)時(shí)的著名學(xué)者和名流,令人矚目。蔡元培1922年在北大時(shí)期就組織過北大史學(xué)會,以此來推動歷史科學(xué)的普及和大眾化。1933年,他聯(lián)署發(fā)起中國歷史學(xué)會,顯然是此項(xiàng)的繼續(xù)。從發(fā)起人組成來看,該學(xué)會以南京中央大學(xué)和上海中華書局的一批學(xué)者為骨干。《啟事》強(qiáng)調(diào)歷史科學(xué)各個分支研究,應(yīng)該做到“分以極其深”,而“合以成其大”的功效。與蔡元培交往的學(xué)人非常廣泛,包括徐寶璜、魯迅、陳獨(dú)秀、張?jiān)獫?jì)、王云五、張乃燕等等。蔡元培在學(xué)人當(dāng)中起了核心作用,他們或多或少地都與蔡元培有著師承、同事、同鄉(xiāng)等關(guān)系,這些人都得到了蔡元培的培養(yǎng),激勵和扶持。以蔡元培與王云五的交往為例,可以反映蔡元培對于學(xué)人的態(tài)度。“1926、1928年,王云五的《四角號碼檢字法》和《中外圖書統(tǒng)一分類法》相繼問世,蔡元培欣然為兩書作序。1929年,王云五因勞資糾紛而辭商務(wù)印書館,蔡元培聘其為中央研究院研究員。”[9]22這是比較典型的支持方式,蔡元培經(jīng)常為各路學(xué)人做序跋廣告,并且在他們落寞潦倒的時(shí)候提供工作和平臺,自己演講或在專業(yè)會議上,也會提攜、欣賞被誤解或尚無名氣的學(xué)人。作為中國近代美學(xué)的主要開拓者,蔡元培研究和提倡美學(xué)的主要目的是想用美學(xué)來代替宗教行使信仰教育的功能,因此,他和很多藝術(shù)家都有來往,也很愿意用自己的名人效應(yīng)為他們做廣告宣傳。除了之前提到的劉海粟和羅鈍翁的潤例代訂廣告外,蔡元培還會為一些藝術(shù)家的畫集題詩。例如,金石家王式園精通鑒賞收藏,好金石書畫,以瓷器見長,致力于宣傳中國當(dāng)代畫的優(yōu)秀作品,是當(dāng)時(shí)的文化藝術(shù)事業(yè)先驅(qū)者,與蔡元培關(guān)于藝術(shù)宣傳的很多觀點(diǎn)不謀而合。1929 年王式園設(shè)想編印《式園時(shí)賢書畫集》,請蔡元培題詩,蔡元培當(dāng)即作《題〈式園時(shí)賢書畫集〉》一首,1930年6月22日再作《又題〈式園時(shí)賢書畫集〉》。[10]蔡元培的報(bào)刊活動經(jīng)歷十分豐富,《蘇報(bào)》時(shí)期,蔡元培發(fā)表了一系列文章極力宣傳反帝與排滿,如所作《釋“仇滿”》,言論激烈。在他的庇佑下《新潮》、《國民》等雜志順利發(fā)行。《新青年》也遷來北京,以北大為陣地,宣傳文學(xué)革命,成為五四運(yùn)動的主要旗幟。
蔡元培的廣告活動再現(xiàn)了名人效應(yīng)的轟動性特征,而他從事這些廣告活動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即為各行各業(yè)推薦相關(guān)優(yōu)秀人才,推薦的基本準(zhǔn)則是“于國有裨益”并有助于宣揚(yáng)民主革命。蔡元培針對當(dāng)時(shí)中國的教育狀況提出了先進(jìn)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教育理念,這絕不是對新舊文化采取不偏不倚的簡單態(tài)度,而是致力于尋求舊文化和新文化的一種融合兼并,以促進(jìn)新文化的發(fā)展為目標(biāo)的一種文化策略。在兼容并包思想的指導(dǎo)下,蔡元培對所有人才都奉行一視同仁的態(tài)度。他不遺余力地為北京大學(xué)、教育部和各種學(xué)術(shù)圈、藝術(shù)圈推薦大量優(yōu)秀人才,通過作序、致函和啟事等廣告方式讓很多人才擁有發(fā)揮的平臺。而這些人也的確為中國近現(xiàn)代文化事業(yè)的各個方面的輝煌奉獻(xiàn)出了自己的力量,包括文學(xué)、美術(shù)、新聞、音樂、學(xué)科建設(shè)和職業(yè)教育等多個方面。而推薦人才的原則就是“于國有裨益”,蔡元培在1931年為北大肄業(yè)生朱謙之所寫《歷史學(xué)派經(jīng)濟(jì)學(xué)》作的序中提到:“特編此書,不特于歷史學(xué)派與古典學(xué)派及馬克思派的異同,分析甚精,而且于歷史學(xué)派中各種經(jīng)濟(jì)發(fā)達(dá)階段說,詳細(xì)敘述而加以批評,于我國經(jīng)濟(jì)學(xué)界,必有重要的裨益,可以斷言。”[9]23在那個動蕩變化的時(shí)代背景下,我國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藝術(shù)等學(xué)科的學(xué)術(shù)研究都處于急需大力發(fā)展的重要時(shí)期和階段,為了推廣先進(jìn)的思想,為我國學(xué)界帶來多樣的觀點(diǎn)碰撞,為國家造就高質(zhì)量的學(xué)術(shù)隊(duì)伍,蔡元培專門花心思宣傳新的學(xué)科知識,為各種學(xué)術(shù)專著做廣告,通過學(xué)術(shù)碰撞和革命刊物來傳播民主、自由的呼聲。
三、蔡元培名人效應(yīng)廣告對當(dāng)代名人廣告的啟示
當(dāng)代名人廣告大量充斥于我們的現(xiàn)代生活,然而泥沙俱下,在此過程中出現(xiàn)了很多名人虛假廣告。三鹿事件爆發(fā)后,我國名人廣告的混亂現(xiàn)狀得以進(jìn)一步暴露。代言明星卻安然于法律制裁之外,難平社會輿論的譴責(zé)。名人廣告的主要問題就是名人脫離消費(fèi)者的立場,在沒有親身體驗(yàn)過產(chǎn)品時(shí)卻夸大使用效果,誤導(dǎo)了喜愛并信任他們的消費(fèi)者。名人在廣告中是演員,對廣告真實(shí)性負(fù)責(zé)的不是名人,而是廣告主、廣告經(jīng)營者和發(fā)布者。所以,名人才會如此不負(fù)責(zé)任,夸大其詞,道德感缺失。名人代言的虛假廣告,不僅誤導(dǎo)了消費(fèi)者,侵犯了消費(fèi)者的利益,同時(shí)也損害了名人自己的形象,甚至對整個社會的誠信體制都有影響。消費(fèi)者由于受到名人虛假廣告的傷害過于頻繁,現(xiàn)在他們對名人廣告都是充滿了懷疑和憤怒。蔡元培的名人效應(yīng)廣告能夠給予當(dāng)代名人廣告以一定的有益的啟示。
從蔡元培先生大量的廣告活動中,能夠折射出他的廣告活動遵循的基本原則,反映出他的廣告思想,這些原則和思想反襯出當(dāng)代名人廣告的虛假,警示著當(dāng)代名人廣告的規(guī)范。首先,蔡元培先生對各種虛假騙人的廣告也是深惡痛絕的,在1918年10月14日《北大新聞學(xué)研究會成立演說詞》中,蔡元培說:“抑鄙人對于我國新聞界尚有一種特別之感想,乘今日集會之機(jī)會,報(bào)告于諸君,即新聞中常有猥褻之紀(jì)聞若廣告是也。聞英國新聞,雖治療霉毒之廣告,亦所絕無。其他各國,雖疾病之名詞,無所謂忌諱,而春藥之揭貼,冶游之指南,則絕對無之。新聞自有品格也。吾國新聞,于正張中無不提倡道德;而廣告中,則誨淫之藥品與小說,觸目皆是;或且附印小報(bào),特辟花國新聞等欄;且廣收妓寮之廣告。此不特新聞家自毀其品格,而其貽害于社會之罪,尤不可恕。諸君既研究新聞學(xué),必皆與新聞界有直接或間接之關(guān)系,幸有以糾正之。”[11]199從“其貽害于社會之罪,尤不可恕”可以看出,蔡元培先生這段話的主要目的在于批判時(shí)存的各種虛假的或不道德的新聞,但同時(shí)也對各路虛假廣告持明確的批判態(tài)度,主張廣告與新聞一樣要符合社會道德。蔡元培在1918年10月20日的《國民雜志》社成立會上的演說中提到:“如內(nèi)容無價(jià)值,猶旗質(zhì)之不堅(jiān)也。內(nèi)容善矣,而文筆晦澀,編次凌雜,不能使讀者知其真意之所在,猶制旗不合法,不適于表示也。內(nèi)容及形式均善矣,而或參以過當(dāng)之言論,激起反動,或加以卑猥之小品,若廣告,以迎合一部分惡劣之心理,則亦猶國旗之污損矣。去此三弊,則雜志始為完善。而有以副諸君救國之本意,愿諸君勉之。”[11]206由此,蔡元培先生認(rèn)為廣告不能只是為了個別人的某些政治或經(jīng)濟(jì)因素,而完全不考慮其應(yīng)該具有的社會價(jià)值,真正的廣告應(yīng)該和新聞一樣,“自有品格”,真正的廣告業(yè)者應(yīng)該像新聞從業(yè)者一樣注重維護(hù)自身的形象,不要“自毀其品格”, 正如蔡元培先生在《〈國民雜志〉序》中要求新聞品格要像新聞人格一樣,真正的“廣告品格”也應(yīng)該具有如下三大品格:
首要的品格是“正確”。何謂“正確”?蔡元培先生說:“有一事焉,與吾人之所預(yù)期者相迎合,則乍接而輒認(rèn)為真;又有一事焉,與吾人之所預(yù)期者相抗拒,則屢聞尚疑其偽。此心理上普通作用也。言論家往往好憑借此等作用,以造成群眾心理,有因數(shù)十字之電訊而釀成絕大風(fēng)潮者,當(dāng)其時(shí)無不成如荼如火之觀,及事實(shí)大明,而狂熱頓熄,言論家之信用蕩然矣。故愛國不可不有熱誠;而救國之計(jì)劃,則必持以冷靜之頭腦,必灼見于事實(shí)之不誣而始下判斷,則正確之謂也。”[11]254所謂“正確”,就是要明辨事實(shí)和真相,不能以個人預(yù)期和愛好作為標(biāo)準(zhǔn),否則,即使造成如火如荼的“絕大風(fēng)潮”的轟動效應(yīng),當(dāng)“事實(shí)大明,而狂熱頓熄”的時(shí)候,新聞和廣告的“信用”已蕩然無存。真正的新聞和廣告,就如同愛國之心一樣,必須保持冷靜的頭腦,“必灼見于事實(shí)之不誣而始下判斷,則正確之謂也”。
第二個品格就是“純潔”。何謂“純潔”?蔡元培先生說:“救國者,艱苦之業(yè)也。墨翟生勤而死薄,句踐臥薪而嘗膽,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斷未有溺情于耳目之娛,侈靡之習(xí),而可以言救國者。近來我國雜志,往往一部分為痛哭流涕長太息之治安榮,而一部分則雜以側(cè)艷之詩文,戀愛之小說。是一方面欲增進(jìn)國民之人格,而另一方面則轉(zhuǎn)以陷溺之也。”[11]254-255這里要求新聞人和廣告人要有高尚的精神境界,不要“溺情于耳目之娛,侈靡之習(xí)”,避免“一方面欲增進(jìn)國民之人格,而另一方面則轉(zhuǎn)以陷溺之”的雙面人格的可恥與無聊。并祝“愿《國民雜志》慎勿以無聊之詞章充篇幅”,這是辦報(bào)辦刊的新聞人和廣告人都要奉行的一個原則。
第三個品格就是“博大”。何謂“博大”?蔡元培先生是這樣說的:“積小群而為大群,小群之利害,必以不與大群之利害相抵觸者為標(biāo)準(zhǔn)。家,群之小者也,不能不以國之利害為標(biāo)準(zhǔn)。故有利于家,而又有利于國,或無害于國者,行之。茍有利于家,而有害于國,則絕對不可行。此人人所知也。以一國比于世界,則亦為較小之群。故為國家計(jì),亦當(dāng)以有利于國,而有利于世界,或無害于世界者,為標(biāo)準(zhǔn)。而所謂國民者,亦同時(shí)為全世界人類之一分子。茍倡絕對的國家主義,而置人道主義于不顧,則雖以德意志之強(qiáng)而終不免于失敗,況其他乎?愿《國民雜志》勿提倡極端利己的國家主義。”[11]255“博大”作為一個刊物或廣告來說就是要有廣泛而深刻的視野,不要陷入群小利己的窠臼。作為一位合格的公民,其所從事的新聞或廣告不僅要考慮個人利益、家庭利益和國家利益,還要作為世界公民考慮到全人類的利益。由此可見,蔡元培先生提出“博大” 的原則內(nèi)涵著從全人類的角度看問題,其核心則是人道主義。[12]
以上就是蔡元培先生對新聞和廣告行業(yè)和業(yè)者的要求。蔡元培一生只為自己做過兩則廣告,其中一則為征婚廣告,擇偶條件為:a.女子須不纏足者;b.須識字者;c.男子不娶妾;d.男死后,女可再嫁;e.夫婦如不相和,可離婚。由這則廣告的內(nèi)容可以看出,廣告和新聞都應(yīng)該從“我”做起,以“我”為例,是自我的人格的體現(xiàn),自我的人格高尚才能保證新聞和廣告的品格做到“正確”、“純潔”、“博大”,從而達(dá)到移風(fēng)易俗,倡導(dǎo)男女平等,開啟民智,使整個社會為之煥然一新。蔡元培提出的“正確”、“純潔”、“博大”促使新聞廣告等傳播行業(yè)注重培養(yǎng)一種高尚的品格。他通過一生的實(shí)踐身體力行地向時(shí)人和世人詮釋了什么是高尚的廣告活動,因?yàn)樗膹V告活動追求的都是國家的進(jìn)步和人才的發(fā)展,這是一種非凡的品格和氣質(zhì)。自蔡元培先生開始,“自有品格”成為新聞和廣告的特有的一種理論氣質(zhì),這些廣告原則和廣告思想可以給予當(dāng)代名人廣告很多有益的啟示。
[1] 李筑.徐伯軒先生行狀原作者考辨[J].貴州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7(4):30.
[2] 竹內(nèi)好.蔡元培眼中的魯迅與傳記材料[J].魯迅研究月刊,2009(1):39.
[3] 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七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9:215.
[4] 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六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8:271.
[5] 孫振田.蔡元培先生跋文一則[J].圖書館研究與工作,2008(2):59.
[6] 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一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4:137.
[7] 肖東發(fā).蔡元培與北京大學(xué)新聞學(xué)研究會[J].新聞愛好者,2008(12):72.
[8] 王穎吉.蔡元培早期報(bào)刊宣傳活動論略[J].貴州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3(6):97.
[9] 錢濱.新發(fā)現(xiàn)蔡元培與北大學(xué)人相關(guān)的六篇佚文[J].北京大學(xué)教育評論,2008(3).
[10] 錢斌.新發(fā)現(xiàn)蔡元培七篇序文述略[J].紹興文理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9(2):48.
[11] 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三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4.
[12] 汪振軍.新聞自有品格——蔡元培新聞思想述評[J].當(dāng)代傳播,2006(5):14.
(責(zé)任編輯:余志平)
G20
A
2095-4824(2013)05-0055-05
2013-03-15
楊家友(1975— ),男,河南商城人,武漢紡織大學(xué)傳媒學(xué)院副教授,美學(xué)博士,倫理學(xué)博士后。王俊超(1989— ),女,新疆博樂人,武漢紡織大學(xué)傳媒學(xué)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