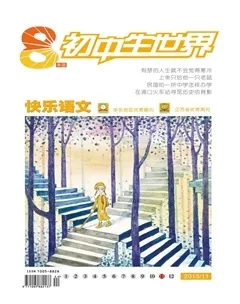綠水三千(節(jié)選)
當我第一次見到日月潭時,我便被那一泓湛綠的潭水和潭上出塵忘俗的幽靜,深深地迷醉了。
潭是平靜而深幽的,但卻姿態(tài)萬千,水的顏色更是一日數(shù)變。我第一次看見它,正是微雨過后,只見四周重疊參差的峰巒,蒼郁茂密的山林,經(jīng)過一番潤澤,更顯得青蔥欲滴,那一片濃綠深翠便簇擁環(huán)拱著一碧萬頃的潭水。波光滟瀲,綠影幽邃,三兩艘小船悠然蕩漾在水影波光里,像幾片輕盈的竹葉;白鷺成雙,在水面翩翔盤旋。我倚欄凝立,默然相對,就在這一刻的默契中,潭上的那一份纖塵不染的潔凈,那一份美妙蘊聚的和諧,那一份寧靜的幽邃,不期然滲入我性靈,融入我心胸,使我渾然忘卻俗世,不留半點人間渣滓,只覺得自己像一片白鷺的羽毛,像一朵出岫的白云,想飛,想在山巔飄游,想在水面回旋。
第二次看到潭時,卻是有霧的清晨。只見煙云縹緲,樹靄溟蒙,晨霧籠罩著潭水,仿佛披了一層縠紗,景物盡在綽約不露中。霧中傳來婉轉(zhuǎn)的鳥聲,卻不知在何處啼唱,如果說晴天的潭是一幅寫意的畫,那霧里的潭該是一個空蒙的夢,一個撲朔迷離、不可捉摸的夢。才從一個夢中醒來又落入一個夢中,連憑欄人也不知身在何處。看不清真面目,潭更顯得神秘空靈,陣陣涼沁的晨風從潭上吹來,霧開始遲緩地移動著,就似迷蒙的山峰間果真有“神女”伸出了纖纖的玉手,一縷縷地挽起萬千層輕絹。初升的太陽在霧靄里突圍著,射出一支支金箭,穿破了逐漸輕薄的霧層——突然間,一個黃澄澄、光燦燦的太陽脫穎而出,瞬時間云消霧散,只見遠山凝黛,叢樹縈翠,一片金光照得潭水閃閃發(fā)亮,綠得似萬頃皎潔明凈不沾半點塵瑕的綠玻璃,竟然是一個透澈晶瑩的世界!
放一艘汽艇,便把人帶進了晶瑩透澈的世界。汽艇輕捷地滑行在平靜如鏡的潭上,一時間玉碎翠裂,船尾在碧綠的水面剪出兩條雪白的浪,一路展漾開去,陽光輝耀下,恰似一長串乍明乍滅的曇花環(huán),船一停,一起都又幻滅了,不留半點痕跡。恢復了平靜的潭水依舊像光滑的綠玻璃,藍天、白云、青峰、翠巒,便悄然安嵌在綠玻璃中,鑲框的是無限的綠色崖岸,參差重疊,曲折綿亙。枝柯掩映中,有露出一角的飛檐峻宇,紅磚綠瓦,那是玄光寺;有古木參天,石級連云,那是文武廟。舍船攀登,在那峻嶺崖頂上縱目遠眺,只見萬壑爭流,千巖競秀,日月潭在腳下浩浩淼淼,一片云水蒼茫。迎風凝立,聽鐘聲撼動在風里,不由得使人悠悠意遠,滿心是超然出塵的感覺,竟然想起古人的羽化而仙……
小小的光華島浮漾在水中央,小得纖巧玲瓏,仿佛風能把它吹走,浪能把它撼動。但它屹立在碧潭深處,像潭上的鎮(zhèn)守使,蒼松列隊拱衛(wèi),矮欄低低護環(huán),四周微波縈回,萬籟俱寂中,只松嘯低低,水吟悄悄,凝止中有著盎然的生意,靜寂中有著不可言傳的和諧……“溯洄從之,宛在水中央”,僅僅是“水中央”這三個字,便喚起了多少奇妙的遐思,多少飄忽的情趣!
(選自《百年美文·游記卷》,季羨林主編,百花文藝出版社2011年,有改動)
鑒賞空間
本文作者兩次來到日月潭。第一次“倚欄凝立,默然相對”,沒有在潭上泛舟,見到的潭水“平靜而幽深”,頓時“忘卻俗世,不留半點人間渣滓”。第二次見到的潭水“竟然是一個透澈晶瑩的世界”,于是趕緊乘上汽艇,“滑行在平靜如鏡的潭上”;而后“舍船攀登”,極目遠眺,云水茫茫,見到一幅精美絕倫的山水畫,令人頓覺“超然出塵”。文章語言優(yōu)美,生動形象,多處運用比喻、擬人的修辭手法,如“船尾在碧綠的水面剪出兩條雪白的浪,一路展漾開去,陽光輝耀下,恰似一長串乍明乍滅的曇花環(huán),船一停,一起都又幻滅了,不留半點痕跡”,不僅描摹出汽艇滑過水面,在陽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輝的情態(tài),而且暗示了水面的晶瑩剔透;更為重要的是,折射出作者游潭時的激動、喜悅之情。
[讀有所思]
同樣是寫潭水,本文與柳宗元的《小石潭記》所營造的氛圍和抒發(fā)的情感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