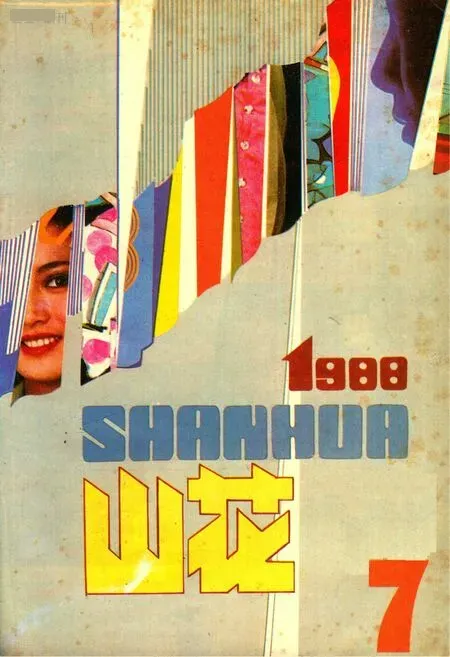卑微的神靈:陳紅旗的繪畫——兼論鄉土繪畫的價值再建構
張建建
1997年,印度女作家阿蘭達蒂·羅易(Arundhati Roy)寫出了后來獲得布克獎的小說《卑微的神靈》(The God of Small Things),同時間,中國貴州的畫家陳紅旗正在畫著表現貴州苗族地區岜沙鄉村風物的繪畫,他已經畫了許多年了。羅易寫作的背景是全球化資本以及隨之而來的全球化政治對于古老社會的侵蝕,陳紅旗繪畫的背景也差不多:中國社會幾乎每一個角落都開始了浩浩蕩蕩的商業及其相關價值的建構;羅易用印度式感性且細密的思維描述著諸多發生在文化細節以及微妙人性當中的社會分裂的現場,陳紅旗則選擇用藝術家個人具有宗教情懷特征的筆觸在描述著岜沙苗寨鄉民們粗糲質樸的日子以及一個微小族群面對的生存挑戰;他們有許多的不同,但是他們亦具有許多共同的思想維度,那就是客觀或主觀地表達出對于族群文化價值加速崩潰的憂傷,表達出藝術家對歷史中某些微小事物的崇敬并且努力再現其人性價值的狀態。
這就是我把陳紅旗與羅易疊加在一起言說的意義所在:其一,類似陳紅旗的一些中國當代藝術家很早就開始了一種對于跨國化藝術語言充斥藝術場域的反思;其二,當代藝術日益加速走向圖像化且平面化的語境,由此推促著藝術家重返繪畫中敘事價值的期待;其三,經過后現代價值批判的藝術家對于宏大敘事的遺棄促進了藝術家重建族群深處的小歷史而帶來的歷史觀念的再認知。它們都體現出藝術家對于現代性侵蝕的當代批判立場。從小說語言與繪畫圖像具有著共同的表征來看,當代藝術領域正在發生著一種新型的政治行為:為微小的乃至卑微的事物重建其人類心靈的價值而努力。
放在二十年前,我們或許會認為陳紅旗的繪畫語言,包括其繪畫的技法與表現性語言,都是建立在舶來基礎上的借用和模仿。其碩大的畫幅體現出西方傳統風景與歷史繪畫的宏大構造,其中厚實且強烈的對象體量感或者人物的動態與凝重的表情,那些精確且富有表現力的空間描述,乃至我們還可以發現畫家對于史詩般繪畫的戲劇化表現的恰當應用,再有其中塑造性極強的筆觸肌理乃至色彩的表達以及藝術家感性之泄露,等等,幾乎傳達出畫家是在西方經典畫法的呵護之下習得的技法。雖然,這是畫家極具專業素養和藝術靈性的展現。但是當我們放眼幾十年來中國當代藝術語言發展的系譜之時,我們會發現,以西方語言為典范的藝術表達方式已經從其發源的國度全面彌漫向世界,藝術語言的國際化態勢已經是不言而喻地建立在世界的各個角落。中國的當代藝術家們毫無例外地加入了這個巨大且獲益甚豐的俱樂部狂歡當中。簡單來說,在當代藝術的場域,語言的創新價值再沒有往昔日新月異般的輝煌場面,在藝術商業的壓抑之下,當代藝術史構建起來一個巨大的規訓法則,藝術家們除了更多反復重現諸種規范化言說之外,就是應用其種種聰明與靈巧在藝術的資本市場里竭盡全力地去分享通過圖式認同而帶來的巨大紅利。在這種語境里面,更加具有傳統特征的技法與繪畫觀念,如寫實的技法及其觀念,繪畫的敘事能力,以及面對現實的圖像觀念和藝術家的激情表達,等等,皆被當前諸多理論稱之為“鄉土的”、“寫實主義的”乃至更進一步被斥之為“老式的”、“落后的”和“商業的”藝術立場,亦即一種價值卑微的藝術立場。因此可以說,從其藝術風格來看,陳紅旗幾乎從開始繪制岜沙系列繪畫之時,就已經走向了與當代藝術之國際化潮流的反面。那時是上個世紀的90年代,正是中國當代藝術狂熱轉型的時代。在偏執且時尚的藝術理論看來,陳紅旗的轉型向更加傳統的藝術語言,或許就構成了一種藝術上的政治不正確,也因此,他的作品一直被棄置在批評家們的視野之外,藝術家本人也沒有更多機會去獲得其應當獲得的重視。

陳紅旗作品-人像局部6
然而,當語言的國際化潮流翻卷成為巨大的漩渦之時,正是藝術家更有必要根據自己的表達需要去進行睿智的選擇之時。這個時候,陳紅旗的選擇,是返回經典的繪畫技法并且在整合經典藝術諸多方法的同時去進行靈性的再發現。無疑,這是一個睿智乃至真誠的藝術家所必要走向的藝術歸途。因此我們也可以看到,陳紅旗的畫風里面,或許有著勃魯蓋爾式鄉間風情的寓意,也有倫勃朗式強烈的光影表現,亦有著如米勒一般的土地情懷,還具有著更為古老的宗教空間的意境,但是在其強勢的風格化里面,這些種種藝術史的遺存,都像是不同歷史時期藝術家間的心靈對話,有效且激烈的匯集起來,其畫幅當中那些沉著且內斂的人物群像敘寫著久遠且獨立的生命情境,那些躍動著的色彩與筆觸亦擔當著藝術家疾書時候的情緒敘寫,其戲劇性場景的瞬間力量以及人物行動時刻的情境推衍與展開,亦傳達出寫實繪畫所必須具備的歷史語境的像喻與連接,尤其是畫家在其表達一個微小族群生活場景時所賦予畫面的宗教性沉思,尤為體現出藝術家強硬的返回歷史深處的精神取向。凝重與憂郁,狂喜與悲愴,這些在美學史里面被充分賦予了宗教寓意和激情表達的表現性概念,在陳紅旗岜沙系列繪畫里面被凸顯起來,由此我們亦可以認為,陳紅旗所使用的藝術語言,當其面對岜沙苗族真實粗糲的生活世界的時刻,是一次重要且準確的選擇,其強烈而有效的藝術表達,體現出藝術家身處龐大紛繁的當代藝術史而做出完全個人性選擇的能力乃至勇氣。
面對陳紅旗重建寫實繪畫的勇氣,我們或許會強烈意識到,當代繪畫已經進入了一個藝術家個人建構其藝術語言的時代,是每一個藝術家個體再次拒斥藝術語言的集體主義狂歡的時代,是藝術家重新回歸藝術史而不是更狂熱地參與瓜分圖像紅利的時代。這是因為,從藝術語言的歷史價值以及其創建時代的美學思維的功能來說,藝術家肯定承載著一份重要的精神擔當。

陳紅旗作品-人像局部7
陳紅旗的岜沙系列繪畫,雖然展開的是一類寫實繪畫的風格,那些現實場景的再現以及高度戲劇性的人物神情,把寫實繪畫擬態狀物的要求予以了十分準確的表現,不過我們也看到畫面中更加富有表現力的那些突顯的光影,那些更加強烈的色彩表達以及超現實情境描述,都在為開端的寫實場景增加著鮮明的藝術家個人表達的特征。寫實的場景寫真和超現實的場景表現,類似宗教繪畫一樣的背景光影的添加,藝術家自己說,是來至對于俄羅斯教堂藝術的傾慕,那么可以說,當藝術家把這些傾慕應用在現實性場景中之時,這些元素無疑也構成了藝術家對于經典寫實性繪畫的形式突破。重要的是,陳紅旗的岜沙繪畫更為關注場景的敘事性結構,不論是人物群像,還是雙人肖像,乃至多種人物搭配,以及人物內在的生命感受通過這些敘事性言說獲得瞬間凝固的力量,強化著這個族群更為深沉的生命品格;喜悅、悲傷以及凝重的場景,得到了敏感且充分的再現;這些再現不僅僅是畫面中那些人物的孤獨出場,而是與岜沙苗族的生存語境作了廣闊的連接,少數族群生存語境在這些充分敘事性場景當中得到了強力的推衍。如果再把藝術家個人性表達的要素置入到敘事結構進行觀察,那么我們看到了更加豐富與強烈的敘事表達,那些急速的筆觸,動感的肌理,鮮明的光影層次,等等繪畫性成分,便成為藝術家與對象間相互關注乃至相互建構的重要手段。鮮明的文學性敘事與鮮明的圖像化敘事,共同結構起陳紅旗式的寫實性表達,藝術家既能夠充分表達岜沙苗族深邃的生命言說,也能夠充分展開藝術家與對象的富有激情的對話。現實對象與藝術表達的無間相遇,在陳紅旗這里亦成為其寫實繪畫重要的表現特征。
在形式主義的原教旨主義者看來,繪畫的敘事性架構應當是純粹形式化的,是勿容文學染指的,這似乎成為了現代主義的教規。但是陳紅旗作品的敘事性結構告訴我們,由于良好的形象塑造與敏感的戲劇性表達,以及藝術家個人情懷的有效融入,文學性價值重返繪畫并獲得了新生,在當代藝術的語境里面,這樣的文學性重建,其實亦是介入性藝術所必須的敘事功能的一種鮮明表達。這也是當代鄉土繪畫所具有的重要特征。
除了形式主義的藝術原教旨主義對于寫實繪畫的抑制之外,在當代藝術場域言說鄉土繪畫也是危險的,如前所說,商業化和國際化的強大規訓力量在其本質上是漠視地方以及與地方相關聯的鄉土的。即使宣揚一種本土性藝術價值,由于其迅速時尚化的機制而使其在展開的同時便迅速喪失本土化的獨立美學品格而迅速融入價值平面的文化與商業場域。鄉土的異域化、奇異化乃至文化觀看的諸多凝視規則對于鄉土價值構成了巨大的威脅。在此,鄉土繪畫的重建,除了需要藝術家對于鄉土藝術諸多藝術要素的更加積極的再認識之外,亦需要藝術家具有對于鄉土價值的更加獨立以及更加富有同情理解的勇氣和智慧。
面對鄉土,就是像貴州岜沙苗寨這樣的鄉土,藝術家們具有著幾乎一致的表現方式,亦即前述形式主義的原教旨主義者的方式,在這種方式中,岜沙苗族的生活場景,原始風貌的空間,服裝上那些絢爛的圖案以及旅游專家所謂“最后的槍手部落”的風情,在相關的藝術表現里面皆被“遙遠的異邦”觀念所籠罩,與旅游業對于岜沙苗族的商業化再現一樣,風情化、符號化地處理岜沙苗寨的異域情調得到了藝術家的認同。因此我們看到太多似是而非的、花團錦簇的乃至絢爛多彩的苗族符號肆虐在諸多藝術作品里面,古典貴族形象與岜沙概念的圖案相得益彰,苗族圖像亦被組織進抽象構成的圖式里面而形成了當代與現代主義藝術之形式意味。凡此種種,幾乎都是在形式主義規制之下的語言再塑,岜沙苗族生存場景中種種挑戰與困惑,皆被組織進一種我們稱之為“商業的凝視”場域之中而喪失其核心的文化生命價值,并且亦被有效地移入到了商業化藝術之中。這自然是圖像紅利時代的集體主義狂歡的結果。由此而言,商業化視角浸透進對于岜沙苗族的表達,與福柯所說的“凝視是一種權力”的浸透共同構建起我們時代另外一類權力的表達。
突破這樣一類權力化再現,似乎是陳紅旗岜沙系列繪畫的初衷。20多年的觀察與進入,岜沙苗族對畫家的生活觀念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自然也對藝術家對于岜沙苗族的藝術再現產生了決定性影響。
由此我們看到,這些作品中的岜沙苗族不再是絢爛多彩的苗族山民,而是喜怒哀樂形溢于色的男女人群,是接親、送親、醉酒、葬禮場景中的當事人,是悲哀與狂喜同在的現場,也是寧靜和喧囂并存的山寨空間。作品中的人物也不是遙遠異邦中的陌生人群,亦是如所有人群一樣處理著生生死死的瞬間。從生到死亡,男人與女人,青年與老人,皆如所有族群一樣日夜徜徉在生存的困境。沒有特別地去再現其族群的特別符號,亦沒有特別去表現藝術家的同情與悲愴。通過這些諸多的場景與人物形象,種種苦澀的、喜悅的,悲涼的和粗糲的生活行為被予以了直觀的再現,種種細微的表情與姿態被予以了精心的表達。這是一個微小卻整體的族群生境,一個微小卻深沉的生命情態,它們一一展開在藝術家筆下,展現在畫幅那些涌動的色彩肌理當中,蜿蜒在那些生動的敘事結構之間。與諸多被形式主義規制馴化了的藝術表達不同的是,這些作品幾乎是放肆地再現著岜沙苗族的真實生命,包括族群內部的倫理悲劇以及放浪的調情喜劇皆被藝術家予以了直觀的再現。
在淼淼人寰之中,岜沙苗族或許只是一個微小的存在,但是這個族群內部的一切生命存在亦是茫茫宇宙間生命存在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沒有每一個微小族群的生命存在亦沒有宇宙間巨大生命的價值。在充分消費主義乃至宏大無比的物質主義時代,岜沙苗族的生命或許亦是一種卑微的存在,但是其生活場景與所有生命情態也是一樣,默默地自我更新與安靜的自我生長于天地環宇之間,其生命價值與天地間全部的生命一樣都同樣具有不可褻瀆的莊嚴。藝術家陳紅旗或許有感于這樣的認知,因此在直觀再現岜沙苗族生命情態的同時,他亦直觀地把對于微小族群生命價值的情感予以了神圣化的處理,那些山邊的霞云或者郁郁山林當中的篝火光影,將這些微小生命場景呵護起來,亦將這些幾乎是卑微的生命情態賦予了神圣的光輝。藝術家將這一份尊重,毫不吝嗇的再現于幾乎所有的畫幅之中。這是陳紅旗岜沙系列繪畫里面最具震撼力的處理。從其碩大的畫幅里面,我們似乎聆聽著一聲聲祈禱的晚鐘,正回響在岜沙苗寨的群山林莽之間。全部的憂傷與悲愴,全部的喜悅與狂放,都被藝術家的傾心關切所籠罩。哪怕只是一個微小部族的生命戲劇,卻仿佛被藝術家將其放置在了人類的巨大舞臺之上而展示出來。
在陳紅旗的岜沙系列繪畫這里,鄉土繪畫與世界性的的族群價值再認知的潮流連接起來。面對全球化語境下的族群同化趨勢,藝術家們反身回到生活世界的內部,努力去發現諸多微小事物的價值,為這些微小的神靈注入了強大的神性,展現出一種更加富有人性的藝術靈智。而這也是印度小說家羅易與中國畫家陳紅旗所共同選取的一種價值回歸。
鄉土繪畫的重建,有待于藝術家對于微小生命情態的細致觀察,對于微小生活場景的深切關注。更為重要的是,鄉土繪畫藝術家有必要保持對于微小事物的持續性的尊重。所謂鄉土,在此才能夠成為藝術家真誠而傾心向往的一片純靈圣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