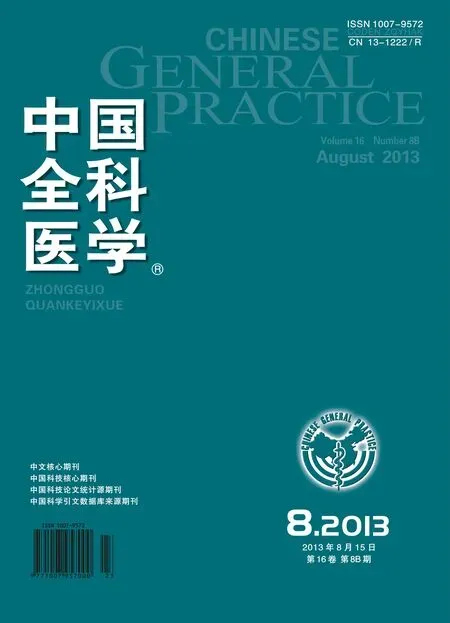永久性心臟起搏器植入患者術后發生囊袋相關并發癥的原因及預防對策
朱芳一,邊惠萍,楊良瑞
植入永久性心臟起搏器是臨床上治療緩慢性心律失常的有效方法,隨著其適應證的不斷擴大和人群老齡化,需要植入永久性心臟起搏器的患者數量逐年增加[1]。據不完全統計,全球約有325萬患者植入了永久性心臟起搏器[2]。盡管循證醫學證據顯示植入永久性心臟起搏器可極大地改善患者生存率,但同時也使患者暴露于手術相關并發癥的危險之下,這其中就包括永久性心臟起搏器植入術后囊袋相關并發癥。我院自2007年2月以來為610例患者植入了永久性心臟起搏器,本研究通過回顧性分析其臨床資料,旨在探討永久性心臟起搏器植入患者術后發生囊袋相關并發癥的原因及其防治措施,以進一步提高起搏器治療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2007年2月—2012年6月在我院植入永久性心臟起搏器患者610例,其中男325例,女285例;年齡27~85歲,平均(65±22)歲。納入標準:符合1998年美國心臟病學學會/美國心臟學會(ACC/AHA)及我國2002年中華醫學會心電生理和起搏年會植入性器械指南中的Ⅰ類和Ⅱ類適應證。610例患者中新植入起搏器440例,更換起搏器170例,永久性心臟起搏器和電極主要為Medtronic、Vitatron、ST Jude Medical等公司產品。
1.2 植入方法 所有患者采用公認的植入方法行鎖骨下靜脈穿刺,植入起搏器電極導線,穿刺側單切口手術植入起搏器。植入起搏器類型為單腔起搏器和雙腔起搏器。所有患者圍術期行心電監護,術中測試電極導線各參數,術后沙袋壓迫穿刺部位6~8 h,平臥休息24~48 h,應用抗生素預防感染3~5 d;一般情況下術后第7天拆線。
1.3 統計學方法 應用SPSS 14.0統計軟件進行分析,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囊袋相關并發癥 610例患者術后共發生囊袋相關并發癥43例,發生率為7.0%;其中囊袋血腫28例(4.6%),囊袋破潰11例(1.8%),囊袋感染4例(0.7%)。
2.2 囊袋血腫 28例囊袋血腫患者首先停用血小板抑制劑、抗凝劑及活血化瘀藥物,積血量少、局部張力小者加壓包扎12~72 h后積血吸收;積血量大、局部張力大者經嚴格消毒后局部穿刺抽吸積血并以沙袋壓迫或加壓包扎12~72 h后積血消失,穿刺抽吸次數1~3次,積血消失時間6~15 d;1例患者經5次局部穿刺抽吸積血及加壓包扎后無效,出血量較大,經外科手術切開引流并壓迫止血后積血消失。不同年齡、血小板計數、營養狀況及是否使用抗凝藥物患者囊袋血腫發生率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3 囊袋破潰 11例囊袋破潰患者局部分泌物細菌培養結果均為陰性,后將破潰處及菲薄組織梭形切除,以過氧化氫溶液、0.9%氯化鈉溶液反復沖洗囊袋,碘伏消毒起搏器和電極0.5 h后重新縫合,7例患者囊袋未再破潰;3例再次出現破潰,經重復上述處理后未再出現破潰;1例患者因囊袋局部反復破潰、3次手術效果不佳而轉至北京阜外醫院,行電極拔除術后對側重新植入起搏器,術后兩側囊袋愈合良好。不同手術次數、營養狀況患者囊袋破潰發生率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4 囊袋感染 4例囊袋感染患者細菌培養結果顯示,表皮葡萄球菌感染2例,金黃色葡萄球菌感染1例,溶血性葡萄球菌感染1例。3例患者經局部消毒、靜脈應用抗生素2周后感染控制;1例感染表皮葡萄球菌患者用藥后感染不能控制,經過氧化氫溶液、0.9%氯化鈉溶液反復沖洗囊袋,碘伏消毒囊袋和電極后,將電極剪短、打結縫扎于囊袋中,囊袋不縫合,經0.9%氯化鈉溶液紗條引流逐漸愈合,植入經股靜脈臨時起搏器,配合全身抗感染、加強營養等,2周后在對側重新做囊袋,植入新電極,術后患者雙側囊袋愈合良好,未再出現感染。不同手術時間患者囊袋感染發生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永久性心臟起搏器植入術后發生囊袋相關并發癥與患者臨床特征的關系〔n(%),n=610〕
3 討論
囊袋血腫、囊袋破潰、囊袋感染是永久性心臟起搏器植入術后最常見的囊袋相關并發癥,處理不當會對患者造成嚴重影響,已成為心血管醫師面臨的難題[3]。
囊袋血腫多發生于起搏器植入術后1~2周,發生率為1.1%~4.9%,若診斷或處理不及時,血腫持續存在會增加囊袋感染的危險性。囊袋血腫的常見原因有以下兩個方面:(1)手術相關因素:術中止血不徹底或囊腔中小動脈出血,囊袋大小不合適,多次穿刺鎖骨下靜脈,因外鞘過大導致電極入口處出血;(2)患者自身因素:長期服用抗血小板或抗凝血藥物、老年、消瘦、皮膚較薄、合并血管疾病等。隨著永久性心臟起搏器植入技術的不斷發展,手術相關因素導致的囊袋血腫發生率越來越低,目前導致囊袋血腫的原因以患者自身因素為主[3-4]。Wiegand等[5]認為,使用大劑量肝素及聯合應用阿司匹林、氯吡格雷等是導致術中出血及囊袋血腫的高危因素,術前停用抗凝藥物并在圍術期嚴格監測凝血功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朱銳等[6]認為,進行抗凝治療的患者起搏器植入術前一定要停用抗凝藥物并至少停用3 d,使患者凝血酶原時間、止血時間達到正常,一直持續到術后7~10 d。總的來說,起搏器植入術前停用抗凝、抗血小板藥物10 d以上可能更安全[7]。本研究結果顯示,老年、血小板計數降低、營養狀況差及術前使用抗凝藥物患者囊袋血腫發生率較高。本組28例囊袋血腫患者經糾正病因、局部加壓、穿刺抽吸等處理后多數愈合良好,僅1例患者行外科手術切開引流后得以恢復。總結囊袋血腫的防治措施有以下幾個方面:(1)術前應加強對老年患者及營養不良患者的評估;(2)術前應停用阿司匹林等抗血小板藥物1周,直至術后2周,并對血小板計數降低及凝血指標異常者予以糾正,必要時推遲起搏器植入術;(3)術前和術后早期盡量不使用抗凝、擴血管、活血化瘀藥物等;(4)發現囊袋血腫應及早處理,出血量小者加壓包扎12~72 h,出血量較大者局部消毒后以20 ml或10 ml注射器在起搏器表面抽吸,再重新以沙袋壓迫止血或加壓包扎12~72 h,多次穿刺后出血量仍多者應考慮拆開引流,但須嚴格無菌操作,防止感染[8]。
囊袋破潰是永久性心臟起搏器植入術后較嚴重的并發癥,本研究結果顯示,營養狀況差、2次及以上手術患者囊袋破潰發生率較高,與國內外文獻報道一致[9-10]。營養狀況差、多次手術是永久性心臟起搏器植入患者術后發生囊袋破潰的危險因素,因此,術前積極加強營養治療,術中規范操作、提高手術技巧有助于減少囊袋破潰的發生。本組10例囊袋破潰患者經1~2次清創處理后均恢復,僅1例患者經3次手術后仍出現囊袋破潰而轉至北京阜外醫院,考慮為原有囊袋偏小張力過大所致,后行電極拔除術后對側重新植入起搏器,患者術后兩側囊袋部位愈合良好。囊袋破潰后及時的清創處理具有重要意義,考慮囊袋破潰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兩個方面:(1)囊袋偏小或與原起搏器形狀不相稱引起皮膚受壓缺血,激發無菌性炎癥而導致囊袋破潰;(2)囊袋所在位置表淺(尤其是營養不良或合并全身性疾病者)影響皮膚血供,或囊袋過于偏外,肢體活動時帶動起搏器不斷與局部組織摩擦而造成皮膚壞死[8-9]。因條件限制,本研究在進行回顧性分析時無既往無囊袋張力的登記,故未對囊袋張力對囊袋破潰的影響進行分析。總之,除術前注意加強患者營養治療、盡量減少手術次數以預防囊袋破潰外,還需注意囊袋張力大小以及深淺以減少囊袋破潰的發生。
囊袋感染是臨床中的棘手問題,國內報道其發生率為0.4%~14.3%[11],本組患者囊袋感染發生率為0.7%。本研究結果顯示,手術時間>2 h患者囊袋感染發生率較高,但不同起搏器類型患者囊袋感染發生率無明顯差異。由于囊袋感染患者例數過少,因此,不完全排除雙腔起搏器植入時間長于單腔起搏器對術后發生囊袋感染的影響。目前,針對囊袋感染患者,尤其是合并感染性心內膜炎的患者,除給予積極的抗感染治療外,還應徹底移除整套起搏器系統(包括起搏導線),這是預防感染復發的惟一有效的方法。Bongiorni等[12]研究表明,關閉囊袋前采用0.9%氯化鈉溶液進行充分沖洗是預防囊袋感染的重要措施。本組4例囊袋感染患者均未合并感染性心內膜炎,經早期抗感染、清創、擇期對側植入新起搏器等綜合治療后痊愈。基于囊袋感染處理的棘手性,其預防顯得尤為重要,術前應加強患者的評估,術中規范操作,不斷提高手術技巧及熟練程度。
總之,成功將永久性心臟起搏器植入患者體內僅是起搏治療的開始,起搏器治療引起的囊袋相關并發癥已越來越受到重視,囊袋相關并發癥與患者自身因素及手術因素密切相關,了解囊袋相關并發癥的特點,重視患者的術前評估,術中做到規范操作,不斷提高手術技巧及熟練程度可以有效地防止囊袋相關并發癥的發生。
1 Cabell CH,Heidenreich PA,Chu VH,et al.Increasing rates of cardiac device infections among Medicare beneficiaries:1990—1999[J].Am Heart J,2004,147(4):582-586.
2 Chua JD,Wilkoff BL,Lee I,et al.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infections involving implantable electrophysiologic cardiac devices[J].Ann Intern Med,2000,133(8):604-608.
3 Klug D,Wallet F,Lacroix D,et al.Local symptoms at the site of pacemaker implantation indicate latent systemic infection[J].Heart,2004,90(8):882-886.
4 Sohail MR,Uslan DZ,Khan AH.Management and outcome of permanent pacemarker and implantable cardioverter-defibrillator infections[J].J Am Coll Cardiol,2007,49(18):1851-1859.
5 Wiegand UK,LeJeune D,Boguschewski F,et al.Pocket hematoma after pacemaker or implantable cardioverter defibrillator surgery:influence of patient morbidity,operation strategy,and perioperative antiplatelet/anticoagulation therapy[J].Chest,2004,126(4):1177-1186.
6 朱銳.廖志堅,李素珍,等.起搏器置入術后出現囊袋血腫三例[J].中國心臟起搏與心電生理雜志,2005,19(5):346.
7 馬長生,霍勇,方唯一,等.介入心臟病學[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11:11.
8 許偉源,郭航遠,彭放.抗凝抗血小板藥物圍術期應用與起搏器植入術后囊袋血腫形成的關系研究[J].中國全科醫學,2011,14(12):4106.
9 王玉堂,張曄.起搏器術后感染的識別和處理[J].中國心臟起搏與心電生理雜志,2009,23(1):75-78.
10 史揚,耿仁義.起搏器囊袋感染相關危險因素分析[J].中華醫院感染學雜志,2010,20(6):797-798.
11 Catanchin A,Murdock CJ,Athan E.Pacemaker infection:a 10-year experience[J].Heart Lung Circ,2007,16(6):434-439.
12 Bongiorni MG,Marinskis G,Lip GY,et al.How European centres disgnose,treat,and prevent CIED infections:results of an European Heart Rhythm Association survey[J].Europace,2012,14(11):1666-16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