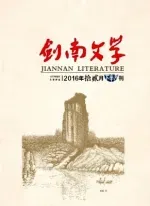追 夢
■何純芳

1
他拉過一把翻板椅,雙手往胸前一抄,斜坐在堂屋門口。那神情,那模樣就像癩蛤蟆遭牛踩了一腳,氣鼓氣脹的。
他三十八歲了,粗壯結實的身材。那張被河風砭刺的黝黑的方臉龐上,一雙深邃的大眼睛。沮喪的目光從摩托車、電冰箱、大彩電上一溜而過,停留在墻上地市委市政府去年給他頒發的 “地震無情人有情,身殘志堅知黨恩”的獎狀上,似乎那雙眼睛卻失去了光彩,無論望著哪兒都發呆出神。即使他車過來,看你一眼,你總覺得他那對明光閃亮的眸子里在思索什么,追求什么,讓人三天三夜都猜不出個名堂。
早晨,雞剛叫,他就睡不著了,摸索著拉亮了電燈。
“秀芳,秀芳!睡死了?”他見她不吭聲,便用腳在她屁股上輕輕地蹬了蹬,哀求道, “老先人,好話說了幾籮篼了。你幫我寫一個吧!好不好?”
本來,這些天妻子就好言好語勸過他,叫他不要去想那些事。
“吃得飽?你生些古怪!”她怒火中燒,“我給你寫寫寫……”像雜技演員表演蹬壇子一樣,兩只腳不住地朝他身上亂蹬。不是他搞得快,差點就滾下床來了。
此刻,他感到有些頭疼,雙手托著下巴,望著自己抖動的腳尖出神。可是,那個問題總在他腦殼里縈繞。
這是個竹林掩映的大院子,十幾家鄰居無不嘖嘖稱贊這小倆口婚后十多年連紅臉話都沒說過一句。在大河邊開了個石灰窯,他倆勤扒苦做,幾年時間就把一個清貧的家搞得 “尖冒冒”的了。州里有名,縣上有榜。可是,這一大清早,人們沒出門干活,都在各家的階沿上、院壩里,做點手面活兒,時不時卻乜斜一眼正房子那兒。哪怕是一聲細微的嘆息聲都不放過。偶爾聽到沒頭沒尾那么一句。唉,真叫人“丈二和尚--摸不著五筋頭腦”!也許是你啊,恐怕也要歪起想:昨晚黑,他是不是沒……
“洗臉吧,永貴。”秀芳把一盆冒著熱氣的洗臉水放在階沿邊的洗臉架上。
她比他小三歲。臉頰上一年四季都是紅撲撲的,好像三月間的櫻桃,指頭輕輕一彈就會冒水。腰上拴了條半新舊的藍布圍腰,看上去顯得輪廓分明,線條柔美。床上的爭吵,她覺得實在有些過分,因此主動給他端來洗臉水。她久久地注視著他那張愁眉不展的面容,心中有些不忍,便輕聲細語地勸道:
“永貴啊,地震你好不容易撿了條命,要好好珍惜。現在我們這個家,有啥不好哇?地震損壞我們的小青瓦房,我們卻換成了小洋樓。又只有一個娃兒,你在地震中雖然帶了殘疾,我不會嫌棄你。有吃有穿有錢花,就對啦!不要去想那些……”
“哼!虧你還是個初中生。”他沒等她說完,就打斷她的話, “知恩不報要遭雷打呀!”他低勾著頭,一雙大手胡亂地揉搓著頭發,心里產生了一種難以言狀的痛苦。
25年前,他媽去世不久,爸爸也跟著去了。留下他孤身一人。爸爸臨死前拉著他的手說,狗娃子,我不行了,你要好生做人喲。記到起,你媽和我都是苦命人。民國24年,我只有16歲,你媽14歲,我和你媽從很遠的地方討口到這北斗鎮大河邊落腳。幾十年了,這里的人心眼好。你若有出息,要替爸媽多多報答鄉親們。這二年,政策也好了,為你爸和媽爭口氣,把地種好。哎,爸沒出息,對不起你,只給你留下三間爛草房呀……
王永貴想起這些眼眶就濕潤了。汶川特大地震發生時,他和妻子正在裝窯,剛裝到一半,大地不住地顫抖,他還沒反應過來,轟隆一聲石灰窯垮塌了,把他埋在了亂石堆里,妻子幸運被摔在一邊,只受了一點皮外傷。村支書楊二爸聞訊后帶領十多名黨員救援隊從亂石堆里把他救了出來。王永貴的左腿被石頭壓斷,楊二爸和幾名黨員把他背到鄉衛生院救治,雖然帶了殘疾,走路一顛一跛,總算撿回來一條命。自己這個苦命人,是怎么有了今天的呢?他心中完全明白。唯獨妻子一點也不理解自己的心事呀。人,一旦富了,難道就把那不該忘記的也忘卻了么?良心啊,良心!王永貴心里產生了一股酸溜溜的味兒。
哦,他心中有怨。難道自己就沒有么?這幾天丈夫總對她發火,她默默地忍受了。因為她知道一個幸福的家庭往往就為一些口角言語帶來不幸。秀芳覺得他的腿不方便,就把放在洗臉架的水端到他面前,心平氣和地說: “永貴呀,莫忘了我們在河壩頭日曬雨淋,肩挑背磨,熬更受夜……”她攤開雙手, “你看,我比你少了個死繭,還是少落了一層皮,啊?你送給村上20噸石灰修水渠,前年玉樹地震你又捐獻三千元。吔,你看我沒說啥,背著你慪了好久喲!現在,你又要想入……”她把最后那個字沒說出來,怕院子里的人聽見。哎,昨天晚上,不!這幾天來,打了許許多多的比方給他聽。這是他多年的夢,看來他硬要犟出頭啊!不知什么時候,她眼眶里涌出了一團淚花,豐滿的胸脯不住地起伏,“反正,我不給你寫!”
“秀芳!”他眼里透出一股焦灼、茫然的光,聲音也有些嘶啞, “你你你,忘本了,忘了我這條命是怎么來的,忘了黨的……”
“永貴哩——,你想那些,總不是場好事啊!”她急忙打斷他的話。
“啥?你說的啥?”他不禁一怔,心里一陣愧疚、惆悵,覺得眼前的她判若兩人。眼下,他不想跟她展牙巴勁,心想:你不給我寫,好吧。我長得有嘴!他猛地立了起來,身胚像半截鐵塔。
“你要做啥?”她見他神色俱變。
“找楊二爸!”
“啊?你硬是當了真的啊?啥?富了?還不是靠自己!黨?黨未必幫你揀了坨圓寶石,還是幫你搓了個碳圓兒?”她見他走下階沿石梯子了,心中的憤懣涌上心頭,順手端起那盆洗臉水,使勁向他潑去。
水從他頭上淌下來,一直涼到了腳板心。花瓷盆在院壩里 “叮叮咚咚”旋轉了很久,很久,倒扣在地上。 “算了,算了……”人們模棱兩可地勸道。
他頭也不回地一瘸一拐地走了。
她把住門枋,不住地聳動著兩肩……
2
夏天的太陽剛爬上山頭,就讓人覺得烤烘烘的。寬闊的安昌河岸涌滿了金色的光輝。河面上,幾只藍頸脖、藍嘴殼的野鴨把頭斜插在翅膀里,順著玫瑰色的河水悠然自得地飄流,倏地騰飛起來,水面上蕩漾著一圈圈耀眼的波光。
王永貴沿著逶迤的河岸默默地走著,腳上像綁了坨百多斤重的石頭一樣沉重。那神情,那模樣,仿佛是要從流逝的河水里,追回他美好的夢。
那是初春的一天。村支書楊二爸找上門來說,狗娃啊,看你都十八、九歲了,光種幾分包產田,哪富得起來呀。趁早學個手藝。楊二爸,你說我學個啥手藝合適?王狗娃問道。明天,跟到我學燒石灰。楊二爸帶著命令似的口氣說道,工錢10元一天。王狗娃十分高興,第二天天剛麻麻亮他就到了楊二爸的石灰窯上。從這以后,楊二爸先是在河壩頭教他識別什么樣的圓寶石才可以用來燒石灰,哪些石頭燒的灰最白,最好賣。后來,楊二爸又手把手地教他裝窯,燒火,看火。石灰要燒過,火色不老不嫩才要得。王狗娃把這些一樣樣都記在心頭。幾年下來,他練就了燒石灰的一把好手藝,楊二爸還把石灰窯讓給他開辦。王永貴左思右想,沒有楊二爸的幫助,就沒有他富裕的家,更沒有如花似玉的老婆。
六月的一天,驕陽似火。秀芳姑娘在河邊低洼處洗衣服。突然,神不知鬼不覺地從上游涌來一股大洪水,把秀芳卷進洪流中。啊!救命……救命呀!這時,王永貴正在河對岸的石灰窯上干活,尋聲望去,只見秀芳姑娘在洪水中掙扎著、呼喊著,順水漂流而下。眼看就要沖下灘,掉進深潭里。王永貴奮不顧身跳進河里,把秀芳姑娘救上岸來。自從救了秀芳以后,他覺得秀芳不同以前了。她經常到石灰窯上來耍,聽楊二爸擺龍門陣。楊二爸似乎看出了一些什么,就專門講些英雄救美人的故事給她聽。
一天晚上,王永貴忙完了活路,一個人坐在工棚里抽煙。突然,篾笆子門吱的一聲開了。永貴哥,你還沒有睡啊?啊!是秀芳呀。沒有板凳,他趕忙抱來一坨大石頭,用手抹了抹灰,快坐呀!這些天,你很累,我來看看你。她從懷里掏出5個熱乎乎的熟雞蛋,雙手遞給他。永貴哥,快吃吧。他緊緊地捧住她的手,半天都不想松開。她順勢倒在他的懷里,永貴哥,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愛你,喜歡你。他一言不發,緊緊地抱住她……
雞鳴。狗吠。哦,攏了。王永貴默默地吸著煙,在楊二爸房側邊久久徘徊。哎,見到楊二爸,咋個好開口呢?回去吧,這是自己多年來的愿望……不知怎么起的,他鼓足了勇氣,走進了楊二爸的院壩。
怎么,關門閉戶的?楊二爸一家到哪兒去了?他感到很失望,順勢坐在院壩邊那塊洗衣石板上,冰涼冰涼的。 “秀芳,要是你真幫我寫一個多好啊。”他的目光盯著楊二爸睡房的玻璃窗子,窗戶沒有關嚴實,開了一道縫。心想,從那兒丟進去,楊二爸回來肯定能看見的。哦,自己寫!他取下鋼筆,忙在衣袋里掏紙。唉,存折。一張兩萬元的存折!昨天下午才存到信用社的。前幾天,他跟秀芳商量過,打算把全部積蓄用來辦洗沙廠,然后再辦水泥預制廠。他覺得心中掀起了一股巨大的熱浪。這一瞬間,好像有許許多多的人和事,在他腦海里涌現。
記得結婚那天,楊二爸主持婚禮興高采烈地說,鄉親們,我們共同祝愿這小倆口,幸福美滿,白頭偕老。永貴這娃兒從小就沒爹沒娘,現在還住草房子。今天,當著眾人的面,我把我的石灰窯讓給這小倆口經營。我呢,打算利用這條安昌河的優勢,搞個兩萬只良種鴨繁殖基地,還要開抱房,到時候給鄉親們提供小鴨兒飼養。鴨子喂多了,就辦個板鴨廠。每當想起這些,王永貴心里就像刀絞一般。
這時,他顧不得想過去哪些事,拿出一個空煙盒紙,慢慢撕開,墊在大腿上,摩得平平展展,還沒擰開鋼筆,眉毛卻皺成了疙瘩。
記得婚后不久的一天晚上,他叫秀芳幫他寫入黨申請書。
“為什么入黨?”她笑吟吟的問他。
“這,你知道啊。有了你,我這個孤兒,就有香火后代啦!”
“你壞你壞……”秀芳用軟綿綿的拳頭不停地捶著他的肩膀。
“真的,秀芳。我這個孤兒怎么活出來的呀,全靠楊二爸和眾鄉親,你一瓢,他一碗,把我拉扯大。嗯——,為了讓我們村的老百姓都過上好日子,我愿意落幾層皮,掉幾身肉,為黨出把力……”
秀芳沉思了片刻,柔聲細語地說,入黨?你這個夢,恐怕一輩子都圓不了。你呀還不夠格。住的是茅草房,咋個能起模范作用……
“咯咯——”雄雞迎著太陽聲聲高歌。打斷了他的回憶。楊二爸院壩邊,蔥籠的竹林里,雀鳥啁啾。他久久地望著金燦燦的天空,怦怦跳動的心胸忽然開闊了許多。
啊,我這個孤兒富了,興起家立了業。那么大的地震災難,要不是全國人民的支援,全村三百多戶人家能修起嶄新的樓房嗎?還修了水泥公路、學校、醫療站……所有這些全靠黨呀!哎,對得起黨嗎?為黨和人民做了多少有益的事呢?心里真慚愧呀!此刻,他覺得一個富裕了的孤兒,心里有許許多多的話要說。可是鋼筆都捏出水了,卻還沒寫下一個字。唉,只讀了兩年書,怎么寫呀?他憋得汗水直淌,努力在自己的記憶里尋找寫得起的字,暗自在心里編了好半天,才歪歪斜斜地寫下了一句——
楊二爸:
我要入黨!請你介紹。王永貴2013年6月8日
金色的陽光從婆娑搖曳的竹梢間篩灑到他的臉上、身上,紅殷殷的。這會兒看上去,他好像年輕了很多。他望著楊二爸家那玻璃窗口, “咚咚”地拍了拍胸脯,自言自語地說: “哼!讓大家看看吧,我王狗娃,難道硬是個沒有良心的人么?”
他捏著那張不平常的入黨申請書,朝著楊二爸家的玻璃窗口,一瘸一拐地走去,走去……
3
深邃的夜空,月明星稀。
藍幽幽的霧靄牽在大河兩岸,蒼茫迷蒙。遠處的灘口流水,嗡嗡直響。王永貴站在寶塔似的石灰窯邊,伸手摸,窯幫子烤人。抬頭望,窯頂上冒著縷縷淺藍色的余煙,空氣中散發出一股濃重的煤氣味兒。他圍著窯幫子這兒聽聽,那兒看看,仔細地檢查著。每窯石灰,他總是精心管理,火色拿得很穩,不老不嫩。因此縣城里許多單位守到城門口的不買,常常跑十幾里來照顧他。哦,明天縣上建筑公司的要來買,天亮挖開窯,把石灰晾冷,車一攏就裝。他邊想,邊走進那個三角支撐起的草棚。他熬了好幾個夜了,感到很疲乏,仰躺在稻草上,似睡非睡。然而,前天那幕鬧劇又浮現在他眼前。
半上午時,熾熱的太陽照在人身上,像背了個火籠似的烤人。王永貴從楊二爸家出來,剛踏上楊家大院子門前那座小橋,突然罵聲就從田野里綠色的浪尖上滾了過來:
“砍腦殼的!你富了,顯不出去了?做夢都在想要入黨,把30噸石灰和三千塊錢拿去繃面子!你的心是黃泥巴做的,也該裂點口口哇……”
呵,是她——秀芳!站在綠茵茵的河岸上,那惡咄咄的架式,像一頭攔路虎,恨不得一口把他吞了。
在秧田里干活的人們,伸長脖子,鼓起眼,灼人的目光盯滿了他渾身上下。小孩子就更不消說了,生性就喜歡鬧熱、新奇,早就把他圍起了。
“唉喲!這個婆娘咋成了母老虎啰?”
“永貴哥這個人呀——太瓜了!”
聽到這些議論,王永貴像打悶了的雞。
“瓜?”有人反對小伙子的偏見,說:“人家富了沒忘記黨,沒忘記眾鄉親。村上修水渠,他送了那么多石灰。玉樹地震他又帶頭捐錢。這是瓜么?螺螄有肉在殼殼頭!你切莫小看王狗娃這個家伙,簡直有個頭腦哩!看看他那個石灰窯吧,恐怕你們這些初、高中生,給人家提爛草鞋,人家也不要哩!”
“哼!沒聽見嗎?王跛腳為了撈黨票,想當官。丟臉!”一個小伙子尖刻地說,說得很大聲,好像有意讓他聽見似的。
哦,村上那截水渠,年年修,年年垮,我捐了幾十噸石灰才修起,自己也要享受呀!人要知恩圖報,因此玉樹地區的少數民族遭受地震我捐了三千。鄉親們呢?都是好鄉親。父母去世那些年,這個給菜,那個送米。逢年過節,這家請,那家拉,農忙時節鄉親們還幫我種包產田……楊二爸呀,楊二爸。前幾天,你在廣播喇叭上說,實現中國夢,要大家齊心協力,農村是大有希望的。實踐證明地震壓不垮我們莊稼人,莊稼人的日子會越過越紅火。我想入黨,為黨出把力!難道是丟臉?老婆啊,怎么你也不能理解我的心么?
“吱嘎”一聲。篾笆子門開了。王永貴一驚,坐起身,見是她來了,便鉆出草棚。
河風輕輕地吹。近處,流水潺潺。河面上月光溶溶,一輪圓月映在水中,顫顫跳動。
“唉——”他長長地嘆了口氣,坐在一坨抱大的圓寶石上,出神地望著波光粼粼的河面。耳邊似乎響起讀書時,老師教他唱會的第一首歌:
唱支山歌給黨聽,
我把黨來比母親。
……
哦,這些天,他總是想躲開我。一天三頓,碗筷一放,就到石灰窯上了。她知道他性子犟,擔心怕他出事,卻怎么也睡不著,鎖上門,悄悄地來了。
“永貴,明天就挖窯了,用不著守。走,回去吧。這兒蚊子多,河風也大,容易著涼。”她慢慢地踱過去,緊緊地偎依在他身旁,一只纖細的手掛在他頸項上,“楊二爸的恩是該報答的。等到下半年,我們去把他在信用社的貸款幫助還了,不讓他曉得。唉,說話呀!”她輕輕地搖了搖他。
“這個主意要得。不過,那天你簡直把人臉皮臊夠啰。”
“嗯。”她很坦率地,說, “我是有些不對。我擋你,也是為你好啊!聽我媽說,我爸教書就入黨,后又整成右派,下放農村改造,還挨批斗,氣死了。害得我媽守活寡。所以,叫你莫入……
“別說了!那都是過去的事……”他喉嚨里像塞了團棉花,胸口敝得慌。
“這二年,哪個管他入不入黨喲!白貓、黑貓,咬到耗子就是好貓。入黨有啥甜頭?說遠的你不曉得,你看楊二爸,一天忙了自己的,還忙別人的,像打不落的毽兒。當了幾十年村支書,吃?沒吃過啥。穿?倒土不洋。你看,累得只有兩個眼睛在轉了,還貸了一屁股的賬。聽說,這回要開門整黨,公開海選,楊二爸都自愿不當了,你入黨做啥?打消這個夢吧。”
哦,這二年,我真正覺得黨是了不起的!人啊,生在福中就不知福么?良心都不要哇?他記得有一回,大雪紛飛,北風呼嘯。他衣不遮體,坐在火堆旁不敢出門。楊二爸和幾個工作隊員,披著一身雪花鉆了進來,笑咪咪地把人民政府的救濟款、救濟糧、寒衣、棉被,還有些過年貨親自送到他家里……孤兒,怎么忘得了啊!不是一年,而是連續十幾年呀!想到這些,王永貴猛地站了起來,沖著她嚷道:
“吃了菌子莫忘了疙瘩恩呀!想過沒有,我們咋富了的?”
“靠自己,靠這雙手!勤扒苦做!”她朝著他甩去一句句硬頭冰梆的話,似乎牛都踏不爛。
“你在胡說!解放前那么多討飯的,包括我爸他們不也是有雙手嗎?”
“啊?不說。我不說,你就不曉得!”她油腔滑調地, “這二年,入黨又怎么樣?占不到點點便宜了。現在,不是那二年,只圖有塊金字招牌。銀子錢才是硬頭貨……”
吔,太歪了!簡直把人碼干了!他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憤怒,驀地沖過去 “啪啪”,出其不意給了她兩耳光,大聲吼道:“你給我滾!滾……”大河兩岸響起重疊不散的回音。
河風還在吹……
4
天剛拂曉。
王永貴拿起家伙, “乒乒乓乓”挖開石灰窯。剎時,濃煙翻滾,嗆得他不時跑到一邊,忍不住直打噴嚏。他吸了幾口新鮮空氣,又沖進塵煙迷霧中……
哦,真不該那樣做!她是個火暴性,人又小氣。唉,不怕一萬,就怕萬一……他忙完活兒,回家吃早飯,邊走邊想。她那張嘴厲害,可手兒巧,心眼好。不光是燒茶煮飯,犁牛打耙樣樣都行,不是那種好吃懶做的女人呀!不然,這個家怎么會……呵,她來了,上下一身新。在那青幽幽的綢帶兒似的田坎上,面對面地來了。
老遠,她看見了他。她急忙倒拐,又一條窄窄的田坎上。不知怎么起的,她仿佛覺得兩腿被什么拉著,邁不開,走不動。
“秀芳,秀芳……”他一瘸一拐地跑上去,拉住她。
“放開!我滾,我滾……”她哭嚷著,同他抓扯著。
“別說了,秀芳。我沒有這個意思……”他一把又拉住她。他知道這個家離不開她,他又是多么需要她啊。 “走,回家去吧。”
“快去入你的黨吧,莫管我!”
“秀芳,俗語說一日夫妻百日恩,這么多年,你……”
十多年的夫妻!甜的愛,苦的夢都有。唯獨沒有今天這一幕。
他見她不住地啜泣著,心中有些不忍,喃喃地說: “愿諒我一回吧,秀芳。我保證不打你了。”他反過手拉起她往回走。
鄰近,院子邊有很多眼睛在盯著他倆。她心想:這次不把他收拾倒,下次呢?干脆回娘屋耍上十天半月,表面上鬧離婚。入黨么?他自然會給我下趴 “蛋”……她猛地掙脫他的手,轉身就走。
他冷不防一個趔趄,霍地跳進秧田里:“哎喲——,我的腿桿!”
走了一段,她站住了,回頭看見他坐在田坎上,深深地勾著頭。怎么?她默默地走近他。唉,那是什么?紅殷殷的,和著泥水順著腿桿直流。怎么,他的腿桿?不!一身都在抖呢?她連忙蹲下身子,澆起田里的水,輕輕地、輕輕地給他洗著。好大兩條腿呀!青筋直冒,像一條條蚯蚓,彎來拐去,手一摸,她感到鼓棱棱的。呵,看見了!渾圓的膝蓋下,一條寸把長的口子。她用手一抹,又冒紅的……與其說那條口子劃在他腿上,不如說劃在她的心上……
哎,怎么?一點、兩點……背上冰涼冰涼的呢?哦,糟糕!暴雨要來啦!天空,一朵烏云涌了過來;近處,南山坡上,天地間像掛起了無數的珠簾,天河水 “嘩嘩”響。 “哎,天變一時,人心難估呀!”說完,他風風火火地向大河邊石灰窯一瘸一拐地跑去。
她跟在他后頭,邊跑邊哭嚷著說:“這個龜兒該安逸了哇?敗家子!一天都黨黨黨,你擋風,還是擋雨?這陣你把黨喊來嘛……”
閃電即逝, “啪啦”一聲霹靂,地下都在抖動。
“哧——!”暴雨落在石灰上,一點一個泡。遇水的鮮石灰,就像放鞭炮似的,“啪!啪!”炸響,立即開花開朵,白一片,散一壩。瞬間,石灰窯上白煙翻滾;滿地下,像白色的奶液在流淌。
王永貴猛地沖進那團神奇異常的煙霧里,只聽 “哎喲哎喲……”趕忙跑出來,兩腳燙得直跳。
“天啦——”秀芳忍不住地仰天嚎哭。
“完啦……”他在那團白色的煙霧里,跑過去,奔過來,急得抓天也不是,抓地也不是。
“一天都晚到吵吵吵!人吵敗,豬吵賣呀!”
“哼!千怪萬怪,還不是怪你!”她哭哭嚷嚷地沖到他面前, “入黨入黨,我曉得你是安心把這個家搞垮!人家好看笑話……”一股旋頭風卷起白茫茫的石灰,把她整個兒淹沒了,嗆得她喘不過氣,又打噴嚏,又流眼淚。
唉!對面河坎上哪來那么多人?哦,楊二爸跑在最前頭,后頭跟著十幾個黨員、團員,還有一長串鄉親哩!王永貴看見那條五色長龍正朝這邊跑來。
頓時,石灰窯上沸騰了。蓑衣、斗笠,一蓋上去就 “哧哧”冒青煙。塑料布一鋪上去,就燙成了卷卷,散發出一股怪味兒。電閃,雷鳴。雨不住地下。風,更不近人情,卷起漫天的石灰,弄得人睜不開眼。石灰水也順著鼻子、眼窩流,就像撒了干海椒面一樣,干澀、發痛,氣也出不贏,還忍不住直打噴嚏;石灰水流進嘴里了,那種味道才難受呀!
“喂,快過來。抬草棚!”
楊二爸一聲吆喝,提醒了大家。人們立刻圍住那 “千柱落腳”的三角草棚,“預備起!”眾人一伸腰, “嘿左,嘿左……”迎著狂風暴雨一步步硬抬過去了,嚴嚴實實地罩在石灰上。
風停了。雨漸漸小了。
“喂,你們再去看看劉興云的瓦廠。”楊二爸向旁邊的抗洪搶險救援隊說道,“我馬上就來。”
王永貴和秀芳望著那些遠去的背影,心里有說不盡的感激之情。
“永貴呀,秀芳。你們過來。”楊二爸站在草棚邊,一身濕漉漉的,連鼻子、眼窩都巴滿了雪白的石灰漿漿。
王永貴和秀芳慢慢地向楊二爸走去,忽然不知怎么起的停下腳步,便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深深地勾下了頭。好半天,秀芳開口說道,楊二爸,我對不起你。 “撲通”一聲跪在地上。王永貴也跟著跪了下去,說: “楊二爸,真謝謝你!”
楊二爸趕忙把她倆扶起來,微笑著說:“不用謝,這是我們黨員、干部應該做的。秀芳呀,你把這個申請書重新給永貴寫一下,行么?”他把一本黨章和那張不平常的入黨申請書遞給了她說, “永貴這入黨申請書太簡單了。你把黨章讀給他聽聽,對黨的認識要深刻才行。”
“嗯!”秀芳羞怯地點了點頭,說,“這是他多年追逐的夢,我也該成全他一下了。”
楊二爸微笑著,點了點頭,說: “但愿如此。”他便告辭走了。
雨住了。云縫里投下萬千條耀眼的光柱,一道奇異的彩虹從大河邊上,直牽到南山坡那邊。
天空,艷紅、奇麗、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