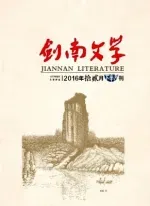屋檐下的歲月
■北 草

記憶里,屋檐屬于舊時,屬于老屋,屬于故鄉。
那時,我只有五六歲,老屋的屋檐很低。到了漫長的冬天,會有一場又一場的雪接連不斷的落下來。村子里那些高高低低的屋檐下,一條條倒掛的冰溜子在太陽光的照射下顯得晶瑩剔透。若從屋檐經過,一不留神就會有一小塊冰碴子或融化的雪水跌落在衣服領子里,颼颼涼。這一幕,不管是大人還是小孩,都會牙呲嘴咧幾下后,縮著脖子打幾個冷顫,兀自又忙作起來。
等雪停了,孩子們聚集屋檐下,搬個凳子,仰著脖子,用瘦長的胳膊使勁夠那些冰棱兒。有調皮的直接拿著竹竿朝著屋檐一陣胡亂敲打,散落的冰棱兒四下飛濺,惹得伙伴們嘰嘰呱呱一陣呼喊亂叫。還有的,用凍得通紅的小手接住,躲過家人嚴厲的目光,偷偷縮在墻角咯嘣咯嘣的吃著冰棱兒,嬉鬧不休。那架勢,就像現在我女兒坐在沙發上,夏天咀嚼冰淇淋和雪糕一樣有滋有味。
很快,冬天過去了,春天來了,門口的屋檐下總會站著和母親一樣的女人。她們圍著圍裙一邊撿拾柴禾一邊急急的向村口張望,直到看到自家男人一手牽著耕牛一手扛著鋤頭懶散而歸。那牛蹄兒敲打著土疙瘩路的悶響聲漸漸走近了。男人穿過上房的屋檐進了后院,將牛拴在樁子上,然后回到前院,接過女人遞過來的臉盆,撩起水,擦洗去一天的勞頓和困乏。
后來,搬遷了,低矮的屋檐被青磚灰瓦的屋頂替代了。但我依然記得,父親和母親省吃儉用,一塊磚一片瓦,一條檁子,一車沙子,一袋水泥,艱難湊齊了蓋房所用的材料。挑了日子,放了鞭炮,請了鄉鄰,經過近乎兩個月的日夜忙做,終于換來了我家的幾間大瓦房。喬遷新屋那天,廚房的大鍋里酸菜燉肉,院子的飯桌上觥籌交錯,好生熱鬧。安頓好了后,父親在房前屋后,栽上了李子樹,海棠樹、桃樹,葡萄樹,土槐樹。這些樹,經一縷縷的風兒輕拂,一場場的雨兒滋潤后,枝干一日日粗壯,莖葉一日日茂盛。
流年似水,不知不覺中,我和那些樹兒一起成長。只是我忽略了,一直為我遮風避雨的老屋和填滿我歡聲笑語的屋檐,正一年年的被風雨殘蝕而漸漸衰敗。我更忽略了,當我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時,父親和母親,卻在這片老屋的屋檐下,慢慢老去。如門房檐下的那兩棵土槐樹,仿若被歲月拽著奔跑似的,恍然間已根深葉茂,綠蔭婆娑。而我卻在一個有著收獲和豐盈的九月,要與它分別了。從此,這屋檐成了我生命里一道酸楚而甜蜜的回味。每當我在異鄉飄泊中疲憊和倦怠時,每當我在人世浮沉中浮躁和茫然時,那屋檐下總有母親慈愛的呼喚,總有父親平和的注視,而我,就像服了一劑心靈的湯藥,頓然溫暖,頓覺豁然。
今年秋天,我又回到了老屋。偶見檐下那棵老槐樹上,爬滿了一層層的蜘蛛網,有蟬兒罩在上面嘶鳴。我的心忽而溫軟起來。那些和伙伴們上上下下爬樹、撲蟬、掏鳥蛋的歡樂,又一次映襯在眼前。還有老屋檐下飄過的一縷風一陣雨,也是那么的熟悉和親切。大抵也是這風聲和雨聲里,曾經掩著太多我們檐下玩泥巴、捏泥人,捉迷藏的開懷吧?
整整一個假日,我盡情攤開自己的身心,行走在故鄉的每一條小路,每一片田埂,觸摸一份遠離城市的安靜和清新。其實,這些年,這樣的歸去來兮,總在門口那片屋檐下一次次的迎來送往中,讓我的腳步不停的駐足和回望。雖然,我尋不到幼時那低矮的屋檐了,那個有著燕子呢喃的屋檐,那個麻雀壘窩的屋檐,那些在冬天掛著長長冰凌的屋檐,那些在雨季里長滿青苔的屋檐,永遠不再。而我甚感欣慰的是,一直有老母親和老父親,在老屋的檐下,一年一年的默默守候我,與我而言,何嘗不是幸而又幸呢?
這般想的時候,我心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