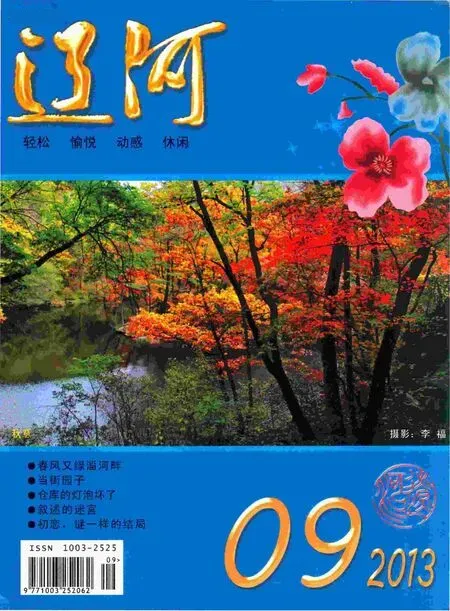農家小院
王吉慶
在陜南,翻過一座山,走進一條溝,穿越一片林,隨便走到哪里,總有一條條彎彎曲曲的小路,一彎曲曲彎彎的小河,牽引著你往前走,總能看到一座座遺失在山間的村莊。
拐過一道彎,走上一道坡,繞過一道坎,你就會看到,或一叢竹林,或一片樹林,那里一定就會藏著三、五戶人家。一戶人家就是一個小院,這些小院沒有規則,不受約束,零零散散地散落著。房子被樹林和竹園包圍著,竹根連著屋基,樹冠遮著屋頂。白色的墻壁,灰青的瓦頂,矮矮的豬舍,寬敞的庭院,還有三五成群的雞鴨游蕩在院子的角落里,一只或白或黃或黑的狗匐在院子門口,一個農家小院的精妙輪廓就顯現在人們的眼前。
縱橫交錯的路,像一張撒出去就永遠無法收回的網,卻能網住山丘,網住田野,網住游子的心,最終九九歸一的打上一個結,牢牢地系在農家小院里。
清晨,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家小院,被一聲聲金雞報曉的晨曲早早叫醒,大門里會走出兩個女人,站在臺階上的老者將五個干癟的手指往開一散,嘴里吆喝一聲長音歌似的語音,一群活蹦亂跳的雞鴨便振翅活躍起來;站在圈舍邊的少婦嘴里就那么一叫喚,手在盆邊就那么一敲,大大小小的豬小子,就爭相開始了他們的早餐;一雙泥腿子,就荷著鋤锨立在黑黑的田埂上,十個和泥土一樣顏色的腳趾,穩穩地扣進泥土,像凸出地面的樹根,農家小院一天的生活就這樣開始了。千百次地重復著同樣的動作,千百次地望著成長的禾苗,他們的笑容里藏著的一定是收獲的甜蜜。
正午,日頭當頂,就到了吃午飯的時候了,小小的方桌,往堂屋中間一擺,村婦們就會將早已做好的飯菜端上來,桌下放著三、五雙長短不一的泥腿子。桌子中央是一碗農家特有的腌制臘肉,賢惠的媳婦會夾一塊大的給婆婆,夾一塊中的給丈夫,夾一塊小的給孩子,這個時候聰明婆婆也不忘了夾一塊給媳婦,在筷子的交往中和睦了自古以來就難以彌合的婆媳之爭。幾束陽光從屋頂上照下來,像幾枚金燦燦的銅錢,滿屋生輝,其樂融融。
傍晚,勞累了一天的人們,飯后美美地打上一聲哈欠,夸張地伸上幾伸懶腰,就開始相互串著門了,他們聊張家的小子有出息,聊李家的閨女長得俊,聊天氣的酷熱與寒冷,聊莊稼的收成好與壞,聊誰家的賢惠媳婦孝敬公婆有好處,聊誰家的不孝逆子虐待老人遭報應。他們海闊天空,無所不談,從他們的談話中,看得出泥腿子一樣懂得什么叫真、善、美,什么叫假、丑、惡,就是在這樣的閑聊中讓農人們打發著寂寥的日子,也讓我們的古國文明在古樸的農家小院里得到了傳承。
走進農家小院,一種淳樸、溫馨、安靜的感覺立即會停留在你的記憶里。房前屋后栽滿了櫻桃、蘋果、葡萄、石榴、梨樹、棗樹、柿子、核桃各種各樣的果樹,一年四季果甜花香,就是到了冬天有客人到來,好客的農家人也會將珍藏的蘋果、梨、核桃、柿子之類的自產貨,拿出來招待客人。小院的風情得到完美的展現,也體現了山里人誠實厚道的至誠本性。
到了秋季,進得農家小院,你就會被那懸掛著的喜悅所沉醉:那倒掛著的紅高粱,血一樣紅,像村婦的紅頭巾;房前檐下樹叉上掛滿一串串黃燦燦的玉米,像農夫金燦燦的笑臉!而點綴中間的或是一串串火紅的辣椒,或是已失去水分卻留有青春的各色蔬菜,屋頂上還有那白白的薯片,琳瑯滿目,無不透露出農家小院的豐收與富足。
陜南的農家小院是一道獨特的風景,在城市里是無法看到的。它的大門是與眾不同的,門的頭上和兩邊是用水泥搪好的,是專門用來貼對聯的。再窮的人家過年時大門小門都要選上幾副絕好的對聯貼上去,到了四五月的時候仍保存完好,當你一走進農家小院的時候,就會感到喜慶的氣氛。紅漆的大鐵門上還貼了兩張大大的金“福”,太陽一照“福”字就會放射出耀眼的金光,使那兩扇紅漆的大鐵門顯得更加喜慶了。進了農家,堂屋里通常會擺上一張黑漆的大方桌,對于經常小聚的農家來說再合適不過了!最顯眼的莫過于堂屋的壁墻了,后墻正中央是“天、地、君、親、師”位,兩旁是容納孝道內涵之楹聯,上方就是體現姓氏宗祖的堂別了。
農家小院,無論什么時間,無論什么地點,總是富有那么一種無可比擬的美。我們走進農家小院,總有一種向往;走出農家小院,更有一種留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