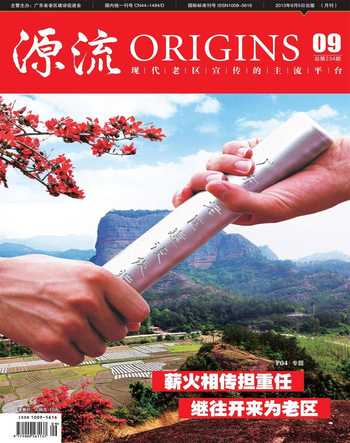1941年的“吃飯”愛國運動
瀟湘雨
為了支持祖國的抗戰(zhàn),1941年7至9月間,由宋慶齡在香港倡導的“一碗飯運動”,引起香港各界極大的震動。香港民眾紛紛上街購買飯券,吃“愛國飯”、“救國飯”,資助抗戰(zhàn),救濟同胞,充分體現(xiàn)了香港同胞的愛國熱情。
籌辦“一碗飯運動”
“一碗飯運動”原是美國醫(yī)藥援華會等團體于1939年首倡的。它每年舉行一次,在美國人民和華僑中募集捐款,以購買醫(yī)藥和醫(yī)療設備,支援中國抗戰(zhàn)。不久,“一碗飯運動”擴展到英國、加拿大、南美等許多國家。
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開始進攻香港之前,香港成為抗日救亡運動的據(jù)點。為募集資金,救濟傷兵難民,時任保衛(wèi)中國同盟(簡稱“保盟”)主席和中國工會國際委員會名譽主席的宋慶齡,在香港發(fā)起和領導了這場轟動全港的“一碗飯運動”。她認為在香港發(fā)起這樣的運動,對激發(fā)150余萬香港同胞的愛國救亡熱情、募集救災救難的經(jīng)費具有重要意義。
5月初,根據(jù)宋慶齡的倡議,“保盟”在香港成立了以宋慶齡為名譽主席,香港立法局華人首席議員羅文錦律師為主席,香港醫(yī)務總監(jiān)司徒永覺的夫人克拉克為副主席,并包括香港華商總會負責人在內的“一碗飯運動”委員會。經(jīng)研究,委員會決定發(fā)售餐券1萬張,每張港元2元,餐券的價值本可享受幾道菜肴,但認購者只能持券到提供贊助的餐館吃炒飯一碗,這種差額盈余將交給中國工業(yè)合作社為救濟西北難民的基金。
舉辦“一碗飯運動”,立刻在香港各界引起極大的震動。第一位捐助者是威靈頓街麗山餐室的老板溫梓明,他表示愿捐飯500碗。在他的帶動下,香港各酒樓、餐室紛紛響應,幾天中,就有13家餐飲店參加,共捐飯5000余碗。大家把它稱作“救國飯”。
“一碗飯運動”成立大會召開
7月1日晚上,在香港灣仔著名的英京酒家,由宋慶齡主持了規(guī)模盛大的“一碗飯運動”開幕典禮。“一碗飯運動”委員會的大部分成員以及香港各界中外人士150多人出席了開幕式。宋慶齡首先向在座的各位介紹了開展“一碗飯運動”的意義。她指出:“‘一碗飯運動不但是募了捐去救濟被難的人們,并且是要節(jié)飲節(jié)食,來表示犧牲的意思,這是我們做人的美德,無論中外,無論古今,都是值得贊揚的。”并強調說:“‘一碗飯運動是同情于我們抗戰(zhàn)建國,而發(fā)揚民主精神的表示。”,“更含有一種深長的意義,因為這次捐款是要幫助工業(yè)合作社去組織及救濟難民、傷兵,這是鞏固生產(chǎn)陣線,是生產(chǎn)救國,是幫助人們去幫助自己,是最妥當?shù)囊环N救濟事業(yè)。”
在大廳主席臺上,陳列著一些宋慶齡捐贈的孫中山生前珍貴的墨寶及其它文物和紀念品,并當場義賣,作為向“一碗飯運動”的捐款。不多時這些珍品便被爭購一空。
成立大會后,“一碗飯運動”委員會通過新聞、文藝界進步人士,展開了廣泛的宣傳和動員活動。在社會各界的大力宣傳、鼓動下,香港餐飲界對“一碗飯運動”的反響非常熱烈。以麗山餐室首先宣布捐贈炒飯后,上環(huán)水坑口的樂仙酒家立即表示捐助3000碗。接著,英京、龍泉、廣州、漢商、天燕、小祗園等酒家、餐室、茶居等也踴躍捐飯。截止8月1日,捐助數(shù)已達14700碗。與此同時,香港工、商、婦、學等社會團體也紛紛響應“保盟”的號召,協(xié)助“一碗飯運動”委員會推銷飯券,他們是:華商總會、南華體育會、中國青年救護團、嶺南同學會、港九居民聯(lián)合會、華人機器會、婦女慰勞會等等。此外,荃灣的天天酒家、中豪聯(lián)商會、國華銀行、五邑工商會等社團,以及鄭鐵如、唐譚美、高福申、羅文錦等人,也都為“一碗飯運動”捐款。
“一碗飯運動”轟動全港
1941年8月1日,計劃進行3天的香港“一碗飯運動”正式拉開帷幕。
清晨,克拉克夫人等“保盟”工作人員就分赴各酒家、茶室,巡回各店的準備情況,對他們的精心布置、有序準備表示滿意與感謝。
英京、樂仙等13家酒家、餐室都將自己的廳堂門面布置得新穎別致。有的在門上掛出“歡迎來吃救國飯”、“愛國之門”、“光榮之門”的橫幅,有的在店堂內張貼愛國宣傳畫,還有的展出了抗日戰(zhàn)士英勇殺敵、工合社員努力生產(chǎn)的圖片等,準備工作井然有序。地處灣仔的英京酒家在二樓專設一廳為接待“一碗飯運動”顧客,并免茶資費。樂仙酒家更是別出心裁,對捐款達100元以上者,則用該店珍藏多年的大紅古碗盛飯款待。
公共汽車、電車上,也張貼著標語和宣傳畫,有寫著“為祖國無家可歸的難民請命”、“大家來吃愛國飯”、“全部收入撥交中國工業(yè)合作社擴大救濟工作”等口號。特別是當天上午,一只特制的大碗模型出現(xiàn)在街頭時,把活動推向了高潮。一大群人簇擁著這只“大碗”喊著“多買一碗飯,多救濟一個難民”的口號,穿過中環(huán)、西環(huán)、灣仔等鬧市區(qū),給本來就已是家喻戶曉的“一碗飯運動”增添了氣勢。
這一天,香港民眾紛紛上街購買飯券,大家都以能夠為資助抗戰(zhàn)、救濟祖國同胞為榮。他們美稱炒飯為“愛國飯”、“救國飯”,是為救亡盡力,故而個個臉上呈現(xiàn)自豪的神色。一個小攤販說:“平時各項開支省了再省,即使是一根火柴錢也都要掂掂分量,唯獨買‘一碗飯運動餐券不能小器。我買了5碗,妻子兒女都吃了,雖然用去了好不容易賺到的10元錢,心里卻十二萬分的高興,因為我們一家算是盡了中國人應盡的一份責任,良心上感到安適。”
各餐室的老板、店員都視參加“一碗飯運動”為一生中最有意義的事,如辦喜筵那樣著意配料加工,以空前優(yōu)質的服務接待食客。有個衣衫襤褸的乞丐,瞻前顧后上了英京酒家二樓“一碗飯運動”專廳,揀角落里座位坐下。他一生中可能從未進過如此豪華的酒樓,顯得很不自在,正心神不寧時,漂亮的女招待端著熱氣騰騰的炒飯,送到他面前,微笑著說:“請用飯。”現(xiàn)場采訪的記者目睹了這一不同尋常的場面,問酒家經(jīng)理高福中:“討飯的也來貴店吃炒飯,你們不討厭?”高經(jīng)理正氣而言道:“愛國不分貧富,凡是來吃愛國飯的,我們一視同仁都是熱誠歡迎接待。”
8月2日、3日,正值周末和星期天,市民把參加“一碗飯運動”作為最光榮、又留永恒紀念的活動,或攜幼扶老舉家共食;或和朋友同去餐室。家境貧寒的,買一碗回去,一家老小圍坐,你一筷,我一匙分享;病老不能出門的,托人捎帶。香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中外,個個都知“一碗飯運動”,他們階層不同,然同情傷難,支持工合,奪取抗戰(zhàn)勝利的熱情一致!
在當天的《華商報》上,頭條刊登宋慶齡的題詞:“日寇所之,骨肉流離,凡我同胞,其速互助。”
“一碗飯運動”延長了日期
原定進行3天的“一碗飯運動”很快就過去了,可仍有許多人為沒能吃上“一碗飯”而遺憾。各界人士也紛紛呼吁,希望能延長時間,以便能讓更多的人吃到一碗“愛國飯”、“救國飯”,以表達他們的一片愛國救難之情。在這種情況下,結果多數(shù)餐室延長了日期,其中龍泉茶室延至8月10日,天燕餐室延長至15日,而樂仙、小祗園兩家一直持續(xù)到了8月30日。售出的餐券,遠遠超過了原定的2萬張的指標,“一碗飯運動”取得了圓滿的成功。
9月1日,“一碗飯運動”勝利落幕,在英京酒家舉行了結束典禮,宋慶齡到會主持。會上公布了“一碗飯運動”收入:扣除各項開支,凈余港幣25000元,法幣615元。勝利進行曲中,宋慶齡頒發(fā)獎品,把有她題寫“愛國模范”的錦旗,授予認捐炒飯的13家優(yōu)勝餐室;又向英京、小祗園、樂仙三家業(yè)主高福中、歐陽藻裳、龐永棠贈送了孫中山先生遺墨“努力向前”,以資特別鼓勵。
“一碗飯運動”取得了圓滿成功,所得收入全部捐贈給中國工業(yè)合作運動,有力地支援了中國的抗戰(zhàn)。它的成功,一方面離不開宋慶齡的大力支持,另一方面,更離不開香港同胞的愛國救亡熱誠。
香港自古是中國的領土,香港同胞是中華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歷史悠久的中華民族,造就了共有的民族意識。它一方面表現(xiàn)于人們對故國故土和傳統(tǒng)文化執(zhí)著眷戀,具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民族責任感;另一方面,表現(xiàn)為民族的凝聚力和一致性,在民族敵人面前團結為一體,同仇敵愾。事實證明,香港同胞的這種傳統(tǒng),在19世紀40年代以后,在中華民族蒙受苦難中和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斗爭中,得到錘煉,經(jīng)歷過抗日戰(zhàn)爭的洗禮,更見鮮明。宋慶齡正是基于對香港同胞的這種民族意識的肯認,才決定在香港發(fā)起“一碗飯運動”。也正因此,“一碗飯運動”才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