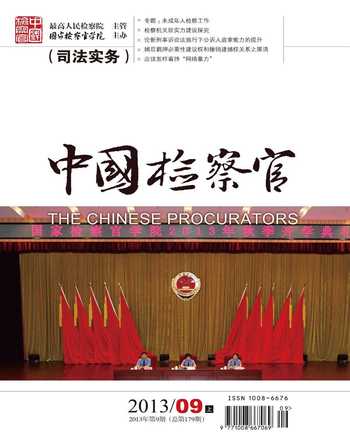淺論檢察環節的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
鄭小敏
一、檢察環節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存在的問題
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建立,是修訂后刑訴法的一個亮點,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對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并沒有做出完整的程序性規定,不可避免地將影響到該制度的實施效果。對于檢察環節而言,可能存在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缺乏必要的前置封存程序。《未成年人保護法》第58條明確規定:“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聞報道、影視節目、公開出版物、網絡等不得披露該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圖像以及可能推斷出該未成年人的資料。”但值得注意的是,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并沒有就此作進一步細化,在偵查、起訴、審判等各個階段設立完善的案件材料封存或保密制度,使得《未成年人保護法》的這一規定形同虛設。事實上,信息保密和資料封存是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前提。根據修訂后的刑訴法,犯罪記錄封存適用于“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的未成年人。根據“無罪推定”原則,在法院尚未作出判決的偵查、檢察環節,犯罪嫌疑人在理論上是被推定為“無罪”的,其涉嫌犯罪的各種信息資料更應當得到保護。否則,如果在偵查、起訴環節的各種信息資料不當泄漏,社會對涉罪未成年人已經貼上了標簽,判決作出后再進行“犯罪記錄封存”就失去了意義。以李天一案件為例,在刑事拘留階段,媒體已經披露了李天一的大量的相關信息,包括照片、家庭、成長歷程等等,各種不利于未成年人保護的謠言在各大媒體競相爭奪眼球,在“百度”上搜索“李天一輪奸”竟然可以搜出963,000個結果,李天一的個人隱私權遭到無情踐踏。以至于法律界人士忍不住呼吁:“保護未成年公民李天一的合法權益”,“莫讓未成年人保護制度成為空文”。[1]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日后李天一被判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對他實行犯罪記錄封存,也已經失去了應有的意義。因此,建立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前置程序就成了包括人民檢察院在內的司法機關在貫徹落實修訂后刑訴法中亟須解決的問題。
第二、法律規定較為模糊,容易產生不同理解。首先,有權查詢未成年犯罪記錄的主體不明確。其次,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缺乏配套制度,各部門聯動配合難。再次,犯罪記錄封存制度可能與有關法律產生沖突,可能給執法者帶來執法的困惑。如我國《教師法》、《會計法》、《醫師法》等都有受過刑事處罰不能執業的規定。犯罪記錄封存后,能否接受這些單位的查詢?如果可以,是否會對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執行效果大打折扣?如果不行,這些法律的效力又該如何體現?
第三、檢察監督制度缺位。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沒有設定檢察機關對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執行情況實行監督可操作的具體程序,《人民檢察院訴訟規則》也缺乏相應的規定。由于對犯罪記錄封存制度檢察監督的缺位,檢察機關對犯罪記錄封存中的種種違法行為將難以開展監督。如:有義務封存未成年人犯罪記錄的主體,如不封存相關記錄檢察機關該如何監督等等都是檢察環節執行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中應當思考的問題。
二、對檢察環節執行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建議
(一)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的前置程序
所謂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的前置程序,是刑事訴訟程序啟動之日至法院作出判決之前,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對認為罪行輕微、可能判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未成年人涉案材料單獨裝訂,相關信息嚴格保密,非經批準不得對外披露的工作制度。這一程序是犯罪記錄封存的一個前置程序,服務于犯罪記錄的封存,保障犯罪記錄封存的效果。筆者建議犯罪記錄封存的前置程序至少可以包含以下內容:
1.從立案開始對涉案未成年人的材料單獨裝訂。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進一步加強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的決定》,檢察機關應當建立健全分案起訴制度。對于受理的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在不妨礙查清案件事實和相關案件開庭審理的情況下,應當將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分案提起公訴,由法院分庭審理和判決。實踐中,在審查起訴階段,檢察機關一般將涉案未成年人的卷宗單獨裝訂,分案起訴。筆者認為,從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避免信息泄漏的角度考慮,分案裝訂的程序可以向前延伸至立案。盡管立案程序由公安機關完成,但檢察機關偵查監督部門可以對公安機關提出分案裝訂的要求,對未單獨裝訂的案件原則上不予受理。特殊情況也可先受理,在做出是否批準逮捕的決定后要求公安機關將未成年人涉案材料分案裝訂,移送起訴。單獨裝訂的案件材料應粘貼“擬封存”標識,與其他案件材料區分,嚴格管理,避免泄漏。這一做法可以避免涉案材料的分散性,增強涉案材料管理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2.建立社會調查的程序保密制度。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第268條:“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據情況可以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情況進行調查。”然而,從各地試點未成年人社會調查的情況來看,盡管總體效果良好,但一些地方因缺乏必要的程序規范,也出現了泄漏未成年人信息的情況。為此,建議檢察機關建立社會調查的保密制度。具體可以考慮作如下制度設計:規定檢察機關辦案人員進行社會調查時,不穿制服、不開警車,以對涉案未成年人造成最低影響為原則。調查前,應告知被調查人須承擔保密義務,并簽署保密承諾書。在調查過程中,如無必要,不應向被調查人透露相關案情及案件處理的情況。對違反保密義務的單位和個人,應予以監督糾正,及時消除影響(下文將對此進行論述,此不贅述)。
3.法律文書對可能判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人不使用實名。實踐中,為回應社會輿論的關切,司法機關在許多情況下不得不向外界透露案件辦理情況。雖然為保護未成年人,都會對涉案未成年人的姓名和身份信息作保密化處理,但因各地不同,這種保密化處理也不盡相同,以如李天一案件為例,有的稱“李某”,有的稱“李某一”。這種處理方式在很多情況下依然可以為外界提供不少身份推導的線索。在很多情況下,未成年人案件并非單獨犯罪,而是既有成年人又有未成年人的共同犯罪。雖然對未成年人實行了分案起訴制度,但在對同案成年人的審判過程中是公開進行,在庭審證據出示及質證的過程中,依然可能泄露未成年人的有關信息。從更好地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角度考慮,建議整個訴訟過程中的法律文書,對可能判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人一律不使用實名。事實上,這樣做并非沒有依據。根據《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對于身份未能查清的被告人,檢察機關可以依照其自報的姓名起訴。這意味著“實名起訴”并不是公訴的必然要求。從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實際需要來看,建議借鑒身份證號碼編號的方式,對未成年人實行編號并使用于訴訟過程中的各種法律文書,與編號相對應的真實身份信息及社會調查材料單獨裝卷,加密保管。在回應外界對案件的關切時,對可能判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人一律使用編號。
(二)應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對明確有權查詢未成年犯罪記錄的主體作出明確規定
首先,對“有關單位”單位的界定,應當盡量嚴格,要求其查詢行為必須有相應的法律依據,換句話說,“有關單位”查詢犯罪記錄,應當是其負有查明被查詢對象是否有犯罪記錄的義務。如《教師法》中規定:“受過剝奪政治權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處罰的,不得取得教師資格;已經取得教師資格的,喪失教師資格”,教育部門基于這一規定,對擬招錄或招聘為教師的人員的犯罪記錄進行查詢,應當允許。再如《法官法》、《檢察官法》、《警察法》也規定受過刑事處罰的人不能當法官、檢察官、警察,這些部門對擬招錄的人員進行政審而查詢犯罪記錄應當允許。其次,雖然有查詢特定犯罪記錄的法定義務,但未成年人所犯罪名與該類犯罪無關的,應當不予查詢。除此以外的其他單位對犯罪記錄進行查詢,應嚴格控制。如根據《會計法》第40條之規定,如被查詢人在校期間曾犯故意傷害罪,這一罪名顯然與《會計法》所規定的罪名無關,檢察機關不應提供查詢。
(三)完善未成年人犯罪封存的配套制度
一是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的部門聯動配合制度。建議最高人民檢察院與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司法部、教育部、民政部等相關單位制定規范性文件,明確各部門在未成年人保護中的權利和義務,建立共同聯動配合機制。防止因缺乏相應的銜接配套制度,各部門對該項制度的實施可能存在相互推諉,各部門都管,實際沒人管現象的出現。其次,是明確涉案未成年人信息泄露的責任。2012年《刑事訴訟法》及《犯罪記錄制度意見》均未明確:有關人員或機構違法泄露未成年被追訴者的犯罪信息時應當承擔何種責任,這恰恰是實際生活中未成年犯罪信息不脛而走的根源所在。為增強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實效性,我們應當明確違法泄露被封存的犯罪信息的行為性質及應承擔的責任。從世界各國來看,許多國家都沒有制定專門的法律來明確保護犯罪記錄資料。如,美國《隱私權法》規定:“行政機關必須建立行政的、技術的和物質的安全保障措施,以保障個人記錄的安全、完整和不被泄露,并防止其它可能對被記錄者產生損害的危險”、“個人記錄涉及教育、經濟活動、醫療歷史、工作履歷以及其他一切關于個人情況的記載”、“普遍免除只適用于中央情報局和以執行刑法為主要職能的機關所保有個人記錄,但仍應履行被記錄人同意、保證記錄正確性、違反法律承擔刑事責任等義務。”[2]在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對違反該法的責任作了框架性的規定,如該法第60條的規定,從性質上而言,未成年人犯罪記錄信息應當屬于隱私權的范疇。只要惡意泄露被封存的犯罪信息,造成嚴重后果,就已經侵犯了他們的人身權利也損害了國家對個人信息的管理秩序。致害人的行為已經符合《刑法》第253條之一的規定,構成出售、非法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罪。為避免實踐操作的混亂,建議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最高人民法院對此作出相應司法解釋。
(四)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檢察監督程序
對于檢察機關而言,除了要重視法律的正確適用以及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本身的構建外,還應當關注和研究如何立足檢察職能,加強和完善對這項制度執行的監督問題。筆者認為,從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檢察監督的內容來看,主要可以從適用法律和執行制度兩個環節予以設定。在法律適用環節,對于法院因判處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而決定封存未成年人犯罪記錄的,應當針對法院作出的刑事判決,重點審查被告人的主體身份是否屬于未成年人、判處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是否符合刑法規定的量刑標準,以監督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的適用是否具備法定的實體要件。在制度執行環節的規范性監督方面,司法機關作出案件處理結果并決定封存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后,檢察機關應監督包括決定機關在內的諸多職能部門和單位,如公安機關、司法行政機關、教育部門(學校)、用人單位、街道及社區基層組織等,是否承擔起依法執行封存決定的義務,包括是否依照司法機關的決定,及時封存了相關案卷、檔案等材料,是否制定了專人保管、分類管理的工作制度,是否落實了相應的保密措施等;二是對特殊情況下查詢和公開刑事記錄的規范性進行監督,包括查詢的主體和事項是否符合法律規定且具有必要性,相關職能部門和單位是否嚴格履行了制度規定和審查程序,其批準公開的犯罪記錄內容和范圍是否符合限制性要求,是否告知查詢單位不得擅自公開查詢內容的保密義務等。
在檢察機關如何履行檢察監督權方面,筆者認為可以有以下幾種方式:1.檢察建議。在對執行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情況進行監督的過程中,尤其要重視發現制度執行不規范、不到位的“一類問題”,有針對性地制發檢察建議,督促、幫助執行單位制定整改措施、健全工作制度。對于存在的如泄露未成年人信息等違法行為,還可以建議相關單位根據《未成年人保護法》的相關規定,給予行政處分。2.糾正違法通知。如發現相關單位存在不應當公開而予以公開,或者應當公開而不予公開的情形,可及時書面通知執行部門糾正。3.監督立案。如行為人的行為已經符合《刑法》第253條之一的規定,構成出售、非法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罪的,應監督公安機關立案偵查。4.刑事偵查。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執行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過程中,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對應當封存的犯罪記錄不予封存,并且因違法公開未成年人犯罪記錄而造成嚴重后果,構成犯罪的,檢察機關應當依法立案偵查,追究其刑事責任。
總而言之,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是我國未成年人保護制度的進步和飛躍,筆者因為缺乏實踐驗證提出的相關思路,可能存在不周全甚至理論硬傷,在此僅作拋磚引玉,希望引起同行共鳴,在未來落實這一制度進一步就相關問題探討出更好的解決思路。
注釋:
[1]《莫讓未成年人保護制度成為空文》http://www.rmlt.com.cn/News/201302/201302251004277849.html,李蒙:《網絡暴民,請你們不要繼續傷害一個未成年人》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9004415。
[2]參見高一飛、高建:《犯罪記錄封存的制度安排與實施機制》,載《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