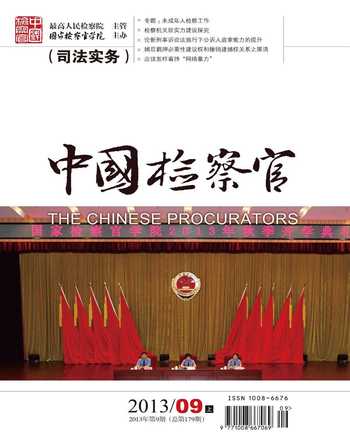技術偵查使用原則之域外探析
鄭雷
技術偵查作為一種應對犯罪形勢新變化而為偵查機關在重大犯罪中廣為采用的偵查措施,已為美、英、德、意、日等西方先現代化國家在立法中所確立并規定了嚴格的實施程序。我國在繼1993年制定的《國家安全法》和1995年制定的《人民警察法》規定技術偵察措施后,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中進一步明確和細化了技術偵查措施的使用。作為一項刑事訴訟法新設立的極易侵犯公民基本權利的偵查措施,必須予以規范、制約和監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先現代化國家在技術偵查措施使用中所遵循的一系列正當程序原則對該措施在我國的使用不無裨益。英美法系國家從近代以來,大力倡導“正當程序”觀念,認為政府在處理有關人民生命、自由和財產等問題時,必須遵守正當、合理的法律程序。大陸法系國家在傳統上雖無“正當程序”理念,在偵查模式上也采用強化偵查機關職權,有利于打擊犯罪的職權主義偵查模式而與英美法系的對抗式偵查模式有別,但在技術偵查的程序設計上卻與英美法系各國有異曲同工之妙。其根本指導思想均是:技術偵查以忽視人的尊嚴、侵犯公民隱私權為代價,其采用應受到嚴格的程序控制。總體來看,兩大法系為偵查機關實施技術偵查措施設計了以下共同的程序原則。
一、適用案件范圍特定原則
由于技術偵查的實施與人權保護密切相關,因而對于一般性的危害不大的刑事案件,不宜采用技術偵查。在西方學者看來,采用技術偵查這種對公民隱私權損害較大的手段去偵查危害不大的犯罪案件,是得不償失的[1]。因此,西方各國大多規定技術偵查只能針對重大復雜的刑事案件實施。美國對于可實施監聽的案件范圍采取了兩種規定方法:一是對部分犯罪采“罪行輕重限定法”,這是指《美國法典》第42編規定的可處死刑、無期徒刑或一年以上監禁刑的犯罪;二是對于其他犯罪采“罪名列舉法”,計有14項60多種犯罪,如謀殺、綁架等[2]。我國臺灣地區的《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規定預備內亂罪、預備暴動內亂罪等犯罪及最輕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可以實施監聽。但基于一些犯罪手段的特殊性,犯罪本身并非重大犯罪,立法機關也將其納入可以技術偵查的對象。由此可見,技術偵查主要適用于兩類犯罪:一是重罪,即處罰較重的犯罪;二是技術化、隱秘化的特殊類型的犯罪。前者反映出被害權益的重大性,針對這類犯罪采用技術偵查足以抵消因忽視人的尊嚴、侵害公民隱私權而帶來的負面影響;后者由于其犯罪行為的特點,給偵查機關的偵查帶來重重困難,不采取技術偵查,實難以發現犯罪、偵破案件。
二、最后手段原則
確立最后手段原則的法理在于:國家權力的行使,以僅達目的為己足,不可過度侵害公民的自由權利,當國家偵查機關為達同一目的有多種適合手段可供選擇時,應選擇對當事人損害最少的手段。也就是說應貫徹任意偵查原則,此原則要求凡是偵查活動應當盡可能采取任意偵查的方式,強制偵查只有在法律規定的例外情形下才能使用。技術偵查作為一種強制偵查措施[3]與諸如詢問證人、被害人之類的任意偵查措施相比,對公民自由侵害較大,就是較搜查、扣押等其他強制偵查措施而言,由于技術偵查是非公開進行的,難以受到來自訴訟參與人及社會公眾有效的監督和制約,且直接觸及公民個人的尊嚴和隱私,其對受處分人重要權益的侵害程度較深。因此只有在采用一般偵查手段無法達到偵查目的的情況下,偵查機關迫不得已才能采用技術偵查。美國1968年《綜合犯罪控制與街道安全法》規定,法官必須以合理的原因相信一般的偵查手段已經嘗試過并失敗了,或者即使采用也不太可能成功或太危險的情況下才可批準采用監聽手段。《法國刑事訴訟法典》第一百條規定“為了偵查的必需,可以決定截留、登記和抄錄郵電通訊。”按照法國權威學者的解釋,偵查的必需是指當傳統的偵查技術不太有效時,即可以采取這種偵查手段(例如,毒品走私犯罪活動、秘密賭博犯罪活動)[4]。
三、最低限度原則
一旦確定技術偵查有其必要性,須進一步考慮比例性,而最低限度原則實際上則是這兩項在技術偵查中的具體運用。技術偵查關乎維護公共秩序與忽視人的尊嚴及侵犯人之隱私權,然可否為了維護公共秩序,而不加限制的對所有的人、內容實施技術偵查,并且在實施期限的長短上也不加以限制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技術偵查所欲達成之偵破犯罪與維護公共秩序的目的,應估量到個別可能因此而被侵犯的法益,簡言之,即利益權衡。具體而言,最低限度原則又包括人的最低限度原則、內容的最低限度原則與期限的最低限度原則。
(一)人的最低限度原則
各國在立法確定技術偵查對象時普遍貫徹了最低限度原則。具體說來,技術偵查對象除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外,還包括傳達人和提供人,前者指為犯罪嫌疑人發送、傳達、收受信息等人,后者則指為犯罪嫌疑人提供通訊器材、處所等人。可見,為了有效的發現案件事實,技術偵查不可避免的會波及第三人,但只要技術偵查的實施遵循嚴格的程序要件和追訴重大犯罪的需要,基于利益權衡,對于第三人的技術偵查也是不得已的手段[5]。對犯罪嫌疑人之技術偵查除要遵從上文所述對象特定原則和最后手段原則外,在簽發監聽令狀時還應基于合理根據,這將在下文的司法審查原則中加以論述。
對傳達人實施技術偵查,無涉傳達人是否明知或有意促進或支持犯罪嫌疑人犯罪目的之達成,而系盡可能的防止犯罪嫌疑人利用他人以規避偵查機關的偵查[6]。如若不對特定傳達人實施技術偵查,通常技術偵查不能取得成效。對犯罪嫌疑人和傳達人之技術偵查,二者在法益之侵犯的危險程度上自然不相當,因而對傳達人的技術偵查應限于絕對必要,也就是說除對犯罪嫌疑人技術偵查無結果,或有事實足以認定對傳達人技術偵查可獲得豐富之成果外,原則上不應任意準許。另外,對傳達人之技術偵查還涉及的一個問題是,在諸如綁架類案件中可否將被害人親友視為收發信息之人,而對之實施技術偵查(此處僅限于排除被害人親友同意技術偵查之情形)。筆者認為在此情形下犯罪嫌疑人并非是利用被害人親友以規避偵查機關之偵查,與立法規定可對為犯罪嫌疑人發送、傳達、收受信息之人實施技術偵查之目的有別,且基于公民基本權利干預措施限制解釋原則和刑事司法實務經驗,不應將被害人親友任意擴大解釋為傳達人,但基于偵查實務的需要,綜合考慮案件性質、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大小等因素,也可將被害人視為與犯罪活動直接關聯的人員加以技術偵查。提供人亦如上述傳達人,無涉其是否明知或有意提供犯罪嫌疑人通訊器材、處所等,只要有事實足以認定犯罪嫌疑人有使用之可能即可對其實施技術偵查,但對提供人實施技術偵查較具爭議性之問題為對公用電話監聽應否準許之問題。盡管對犯罪嫌疑人、傳達人、提供人實施技術偵查均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大量無關技術偵查目的之對話被監聽的問題,但對公用電話實施監聽無疑會侵犯更多無辜第三人之法益,因此獲取監聽令狀的條件應更為嚴格限制。德國學者Aubert、Duennebier、Schmidt等對公用電話之監聽均持肯定的立場,但認為除于刑事偵查實務經驗中發現之組織犯罪、毒品犯罪、擄人勒索案件等少數例外情形,監聽之時間應盡可能縮短為一天或兩天以下,盡可能限制為監聽一個公用電話外,原則上不得準許之[7]。
(二)內容的最低限度原則
由于人社會生活的復雜多樣性,即便是犯罪嫌疑人,其除了涉嫌的犯罪活動外,仍有一些僅限自身的而不愿為外界所知的私生活領域,因而,如若不加區分的對所有通訊、行蹤、場所等予以技術偵查,其勢必侵犯被偵查者的權益,所以在各國的技術偵查立法中大多對技術偵查的內容加以限制,盡最大可能的在偵破犯罪與公民權利的保護之間尋求平衡。日本《關于犯罪偵查中監聽通訊的法律》第6條規定:“監聽令狀應當記載應予監聽的通訊”,此外第13條還規定:“對于在實施監聽中已進行的通訊是否屬于監聽令狀記載的應予監聽的通訊不明確的,為判斷該通訊是否屬于應予監聽的通訊,以必要的最小限度范圍為限,可以監聽該通訊。使用外國語進行的通訊或者使用暗號及其他不能即時復原其內容的方法進行的通訊,由于在監聽時難以知悉其內容,而不能判斷是否屬于應予監聽的通訊的,可以監聽該通訊的全部。在此場合,應當迅速判斷其是否屬于應予監聽的通訊。”這些立法總的一個指導思想就是監聽的內容應盡量限制在與偵查目的有關的內容上。
(三)期限的最低限度原則
因為技術偵查極大的影響個人權益,若不對其實施的期限采取限制,則等于是將決定權交給了偵查機關,因為偵查機關只要獲得了審批,即可自行決定隨時采用,而當事人的權益則長時間、不定期的籠罩在國家權力的陰影之下,處于極不穩定的狀態之中,因此非常有必要對技術偵查的期限加以限制且限制在最低限度,以盡可能的結束當事人權益的不穩定狀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1967年伯格訴紐約州(Berger v. New York)一案裁定紐約州關于監聽的法律違憲,其理由是該法授權長達兩個月的監聽無異于讓偵查人員僅憑一個莫須有的理由就可以反反復復地侵入私人場所,其次該法還以所謂的“保護公共利益”為由,允許在兩個月的基礎上再延展監聽期,這顯然是將偵查人員首次獲取監聽令的理由又作為申請展期的理由,再次,一旦偵查人員所需的談話被監聽到了,該法就不再限定監聽的期限,這實際上是將監聽期限的決定權完全賦予了偵查人員,總之,該法寬泛的授權規定缺乏足夠的司法監督和程序保障[8]。為了加強對監聽期限的控制,美國在次年通過的《綜合犯罪控制與街道安全法》中規定,監聽令狀所授權的監聽期限不得超過完成所授權的監聽所必要的限度,最長不得超過30天,自偵查機關開始監聽之日或監聽令下達10日之后起算(以先成就的一個為準)。監聽期限可以延長,但必須按照法定的申請、批準程序和條件重新辦理手續。延長的期限不得超過第一次授權的監聽期限,最長不得超過30天,但法律對于申請和批準延期的次數沒有限制,且規定達到授權監聽目的后必須立即停止或最多不超過30天。
四、保密原則
由于技術偵查不可避免的要侵入當事人的私生活領域,因此對在實施過程中所獲取的有關信息要保守秘密,并將這些信息的使用限制在最小范圍之內,保證信息的安全,從而盡可能地保護被偵查者的隱私權。當然這里的保密主要是針對社會成員而言,因為為了加強當事人對程序的知情權、監督權、控制權,技術偵查所獲信息應適時向相關人員披露。美國1968年《綜合犯罪控制與街道安全法》規定,即便監聽的通訊內容是有事實根據的也不能隨便泄漏,除非是根據法院專門的授權,但那也僅是在某種程度上泄漏監聽的內容,同時,對有關記錄材料還應進行封存。日本《關于犯罪偵查中監聽通訊的法律》規定,在中斷或終結監聽時,應當對媒介物記錄進行封存;對與偵查目的無關的記錄予以刪除;檢察官或者司法警察員,對于已經監聽的通訊,除監聽記錄記載的以外,不得使他人知悉其內容或者予以使用,即使在退職以后,亦同。
五、司法審查原則
盡管各國的政治體制、歷史、文化傳統乃至法律制度不同,但基于公民的基本人權不可侵犯、國家權力的有限性和國家權力的分權與制衡的理念及體現刑事訴訟追求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的訴訟目的、現代法治國家建立訴訟職能的區分與制衡機制和符合刑事訴訟規律、符合人權保障的法理基礎,各國普遍針對強制性偵查措施建立了司法審查機制。通過對偵查機關所實施的強制性處分進行司法審查來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早已被英美普通法律所確立,并被德、意、日等國的法律所吸收,這也是人類社會文明、民主與進步的必然要求 。技術偵查作為一種強制性偵查措施已為各國所確立,因此對偵查機關實施技術偵查進行司法審查已基本成為現代法治國家的通例。
對技術偵查進行司法審查的機制,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通過實行令狀主義進行事前審查;二是對緊急情況下偵查機關實施的未取得司法令狀的技術偵查進行事后審查,以確認這種措施是否具有合法性;三是運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對偵查機關非法收集的證據材料加以排除,從而達到對技術偵查措施進行審查的目的。本文在此僅討論前兩種審查途徑。美國《綜合犯罪控制與街道安全法》要求偵查機關需要采取監聽時,除經通訊一方當事人事先同意的以外,原則上必須事先申請有管轄權的法官授權(有證監聽),在緊急情況下,也可以先進行監聽,然后申請有管轄權的法官認可(無證監聽)。為了明確偵查機關取得監聽令狀的標準,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1967年伯格訴紐約州(Berger v. New York)一案裁定,偵查人員取得一張司法令狀不僅要以由宣誓或保證所確信的充足理由為前提,而且必須在申請書中詳細描述相關情況的材料以及可靠的證據,法官綜合各種情況考慮是否有合理根據[9]。但為了適應偵查犯罪的緊急情況,該法又賦予了司法部長等人在合理地認定符合以下兩個條件時,可以不經法官批準而監聽通訊:其一,存在下列緊急情形之一的:(1)有導致任何人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的迫在眉睫的危險的;(2)有威脅國家安全利益的密謀活動的;(3)有組織犯罪的密謀活動,并且在經適當努力獲得法官授權之前必須對有線的、口頭的或電子的通訊進行監聽的。其二,有多種理由認為根據本法規定將會獲得授權監聽的令狀的。但是,無證監聽時,必須在監聽開始后48小時之內向法官提交認可申請。如果沒有獲得法官認可后簽發的令狀,監聽活動應當在獲得準備竊取的通訊時或者申請被駁回時(以先成就的一個為準)立即停止。針對“有威脅國家安全利益的密謀活動”這一例外情況,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1972年“美國訴美國地方法院”(U.S.v.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一案中裁定,涉及的犯罪并沒有外國勢力的介入,完全是國內性的,涉嫌的人也都是美國公民,因此緊急情況不存在[10]。
盡管對技術偵查實行司法審查已基本上成為世界各國的通例,但仍有些國家基于維護自己國內秩序的需要未將其納入司法審查的范圍。英國1985年《通訊攔截法》沒有規定任何形式的司法監督,監聽所需的只是一名中央政府的部長——內政大臣批準的令狀,雖然該法已經廢除,但1997年通過的《警察法》和2000年的《偵查權限制法》仍沿襲了監聽不需司法審查的規定,這兩部法律仍將實施監聽的權力賦予警察自身而不是任一獨立的司法機構。《警察法》第93條開列了一張可以授權監聽的高級警官的詳細清單,例如警察局長、警署委員和國家犯罪情報處主任。《偵查權限制法》第30、32條也將權力賦予了高級警官或(在緊急情況下)他們的副手。
但在將技術偵查納入司法審查的國家,除了緊急情況的例外外,一般還存在兩種例外:一是第三人同意的例外;二是基于政治的考慮,維護國家安全的例外。如美國1968年《綜合犯罪控制與街道安全法》立法本意就不限制總統的憲法性權力去采取他認為必要的措施去獲得認為對維護美國國家安全必不可少的外國情報。1978年的《外國情報監視法》規定,如果總檢察長以書面誓詞的方式保證,該監聽完全是為了獲取通訊方都是外國勢力的通訊的內容以及不存在將會獲取通訊一方是美國公民的通訊的內容的實質性可能,總統即使沒有法庭的令狀也可以授權進行最長期限長達一年的電子監聽以獲取外國情報。在9·11事件后美國基于維護國家安全的需要,在《愛國者法》[11]中進一步規定,聯邦執法部門在未經司法審查的情況下有權獲得與美國公民有關的敏感信息,以及通過秘密偵探竊聽得到的信息。
注釋:
[1]樊崇義主編:《刑事訴訟法實施問題與對策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72頁。
[2]詳細的清單,參見《美國法典》第3編第2516條第1款第1至14項。
[3]任意偵查與強制偵查的區分標準,筆者采日本學者田口守一的重要權益標準。參見田口守一:《刑事訴訟法》,劉迪等譯,法律出版社2000版,第30-31頁。
[4]卡斯東·斯特法尼等:《法國刑事訴訟法精義》(下),羅結珍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582頁。
[5]吳微、郭志媛:《日本<犯罪偵查通信監聽法>評介》,載樊崇義主編的《訴訟法學研究》第二卷,中國檢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423頁。
[6]假若傳達人以幫助犯罪之犯意而發送、傳達、收受通訊,則其為某種犯罪之共犯,自應對其實施監聽。
[7]江舜明:《監聽界限與證據排除》,《法學從刊》第171期,第98頁
[8]李學軍主編:《美國刑事訴訟規則》,中國檢察出版社2003年版,第262頁。
[9]同上,第263頁。
[10]李義冠:《美國刑事審判制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頁。
[11]“愛國者法”正式的名稱為“Uniting and Strengthening America by Providing Appropriate Tools Required to Intercept and Obstruct Terrorism Act of 2001”,取英文原名的首字縮寫簡稱為“USA PATRIOT Act”,而“patriot”也是英語中“愛國者”之意,因而簡稱為“愛國者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