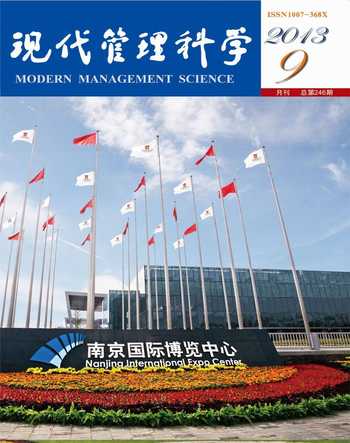團隊承諾對知識分享的影響機制研究
林巍 嚴廣樂
摘要:整合團隊承諾與知識分享相關理論,探索情感承諾對任務承諾的影響,情感承諾和任務承諾對知識分享的影響。文章利用長三角地區79個研發團隊的實證數據表明:情感承諾與任務承諾顯著正相關,情感承諾與顯性知識分享和隱性知識分享顯著正相關,任務承諾與顯性知識分享和隱性知識分享顯著正相關。研究結果為組織利用任務承諾與情感承諾提高團隊知識分享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關鍵詞:情感承諾;任務承諾;顯性知識分享;隱性知識分享
一、 引言
在全球化競爭日益激烈的環境下,伴隨著產品和服務的快速流動,知識被認為是企業最重要的戰略資源。這是因為知識能夠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同時為企業創新提供必要的支持。組織管理者必須激勵組織成員主動地把個人智能和工作經驗轉化成組織財富,組織知識才能不斷創新,組織的競爭優勢才能保持。充分的知識分享能夠幫助團隊成員更為便利和快速地獲得知識,團隊成員還可以借助知識分享再造和使用知識以提高知識管理的績效。一旦團隊寄予團隊成員之間的知識分享足夠的激勵,大量的知識必然會應運而生。但要鼓勵團隊成員進行知識分享, 組織必須更多地依賴于個人、社會心理因素這些內在激勵因素, 而不單單是傳統的經濟激勵和社會激勵。Hislop(2003)研究認為組織承諾是影響知識分享非常重要的內在因素之一。但在企業的實際研發活動中,研發工作都是以團隊的形式展開的,因此團隊承諾更能影響員工在團隊內的知識共享行為。為豐富這一領域的研究發現,本研究提出團隊承諾的兩個維度,情感承諾和任務承諾對知識分享影響的研究假設。隨后,本研究通過長三角地區研發團隊的實證數據來驗證這些研究假設。
二、 理論基礎
1. 知識分享。傳統上,根據知識的隱性程度,知識被劃分為隱性知識(Tacit Knowledge)和顯性知識(Explicit Knowledge)兩種。顯性知識是指那些通常意義上的、可以用公式、命題、符號、模型、圖紙等明確表述的知識。而隱性知識是指那些具有高度個性化,難以正式化和編碼化,只可意會不可言傳,而且深植于個人的經驗、判斷、聯想、創意和潛意識的知識。隱性知識相對顯性知識而言,在企業的戰略決策中扮演著更為重要的作用。因為隱性知識作為高度個性化的知識只有轉化為組織知識,并能夠被組織中的其他成員所利用,才能有效提高整個組織的績效,從而提升組織的競爭力。所以促進知識共享是知識管理的關鍵部分。
2. 情感承諾和任務承諾。Mowday等(1979)將組織承諾定義為個體對組織目標和價值觀的強烈信任感與認同感,愿意為組織的利益付出大量努力,對維持組織中的成員關系有強烈期望。這一定義體現了一個相對寬泛的主題,即組織承諾體現的是員工對組織的情感承諾,體現了對離開組織會造成一定損失的認同以及對組織應該擔負的道德責任。在這之后,加拿大學者Allen和Meyers將組織承諾將組定義為體現員工和組織之間關系的一種心理狀態, 暗示了員工對于是否繼續留在該組織的決定。并且分為三個維度,包括情感承諾、持續承諾和規范性承諾。其中情感承諾是指員工對組織的感情依賴、認同和投入,員工對組織所表現出來的忠誠和努力工作,主要是由于對組織有深厚的感情,而非物質利益。Mowday等(1982)通過實證研究認為,組織承諾應該是是單維的,主要表現為員工對組織的感情依賴,即情感承諾。
然而Setphen(2000)研究認為,在當前競爭激烈的環境中,經典的組織承諾理論越發顯得不夠完整,因為上述理論關注的僅僅是員工正面的心理狀態,而忽略了目標任務的一致性,業績導向和創新行為。所以有學者認為,與目標任務相關的承諾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為在殘酷的市場競爭中,絕大部分企業首要關注的必須是組織的目標任務能否按時完成,只有在這個前提下,企業才會去關注員工的心理狀態。Locke和Latham(1990)從目標設置理論的角度出發提出了目標承諾的概念,是指個體自覺地阻止目標的改變,下定決心努力達成既定目標的程度。Gallie和White(1993)認為組織承諾是員工對于組織價值觀的接受程度和愿意留在組織中的意愿,任務承諾是員工工作投入的努力程度。Porter(1996)則強調任務承諾是員工高標準完成工作任務的決心。結合上述觀點,本研究提出任務承諾是指為了高標準地完成任務,克服各種障礙,努力達成目標的決心。任務承諾意味著個體以高標準向既定的工作目標努力的程度,即使面臨挫折也不愿意降低或放棄目標,而這正是團隊領導所期待的。本研究將團隊承諾分為兩個維度,即情感承諾和任務承諾。
三、 研究假設
1. 情感承諾對任務承諾的影響。任務承諾對工作任務能否高標準地完成有積極的作用,而情感承諾可以促進任務承諾,從而進一步提高績效水平。情感承諾不僅可以提高成員的忠誠度和歸屬感,而且還是維系與工作任務相關的組織成員任務承諾不可或缺的因素,因為情感承諾程度高的組織往往表現為注重組織的凝聚力和穩定性。在情感承諾高的團隊中,團隊成員更愿意發表自己的真實想法,敢于公開交流,從而在團隊中創造出良好的人際關系和友好的氛圍,任務承諾也隨之得到提高。也就是說,情感承諾高的團隊鼓勵團隊成員關注團隊目標,這意味情感承諾可使成員以工作任務為中心,專注于與工作任務相關的活動。Wasti 和Can(2008)的研究表明,情感承諾與任務的主動履行相關,團隊的情感承諾越強,團隊成員就越愿意為圓滿完成任務而發揮主觀能動性。因此,情感承諾能夠促使團隊成員公開交流、營造和諧氛圍,從而增強了組織的任務承諾。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設:
H1: 情感承諾與任務承諾正相關。
2. 任務承諾對知識分享的影響。對于知識型員工,任務承諾的建立和發展不但能夠提高他們的工作績效,影響工作情緒,還會對團隊成員的知識共享產生很大的影響。因為知識共享可以被視為一種利他行為,分享的基礎建立在團隊成員愿意為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努力并把組織知識當作共同利益,信任被認為強化了這種意愿。Porter(1996)研究認為,信任是任務承諾的結果,團隊成員高標準地完成任務會帶給他們內在的滿足,這種對任務的執著驅使他們在完成任務的過程中,團結一心,彼此信任,主動尋找新的解決方案。也就是說,當團隊的任務承諾高的時候,團隊成員會全力調動自身的認知和行為資源去完成共同的任務,他們之間的相互信任感也會顯著增強,團隊成員進行知識分享的主動性就會顯著提高。而團隊的任務承諾低的時候,團隊成員對于組織目標缺乏認同,很自然地會喪失對組織可靠性的信心,就會去做一些和目標任務不相關的事情。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設:
H2:任務承諾與顯性知識分享正相關;
H3:任務承諾與隱性知識分享正相關。
3. 情感承諾對顯性知識分享和隱性知識分享的影響。知識分享是一種角色外行為,很明顯團隊認同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團隊的情感承諾越高,團隊成員對團隊的認同感就越強烈,就更愿意為其他成員提供支持和幫助,就越有可能分享自己的知識。在多元化的團隊中,組織認同是一種正面的力量,具有高認同感的團隊會表現出更多的學習行為和更好的組織績效。也就是說,情感承諾為知識分享創造了有利的條件。Meyer和Allen(1997)認為情感承諾和個人為工作額外付出努力的意愿正相關,情感承諾和知識分享的意愿相關。Hooff和Ridder(2004)研究也表明,情感承諾對團隊成員的知識貢獻與知識收集均產生積極影響。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設:
H4:情感承諾與顯性知識分享正相關;
H5:情感承諾與隱性知識分享正相關。
四、 研究方法
1. 研究對象。本研究在正式調研開始之前完成了預調研,之后選擇了來自上海、浙江、江蘇的81家企業的126個研發團隊進行了調查,研究中所選取的研發團隊成立的時間都在3年以上。本研究采用的是網上填寫問卷的形式,從每個研發團隊隨機抽出3~7名成員在網上填寫問卷,一共發放了問卷鏈接524條,回收問卷382份,回收率為72.90%,其中有37份問卷的數據出現填寫不完整或數據出現雷同而被剔除,最終收回了問卷345份,有效回收率為90.31%,分別來自92個研發團隊。團隊所屬企業在上海的占31%,在浙江省的占43%,在江蘇省的占26%。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局行業分類標準(GB/T4754-2002),92個研發團隊共涉及70家企業5個行業,其中:化工21個(22.83%),制藥10個(10.87%),機械制造23個(25.00%),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26個(28.26%),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12個(13.04%)。企業性質為國有企業21家(30.00%),民營企業30家(42.86%),合資企業10家(14.28%),外商獨資企業9家(12.86%)。在92個研發團隊中人數最少為3人次,最大人數為15人次,平均6.88人次,標準偏差為3.51。調查中男性為225人(65.22%),女性120人(34.78%)。學歷高中及以下25人(7.25%),大專121人(35.07%),本科178人(51.59%),研究生21人(6.09%)。研發團隊內工作1年~2年的成員占15.8%,3年~5年的占54.6%,6年及以上的占29.6%。
2. 研究測量工具。本研究問卷中包含了任務承諾、情感承諾、顯性知識分享和隱性知識分享四個變量的測量,共設19個題項。問卷中均采用5點Likert 量表,1代表“完全不同意”,5代表“完全同意”。其中任務承諾測量問卷主要改編自Hollenbeck等(1998)和Porter(1996)開發的問卷,由6個題項構成;情感承諾測量問卷主要來源于Meyer等(1993)開發的問卷,由6個題項構成;顯性知識分享測量問卷改編自Lee(2001)開發的問卷,由4個題項構成;隱性知識分享測量問卷改編自Lee(2001)和Holste與Fields(2010)開發的問卷,由3個題項構成。為了提高本研究的準確性,控制變量由團隊規模、企業性質和所處行業組成。
任務承諾和情感承諾的信度系數分別為0.79和0.78,顯性知識分享和隱性知識分享的信度系數為0.74和0.79,均超過0.70,表明量表具有較高的信度,內部一致性良好。本研究采用驗證性因子分析的方法來考察測量的結構效度,分別比較虛模型、單因素模型、兩因素模型、三因素模型和四因素模型的擬合度。假設的四因素模型比其他嵌套模型顯示出更優良的擬合度,表明四個變量之間具有較高的判別效度,設置合理。對于個體變量能否聚合到團隊層面,13個團隊的Rwg(J)系數小于0.60,故將這13個團隊的數據刪除后再進行檢驗,跨級相關系數ICC(1)和ICC(2)的值都分別大于James的經驗標準0.05和0.50,且ICC(1)的F統計量均大于1,且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說明這些變量的組間變動均顯著高于組內變動。所以本研究中的4個變量79個團隊的個體數據可以聚合到團隊層面。
五、 研究結果
各變量團隊層次的Pearson相關系數(缺失值Pairwise)分析顯示,變量間的相關系數最大值為0.37,遠小于多重共線性問題的閾值(r=0.75),表明模型的多重共線性問題并不嚴重。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結果表明,情感承諾對任務承諾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作用,非標準化回歸系數為0.21(p<0.05),同時模型具有較高的顯著性水平(F=1.94,P<0.05),所有預測變量至少能夠解釋任務承諾13%的變化,假設H1得到支持。任務承諾對顯性知識分享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作用,非標準化回歸系數為0.18(p<0.01),模型具有較高的顯著性水平(F=1.87,p<0.05),所有預測變量至少能夠解釋顯性知識分享11%的變化。而情感承諾對顯性知識分享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作用,非標準化回歸系數為0.15(p<0.05),模型具有較高的顯著性水平(F=2.06,p<0.01),所有預測變量至少能夠解釋顯性知識分享12%的變化。故H2和H4得到支持。任務承諾對隱性知識分享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作用,非標準化回歸系數為0.20(p<0.05),同時模型具有較高的顯著性水平(F=2.51,p<0.05),所有預測變量至少能夠解釋隱性知識分享11%的變化。情感承諾對隱性知識分享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作用,非標準化回歸系數為0.25(p<0.01),同時模型具有較高的顯著性水平(F=2.10,p<0.01),所有預測變量至少能夠解釋隱性知識分享12%的變化。故H3和H5得到支持。
六、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探討了團隊承諾對知識分享的影響機制。首先,本研究在理論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系列假設,然后通過多元線性回歸分析法對提出的假設進行了驗證,本研究具有以下結論與管理啟示:
1. 情感承諾對任務承諾有著顯著的正向預測效應, H1得到支持。團隊情感承諾有效提升了團隊成員對團隊的忠誠度和認同感,加強了團隊的凝聚力和戰斗力,高情感承諾為與工作任務相關的活動提供了更多的激勵和支持,促使全體成員發自內心地關注組織績效,強化了團隊成員高標準完成團隊任務的決心。因此,提高研發團隊的情感承諾具有非常重要的實踐意義。
2. 任務承諾對團隊的顯性知識分享與隱性知識分享都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效應,H2 & H4得到支持。在任務承諾高的團隊中,團隊成員關心任務績效的好壞,在強有力的工作目標的指引下,他們會施展渾身解數,高標準地去完成任務。在這種情境下,研發團隊內部的知識分享的頻率會加快,知識分享的程度會加深。從管理實踐的角度出發,研發團隊必須努力實現組織的任務目標和團隊成員個人目標的和諧統一,團隊成員只有對團隊任務目標有強烈的認同感,在團隊內部才愿意主動進行知識分享,組織的知識管理績效才會提高。
3. 情感承諾對團隊的顯性知識分享與隱性知識分享都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效應,H3 & H5得到支持。情感承諾影響了團隊成員對于團隊的忠誠度和滿意度,高情感承諾有利于提升團隊成員的歸屬感,強化對于團隊的認同,充滿認同感的團隊氛圍促使團隊成員主動進行知識分享。從管理實踐的角度出發,團隊領導者必須加強團隊成員情感承諾的培養,同時應避免打擊員工忠誠度的事情發生,通過增強員工對團隊的認同感,營造團結、信任、融洽的團隊氛圍,提高團隊內部知識分享的水平。
參考文獻:
1. Nahapiet J, Ghoshal S.Social capital,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8,23(2):242-266.
2. Yang J T.Knowledge sharing: Investiga- ting appropriate leadership roles and collab- orative culture.Tourism Management,2007,28(2):530-543.
3. Huber G.Transfer of Knowledge in Kno- wledge Management Systems: Unexplored Issues and Suggested Studies.European Journal of Info- rmation Systems,2001,10(2):72-79.
4. Hislop D.Linking human resource mana- gement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via commit- ment: a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Employee Relations,2003,25(2):182-202.
5. Hooff B V, Weenen F L.Committed to share: Commitment and CMC use as antecedents of knowledge sharing.Knowledge and Process Mana- gement,2004,11(1):13-24.
6. Polanyi M. The Tacit Dimension.Lond- 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6.
7. Alavi M, Leidner D E.Review: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s: conceptual foundations and research issues.MIS Quarterly,2001,25(1):107-136.
8. Mowday R T, Steers R M, Porter L W.The measurement of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1979,14(2):224- 247.
9. Allen N J, Meyer J P.The measurement and antecedents of affective, continuance and normative commitment to the organization.Jour- nal of Occupational Psychology,1990,63(1):1-18.
10. Mowday R T, Steers R M, Porter L W.Employee organization linkages: The Psychology of Commitment, Absenteeism and Turnover.New York: Academic Press,1982.
11. 張生太,梁娟.組織政治技能、組織信任對隱性知識共享的影響研究.科研管理,2012,33(6):31-39.
作者簡介:嚴廣樂,上海理工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林巍,上海理工大學管理學院博士生,溫州大學城市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