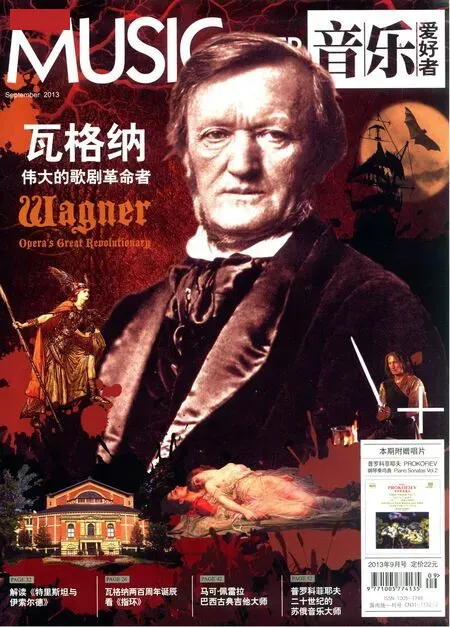馬蒂亞斯·弗萊茨伯格 我只是一個“復制者”
胡越菲
馬蒂亞斯是一位充滿活力與激情的指揮家。他語速極快,侃侃而談,原定二十分鐘在排練休息時進行的采訪,直到助理再三催促,他才意猶未盡地回去排練,臨走時滿懷期待地看著我:“你要走了嗎?還是你可以待到排練結束,我們還可以再聊一會兒?”我望了一眼手中才問到一半的采訪提綱,毫不猶豫地給了他一個肯定的答復。
戶外音樂會必須請最好的音樂家
在名團濟濟的維也納,美泉宮交響樂團也許算不上最有名的一支,但仍然以其和諧的音色、迷人的臺風以及高藝術水準而深受歡迎。樂團非常重視對維也納風格作品的還原,擅長詮釋海頓、莫扎特、施特勞斯以及同一時代作曲家的作品,自1994年成立以來,每年舉行一百五十多場音樂會。和維也納愛樂樂團一樣,美泉宮交響樂團不僅每年定期在美泉宮舉辦戶外音樂會,還出訪過日本、克羅地亞、捷克、瑞典和丹麥等國家,獲得巨大成功,成為奧地利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
由于前陣子上海的辰山植物園剛剛舉行過一場大型戶外音樂會,我們的話題便自然而然地從此開始。馬蒂亞斯告訴我,他本人對戶外音樂會相當喜愛,他覺得這是一個讓人們了解古典音樂的絕佳方式,而不用去劇院正襟危坐。“當然,古典音樂需要非常集中注意力,這是很重要的,但同時它也需要以另一種輕松的方式向人們開放。”在他看來,古典音樂也有娛樂性的一面。“兩百年前,在維也納的沙龍上,貝多芬、莫扎特在演奏,人們聽著音樂、聊著天,分享聽到的美妙旋律。就連巴赫都會對他的孩子們說,這個美好的下午,讓我們吃吃喝喝,唱唱歌,再演點音樂吧。這就是音樂的意義所在。”而這樣的心情在戶外音樂會上也能復制。“你可以支起一個帳篷,一邊野餐,一邊欣賞音樂。也許有那么一天,這些在戶外音樂會的人就會去音樂廳欣賞音樂了。”
說到一場戶外音樂會的籌備,人們通常認為,由于其欣賞群體大多是普通觀眾、非專業樂迷,所以并不需要請一流的藝術家。對此,馬蒂亞斯則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因為有了擴音系統,每一個犯的小錯誤都會被無限放大,如果樂團中有一個人奏錯了一個音,擴音系統會將它傳送到每一個角落,“所以戶外音樂會必須請你能請到的最好的音樂家”。
在準備一場戶外音樂會的曲目時,馬蒂亞斯表示,自己會有所“混搭”。首先,他一定會選擇那些非常古典、嚴肅的曲目,比如勃拉姆斯或者貝多芬的交響曲。“為什么不呢?我覺得每個人都可以接受有價值、有質量的音樂,只要它演奏得夠好。”這又是一個非常新穎的觀點,人們總是認為,戶外音樂會應該選擇那些娛樂性較強、通俗易懂的曲目。“對于那些不太了解音樂的觀眾來說,他們不會說,哦,這個樂章演得快了點兒,那里的技巧表現得不太好。和一些音樂專家相比,他們對音樂全無偏見,只會帶著一種最本真、最自然的感情去欣賞音樂,因此他們更需要高質量的音樂,否則就容易產生誤導,會讓他們覺得原來古典音樂是這樣的。”當然,他還會加一點流行音樂、電影音樂,“如今有很多優秀的流行古典音樂和電影音樂,我覺得應該由很好的樂團來演奏,然后我們會發現,也許它們與一些古典音樂具有同樣高的價值”。
得了布索尼獎卻覺得“該死”
馬蒂亞斯在許多國際知名的鋼琴比賽中獲得過至高獎項,包括1984年的布索尼鋼琴大賽銀牌、1986年魯賓斯坦鋼琴大賽金牌、1988年貝森多夫鋼琴大賽第一名等等。然而馬蒂亞斯卻表示,自己從來沒想過成為一名鋼琴家,事實上他想學的是建筑。就在那一年,他的鋼琴老師建議他去參加布索尼鋼琴比賽,滿載而歸后,他當時的感覺卻是:“啊哈,我想學建筑了,但我今年卻得了鋼琴比賽的獎。該死!”面對我將他稱為“天才”的贊美,他認真地澄清道,天才是指那些創作(Create)音樂的人,而自己只是一個很好的“復制者”(Reproducer):“我將自己看作是一個用手和手指工作的‘工匠(Craftsman)。”
得了獎后,馬蒂亞斯常常以演奏家或獨奏家的身份與知名樂團合作,包括以色列愛樂樂團、波爾多交響樂團、西班牙國家交響樂團等。在接下去的五年里,他參加了大約一千場音樂會,他很少在家,不是在巡演、就是在去巡演的路上,和朋友的聯系也越來越少。終于有一天,他對自己說:“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在接下去的五十年里我不要這樣生活。”于是,在女高音歌唱家伊麗莎白·施瓦茨科普夫的鼓勵下,經過漢堡和巴黎歌劇院幕后管理者羅爾夫·利伯曼(Rolf Liebermann)的推薦,馬蒂亞斯開始了他的第二生涯——指揮家。短短時間內,他就征服了眾多曲目:在薩爾茨堡演出的《費加羅的婚禮》中,他與彼得·烏斯蒂諾夫(Peter Ustinov)共同擔任指揮助理;在布拉格國家歌劇院演出的《魔笛》中,他擔任維也納藝術節歌劇制作的音樂總監;他在瑞士的圣加侖歌劇院擔任總指揮,直到2000年……
不過,指揮家不也是要四處巡演的嗎?那么和鋼琴家有什么不同呢?馬蒂亞斯告訴我,指揮家雖然也需要外出巡演,但如果準備歌劇的話,就可以在一個城市待一至兩個星期。“你能生活得更從容,有更多的時間,見你想見的人。”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指揮家可以和許多人一起工作,“我喜歡與人交流,那很有趣,我總能學到東西”,而鋼琴家即使巡演時也總是獨自一個人,寂寞地躲在那個巨大的“黑盒子”后面,“音樂會后,你只能和主辦方一起吃飯,然后回賓館睡覺,因為第二天清晨五點你就要起床,趕往下一個演出地”。
當指揮讓他“學會呼吸”
從鋼琴家轉行到指揮,馬蒂亞斯覺得給他帶來的最大影響就是,學會了“如何呼吸”。“當你練習鋼琴的時候,你從來不會去學習如何呼吸,或者說遠遠不夠,因為你的注意力永遠是在技巧上,包括手指移動的快慢、聲音聽起來如何等等。‘呼吸是我從歌唱家那兒學到的,我學會了每個樂句、每次呼吸要用多少時間,我學會了如何在鋼琴上演唱。”斯特拉文斯基曾說過鋼琴是一件打擊樂器,馬蒂亞斯覺得這個觀點是完全錯誤的,“鋼琴絕對是一件旋律樂器,但你需要學習如何讓它變得旋律化”。
馬蒂亞斯從指揮中學到的另一件事,就是讓樂句慢慢來。“樂手可能會告訴你,一條美妙的旋律充分地發展、變化需要多長的時間,作為指揮家你必須認真考慮這點,并給出足夠的時間。”他發現如今很多指揮家與鋼琴家合作時常常會犯這個錯誤,他們總是拘泥于1、2、3、4的節奏,卻忘記了聆聽音樂,讓音樂自己流動,“每個音樂都有自己的時間”。
那么作為一個過來人,他認為一名演奏家必須做好怎樣的準備,才能轉行當指揮呢?“好吧,對于指揮這件事本身,只需要十分鐘就能學會了,你看,1、2,1、2、3,就是那么簡單。”馬蒂亞斯俏皮地向我演示道,“如果你站在樂隊面前這么打拍子的話,他們就會跟隨。然后,真正的工作就開始了。”他狡黠地眨了一下眼睛。“首先,一名指揮需要把一個樂隊中的所有樂器糅合在一起;其次,他必須是個能活躍氣氛的人,每個人的情緒都起起落落,你必須感受每個樂句和這些情緒,并將它傳達給樂手和觀眾;第三,他必須善于危機處理,他必須提前知道,誰有可能會在什么時候出錯,然后在他真正陷入危機之前幫助他……”
馬蒂亞斯坦言,自己并不是十分喜歡“跨界”(Crossover)這個詞,因為它給人的感覺好像不太認真,甚至有一點不專業。在歐洲,跨界有“不太嚴肅的音樂”(Less-serious music)的意思,他覺得這是不對的,“哪怕你在演奏搖滾音樂時,也應與演奏貝多芬交響曲時一樣嚴肅”。無論是傳統音樂會、戶外音樂會還是舞會音樂會,馬蒂亞斯對待它們的態度都是同樣的認真、專注,這一點,我們可以確信,因為即使在排練時,在沒有任何音響設計的普通大廳里,樂團奏出的音樂依然攝人心扉,彌漫到了房間里的每一個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