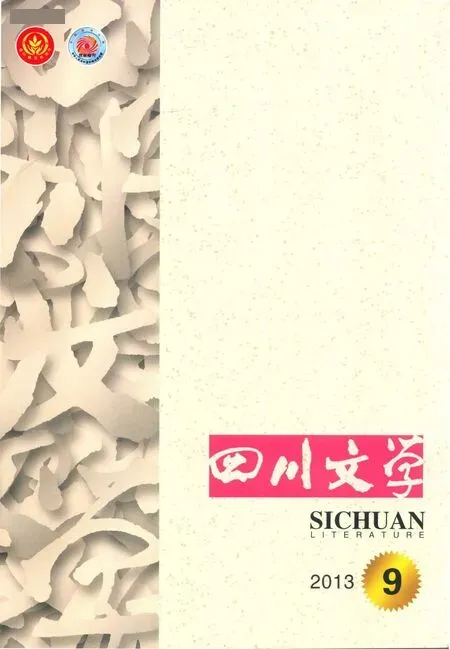張心陽雜文精選小輯
作者簡介:張心陽。安徽桐城人。高級編輯。1979年2月參加南疆作戰。三次立功。1988年從事專業媒體工作并開始雜文隨筆寫作。現為北京雜文學會常務理事、副秘書長。出版《帶毒的親吻》《中國雜文·張心陽集》等多部文集。十余篇文章選入中學生課外讀物。對蘇聯問題的研究并撰寫的系列雜文曾在文壇引起波瀾。
我相信這樣的“陣痛邏輯”
管轄湖南鳳凰古城的縣政府以神不知鬼不覺的方式,連同沈從文、吊腳樓、苗寨風情、苗家美食等一起,將古城以51%的股份賣給了開發商,繼而以每位游客148元的價格收取門票。因為限制了游客進城,古城里酒店、客棧、船主等商戶頓時生意慘淡,于是一起群體性事件在美麗的古城持續爆發。抗議者擁向街道、擁向城門。擁向河邊。
面對群體性事件,我們的政府已然學得相當成熟。氣舒神定,他們只動用警察,沒有慌張。沒有退縮,也不必對商戶妥協。縣主管官員帶著領袖般的口吻對媒體說:“這是新政帶來的一個現實”,“新政陣痛是必然的。”
我非常佩服這位官員的水平,他的話深得中國目前社會管理之精髓,人們的一切心結都可以從中釋然,沒有絲毫的理由不相信這樣的“陣痛邏輯”。當代中國人就是這樣從一個個陣痛中走過來的,隨著人們適應和習慣一個個陣痛。讓陣痛變成長痛,長痛變得麻木,之后就不再有痛感了。這次鳳凰城商戶的陣痛,無非是生意蕭條的陣痛,須知,中國人有多少陣痛要比這高出N“分貝”。
人們印象里最早的是物價之痛,那年頭一說鹽要漲價、米要漲價、煤球要漲價,人們那個搶購,用排山倒海來形容也不過分。后來是什么東西都漲價。想漲價就漲價。不該漲價的也漲價,就再罕見有多少人排隊搶購什么東西了,聽到漲價的聲音就像秋天聽說樹要落片葉一樣。這就是陣痛變成了長痛而不覺得痛的感覺。
近幾年的住房也是百姓心中一個痛,當初房價漲一漲,百姓痛一痛,政府管一管。而將實際情況連成一條線來看,政府越管,房價越漲,管了十年,瘋漲十年。人們懷疑。這政府是不是房產商的托兒,或是房地產商后臺老板?現在百姓再也沒有心情焦慮和疼痛了,因為敏感的神經早已碎成N段,不再指望政策,也不質疑政策,能做的。就是看政策里有什么漏洞,比如婚姻與住房的關系,通過離婚再復婚、復婚再離婚的折騰,鉆點房政空子。
如果人們不會忘記,某年的社會動蕩與腐敗有著密切關系,因為那時人們神經還敏感,充分感受到腐敗之傷痛,對查出個貪污幾十萬的貪官就恨不能碎尸萬段。現在早已不這樣了。出現貪污幾千萬乃至上億的官員,也當成笑話調侃,誰要是錢貪少了、情婦養少了,被舉報出來還覺得挺冤,深表同情。因由也自不必說,過去人們痛恨腐敗是沒有適應腐敗,逐漸地腐敗人物多起來,腐敗質量提高,成為常態,大家就習慣了。不信試試,中國人三個月不聞腐敗事件。反而覺得身上像沾了跳蚤似的,很不習慣。
這期間自然還有下崗陣痛、教育陣痛、醫改陣痛、鈔票貶值陣痛、有毒食品陣痛、禁言禁語陣痛、被代表被增長被幸福被死亡陣痛……中國百姓似乎命里注定要經歷人生全方位、全過程的陣痛,從經濟利益到民主權利,從自然生態到人身自由。從維護私有財產到維護人格尊嚴……從上幼兒園開始就接受待遇不公的陣痛,從走上社會就開始面對機遇不公的陣痛,從一行使個人權利開始就遭遇權利不公的陣痛。從走出產道的陣痛,一直到焚尸爐的陣痛。
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我們的一些社會管理者深諳此理。天天侵占你的利益,久而不知利益被侵占;天天剝奪你的權利,久而不知權利被褫奪;天天麻醉你的神經。久而不知神經已被麻醉。我不相信,鳳凰古城被政府和開發商強行奪走壟斷經營權后,普通商戶僅僅是個陣痛,十天半個月又能恢復經營生機。門票的意義就是要把一部分人甚至很多人擋在門外,這是傻子都曉得的道理。我相信的是,縣長大人所說的“陣痛邏輯”是真理,商戶們強忍著慘淡的生意,持續地強忍著慘淡的生意,最后不得不使一部分人撤離市場,關門大吉,淪落為民工或盲流,中產變成無產。對新政造成的“陣痛”成為一生刻骨銘心的回憶。因為他們正在精制地制造著又一個“陣痛邏輯”的標本。
“陣痛邏輯”衍生出難以數計的新概念和現實,比如,多少人以為當下熱門詞匯“屏絲”是個庸俗不堪之詞,然而我就不這樣認為。這是人們經歷了一次次陣痛的結果,是長痛、久痛之后神經麻痹的哀嘆。有識之士呼吁,不要讓有志青年都成為屌絲。可屌絲的感覺就是國人經歷了一次次陣痛的感覺,它是時代留下的一個深刻的符號。
氣場乎 氣虛乎
有一個說法:大人物是有氣場的。說這個氣場散發一種人難見、神莫測的能量,可以形成一種沖擊波,讓人自我矮化。不擊自潰。許多人都在這么說,但好像都沒怎么經歷過。不過,我倒是看到有人經歷過。
那是在某單位成立×周年的時候,某大人物要來視察。大家早早就剃好胡子理好發,還有女同胞專門買了鮮艷的衣服,如同過年。視察那天,大家站好準備與大人物合影的隊形。靜靜地等待大人物的出現。可是,大人物就是遲遲不出現,于是大家就耐心地等待,半小時、一小時地等待。許多人越是等待,就越有一種期待感,越有期待感,就越感覺到自己在一點點地失重。終于,突然有人宣布,大人物已到,請大家熱烈鼓掌。于是,我明顯地看到有人就像受到一種無形能量的沖擊,重心頓時不穩。身體開始晃動。行止有些失常,頭腦像是出現了空白……我想。這大概就是大人物氣場所產生的作用吧。
可能是我天生木訥,神經不夠敏感,與許多人不太一樣。沒有感受到大人物有那么大的氣場,就那么呆呆地站著,也沒有太多的心理和生理反應。不過過后我還是似信非信地認為,大人物是有氣場的,不然,一見大人物怎么那么多人反應強烈。
然而,有一件事把我將信將疑那點想法顛覆了。那是在H國發生的一件事,一位出租車司機像往常一樣拉客賺錢。傍晚時分他拉到一位顧客,與平常一樣看也沒看拉著就走。走著走著彼此就不由自主地攀談起來,談社會、談人生、談生活不順心的事,有時還不免夾帶一些臟話。后來遇到堵車,司機瞅了顧客一眼,這一看不要緊,原來這顧客不是別人,正是他早有耳聞的大人物。這時突然就慌了神。腦子有點蒙,心跳也加快,汗不住地往下淌,想接著再說點什么,可就是說不出來。一句話,當初與顧客閑聊時的那種自然,那種心平氣舒,頓時蕩然無存。
為什么說我得知這件事后,當初以為大人物是有氣場的觀點就被徹底顛覆了呢?你看那出租司機,在不知身邊坐著的是大人物時,他什么特別的感覺也沒有,一如往常,十分平靜;而當他得知他是大人物時,一下子就像遭遇了沖擊波,心理支撐頓時坍塌,汗水出,話語塞,頭腦蒙。你想,如果大人物真有氣場的話,那他一上車司機就會感覺到非同尋常,偉光四射,車壁生輝,心情亢奮,猶如被如來佛光照耀。可他沒這感覺,一點也沒有。
我曾一直想建議氣功大師將大人物是否有氣場這個問題作為一個重大工程來研究。倘能研究個成果出來,通過測定氣場來斷定何人將來能成大人物,寫出“氣場決定論”論文,就能申請國際發明專利或諾貝爾獎什么的。氣場屬于物理現象,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大陸人獲物理諾獎還是空白,如果我們得上了,那又可以像莫言得文學獎一樣,讓咱們傲視世界一回。只可惜,這個試驗讓一個出租司機在不經意間做了,讓人很失望地感到,大人物一點氣場也沒有。
斷言大人物沒氣場,還有一件事情可以佐證。不久前,英國首相卡梅倫到醫院考察工作。結果被醫生認為擋了給病人治療的通道,叫卡梅倫等一干人統統滾出去。開始卡梅倫以為自己有氣場,不可能讓人撼動,只叫隨行人員出去。可醫生就是沒有感受到這個大人物氣場的存在,口中嚷嚷著“我不吃這一套”什么的,讓人覺得倒是這個醫生氣場極強,最后卡梅倫想發功也不成,只好悻悻離開。
我在想,為什么大人物和普通人一樣就是沒氣場呢?后來在掉到地上的一張紙片上看到也是一個大人物說的話:“偉大人物之所以偉大,是因為我們自己跪著。”終于大釋所然。中國人真的跪得太久了,都世界GDP老二了,都把人送上太空了,精神上還在跪著。還說本文開頭所說的接見,且不說制度體制、宣傳機器早已把大人物營造得神秘莫測、神通廣大。就是那現場環境和氣氛的營造,也讓大人物如同神從天降。大人物要在莊嚴肅穆的環境中出來,要人們等到心理幾近崩潰才出來,要在前呼后擁中出來。這絕對是一個心理戰,這種戰法本身就在構成了一種沖擊波,從心理上先把常人打垮。
貌似被大人物打垮,實是我們自己把自己打垮。我們自己一直在跪著。崇拜權力,極度崇拜極端的權力;敬畏權力,極度敬畏極端的權力。沒有人告訴我們,我們多少人根本也不知道,大人物權力原來不過普通人授給他們的,大人物之以所以能活著,是因為普通人用糧食喂養的。你哪一天斷了他的糧食試試,看他還有大人物樣子沒有?人們哪一天不在他的周圍唱贊歌試試,他還有大人物的譜兒沒有?
說大人物有氣場是唬人的,而普通人自造神仙,見了神仙就暈場,才是事實。
哪有氣場,只有氣虛。
丑行不在于腳蹺多高
一位左派人士像發現新大陸一樣,以極其夸張的手法,把英國《每日郵報》刊登的一組美國總統奧巴馬在不同工作場合蹺腳、以至引來其身邊工作人員不屑的照片轉發到網上。該左士對此情緒頗為激動,弦外有音地感嘆道:“哇塞,這只是習慣嗎?”
蹺腳或者說蹺二郎腿,對很多人來說就不過是個習慣。有醫生說,這是個不壞的習慣,適當的時候把腳抬高,有利于增進血液循環。這里,我們很想知道,如果不是習慣,如果不是本能地增進血液循環,那該是什么呢?如果按照某些愛用“左”眼觀事者的思維,或許應當從政治層面來解讀。比如,一個可以在總統府里把腳蹺到辦公桌上的人。那他也一定能把腳蹺到人民的頭上:一個在生活上都不注重小節的總統。政治上也一定會為所欲為。這樣的演繹,一點也沒越出他們的慣用邏輯。
其實,這種“生活小節決定論”早已被二戰時期的著名人物羅斯福、丘吉爾和希特勒打破了。羅斯福的相信巫術、搞婚外情。丘吉爾的嗜酒如命、吸食鴉片等惡習,不知要比愛國信仰堅定、保持素食主義、做事極有條理、無任何不良嗜好的希特勒的“良好品行”要惡劣多少倍。但他們給國家和人類留下的結果,卻完全是另一回事。
重要人物從來都被作為社會道德楷模來看待,其一言一行既代表一國之形象,也對國人具有示范效應,不謂不重要。比如最近,俄國總統普京在日本首相安倍來訪發言時玩手中的鉛筆,就很受國際社會詬病。比爾·蓋茨在接受韓國總統樸槿惠接見時,一只手插在褲兜里。被韓國媒體視為不知禮節而被罵得狗血噴頭。不過,往根子上說,人們看待政要,覺得順其自然、不刻意掩飾普通人的一面,還是要比把內心的骯臟偽裝起來,成天作正人君子狀。要可愛得多。
在歷史的大人物中,不只是希特勒以其完美無缺的外在形象示人。前蘇聯的某個領袖也曾經多少年被人當作無比崇高、無比偉大的“上帝”供奉著。然而就是這樣一個領袖,專門以虐殺善良的動物為快樂,專門以聽取同僚被契卡施以肉體折磨而發出的嚎叫聲為快樂,他不僅斬殺了當年和自己一起起家的大部分戰友,而且致使數百萬有思想、有知識、有能力的人人頭落地。而我們去察看一下他的從政史,卻是從來沒有過蹺二郎腿之類惡習記錄的。不僅如此,而且沒有一個夜晚不是“辦公室里的燈亮到天明”,沒有一個時候不為“人民群眾的利益操碎了心”。
這個世界上有一種體制,就是運用各種宣傳機器甚至暴力來遮蔽那里的大人物的丑行。他們貪得無厭,富可敵國,展示給世人的是一副清心寡欲、天下為公的形象;他們殘酷無情、剪除異己、滅掉政敵,卻被作為純潔本黨、為我人民來大加渲染:他們權力嫡傳、基因決定、用人唯親。卻被說成是人民的意志、歷史的選擇;他們喜新厭舊、玩弄女性,卻以志趣相投、理想遠大而加以贊美;他們各立山頭、拉幫結派、相互傾扎,卻被表現成一派精誠團結、同舟共濟……很難列數這個世界上這種組織有多少,但已垮臺的前蘇聯和羅馬尼亞等東歐政權無疑是典型代表。人們確實不曾見過關于斯大林、勃列日涅夫、齊奧塞斯庫等蹺二郎腿的有損其光輝形象的報道,但上述所有行為無一不是他們政治生涯中的家常便飯。對此,不知道我們某些富有發現眼光的人。為何一點也不驚訝、不感嘆。
大人物真正的丑行其實并不是一個人在不適當的場合蹺了多少次二郎腿,也不是半夜起床還要貪喝幾夸特威士忌,甚至不是意淫過誰和感情移位。而是政治上的丑行、人格上的丑行。反人類、反人權、出賣國家利益的丑行,并且還要將其掩蓋起來。大加粉飾,渺小被歌頌為偉大,拙政被吹捧為盛世,造孽被美化為造福。這種人才真正的禍國殃民,才是最大的丑惡。
在一個好的政治制度下,大人物再有能耐最多也只能把腳蹺到桌子上。在一個不好的政治制度下,大人物的腳也許不蹺在桌子上,但往往蹺到人民的頭上。蹺起看不見的腳比蹺起看得見的腳更可怕。
此蘭彼蘭
漢文化里因為一個人而誕生一個新漢字——(“√”下面一個“三”字)。這個字這樣釋義:上面“√”表示同意。下面不是“三”。而是一十二,舍起來就是一十二次都同意。此人崗位神圣,手舉神器,代人入廟堂議政,歷時六十載,代表十二回,人謂之為共和政權之活化石。這個字由“蘭”字變異而來,緣于此人尊姓大名中有個“蘭”字,姑且音也讀“蘭”。
這恐怕是世界政壇上極其罕見的活化石,也是現政體的活標本。典型意義必定永載史冊。當年克林頓調侃與米國相鄰的某國元首:當初我上幼兒園時,他就是總統:我上小學時,他是總統;我上中學時,他是總統;我上大學時,他是總統;我工作后,他還是總統;我結婚后,他還是總統;我當總統了,他仍然是總統;我總統任期滿了,他居然還是總統。克林頓如果遇見活化石,完全可以將這番話語套之一用:我上幼兒園時,她手舉神器;我上小學時,她手舉神器;我上中學時,她手舉神器……我總統任期滿了,她居然還手舉神器。
一個人高居廟堂,能把神器舉這么久,最大的秘訣就是“三”上面那個“√”。她說:“我從來不投反對票”,“‘忠誠二字可形容我一生”。章伯鈞不懂得這個道理,握神器僅四年即旁落。馬寅初不懂得這個道理,握神器僅十年即喪失。彭德懷也不懂得這道理,握神器也不過十來年,最后連性命都搭進去了。
廟堂之上的事情我不大懂。由此聯想到的是我娘姓名中也諱一個“蘭”字——淑蘭。她是不識多少字的家庭主婦,小得不能再小的人物,四方鄰居只知她叫“張老太太”,欲知其真名實名得上公安局查戶口簿。她與她年齡相仿,但此“蘭”永遠也不比彼“蘭”幸運。
生活就是一個選擇,或代表自己或代表別人,或選擇同意或不同意。我娘也常面臨如此選擇,她很多時候也選擇“同意”——盡管不知表決器為何物。
那年吃大食堂的時候,樹皮樹葉被人吃光,觀音土也都被挖空,許多人餓成浮腫,許多人頭天還在食堂照過面,第二天就草席裹走了。大食堂成了地地道道的食人堂。這天一樣也在食堂等著撈不著米粒的飯食,公社書記走過來,我娘不知哪來的膽子,靠上去說:“書記,你敢不敢把食堂解散了?你要是怕擔責,征求意見,我今天說的話算是第一個同意。”那年代,說這檔子話是犯天條的事,好在書記和我父親私交不錯,母親的同意注定不會被同意,但也就算什么也沒有說。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喊“萬歲”喊得驚天動地、燦爛輝煌,俺娘一聽就不耐煩:“古時候哪個皇帝不被喊萬歲,見誰萬歲了?我看都萬睡了。如果喊萬歲,實活百十歲,那等于打到一折,還是個短命的哩。要是喊個‘身體健康什么的,我倒同意。”
我父親是個兩肋插刀、疾惡如仇的人。一輩子除了稅務工作就是替人主持公道、打抱不平,對仗勢欺人、以權壓人、橫行鄉里的人。能豁出命來和他們干。這其實是要給自身和家庭添麻煩的,可我娘居然從來沒反對過。有一年大年除夕,我娘一開門,便見門口擺著一擔稠稠的人糞,她很快知道是什么意思,遭人“行為藝術了”,很想哭,但她沒哭,一抖擻精神,把那擔糞挑進了田里澆了小麥。回過頭來對我們說:“開年遏吉兆啊,有人給我們送肥料,那是祝咱家五谷豐登、人畜興旺。”我娘對我爸的行為從未說同意,但同意在心里。
她同意人要明是非、知丑惡、持公道、講正義。反右你同意、反左你也同意,吃大食堂你同意、包產到戶你也同意。閉關鎖國你同意、改革開放你也同意,斗私批修你同意、不論姓資姓社你也同意。對這樣的人,用我娘的話說:“那叫思想婊子。”
我娘很喜歡她名字里那個“蘭”字。繁體是“一”下面一個“門”,門里有個“柬”。她說,即使是一棵小草,那也要長在門頭上。那該說的真話還要是說。我說,蘭與蘭不一樣,您是那高貴典雅的惠蘭,可還有頭朝下的吊蘭。娘說:“你以為頭朝下吊著不造孽啊。”
“蘭不生當盧,別是閑庭草。夙被霜露欺,紅榮已先老。”李白這首詠蘭草詩的前兩句,俺娘是用得上的。她沒進過廟堂,她沒舉過神器,她就是一棵普通的草。確實不及有的草那么幸運。但她有無數無名草的高貴品格,不是風吹兩邊倒的草。不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虛偽的草。吃自己的飯。做自己的草,無愧于自己,無愧于自然,無愧于草朋草友。
李白這首詩還有后兩句。詩云:“謬接瑤華枝,結根君王池。顧無馨香美,叨沐清風吹。”這大概就是原本是棵無名草,搖身一變成為“√”字頭的草了。接在瑤池邊。伴在君王側,看上去風光無限。但說到底也就做了個花盆而已,等到那點可憐的馨香沒了,就風吹雨打去了。
責任編輯:卓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