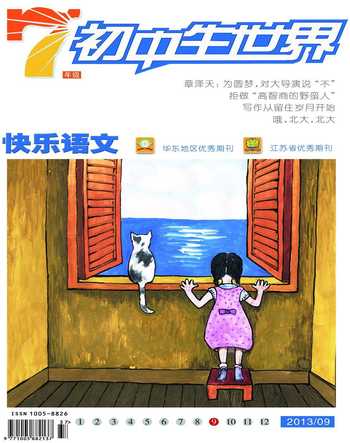先去送個外賣,再決定要不要上大學
2013-04-29 16:16:12周菁
初中生世界·七年級 2013年9期
周菁
我曾在6個國家做過義工,因此便有機會結交到不同國籍不同文化的同齡大學生。
在泰國的基金會里,我們27個國際志愿者,就有10個來自歐美。23歲的Deran畢業于美國名校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歷史系,提及文憑學歷,他總是笑道,這些都只是一張紙,真正讓他有所收獲的,是不斷離開美國,去別的國家行走過程中的發現。
后來,Deran申請到了一個新加坡 NGO組織,算是以全職員工的身份“正式”參加工作了。不過Deran的這種生活方式,按他的話來說,在美國并不常見。和中國大學生一樣,大多數美國學生在畢業后選擇攻讀研究生,或者立刻找工作。
另有一個丹麥的19歲義工,剛剛高中畢業。她告訴我,在丹麥,他們班上一共25個人,她是唯一一個到泰國做義工的,其他的23個人畢業后都不著急先上大學,而都找了份臨時工作:銀行收銀員、車庫管理員、送外賣的、送快遞的……僅有一個直接去念大學。
我問她送外賣能學到什么,她說,上大學前去接觸一下社會,和不同的人交流,以這種方式去了解他們的工作環境、工作方式,能夠更加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在丹麥,大部分學生都這樣。
我認識的,還有兩位英國的大學畢業生,一個是英語文學專業,一個是教育學專業。在泰國干了6個月的志愿者工作后,他們一個留在泰國教英語,一個回英國繼續當老師,算是都發揮了專業優勢。他們說,在英國,很多年輕人高中畢業后,就去其他地方做義工。
不過,這樣的“畢業選擇”在英國并沒有被捧上神壇,只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也有被“強制”做好人好事的。我和一群印度大學生在加爾各答一起參加過臨終關懷服務。原來在印度,很多大學對于學生的社區志愿者服務都有學時要求,比如必須做滿40個小時,才能拿到相應的學分,順利畢業。
(摘自《壹讀》2013年第9期,有改動)
猜你喜歡
中學生天地(A版)(2022年6期)2022-07-14 12:39:26
瘋狂英語·初中天地(2021年6期)2021-08-06 09:03:24
大學(2021年2期)2021-06-11 01:13:12
海峽姐妹(2020年12期)2021-01-18 05:53:08
民主與法制(2020年16期)2020-08-24 06:54:50
中國外匯(2019年21期)2019-05-21 03:04:06
下一代英才(酷炫少年)(2019年3期)2019-03-25 02:34:18
少年漫畫(藝術創想)(2018年12期)2018-04-04 05:29:10
黃河之聲(2017年14期)2017-10-11 09:03:59
中國火炬(2013年7期)2013-07-24 14:1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