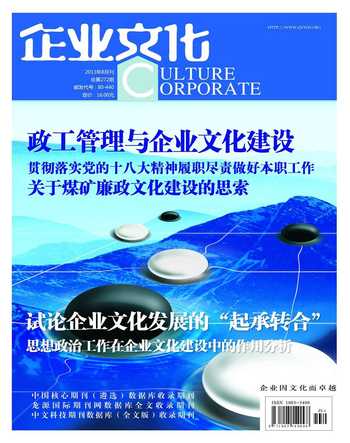中心城市區(qū)域經(jīng)濟轉(zhuǎn)型發(fā)展的必由之路
摘 要:在經(jīng)濟全球化進(jìn)程中,開放合作、互惠型經(jīng)濟發(fā)展模式已成為發(fā)達(dá)經(jīng)濟體必然的選擇。深圳市作為我國經(jīng)濟特區(qū),一直走在改革開放的前端,實現(xiàn)了經(jīng)濟的突飛猛進(jìn)。然而在區(qū)域經(jīng)濟轉(zhuǎn)型發(fā)展的局勢下,同樣面臨著各種瓶頸。在“十二五”規(guī)劃中深圳市明確要強化深圳全國經(jīng)濟中心城市的服務(wù)能力、輻射能力和帶動能力,以外溢發(fā)展突破城市空間制約,以區(qū)域合作優(yōu)化要素資源配置,實施外溢型經(jīng)濟發(fā)展戰(zhàn)略。首先,文章在理論上創(chuàng)新性地對外溢型經(jīng)濟的概念進(jìn)行界定,并分析了它的特點及其模式類型。然后從區(qū)域經(jīng)濟戰(zhàn)略的角度出發(fā),基于SWOT分析深圳市外溢型經(jīng)濟發(fā)展優(yōu)勢、劣勢、機遇及挑戰(zhàn),在此基礎(chǔ)上提出了深圳市發(fā)展外溢型經(jīng)濟的對策及建議。
關(guān)鍵詞:外溢型經(jīng)濟 SWOT 中心城市 區(qū)域經(jīng)濟戰(zhàn)略
一、引言
外溢型經(jīng)濟是基于外溢效應(yīng)理論提出的一個新概念,國內(nèi)外經(jīng)濟學(xué)界對外溢型經(jīng)濟作為一種經(jīng)濟形態(tài)論述較少,比較接受的一種定義是:外溢型經(jīng)濟是經(jīng)濟體之間在技術(shù)、成本等勢能落差的作用下,處于優(yōu)勢地位的經(jīng)濟體通過貿(mào)易和投資等經(jīng)濟活動,溢出知識、信息、資本等要素,獲得經(jīng)濟收益并對外部經(jīng)濟體產(chǎn)生顯著外溢效應(yīng)的經(jīng)濟發(fā)展模式。外溢型經(jīng)濟不同于外向型經(jīng)濟,它具有開放、合作、互惠的特征,對相關(guān)行業(yè)、周邊區(qū)域乃至整個國家的技術(shù)進(jìn)步和經(jīng)濟發(fā)展產(chǎn)生巨大推動作用。國外許多學(xué)者針對不同要素溢出效應(yīng)的存在及其對區(qū)域經(jīng)濟的影響作用進(jìn)行了研究分析。如羅默[1](1994)提出了知識溢出模型,意識到知識具有外溢效應(yīng),知識生產(chǎn)部門通過外溢效應(yīng)機制可提高全社會勞動生產(chǎn)率。盧卡斯[2](1988)的人力資本溢出模型指出人力資本高的人對他周圍的人會產(chǎn)生有利影響,提高了周圍人的生產(chǎn)效率。MacDougall(1960)[3]在分析FDI的一般福利效應(yīng)時,第一次把技術(shù)溢出效應(yīng)視為FDI的一個重要現(xiàn)象。國內(nèi)對外溢效應(yīng)的研究大多是在國外研究基礎(chǔ)上的應(yīng)用研究,韓燕[4](2004)在對FDI對東道國的外溢效應(yīng)及影響因素的研究中認(rèn)為FDI技術(shù)外溢是跨國公司實現(xiàn)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載體,并認(rèn)為FDI技術(shù)外溢能夠?qū)|道國產(chǎn)生正外溢的效應(yīng)。惠寧[5]對知識外溢進(jìn)行了研究,周平[7]、陳美蘭[8]等學(xué)者通過量化模型對人力資本外溢與經(jīng)濟增長的關(guān)系進(jìn)行了實證研究。
二、基于SWOT的深圳市外溢型經(jīng)濟發(fā)展現(xiàn)狀分析
(一)優(yōu)勢分析
1.資本溢出規(guī)模不斷擴大
作為國內(nèi)主要的金融中心城市之一,深圳已經(jīng)成為全國重要的資金集聚和擴散地,發(fā)揮著重要的資本溢出功能。截至2010年6月底,深圳金融機構(gòu)通過銀行間同業(yè)拆借與債券交易系統(tǒng)流入資金8.21萬元,流出資金7.08萬億元。2010年深交所新上市公司321家,位居全球第一,籌集資金4083.79億元,位居全球第二。深圳已經(jīng)成為名副其實的資本外溢中心。
2.產(chǎn)業(yè)外溢步伐不斷加快
伴隨著深圳經(jīng)濟的快速發(fā)展,深圳市產(chǎn)業(yè)向外溢出步伐不斷加快。隨著改革開放步伐加快,內(nèi)地投資環(huán)境不斷完善,深圳產(chǎn)業(yè)外溢逐步多元化。在國內(nèi)方面,2006-2010年深圳市屬國有企業(yè)在廣東省內(nèi)投資項目共39個,項目投資總額638億元,投資地點涵蓋全國大部分省際城市。在國外方面,2010年深圳經(jīng)核準(zhǔn)新設(shè)境外投資項目257個,經(jīng)核準(zhǔn)境外投資協(xié)議投資額88671.72萬美元,中方協(xié)議投資額71464.62萬美元,海外并購項目30個,并購項目逐漸深入世界領(lǐng)先的技術(shù)和研發(fā)領(lǐng)域。
3.技術(shù)外溢效應(yīng)正在逐步增強
截止2010年,深圳各類專業(yè)技術(shù)人才已達(dá)98.58萬人,國家級高新技術(shù)企業(yè)1044家,從事高新技術(shù)產(chǎn)品開發(fā)的企業(yè)超過3萬家,具有自主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高新技術(shù)產(chǎn)品產(chǎn)值6832.43億元,占全部高新技術(shù)產(chǎn)品產(chǎn)值67%,發(fā)明專利授權(quán)量全國排名第二。此外,在空間地理上,基本上形成了以深圳為技術(shù)研發(fā)中心—東莞、惠州為加工制造中心的產(chǎn)業(yè)布局,深圳作為區(qū)域技術(shù)創(chuàng)新中心所發(fā)揮的外溢作用越來越顯著。
(二)劣勢分析
深圳經(jīng)濟特區(qū)成立以來,深圳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從1980年的2.4億美元增長到2010年的43億美元,F(xiàn)DI資本、技術(shù)、管理經(jīng)驗對深圳的溢出,對推動經(jīng)濟增長作出了巨大貢獻(xiàn)。其中1991-1996年間最為明顯,深圳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從1990年的3.9億美元,增至1996年的20.51億美元,年均增長40%。20世紀(jì)90年代初期以后,深圳市進(jìn)出口貿(mào)易增速逐步趨緩,對深圳經(jīng)濟增長的貢獻(xiàn)率隨之降低。此外,外商直接投資增速放緩,對深圳的外溢效應(yīng)也逐步減弱。
(三)機遇分析
1.產(chǎn)業(yè)發(fā)展機遇
金融危機之后,發(fā)達(dá)國家加快發(fā)展新興產(chǎn)業(yè)、跨國公司重新整合全球生產(chǎn)供應(yīng)鏈、先進(jìn)服務(wù)業(yè)跨境轉(zhuǎn)移、國際人才流動加快、國家加快轉(zhuǎn)變經(jīng)濟發(fā)展方式、推進(jìn)區(qū)域經(jīng)濟均衡發(fā)展以及,都為深圳發(fā)展外溢型經(jīng)濟帶來了難得機遇。低碳經(jīng)濟、信息技術(shù)、生物科技和新能源產(chǎn)業(yè)成為國際跨境投資新的重點領(lǐng)域,而中國等新興經(jīng)濟體國家成為跨國公司投資新興產(chǎn)業(yè)研發(fā)、制造活動的重要地區(qū)。深圳作為我國對外開放先導(dǎo)區(qū)和經(jīng)濟發(fā)展中心城市,擁有發(fā)展新興產(chǎn)業(yè)的技術(shù)、人才、產(chǎn)業(yè)基礎(chǔ),同時具有吸引國際投資的豐富經(jīng)驗,有成為國際新興產(chǎn)業(yè)外溢技術(shù)、外溢資本重要承接區(qū)的條件和可能。
2.政策機遇
近年來,國家加快轉(zhuǎn)變經(jīng)濟發(fā)展方式、推進(jìn)區(qū)域經(jīng)濟均衡發(fā)展,為深圳創(chuàng)新發(fā)展方式、創(chuàng)新區(qū)域合作機制、加快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升級營造了良好政策環(huán)境。如《國務(wù)院關(guān)于中西部地區(qū)承接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的指導(dǎo)意見》以及廣東省“雙轉(zhuǎn)移”政策的推出,為深圳向外溢出產(chǎn)業(yè)、資本、技術(shù)、人才,吸納優(yōu)質(zhì)資源提供了更加有利條件。《珠江三角洲地區(qū)改革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2008-2020年)》加快了深莞惠一體化和深港創(chuàng)新圈、金融合作區(qū)建設(shè)進(jìn)程。此外,新的歷史時期,中央再次授予深圳四項“先行先試”權(quán),新的政策優(yōu)勢,為深圳設(shè)計、制定走外溢型發(fā)展道路的體制機制,提供了法律依據(jù)。
(四)挑戰(zhàn)分析
近幾年來,涉華貿(mào)易救濟案件及安全問題嚴(yán)重限制深圳產(chǎn)品出口與技術(shù)獲取,阻礙外溢型經(jīng)濟發(fā)展。未來深圳在吸引國際直接投資與增加出口方面,將面臨來自發(fā)展中國家與國內(nèi)其他城市的激烈競爭。在國內(nèi)區(qū)域經(jīng)濟方面,受行政區(qū)劃與地方利益的影響,國內(nèi)每個地區(qū)都立足于本地區(qū)經(jīng)濟利益,產(chǎn)業(yè)同構(gòu)、同質(zhì)競爭、地方保護等問題嚴(yán)重阻礙經(jīng)濟要素的自由流動與產(chǎn)業(yè)分工協(xié)作;同時,由于醫(y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制度性的差異,也限制了區(qū)域間人力資源的自由流動;此外,深化深港合作還存在體制障礙,兩地不同的政治和經(jīng)濟體制阻礙了人才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以及教育合作的順暢開展,嚴(yán)重影響了兩地資源的共享和雙方優(yōu)勢潛力的發(fā)揮。
三、相關(guān)措施及建議
(一)突破空間和資源瓶頸制約,增強承接外溢和輻射能力
隨著深圳市經(jīng)濟的快速發(fā)展,基礎(chǔ)性資源的緊約束、城市發(fā)展的結(jié)構(gòu)性矛盾、社會發(fā)展模式的脆弱性、戰(zhàn)略性空間的低效利用的四大問題日益凸顯。深圳要發(fā)展外溢經(jīng)濟,必須擁有自身作為“增長中心”的強大實力,強化極化效應(yīng),促使生產(chǎn)要素和經(jīng)濟活動快速在自己周圍集中,才能引領(lǐng)外溢發(fā)展的格局。深圳外溢型經(jīng)濟發(fā)展應(yīng)引導(dǎo)各類創(chuàng)新資源圍繞技術(shù)和知識密集化聚集,打造外溢發(fā)展新優(yōu)勢,努力打造高端制造業(yè)中心、全國金融中心、國際貿(mào)易中心、全球性物流樞紐中心及國際文化創(chuàng)意中心搶占產(chǎn)業(yè)外溢發(fā)展制高點。
(二)壯大外溢型產(chǎn)業(yè),加快城市經(jīng)濟轉(zhuǎn)型升級
深圳已然形成了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與優(yōu)勢傳統(tǒng)產(chǎn)業(yè)比翼齊飛的工業(yè)發(fā)展格局,深圳市發(fā)展外溢型產(chǎn)業(yè)首先要將以發(fā)展成熟的、技術(shù)含量低的加工制造業(yè)或車間遷至原料、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的地區(qū),而在深圳本市可設(shè)立相關(guān)總部,主要的任務(wù)是進(jìn)行研發(fā)和創(chuàng)新,設(shè)立行業(yè)的公共技術(shù)平臺,著力實施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和產(chǎn)業(yè)升級同步策略;其次,為了提高企業(yè)的核心競爭力,企業(yè)可以拋棄以往的“內(nèi)部化”策略,采用“生產(chǎn)外包”、“服務(wù)外包”等“外部化”策略;第三,出臺某些產(chǎn)業(yè)發(fā)展的優(yōu)惠政策或建立大型的工業(yè)園區(qū),保持這些產(chǎn)業(yè)上的優(yōu)勢和聚集。
(三)科學(xué)謀劃外溢發(fā)展戰(zhàn)略,通過區(qū)域經(jīng)濟創(chuàng)新提升深圳經(jīng)濟質(zhì)量
深圳市發(fā)展外溢型經(jīng)濟是在探索中曲折前進(jìn)的過程,首先,政府等相關(guān)部門職能必須充分認(rèn)識發(fā)展外溢型經(jīng)濟的重要意義,切實轉(zhuǎn)變觀念。更加高度重視技術(shù)和知識力量,更加高度重視人力資本積累,更加高度重視打造支持知識創(chuàng)新機制。政府必須加快轉(zhuǎn)變經(jīng)濟管理重心,從發(fā)展速度管理轉(zhuǎn)向發(fā)展效益管理;促進(jìn)經(jīng)濟政策制定和政策執(zhí)行職能分離,著力營造適宜經(jīng)濟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外部環(huán)境。其次,發(fā)展外溢型經(jīng)濟國內(nèi)尚無經(jīng)驗可循,必須充分借鑒外部經(jīng)驗,依據(jù)城市中長期發(fā)展規(guī)劃、創(chuàng)造“深圳質(zhì)量”要求以及全球外溢型經(jīng)濟發(fā)展新特點,制訂發(fā)展戰(zhàn)略規(guī)劃;同時應(yīng)當(dāng)健全外溢型經(jīng)濟統(tǒng)計和專項報告制度,對外溢型經(jīng)濟運行實行動態(tài)監(jiān)測,根據(jù)經(jīng)濟運行需要,及時調(diào)整政策措施,避免因經(jīng)濟過度外溢出現(xiàn)產(chǎn)業(yè)“空心化”局面。
四、結(jié)論
隨著我國經(jīng)濟實力的不斷提升,對世界經(jīng)濟的外溢效應(yīng)不斷增強。發(fā)展外溢型經(jīng)濟是中心城市轉(zhuǎn)型發(fā)展的必由之路,深圳市外溢型經(jīng)濟發(fā)展要強化深圳作為全國經(jīng)濟中心城市的服務(wù)能力、輻射能力和帶動能力。按照優(yōu)勢互補、錯位發(fā)展、互利共贏的原則,加快深莞惠區(qū)域經(jīng)濟一體化發(fā)展。深圳作為首個提出外溢型經(jīng)濟發(fā)展的城市,因此要將其打造成外溢型經(jīng)濟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發(fā)源地,經(jīng)濟輻射的基點,全國市場的核心,形成經(jīng)濟增長和城市發(fā)展的良性循環(huán)。
參考文獻(xiàn):
[1]慧寧. 知識溢出的經(jīng)濟效應(yīng)研究[J].西北大學(xué)學(xué)報,2007 (01).
[2]徐盈之,朱依曦.知識溢出與區(qū)域經(jīng)濟增長:基于空間計量模型的實證研究[J].科研管理,2010,( 6):105-112.
[3]Romer,P.M. Increasing Return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94(5): 1002-1037.
[4]Lucas, R.E.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22).
[5]MacDougall, G D.A., The Benefits and Costs of Private Investment from Abroad: A Theoretical Approach[J] Economic Record 36: 1960,13-35.
[6]周平.二元經(jīng)濟理論與人口流動問題分析[J].經(jīng)濟問題,2008,(8):40-42.
[7]陳美蘭.人力資本溢出效應(yīng)、集聚與城鄉(xiāng)差距[J].工業(yè)技術(shù)經(jīng)濟,2010,(02).
作者簡介:吳利霞(1986.12-),女,湖北鄂州人,武漢理工大學(xué)在讀博士,研究方向為系統(tǒng)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