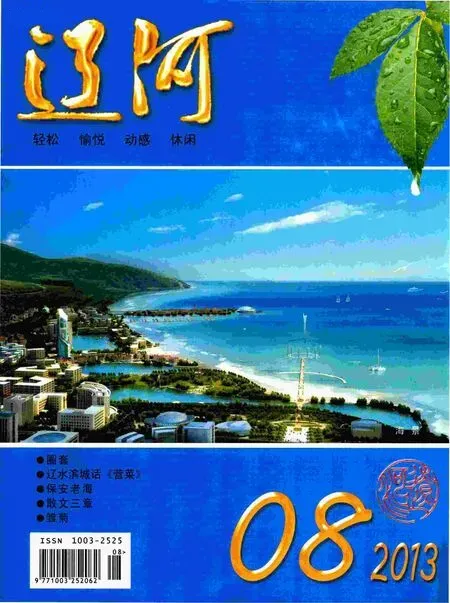狙擊手
李其志
任務結束后,他一遍遍地陷入那個稍縱即逝的回憶中,這都讓他對曾經發生的事情有些模糊了,仿佛那不過也是一次演習,任務失敗,教官講評,然后回到警隊再舒舒服服洗上一個熱水澡,淡漠而不留痕跡。但這次他意識到,一切都變得不同了。
那是一起因情感引起的綁架人質案。綁架人質是刑警隊的事兒,與防暴隊有什么相關啊。但當行兇者手持銳器,將一名人質脅迫到樓頂,聲稱不答應他的條件,就與人質同歸于盡時,他所在的突擊小分隊就要出動了。那是一個中午,他吃完飯正躺在床上看一本書,書是女朋友借給他的,他本不想看,是不想看女朋友借給他的書,他一直覺得他們不是太和的來,也許是他對她沒有感覺,但她卻喜歡他,這真是苦惱人的問題,這段時間,借書還書成了他們之間保持一絲聯系唯一借口,他暗暗對自己說,等這本書看完了,就拒絕她借給自己書,理由嘛,工作忙也好,不想看也罷,只要拒絕她就好。
這時,緊急集合的鈴聲就響了,他嘆了一口氣,把書扔在一邊。
到達現場后,他拎著長長的盒子爬樓梯,按剛才的臨時計劃,他是2號位。上到樓頂,對面盡收眼底,但行兇者卻挾人質蹲在樓頂的水泥煙囪后面。他打開有幾分沉重的盒子,把狙擊步槍拿出來。他是突擊隊里的一名狙擊手。
剛進突擊隊的時候,因為他的視力特別好,也因為他的沉默寡言,被指派做狙擊手,這讓他內心有幾分歡喜。但他沒想到做一名合格的狙擊手竟會這樣難,時間一長,簡直都讓他后悔當初的選擇了。在他的印象中,狙擊手應當是這個樣子,嘴巴里叨著一根哈瓦那雪茄,身披黑色大氅,面目呆滯而寧靜,然后,瞬間一槍將對手斃命,槍口上再冒出瓦藍色的青煙,一切又歸于平靜。在長時間俯臥在地練習時,他經常會想象這一場景,以期消弱內心的失落,可沒料到這不但沒有消弱,反而隨著身體下面的寒氣襲擾,更讓他對自己的處境倍感失望,都有些凄涼的味道了。
好在最初那段艱苦的訓練日子過去了,隨著他的心理素質和射擊技能不斷提高,他漸漸體會到若成為一名優秀的狙擊手,磨難是必須要經歷的,如今,他已經可以到享受做狙擊手的樂趣,當把腮靠到槍柄上,傾聽自己有條不紊的心跳,盯著瞄準鏡里的目標,他都有些喜歡這個等待的過程了,反到是目標應聲而碎時,失落陡生。
依舊沒有下達允許擊斃準備命令,談判還在進行。他有些無聊地把槍口上下移動,外面的景象也在瞄準鏡里忽上忽下。對面那座樓有些熟悉,他好象去過,他這樣想著,掏自己的口袋,想抽只煙,但被隊長呵斥住。他臉上有些掛不住,遮掩似的隨口問,對面是哪間樓啊?隊長說是某某大廈,他嘴里默念著,低聲說怎么會這么巧。隊長說什么巧,他說沒什么,內心有幾分回敬的快意泛起。隨即,他又俯到瞄準鏡前緊緊對著時隱時現的人影。人質顯然是名女子,艷紅的上衣,長發亂轟轟地披散在臉前腦后,從發間不經意流露出的驚恐眼神,卻讓他的心“騰”的一跳。
談判一直沒有結果,已經是下午5點多的光景,天色變得有些暗淡,行兇者已然瘋狂。現場指揮部下達了尋找時機,在保證人質安全的前提下,擊斃兇犯的命令。他的鼻尖滲出細密汗珠,手掌也粘粘的,不得不一遍遍地騰出手來擦汗。他的精神也無法集中,不合時宜地想起女友借給自己的那本書,他對自己悄悄說,如果她再借給自己書的話,不妨再看看也行,他晃晃頭,努力把這些念頭拋走。他的2號位是正位,另外還有1號和3號兩個側位,他的位置不太有利,但他不敢放松自己,他清楚一名狙擊手捕捉的就是瞬間的時機。
但是那個瞬間終究沒有把握住。他不知道為何另外兩側狙擊手為何也未能把握,也許他們的視線有礙,可對于他來說,那是一個百分之百命中的時機,可那個百分之百命中的時機,被他百分之百的錯失了。
兇犯將一把雙刃銳器扎入人質的胸口后,縱身跳下樓去。
隊長說“撤”時,他還一動不動地趴在那里,眼前一直閃著兇犯猛然從水泥煙囪后露出半截身體,人質已虛脫地垂下頭的影像。他被隊友踢了一腳,說:撤了。他的手發抖地把狙擊步槍拿起來,關閉的槍盒卻怎么也打不開,隊友蹲下身,幫他打開,問:你怎么了?他搖搖頭,說沒怎么,有些緊張。隊友冷笑,看透他似的站起身,走開了。
半年后,他和曾經不斷借給自己書的女友結婚了,做為警校的同學,我也去參加了他的婚禮。婚禮進行到尾聲,我在大堂里和他碰面,他笑嘻嘻地告訴我,他已經不做狙擊手了,調到行政科工作,輕松的很,工作沒有壓力。我不禁想起半年前他失誤后不久的一個夜晚,在路邊的小吃攤前,他喝得已然微醉,他說他有心理障礙了,訓練時在瞄準鏡里看到目標時,手便發抖。我問為何,他說不知,也許是因為自己已經沒辦法冷靜,勇敢地面對一切后果,而瞻前顧后,正是狙擊手的大忌。他的話讓我感覺到這個一度木訥的人非常可疑,于是便將他當時的話,看做是一種托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