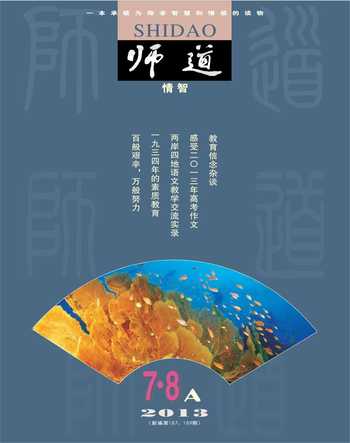自我價值的守望
邱磊
一班一世界
這些天,李玉老師的班級總是神神秘秘,大大小小的花盆、氣球,以及五彩斑斕的旗幟不斷裝點著教室,就連學生的服裝也悄悄有了改變,處處點點中透露著異域風情。這是怎么回事呢?原來,自2006年“蒙臺梭利模擬聯合國”(MMUN)創立后,9至16歲的孩子們又多了個舞臺,他們在世界范圍內掀起了一股“外交風暴”,很多人的語言表達、邏輯思辨、團隊合作等能力都有了新的鍛煉和提升機會。一時間,影響很大。
李老師知道后,就一直在思索這個項目是否能“遷移”,并有效地與班級建設相聯系,于是,組建一個“班級聯合國”的大膽想法就此產生。當他在班級宣布了這項班級活動后,同學們都特別好奇,而聽到“每個人可以代表一個國家”“每小組可以代表一個大洲”“共同討論熱點話題”等等誘人的設想后,同學們的熱情一下子就被調動起來,紛紛報名參加“萬國會”。有的愿意代表英、法、德、意等歐系國家,有的愿意做澳、韓、日、印等亞太國家,南美、非洲等地知名度較高的國家也被不少同學搶占,而對中、美兩國的爭奪最為激烈,幾番商榷,最后才確定下來。
基本框架確定后,第一次“班級聯合國大會”終于確定在下周一的班會課上,主題為“世界環境的‘危與‘機”,設計思路是從“危機應對”與“發展機遇”兩個角度辯證看待當前世界。大家領到主題后,立馬進入了角色扮演,為維護各自的利益紛紛在圖書館、網絡中查找資料,甚至還找到相關老師求教生物、化學、地理、政治等“學術支持”,讓老師們都詫異不已。不僅如此,很多同學還準備了像樣的“禮服”(其實僅是一頂帽子,或是一條圍巾、一個領結等)和道具,并且多是DIY,個性十足。
緊張的忙碌之后,活動正式開始。整個“世界”被分為四大陣營:東西半球和南北半球。李老師稱之為“南北對話”和“東西爭鳴”,這正好對應著教室里的四大組,每組最活躍的不是“發達國家”,而往往是“準備最充分的國家”,尤其是本次話題,讓“非洲國家”有某種天然的受害者心理。他們事先將相關的數據、國際法、生態災難、資源枯竭等情況了解詳盡,現場的“血淚史”哭訴讓人難以招架。
但“發達國家”也不示弱,“美國”表示自己已經盡到了義務,并“引經據典”,從各種材料和文獻中證明其出了很大力氣幫助別國改善環境;“英”“法”更是言之鑿鑿,暢談各自的環保理念和矚目成績……
等大家嘰嘰喳喳地講完了,那位代表“中國”的同學才站起身,朗聲說:“我覺得大家都有道理,但今天這場會議是‘求同存異的,是應該具有建設性的。是不是可以多做點改善環境的善舉呢?比如,保持良好的行為習慣;不亂丟亂拋;盡量多用環保袋;不隨便破壞草木;愛護野生動物;不浪費水電……”一席話讓場面漸漸冷靜下來,這番“說教”在大量的數據和資料支撐下,讓同學們更清楚地看清了世界,也彷佛一下子走進了教科書,讓“學習”走上新的平臺,而不再苦澀和乏味。
這場辯論賽過去很久了,但它開啟了一條先河,因為李老師從中看到了一股新生的力量,自由、公平、辯證、和諧,每個人通過自己“設身處地”的感悟,開始融入了不同國家的文化、宗教、經濟、政治,理解力、分辨力和包容力都明顯提升。很多班主任見了眼饞,也紛紛效仿,放手讓學生自我設計、組建、運行和修正,越來越多的人從中體會到課堂之外的樂趣與活力,甚至還有部分視頻被傳到了網上,一度成為熱門話題,獲得了廣泛的關注。
李老師說,他的下一步計劃是引入“英語對話”,讓這門國際語言扎扎實實地落地生根,將“教學—筑基—實用—成人”串成一條妙趣橫生的“邏輯鏈”,使每個孩子真正找到自己應有的位置。聽說,最近大家都在前所未有地投入“英語攻堅戰”中……
凝重的生涯設計
一千年前,北宋的張伯端曾提出“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口號,這種對自我命運掌控的渴望,一直是很多人的志業。而時下,我們對教育最多的批評正是來自于對“包辦”“灌輸”“填鴨”等強控制思維下的反抗。正是基于此,如何培養一個自由上進、目標明確、志存高遠、堅毅負重的學生,已然成了很多班主任最為頭疼的問題。
張豐老師的突破靈感來自于一次偶談。有老師告訴他,現在有些學校正在做“生涯設計”活動,即在高考之前,對學生未來的人生道路提前規劃,比如報考哪所院校、哪門科系、如何揚長避短等。張老師覺得這是一種將德育與智育完美結合的新型方式,如果能好好利用,必然大有文章可做。
但在具體實施以前,他先做了次“市場調研”,在同年級的8個班中以問卷的形式做了“摸底”,結果發現:有明晰和可操作的人生規劃的學生不足一成,而絕大部分只滿足于“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甚至很多人習慣于被父母、教師、長輩推著走,更不知“生涯設計”為何物。
嗅覺敏銳的張老師從中看到班級活動的新機會。他精心設計了一套“個人成長卡”,從高一到高三,每學期一張,逐步記錄個人目標的達成情況。具體來說,每張卡中,設立“高考目標”(如果是初中年級,也可以設為“中考目標”)“現有基礎”“達成方式”“自我獎勵”“成長記錄”等欄目,尤其是“達成方式”中又細化出“能力要求”“知識貯備”“核心競爭力”等模塊,對一個人生長所需的條件做了逐條梳理。
學生初拿到這張卡,雖然感到新鮮,卻并不能明白它的意義,也覺得無從下手。張老師就以自己為例,他制作了精美的幻燈片,從求學生涯、成長生涯、職業生涯入手,一步步展示人生規劃。他一邊講一邊用圖片、文字鏈接到自己成長中的某些里程碑,直到有一天被評為“教授級中學教師”。大家看得入神,慢慢覺得這是一個既能自我鞭策,又頗具趣味的“規劃游戲”,每天雖然只是在做微不足道的任務,但只要意志堅定,緩緩地累積之下,就可以匯集成一件壯麗的事業。
當意見變成共識之后,大家都細心地填寫卡片,再一字兒地在教室的后墻壁粘貼;每到班會課,張老師請同學來談個人感受和修正計劃,以及老師所需要提供的幫助和建議。細心的張老師還成立了“班級生涯設計委員會”,定期對大家的達成率進行評估,對反應最普遍的阻礙因素提出措施,對進步最穩健的同學進行獎勵。最典型的案例是,每周末的“班級電影課”就是來自于學生的建議,從《阿甘正傳》《放牛班的春天》,再到《肖申克的救贖》,大大延緩了學生的精神疲勞,使每個人都從中看到生活和學業上的希望和力量。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張老師下發了一個小冊子,上面印著全國286個一級學科、677個二級學科的分布和簡介,每一個學生都可以清清楚楚地從中選擇最佳的個人定位,并隨著學業的進行而不斷修正、完善。每當學期結束時,看著卡上滿滿當當的成長記錄,每個人都相信曾經氣吞山河的“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誓言一定能實現。
我愛我生 我敬我師
很多人注意到,當下的師生關系,常常陷入到缺乏活力的泥沼。不管是老師,還是學生,都喜歡站在對方的對立面去思考問題。學生處處“躲”老師,老師時時“抓”學生,雙方像捉迷藏一樣,此消彼長,互有攻防。
為了破解這一點,凌宗偉校長想到了一條妙計:在各班級開展“我愛我生 我敬我師”活動,通過雙方在課外的互通,增進感情,融洽關系,實現更好的學業定位和教育實現。
活動先從老師那端開始,具體規則為:請每位老師對本班的5至8名學生寫一句“愛的鼓勵”,而9門功課的老師就可以覆蓋到班上的每一個學生。他們會從德、智、體等多維度挖掘,告訴學生“你是一個靈氣的孩子”“你是一支優秀的‘潛力股”“你的耐心與細心讓老師印象深刻”。雖然很多學生又“皮”又“頑”,但在這個過程中,老師學會了欣賞、贊美和鼓勵,更學會了耐心、包容與接納,甚至看到了他們之前并沒有關注的世界,比如孩子的善良、淳樸和真誠——這個過程恰如羅丹所說,“生活中從不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美的眼睛”。而對每一個學生來說,老師溫暖的筆觸、中肯的話語、柔和的目光,都將是今后求學之路的慰藉和財富。當所有評價完成后,學校統一制作成版子并張貼在教室內,讓部分厭學、棄學者重拾信心,讓少數自傲自矜者得到警醒,也讓師生關系產生某種“靜悄悄的革命”。
一個月后,活動迎來第二步,即“權力逆轉”,表現為由學生給老師寫評語,比如“你的聲音真好聽”“你講題特別清楚”“你特別能凝聚我們”。學生對有些老師有偏見,但通過與別人的交流可以慢慢得到糾正;有些老師的確存在瑕疵,但在學生包容性的評價、鼓勵性的贊美之下,會產生自我拷問,促進職業進步和師德修煉。
學校在收齊評語后,一樣會制成展板,不過不是掛在教室中,而是附上教師的照片后,整整齊齊地擺放在櫥窗中,請所有的老師和學生共同觀摩。在這樣一個相互評價、相互體諒和相互鼓勵的氛圍中,每個人都在學習找到自己的位置,從原先妄自菲薄或妄自尊大的搖擺中確定參照系,也從不同寄語的對比中找出自己的奮斗目標和前行方向。
活動的最末尾,是師生共同設計一面象征團體精神的班旗,通常情況下,圖案會從學生中投票選出,而老師則主要負責修改和潤色加工。等學期結束時,再由師生共同簽名,以見證這一段共同度過的“光輝歲月”。
從“我愛我生 我敬我師”活動開展以來,已悄然積累下了五代旗幟,這其中的每一面旗,都在飽經滄桑的背后,譜寫著四五十個動人的故事;而慢慢地,它們成為了校本教材中的經典記憶,成為一代又一代傳承下去的最重要的理由。
尋找自我價值的實現
我們知道,不同的管理者、班主任,基于各自對教育理解的向度和深度的不同,以及對價值評定的種種殊異,他們會組織紛繁各異的班級活動。但不管是本文中提到的“小小聯合國”,還是“生涯規劃”和“師生互勉”,抑或是其他類型的活動,其中的一條核心原則是:尋找自我價值的實現途徑。
我們做的種種教育工作,首先需要確認的就是,讓學生(甚至是教師)在活動中重評自己,確認個人的“不可替代性”和“唯一性”,找到前行的希望和迎難而上的勇氣,找到實現人生的價值觀和方法論。在活動中,不斷地反觀內照,體味個人成長這個“小我”和社會萬象這個“大我”之間紛繁復雜的關系,用心在教育的田野中播種,勞作,和等待。
相對于在浮華的世界中迫不及待地宣布成績,我們,——連同我們的學生,可能更需要的僅僅是對自我價值的守望。
(作者單位:江蘇南通二甲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