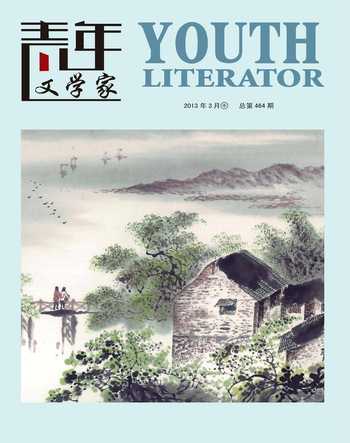結構與解構
摘 要:索緒爾的符號語言學促進了結構文學批評理論和后來的解構主義文學批評理論的產生和發展。但是前者側重以語言結構相似的文本內部結構為基礎,后者側重探討對文本的拆分和讀者的闡釋權,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文學批評理論的關系是辯證統一的,正如“孿生姐妹”一樣。
關鍵詞:符號語言學;結構主義;解構主義;辯證統一
作者簡介:趙娟,文學碩士,研究方向: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
[中圖分類號]:H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3)-8--02
一.結構主義文學批評理論與索緒爾符號語言學
任何社會活動的發生都有其哲學背景,結構主義文學批評理論的理論背景主要就是索緒爾語言學理論帶來的革命性范式轉換。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認為語言是一套符號系統,語言單位有兩重性,一重是作為能指(signifier)的聲音形象(sound image),一重是作為所指(signified)的概念(concept)。索緒爾認為符號的能指和所指之間的結合是任意的,無理據可言。換言之,語言是由任意性符號構成的。對索緒爾而言,語言系統是一系列聲音差別和概念差別的組合,也就是說語言是形式,不是物質。在證明“語言符號的任意性和語言是形式”這個觀點時,索緒爾舉了下邊的例子,“可以把語言比作一張紙,正面是思想,背面是聲音,正面和背面無法切開,因此在語言中也不能把聲音和思想分開,或把思想和聲音分開”。( Saussure,1966:66)
索緒爾還認為符號的意義完全取決于它與其他符號的關系,或者其在整個系統中的位置。一個符號的意義是由這個符號系統中符號之間存在的差異所決定的,并不是由該系統以外任何事物所決定(Saussure,1966:1.20)。這也就是說,語言其實是一個完全封閉的系統。
索緒爾以前普泛地講解語言的對象時,曾把它分為兩個方面,一種是作為系統、體制或規范的語言(langue),另一種是受制于前者,并使前者具體化的言語(parole)。為了人們能夠直觀地理解他的這個觀點,他又形象地把語言(langue)比喻為“象棋”的那套抽象的規則和慣例,而把言語(parole)比作真實世界中人們玩的一盤盤具體的象棋游戲。
其實,這兩個方面不僅存在于“象棋”中,在其他的游戲過程中也是一樣的。比如說我們玩撲克,玩撲克的游戲規則也獨立地存在每一次的具體的出牌過程之外。即先有撲克的游戲規則,然后才有游戲雙方根據這個規則的要求,在不違反規則的基礎上具體地考慮他們自己的出牌方式。在具體游戲時,一張張撲克牌的組合與拆分,則又使游戲規則得以具體地體現在具體的游戲中。在我們的生活中,語言也是如此,“語言的本質超出并支配著言語的每一種表現的本質。索緒爾的這一觀點表明,人的言語行為盡管千差萬別,但都有共同的內在結構-語言。”(朱立元,2005:229)
結構主義文學批評便受到這一“封閉的系統”的影響,幾乎所有的結構主義學者都繼承了索緒爾符號語言學的思想,其目的在于揭示文學結構同語言結構的相似性。強調符號的意義不取決于現實,也不由說話人的主管意圖所決定,因此作家和現實都應該被排除掉而不應作為闡釋作品的出發點。而索緒爾符號語言學中語言和言語的區分也成為了結構主義文學批評尋求文本內在結構的出發點。在該理論中,langue指代文學整體,包括文學規則體系以及具體作品構成的各要素。把“具體的敘事文本稱作“言語”,而把各種敘事共有的并蘊含其中的結構、規則系統稱為“語言”。這是巴爾特在《敘事結構分析導論》一文中的觀點。
語言構成了文學,而結構主義批評者卻把文學又視為語言。在他們的眼中,文學或其規律等同于langue,按照這個規律創作的作品則等同于parole。然后把語言學中能指和所指的關系作為自己理論推導的基礎,進而得出,一部文學作品在現實中沒有所指,它的所指存在于文學系統之中”的結論。結構主義批評理論把敘事文學作為驗證的該理論的對象,希望在自己的研究中能夠找尋到文學本身存在的深層次的結構。即,在所有作品中共同存在的、基本的敘事結構并用這個結構反過來解釋不同的敘事文學作品。
總之,索緒爾語言理論直接催生了結構主義。可以說,文學結構主義就是建立在索緒爾語言理論基礎上的文學批評方法。因此,可以說,“結構主義文論最基本的觀點之一就是把作品看成是一個獨立、完整、封閉而又自足的系統。作品的封閉性自然使結構主義的“文本分析”把包括作品產生的社會和歷史原因的考察以及創作主題等一切外部研究排斥在外,而僅把語言分析作為其研究的唯一內容。”(胡鐵生,2006)
二、解構主義文學批評理論與索緒爾符號語言學
解構主義興起于20世紀60年代末,盛行于70年代,主要領軍人物首先便從結構主義陣營退出,轉向解構主義的羅蘭·巴爾特和另一位解構主義大師雅克·德里達。
其中,德里達的文學批評理論是建立在對“邏各斯中心主義”和索緒爾語言學的批判的基礎之上的。德里達將西方自柏拉圖以來以聲音、言語來直接溝通思想而貶抑書寫文字的傳統,稱為“邏各斯中心主義”。(朱立元,2005:301)“邏各斯中心主義”認定意義在語言之先,語言與思維是同一的,在訴諸語言之前即存在一個明確的中心或意義,語言只是表達意義的一種工具。
索緒爾語言學同樣認為,語言符號的能指功能和所指功能是建立在聲音形象(sound image)與概念(concept)完全吻合的前提下的,兩者的統一使我們在沒說或沒寫前就存在了能指意義。但索緒爾同時也承認差異性原則,即符號的意義存在于與其他符號的差異之中。也就是說,只有當其他符號不在場的情況下,在場的符號才有了意義。但是索緒爾的這個論述卻存在著漏洞,這個漏洞首先被德里達發現并被其利用于自己的研究中。符號之間不能單獨存在,只有當它與其他符號組合存在時才會有意義,單獨的一個符號是沒有意義的。換句話說,當符號組合在一起時,彼此的差異才使它們具有了實在的意義。這也就是說,不論是能指還是所指,以及能指和所指的關系通通都被解構了。為了能更明確地說明自己的這一理論,德里達根據自己的理解獨創了“異延”、“播撒”、“蹤跡”、“補充”等重要概念,并以此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他理論的核心是“延異”這個概念,“延異”是個合成詞,由“遲延”和“分隔”組合而成。這也是為了說明詞義由兩方面決定,一是詞與詞之間的差別,一是詞與詞之間在應用過程中的組合。這兩方面中的任何一方面或兩方面的結合都可以創造新的詞并在原來意思的基礎上產生新的詞義。由此可見,詞義不是固定不變的,這樣看來“傳統形而上學企圖追求和獲得終極的意義”,就變成了不可能。德里達延異思想與傳統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基本等級秩序是彼此相反的:“差異先于同一; 缺席先于在場; 多樣先于單一;有限先于無限”。我們可以這樣說,德里達的解構主義在“延異”的基礎上不斷發展完善。這個理論不僅動搖了“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傳統地位,而且也促進了先前與此相關的哲學觀念、語言學觀念的進步和發展。
三.小結
結構主義者把索緒爾符號語言學應用于文學研究,認為文本的系統結構是單部作品意義的根據和來源,解構主義卻與此相反,雖然其關注的也是文本,但是它否定文本中心和作者權威,關注重點轉向對文學作品內在解構關注的同時,卻特別強調讀者參與與文本意義的創造過程。而解構主義的這一理論恰恰是利用了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的一個漏洞而創立的。索緒爾在其語言學理論中承認語言中存在無肯定項的差異。也就是說,他承認符號的意義在于與別的符號形成對立和差異,并在這種對立和差異中顯現出來,但一個符號可以與無數別的符號形成差異,因此符號的意義就在無效差異的對立關系中變動游移。符號意義的這種變動游移會對語言結構產生什么影響,索緒爾沒有進行徹底嚴密的闡述。解構主義者恰恰抓住了這一點,向結構主義發起了攻擊。解構主義者認為,在一部作品中,出現的符號上都留有未出現的符號的意義(即索緒爾所謂的縱組合方面的對立項)的印記(trace)而這種印記使出現的和未出現的符號都顯得若有若無,而且二者之間相互關聯,所以任何作品里的文本都和別的文本相互交織,與別的文本相互吸收和轉化,從而形成文學作品的“互文性”(intercontextuality)。所有的文本都是“互文”(intertext),而這種互文性決定了文學作品的意義是超出文本之外的和不斷游移的,因此文學作品并不是由一一對應的能指和所指構成,也投有一個固定的結構,而是更像一個成分相互流通的網.一個無中心的系統,并無終掇意義。這個網上的每個符號都相互對立又相互關聯,都在網上閃爍游移,而這種游動的符號最終凝聚到讀者的閱讀中。所以只有讀者才對作品擁有發言權。但讀者是千差萬捌的,所以他們的理解也不會統一,他們對作品的體會也不可能具有終極意義。這樣,解構主義者就完全否定了文學作品 “結構”存在的可能性。使結構主義的似乎明確的“結構”消失在符號的游戲之中,使文學批評運動轉入了解構主義的浪潮。由此可看出,解構主義是建立在索緒爾符號語言學原作中的一些理論縫隙和弱點之上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索緒爾符號語言學同樣對解構主義的產生了重要影響,可以說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是符號語言學共時性角度上的孿生姐妹。解構主義對結構主義文學批評理論的核心內容既有保留又有取舍,正是這種革命性的變革,使兩者具有了辯證統一的關系。
參考文獻:
1. 羅蘭·巴爾特. 敘事作品結構分析導論【A】張裕和譯.符號學美學【C】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
2. 朱立元.當代西方文藝理論【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3. 胡壯麟等. 語言學教程 【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7
4. 胡鐵生. 結構與解構-基于文本的悖論與統一 【A】 東北師大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