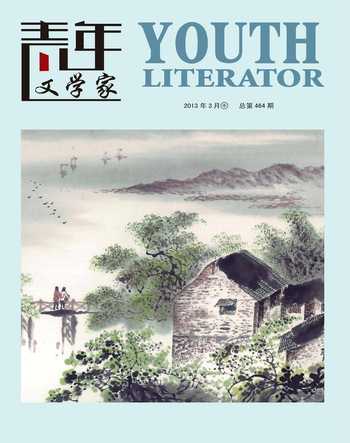駱家輝的“Soft Power”
摘 要:文化外交是近年國際關系研究中極受關注的一個主題,也是傳播學跨文化傳播領域一個新的熱點。但在文化外交的實踐領域,中國政府卻少有出彩之作。反倒是一個美籍華人的到來,讓我們領會到了所謂“Soft Power”的威力。文化外交到底應該怎樣做?“國際傳播”傳播什么才能令人接受和信服?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一個人的言行,就將其所代表的價值觀和理念詮釋得淋漓盡致。當然他也帶來爭論和異議,但正是這些爭議及由此而來的討論,使得其理念和價值觀的傳播更為深遠。
關鍵詞:Soft Power;文化外交;駱家輝;多樣性;普世價值
作者簡介:何慶平,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傳播學碩士研究生。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3)-8--02
進入新世紀,提升文化“軟實力”逐漸成為國際關系領域的新趨勢,文化外交逐漸被各主權國家置于越來越重要的地位。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指的是以文化傳播、交流與溝通為內容所展開的外交。一種解釋是“主權國家以維護本國文化利益及實現對外文化戰略目標為目的,在一定的對外文化政策指導下,借助文化手段來進行的外交活動”。[1]近年來,在政府的推動下中國大陸關于文化外交的研究成果層出不窮,但除了孔子學院開始遍布世界各地外(效果待驗證),政府文化外交實踐中的亮點乏善可陳。花巨資打造的國家形象系列宣傳片似乎外國人并不都買賬。國家形象是宣傳出來的嚒?文化外交應該傳播什么內容?也許我們可以從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的表現中獲得有益借鑒。
一、官媒PK駱家輝
自從2010年8月背著大包小包,全家五口降落在首都機場以來,駱家輝不斷成為新聞話題人物。他的每一次在國人看來與其身份極不相稱的行為都引發媒體及網民的關注與討論,尤其是在微博等新媒體平臺上。針對駱家輝的種種表現,光明網、《環球時報》等官媒先后發表批評性評論,指責駱家輝“給中國官員們上課絕不是駱家輝的目的,為美國收攬贏得中國的民心強化中國民眾崇洋媚外的奴性…借以分化中國斷裂甚至碎裂的意識形態才是這位華裔大使的如意算盤。”[2]“他似乎很享受自己在中國輿論中的‘廉潔秀,盡管他最清楚,他并沒有中國互聯網上宣傳的那么‘樸素。”[3]
2012年5月4日,由于在山東臨沂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出逃美國大使館一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駱家輝及美國大使館受到北京市委宣傳部下轄四家紙媒(《北京日報》、《北京青年報》、《京華時報》、《新京報》)以評論形式的點名批評。其中以《北京日報》發表的《從陳光誠事件看美國政客的拙劣表演》言辭最為激烈。“一段時間以來…新任駐華大使駱家輝的種種行為與其自身職責頗為不符,‘小動作不斷…從乘飛機坐經濟艙、自己背包、拿優惠券買咖啡的‘平民生活秀…再到膽大妄為地以非正常方式將陳光誠帶入使館——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主動攪起矛盾漩渦的標準美國政客”。[4]其他三家報紙亦口徑一致加以批判,京城媒體如此高度統一的同仇敵愾幾乎前所未見,有關部門刻意為之的痕跡十分明顯。
二、駱家輝的“Soft power”與文化外交
駱家輝何以令中國網民如此之關注?又何以令一些官媒尤其是黨報如此之不滿?筆者認為,實質在于他種種行為所體現出的一種“Soft Power”。“Soft Power”這個詞由美國著名國際政治學者約瑟夫·奈在上世紀90年代初提出。李智教授在其著作《文化外交——一種傳播學的解讀》中將“Soft Power”譯為“軟權力”,認為“作為吸引力和同化力的軟權力靠的是示范(demonstration)和勸服(persuasiveness),訴諸人心,包括人的心理、思想、情感和意志,達到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以意(志)化人”。毫無疑問,駱家輝深諳此道。他作為美國政府的部長級官員,出行不坐頭等艙、不住五星級酒店,甚至想拿優惠券買咖啡,讓那些習慣了警車開道、前呼后擁、公款吃喝的“人民公仆”們汗顏不已,擊中了中國官員群體的軟肋,也讓國內普通民眾對美國政府官員的廉潔奉公有了直觀的認識。
駱家輝如此搶鏡,肯定有人不高興,“作秀”的批評甚至陰謀論隨之而來。以其外交官的身份,我們難以否認駱家輝張揚美國式的務實民主、珍惜納稅人錢財,可能有“作秀”成分。但即便如此,能做到一以貫之,則說明他的手腕嫻熟,擅長以小博大,這就是他的“Soft Power”。在媒介多元化時代,政治傳播與“作秀”也屬于市場自由競爭,誰的“秀”更有說服力,要各憑本事。《中國青年報》就曾中肯評論,“指責駱家輝的所作所為‘別有用心,大可不必。一個國家的駐外使節,當然會努力展示本國的正面形象。不管他是有意還是無意,只要他的做法合乎法律和社會道德,能給我們有益的啟示,我們不但沒必要排斥,相反還應該借鑒。對駱家輝所展示的樸素品質感到糾結甚至百般指責,是內心極為脆弱的人才會做出的事。”[5]
三、文化外交的內核:多樣性與普世價值
李智教授認為,將“Soft Power”譯成“軟權力”抑或“軟實力”,其意義有著本質區別。應當把“行為力”意義上的“Soft Power”譯為“軟權力”,亦即上文所述駱家輝的行為產生的力量;而把基于“資源力”意義上的“Soft Power”譯為“軟實力”。軟實力的唯一構成要素是文化,文化軟實力的實現就是文化的權力化過程。[6]
一國文化只有在國際社會廣為傳播并得到普遍認同后才能成為一種軟權力。[7]而這種所謂的權力化過程就是獲得目標對象國民眾的理解接受并使其產生情感和價值觀上的共鳴,進而對其行為產生影響。很多研究都提出了我國文化外交的可行模式,比如加強對外人際傳播的跨國文化交流(如正在推行的孔子學院和“中X文化年”模式),比如強化對外國際大眾傳播(如我們重金打造的國家形象宣傳片)等等。筆者以為,以何種方式去開展文化外交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問題在于這種文化外交的文化內核是什么?筆者以為,是兩個關鍵詞:多樣性與普世價值。
當今世界是個多元化的世界,多元化的國家民族,多元化的傳統文化,多元化的宗教信仰,多元化的社會制度。與多元化的世界對話,需要多元化的視角。時至今日,一個國家在文化外交中若仍以意識形態來定義自己和界定別人,其在國際上必然不會有真正的朋友,也很難取得他國的信任,一如我們的鄰邦朝鮮。承認并尊重多樣性文化,特別重要一點就是破除中西方二元對立的思維,尤其是政府主管對外傳播的部門必須認清這一點。以意識形態區分敵友的“冷戰”時代早已一去不復返,現在的中國有著全世界最多的人口,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正在自由開放市場的路上蹣跚邁進(雖然舉步維艱),“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年代早已過去,意識形態宣傳早已過時。
關于普世價值,是個議論很久也頗具爭議的話題。普世價值以自由民主為核心,涵蓋的關鍵詞包括:民主,自由,法制,人權等。很多人反對這個詞的理由就是這個詞源于歐美國家,代表“資本主義價值觀”,是西方國家用來滲透、分化、瓦解我們的工具,是文化侵略和文化殖民。但筆者以為,普世價值之所以普世,就表明它不僅代表歐美國家民眾的價值觀,它同樣適合于中國,適合于所有亞非拉國家,適合全世界每一個國家每一個人。所謂普世,意即作為一個正常的個體(無論其國家、民族、語言等有多么不同)都會接受并認同、踐行的價值觀,因為它是對人本身的關懷。我們只要思考下民主、法制、自由等對于個體的生存與發展是否重要,就可以明白普世價值對我們的意義。
四、駱家輝的啟示
我們的文化外交更多強調的是宣傳,意在傳播國家形象的廣告片也被命名為“國家形象宣傳片”。“宣傳”這個在歐美國家頗為禁忌的詞,在中國被毫無顧忌地在各個領域廣泛使用,包括對外傳播的內容。僅此一點,也可能會令外人敬而遠之。
再回到駱家輝身上來。網上流傳過一張圖片,作者將駱家輝的頭像PS到一名跪地犯人身上,只見他低垂著頭,像文革被批斗對象般跪在地上,脖子上套了大牌子,牌子上“駱家輝”三字被打了大大的“叉”,另有三行字列數他的罪狀:“坐經濟艙”、“自己背包”、“拿優惠券買咖啡”。作者將圖片題為《美國政客的拙劣表演》,還附上一句斬釘截鐵的警告——“貪污腐敗才是駱家輝大使的唯一出路”。這代表了普通民眾對國內政府官員貪污腐敗的一種反諷,而對比的對象就是駱家輝。試想,一個政府官員出國交流訪問,騎著自行車出行,坐著經濟艙,與民眾深入交流,這本應該是很正常的表現。在中國,卻成為刺激民眾質疑政府貪污腐敗的導火索。由此透視出,一些官媒黨報所奉行的價值觀是與普通民眾的價值觀是相脫離的,與普世價值更是相背離的。
中國的民智在開啟,公民權利意識日益覺醒,民間論政氛圍日漸濃厚,但是官方的回應手法與對外傳播方式卻沒有多大進步。在外交領域,我國外交在世界上聲音微弱,我們所“宣傳”的東西不曾撼動西方,而美國一位外交官卻能攪動中國輿論。其中深奧,除了美國文化外交的嫻熟外,更顯示我國文化外交的貧瘠。中美文化外交上的差異,體現的是文化內核的差異,一個在尊重多樣性基礎上踐行普世價值,而另一個依然緊守著意識形態宣傳不放,說著別人聽不懂的話。
注釋:
[1]、李智:《文化外交——一種傳播學的解讀》,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1月,第24-25頁。
[2]、光明網:警惕駱家輝帶來的美國“新殖民主義”,http://opinion.huanqiu.com/roll/2011-08/1913897.html
[3]、環球時報:希望駱家輝好好做“駐華大使”,http://finance.huanqiu.com/data/2011-09/2026319.html
[4]、北京日報:從陳光誠事件看美國政客的拙劣表演,http://opinion.people.com.cn/GB/17807571.html
[5]、中國青年報:做好自己何必糾結駱家輝,http://zqb.cyol.com/html/2011-09/28/nw.D110000zgqnb_20110928_5-01.htm
[6]、李智:“軟實力的實現與中國對外傳播戰略”,《現代國際關系》,2008年第7期,第57頁。
[7]、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