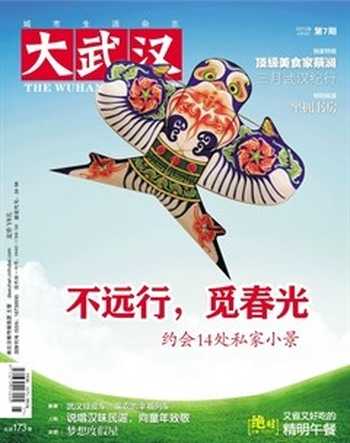王慶云:書法不只創作詩詞歌賦,源于實用
劉莉
【名片】
1929年生,荊州監利人,字木山。現居北京。現任民革中央畫院理事、中央統戰部臺灣會館書畫館館員/顧問、文史研究館館員、中華中山文化交流協會理事、八一書畫院顧問、中國林業書協副主席、湖北省文史研究館館員、湖北書畫院院士。
他玩微博,穿VANS,84歲高齡覓得美籍新銳攝影師,為他的展覽圖錄拍照。他叫王慶云,這個老頭有點潮。
他出身名門,一生為家族光環所籠罩。父親王遐舉被京城書畫界以“書壇八仙”及“五大名筆”稱許,叔父王軼猛在臺灣被尊為“商場書圣”、“獨門之王”。
高山之上,王慶云再做創舉,他用筆以中鋒貫穿全篇,以側鋒協調其間。既沉著,又痛快,筆飛墨走處一瀉千里、濤拍岸裂。
12年前,“荊楚第一隸”移居京城。人未到,京城書畫圈子已一片沸騰。原來民間書畫市場早有人模仿王慶云的筆跡,在市場中賣得高價。聽完這個段子,王慶云一笑而過,書法于他,從不是簡單的詩詞歌賦,早已深深寫進骨子里。
童子功,家學奠基
王慶云的童年隨父親在湖南度過,在采訪現場聊得興起,他站起身來,引吭高歌一支湖南民歌。
5歲時,他在父親條案前研墨牽紙。父親寫個通宵,轉頭想起小兒,卻見他雙目炯炯,毫無倦意。父親心中暗喜,隨即為他挑選顏真卿的《勤禮碑》作為臨習的第一種字帖。顏字遒勁中有飛逸,雄沉中寓舒和,王慶云一練就是十來年。
技藝是前提,歲月沉淀,筆下寫的盡是人生智慧。在抗戰年代,王慶云隨一家人流亡大西南桂、黔等地。路途遙遠,人心惶恐,王家人卻不忘吟詩寫字。少年王慶云更是將背帖作為怡情之事,停下步子,他揀根枝條,在地上練習運筆。愁腸百結的眾人面孔中,王家人的表情,因筆墨滋養,生動而從容。
1947年,父親王遐舉在武漢舉行書畫展,叔父王軼猛趕來協助,王慶云從紙中探出頭來,首次學做“策展”。掛滿了父親書畫作品的中山大道是青年王慶云心中不可逾越的文化豐碑。
40年后,在廣水工作的王慶云第一次在武漢做個展,選的是湖北建筑展覽館(中南路附近)。他結合自己的職業特點,拖來一整車花草,將書法作品和植物完美交融,這場別致的策劃被武漢藝術圈傳為一段佳話。
隸書創新,不忘傳統
練習書法15年后,受家學淵源導引,王慶云的興趣自然轉向隸書。他對兩漢時期血肉俱具、豐神皆異的書法藝術尤為神往,以學《張遷碑》為主,兼學《乙瑛碑》、《曹全碑》。
他不如父親幸運,書法始終未能成為他的終身職業。然而愈是這樣,愈加讓王慶云珍惜業余時間。他受《蘭亭序》影響,且于《集王字圣教序》用功尤勤,書法古樸儒雅。
有人建議他盡快擺脫他父親的風格,王慶云心知肚明,要與眾不同,與古不同,但“根脈不能丟”,逐漸形成研潤雅潔的個性。
精練過篆、隸、正、行、草五體的王慶云,以隸書見長,他以隸體為基調,又吸收魏碑的挺勁,篆書的古雅,行書的流利,讓整個作品更加生動而耐看。有人這樣評價兩代人的書法特點:“若仔細品評,會感到遐翁之書深沉凝煉,結體茂密雄強,以質勝;慶云書則清致透逸,結體蕭散淡然,以雅行,其瀟灑倜儻、天真爛漫處似有青出于藍而‘別于藍之妙,堪稱既區別于前賢與他人,也區別于故我的別開生面的全新完美之作。 ”
他不僅沉迷于書法,還在三年前在政協會議上提議在小學重開書法課。“我讀書時有大字、小字課,紅線劃出的八個格子,讓我今天能寫一筆好字。”
2011年,在武漢舉行的王遐舉、王軼猛、王慶云書法展用200幅精選作品將同門三王團聚在一起,扉頁兄弟父子三人的黑白合照在講述著王家早年總結的研習書法的道理,“專供一家,兼蓄百家,自成一家。”
要先寫中國字,再談書法
(以下D代表《大武漢》,W代表王慶云。)
D:你出生在這樣一個家族,其實像很多名人之后一樣,有時也會為光環所累。有人拼其一生,也難超越前人。你怎么看?
W:每個人都在超越古人,父親也一樣,他的隸書和行書別具一格。我為了避免與父親的字完全一樣,想了很多辦法。傳統的書法是左邊輕,右邊重,我反其道而行之。我的一筆一劃粗細分得很開,粗筆與細筆相差8-10倍,但效果很和諧。無論如何,我寫的還是傳統楷書。創新要作有源之水,要有底線,現在有人寫反字,那已經不是中國字了,何談書法。
D:書法已經成為追隨傳統的一部分,對于一個初學者,你有什么告誡?
W:啟蒙時一定要臨古代的碑帖,現代人的絕不可取。因為中國的古代碑帖經過千年考驗,大浪淘沙后得到歷代書家認可。至于學習哪本帖,要看個人愛好,選定一本帖后堅持寫下去。不要一開始就學怪帖,待到你形成個人氣候以后再出新。
D:據說你搬去北京前就有人模仿你的筆跡做買賣,你介意嗎?
W:不介意。因為我至今不參與市場,但這不代表我不了解市場。我觀察過很多場拍賣會,牌子舉起時,好戲就開演了,我不想成為其中的一個演員。書畫收藏這個市場正在中國形成并壯大,本身是件好事,如果能逐漸形成良性秩序,更加好。
D:你的叔父在臺灣這么多年,你對臺灣的書法創作了解嗎?
W:臺灣的文化傳統保留的更好,書法的運作機制也更加健康。盡管吳作人很多年前就建議廢除書協和美協,但目前來看,難度不是一點點。臺灣沒有書法類的官方機構,寫書法的人要謀生,這反而會督促他們出好作品。沒有官方機構,也就沒有所謂的這主席,那主席,藝術更加純粹,免得亂七八糟的附加值。
D:如果要對書法下一個定義?你會怎么說?
W:老子曾講過一句非常出名的話:道可道,非常道。如果真要加以簡單明了的說明,我認為:書法不一定就是要創作詩詞歌賦,書法源于實用,在實用的基礎上,不管是詩詞,借據,契約,信札;其章法結構文筆都寫得很好,加之字(書法)上升到一定的水準就可成為一種藝術品。它就是書法。
D:書法的實用性隨著電子產品的日益普及,特別是觸屏的發明,正在被人們淡忘。書法會消失嗎?
W:除了實用,書法還是一本藝術,因而它永遠不會消失。3年前我在政協會議上提議恢復小學生的書法課,現在已經開課了,這都是在延續中國的根。我的朋友中現在有很多80后,他們學茶道、打太極、聊儒家思想以及學習書法。有人說這是時尚風潮,我覺得是文化回歸。
D:書法和水墨從古至今都是一種社交手段,你在意自己在公共場合的創作嗎?
W:以前我們辦筆會,我不應酬。現在更不會應酬,因為每幅字都代表著你的水平。你不滿意的,就不要拿出去。一旦拿出去,那就是留給別人的印象。有人三刷子就是一個字,我想那是對自己的不負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