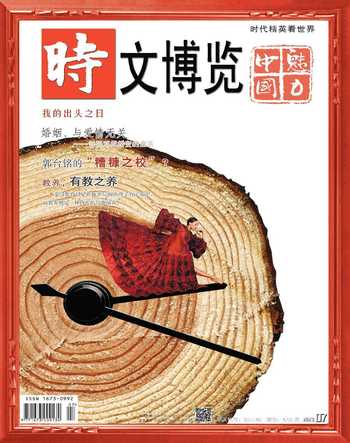最好的告別
阿花
紐約冷到零下12度那天,我們有事必須出門。回到家的時(shí)候,感覺全身都冷脆了,好像戳一下就會(huì)粉碎。晚飯我煮了一鍋滾燙的青菜湯,終于讓自己恢復(fù)了全身的知覺,之后開始舒舒服服地刷微博。然后,我就看到我認(rèn)識(shí)的鄧正來老師去世的消息。
一個(gè)月前我們聽說他胃癌晚期的消息。一天前我們收到一個(gè)朋友的郵件,說才去上海看了病中的他。中午出門前,我一邊吃自制的麻辣牛肉面一邊跟老公說:等晚上回來,你給他打個(gè)電話吧,或者給他女兒打也行,問一下情況。等到我們晚上回來,他已經(jīng)去了。那種冷脆了的感覺又回來了,不過是在心里。
死亡是這樣的猝不及防。靈魂升到半空回望肉身的時(shí)候,一定會(huì)覺得這不過是一個(gè)拙劣的玩笑吧,但是玩笑就這樣被死亡凝固于永恒。
我想起了爺爺去世的那天晚上。晚飯時(shí),他跟兩個(gè)兒子喝了二兩高粱酒,鎮(zhèn)上自己釀的那種,似乎是1塊6一斤。就著20瓦的臺(tái)燈,他小心翼翼地吃了兩條刺很多的鯽魚。一直到我們走時(shí),他還在小心地剔著魚刺,奮力把最后一點(diǎn)魚肉吃干凈。半夜我們接到電話,說他去世了。爸爸不相信,讓我和媽媽繼續(xù)睡覺,他去看看就回來。
十幾個(gè)小時(shí)后,我見到了爺爺?shù)氖w,遠(yuǎn)遠(yuǎn)地?cái)R在一張木板床上,邊上放著一盞盛在粗海碗里的油燈。我的工作就是過一段時(shí)間給油燈加點(diǎn)清油。我遠(yuǎn)遠(yuǎn)地看著他,慶幸自己高度近視,一切都模模糊糊。他的臉看上去和在昏黃的燈下吃鯽魚時(shí)并無兩樣。道士們來作法事,有人指揮大家在某個(gè)時(shí)間點(diǎn)上整齊劃一地哭。我無論如何哭不出來,覺得面前的這一切太虛假滑稽。只有油燈噼里啪啦爆出的火花,還能帶來一點(diǎn)真實(shí)感。
如果死亡可以是一種選擇,毫無疑問這將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會(huì)做出怎樣的決定,是希望死之前兩個(gè)小時(shí)還在吃一條巴掌大的鯽魚,還是和親人們告別再告別?楊絳在《我們仨》里寫道,她一次次把錢鐘書送去更遠(yuǎn)的驛站。“送一程,說一聲再見,又能見到一面。離別拉得長(zhǎng),是增加痛苦還是減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得愈遠(yuǎn),愈怕從此不見。”
在丈夫和女兒先后去世之后,楊絳翻譯了《斐多》。柏拉圖在這本書里討論了死亡和靈魂,他說蘇格拉底臨死前相信,人死后會(huì)得到更大的幸福。我相信楊絳是為離開的丈夫和女兒翻譯的這本書。像《我們仨》里寫的,他們還將重聚。她或許不能逃避至愛的死亡,但她能為自己死前的人生,做出最好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