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蒼白倒流
謝康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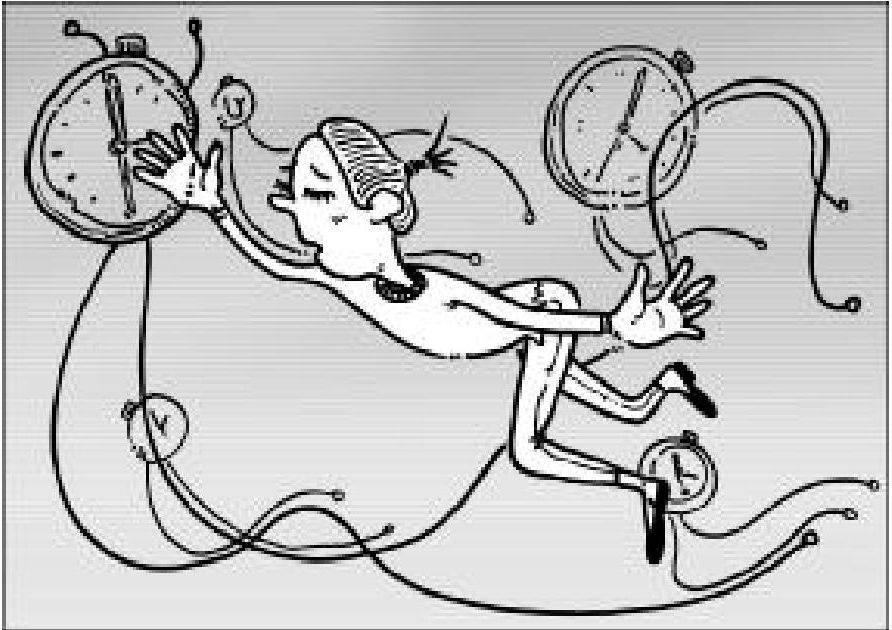
上周的晚自習(xí),同桌突然收到傳來的一張紙條,看完便兀自出神。半晌,拿著紙條說:“剛才她給我紙條,說:‘高二剛分班的時候,你坐在這一組的最后一排,扎著這樣的頭發(fā),這樣的一身衣服,這樣的姿勢。兩年過去了,我什么都沒有干。”
當(dāng)時我們都有些感傷,想真?zhèn)€人生如夢,所謂兩年也似須臾一般。
幻覺總是來得太及時,來得洶涌澎湃,不須片刻便將人拍在回憶里。通常最為蒼白的語言,卻又總能讓人被它獨特的畫面感擊得脫魂一般,然后這些時光便如同幻燈一樣一幕幕從腦海里閃過,似乎又重返過去,而肉體卻還被束縛在這個時空。倒流也變成徒勞的蒼白。
青年節(jié)上午的畢業(yè)照,整個年級1700多人被安排站在一個環(huán)形的階梯上照畢業(yè)照,五月陽光并不是最盛的時候,只是人與人之間貼合的緊密程度,估計連下午6點的公交都應(yīng)自愧不如了,摩肩挨背,人與人之間盡是籠著一層濕熱的氣。這個傳說中將長達(dá)兩米的畢業(yè)照照完之后,整個廣場便是四處拍照的人,似乎我們就要這樣畢業(yè)了一樣。有人在階梯邊模仿泰坦尼克號的場景,有人模仿《那些年》的海報。兩手空空沒帶裝備的我站在一邊看這一片熱鬧的場景,倒有些局外人的感覺了。
我們很少會這么整齊地穿著校服,在我記憶里,似乎只有去年的校慶能夠達(dá)到這個規(guī)模。那次校慶結(jié)束后我和朋友去附近吃飯,之后她和另外一個同學(xué)便出國了。人生處處是長亭。又想起有同學(xué)曾不無傷感地說道:人人都有路,就我沒有。那時正是出國的小高峰,各班出國的人都有好幾個,之后保送的保送,藝考的藝考,眾多座位的主人人間蒸發(fā)。剩下的人繼續(xù)在高考壓力里掙扎,一面掙扎一面羨慕那些看似已經(jīng)上岸的人。雖知“回頭是岸”,可岸也并非人人能上,總讓還在海里竭力掙扎的人感覺前途難卜。原諒我也不解周易亦不懂星術(shù)。剩下的,只有像自殺一般的掙扎喘息。
下午是成人禮暨畢業(yè)典禮,播放了一個我們這屆的短片之后便是各派人物上臺講話,從去年的清華學(xué)姐到家長代表,之后便是各式表彰,花去大概兩個小時的時間,才是一個個的穿過“成人門”的環(huán)節(jié),算是象征著我們正式成年。有的班全班手拉著手穿過去,有的好幾個人抬著一個人穿過去。若是成年真簡單得只是穿過這道門,那倒也好。只是伴隨著“成年”一詞的相應(yīng)的責(zé)任,總不是這么輕松便能承擔(dān)和習(xí)慣的。或許正是因為這樣,我在過去的十七年里,總是故作瀟灑地覺得,總應(yīng)趁未成年時將所有瘋狂的事情做盡最好。于是當(dāng)成年之后,當(dāng)老了的時候,提及這么一段“犯二”的時光和這些傻事的時候,還能很輕松地說一句:“年少無知嘛!”而不是后悔這么一生全無波瀾地度過,講的是別人的故事。或許同樣抱有這種想法的人遠(yuǎn)遠(yuǎn)比我想象的多,于是我時常聽說周圍的人,有人離家出走想自己打拼,有人騎車去拉薩,有人似乎前程似錦,有人似乎做著專屬青春期的無聊的傻事,有人像英雄,有人像夢想家。然前路艱險,諸君還需自行小心。
回憶最似溫柔一劍,刺得有人垂下眼眸,輕顫了睫毛;有人目光放空,心思去了遙遠(yuǎn)的地方。我們總各自規(guī)劃未來,又各自陷入沉默,時光又似回去某個地方,容你再做選擇。
編輯/姚 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