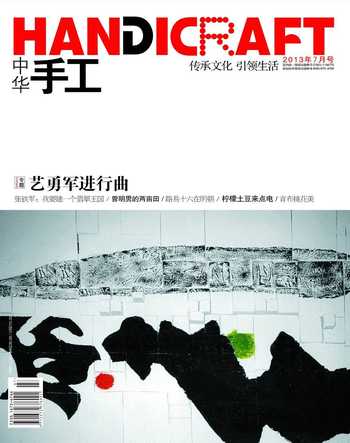葵娃快長大
孫凝異
“我叫葵娃,來自濱海僑鄉江門新會。我的母親是古老的新會葵藝,父親是現代文明,我是他倆引以為傲的結晶……”當公益視頻徐徐閃現時,所有人都被小女孩稚氣的聲音吸引。
長在廣東江門市新會區的葵樹葉闊嬌嫩、光澤柔韌、蒂正骨直,是其他地方所不及,因此,“一柄蒲葵養活千年新會人”的說法流傳已久。那時的新會,滿山遍野長著葵樹,每個山頭鋪滿葵葉,叫做曬葵。這里有三百多家葵藝廠,十多萬人從事葵業,光葵扇的銷售量每年就有1.2億柄。
但如此繁盛的景象已停留在幾十年前。
當家家戶戶都擁有電風扇、空調等科技產品時,我們已很難在悶熱的夏季見到人們手握葵扇一搖一扇的景象了,小時候的記憶也被風越吹越遠。有人難舍其情,于是年紀輕輕拾起千年技藝,執著地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使新會葵藝重新煥發生機,他們就是“葵娃”。
四小天王
“對,我是葵娃……”當廣東外語外貿大學Sife團隊聽到電話里傳來的話語,禁不住激動起來:“謝天謝地,終于找到你們了。”
在葵藝工作室,余惠云走到一個安靜的角落,拿起烙畫筆開始在葵扇上作畫。另一端,何六妹和梁敏華正專心致志地編織。
從2009年正式接觸這門手藝算起,何六妹練習葵藝制作已有4年光景,但家人最開始并不同意她學習葵藝,“半年后我把自己親手制作的葵扇帶回家,爸媽都覺得很欣慰,他們開始認同做葵藝是一件有意義的事。”六妹的聲音稚氣未脫,手中卻嫻熟地將葵葉左右穿插。與這三位女孩不同的是,黃衛明是個大男孩,他不但會做葵扇,還負責葵藝活動的組織、宣傳。
這4人,是新會高級技校葵藝班的學生,全國唯一的葵藝班,入校時班里有30人,臨近畢業,僅剩下五六人。這4個技藝突出、活躍一點的孩子便成立了“葵娃”項目,他們去全國參加傳統文化展示活動,稚嫩的臉龐與長滿老繭的雙手令20歲不到的他們成為焦點,活動舉辦幾天,就手拿烙畫筆幾天,一絲不茍地在扇面上不停地繪,“都沒有時間到外面去看看。”當然,他們是沒有酬勞的,只希望憑借90后的熱情讓葵藝發揚光大,“走出中國”是他們常掛在嘴邊的話。
眾人拾柴齊創新
因為新會葵藝加工工藝保守,花式品種單一,Sife團隊特地找來設計師對葵扇進行創新設計,致力于公平貿易的LAININ(聆音)手工坊便接過了Sife團隊的接力棒。設計師Reachle特地前往新會,并在葵藝班待了一天。
“大片的葵林幾乎消失殆盡,與網絡上蒼翠一片的景象大相徑庭,葵藝廠一家沒剩,只有少數作坊在做葵扇,粗制濫造,偶爾見葵扇、葵籃、葵帽、葵席等零星地出現在街巷盡頭,根本無法將其與‘精美工藝、文化遺產等字眼聯系起來,現在最集中制作和展示葵藝的只有‘葵博園了。”Reachle很是灰心,而且呈現眼前的僅有兩種葵扇,白坯扇與當地人引以為傲卻并不與時俱進的“火畫扇(烙畫)”。
經過考察,Reachle開始在扇面上貼上幾塊碎布料成花朵或孔雀等圖案,建議六妹多采用雙織而非單織方法編織葵扇,“葵扇立馬活了起來。”經過幾年專業學習的六妹也是第一次見到如此造型,很是興奮。有了少量作品,Reachle便把葵扇帶到外賣廟會、創意市集等活動現場,向眾人推介新會葵藝。得知Reachle與葵娃的故事,市集活動上的好些布藝商家主動把一些邊角料送給她,消息傳開了,甚至還有外地網友向她捐贈布料。
步步為營
“設計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我們也在探索葵扇最合適的形態。”Reachle不希望葵扇一直在模仿過去,但創新又不能失去對文化的傳承,于是從繪畫、貼布,發展到皮藝與葵扇結合,現在又推出大紅色鉤花系列,金色丙烯涂染的材質碰撞,愈發簡潔而優雅、實用。
盡管葵娃手藝精湛,但他們不懂經營,聆音手工坊主動承擔起微博與淘寶營銷,“我們預計接受200~500把葵扇的銷量,現在第一批就售出60把。”盡管一些葵扇能以低價在市場購買,Reachle始終不愿意放棄向葵藝班采購的渠道,希望盡一份微薄之力,盡量促成葵藝班有資金購買產品制作所需的原材料,更新老化的工具設備,吸引更多的孩子加入葵藝班。
但“四小天王”的情形已在今年1月份劃上句號,臨近找工作時,就只剩下何六妹與余惠云兩人愿意從事葵藝事業了,運營一年多的“新會葵藝公益項目”微博也因時間有限暫停更新了。
“因為資金有限,我們4個葵娃約定先工作幾年后有了經濟基礎,大家再聚在一起開工作室。”六妹憧憬著美好的未來,現在的她,正準備去新會葵藝傳承人魏寧的工作室深造傳統編織技藝,希望幾年學成之后再與Reachle的設計珠聯璧合,讓新會葵藝以新面貌示人。 “他們說我是kuíshǒu,哎,這是當地方言,不知怎么表達。”Reachle不好意思地笑了。我想,何不索性將此理解為“葵藝推手”的簡稱呢?
盡管有著1600年歷史的新會葵藝日益蕭條,但它應該欣慰,因為它的種子已在一群年輕人心中生根發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