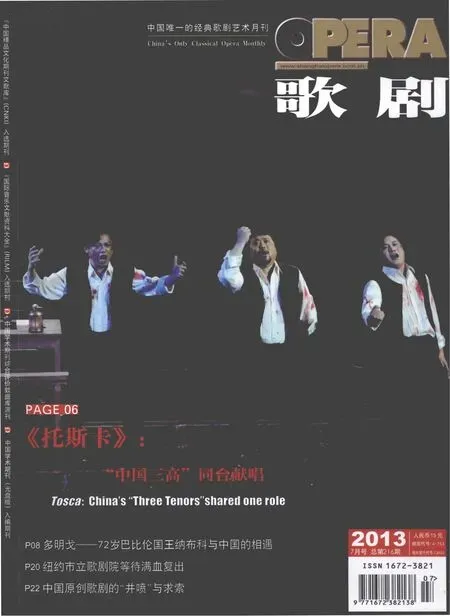每一部作品都是一次生命的排練
趙楊



75年前,1938年的一個晚上,一個11歲的小男孩偶然間聽到了貝多芬的《第八交響曲》,便暗下決心:長大后,一定要當一名指揮家。
當他生命中的第30個年頭到來時,他終于如愿以償。然而,幾十年過去后,他卻毫不掩飾地公開表示:“我曾想成為一個音樂家和一個指揮家,這是我做過的最不理性的決定。”說這句話的人,就是英國指揮家科林·戴維斯(Colin Davis)。倫敦時間2013年4月14日一個普通的周日,85歲的科林·戴維斯因此前的短期微恙而突然離世。此前,他還正準備著在2013年6月16日即將上演的音樂會上登臺指揮。可是,他再也等不到這一天的到來。
大師之路始于業余
1927年9月25日,科林·戴維斯出生于英國倫敦西南部的薩里郡的韋布里奇(Weybridge)。他有6個兄弟姐妹,在了個孩子中,他排行第五。他的父親是一個普通的銀行職員,但并不富裕。他的家庭經濟狀況由于其父曾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服兵役而受到影響,甚至在后來的經濟大蕭條時期還一度陷入了負債的危機。他的父親雷金納爾德擔負著家中幾乎所有的開銷,生活艱苦,科林·戴維斯說他的父親“是一個可憐的人”,雖然辛苦工作,但是家境依然困窘。那段艱難歲月給科林·戴維斯的回憶無比深刻,他說:“我們沒有電所有調皮的孩子們都在煤火前的一個鍍鋅槽里跳進跳出。除了發生火災,你幾乎看不到任何的光線。”
雖然家里沒有鋼琴或者一件像樣的樂器,但是,他的父親有一個留聲機,并收藏有少量的古典音樂唱片,這讓科林·戴維斯為之著迷。在很小的年紀,他就顯示出了和一般孩子的不同之處,在同齡的孩子們打鬧玩耍的年紀,他卻在津津有味地聆聽起那些黑膠唱片,這也成了他童年時代唯一接受古典音樂熏陶的機會。在他11歲時的那個晚上,他從父親的留聲機里轉動著的78轉老式唱片里,聽到了貝多芬的《第八交響曲》。他說:“這是一個啟示,我從未如此聚精會神地傾聽上一個半小時。”
后來,科林·戴維斯的叔叔幫助他在西薩塞克斯的基督慈善學校謀求到一個名額。在那兒,雖然他的老師希望他能夠拿到生物或者是化學的理科學位,但是,科林·戴維斯卻在同學的鼓勵下,學起了單簧管演奏。由于貧窮的出身,他經常受人欺負。一次,他在家里練習單簧管時,鄰居扔進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閉嘴!”。
在科林·戴維斯16歲時,他因獲得了倫敦皇家音樂學院的獎學金而獲準進入該院,師從著名單簧管演奏家弗雷德里克·薩斯頓(Frederick Thurston,1901~1953)。雖然學習的是單簧管演奏,但是,科林·戴維斯卻從來沒想過要在這個方面取得多大的成就。再者,后來成為單簧管演奏大師的,他的同學格瓦斯·德·佩耶(Gervase de Peyer,1926~)單簧管演奏的水準遠遠超過了他,也令他看不到這方面的前途和希望。那時的科林·戴維斯就把自己的目標轉向了指揮,他告訴自己:要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指揮家。然而困難的是,由于他不會彈鋼琴,他遭到了倫敦皇家音樂學院指揮班的拒絕,他被禁止去上指揮課。
畢業后,因為被強制服兵役,科林·戴維斯成為指揮的計劃被打亂了,他成了駐扎在溫莎的皇家近衛騎兵團中的一名單簧管演奏員。不過,那時的他倒是有了不少機會在指揮大師托馬斯·畢徹姆和布魯諾·瓦爾特執棒的音樂會上演奏,這也使他受益匪淺。
1949年科林·戴維斯退役后,邂逅了女高音艾普洛坎泰羅(April Cantelo),并很快結婚。婚后,科林·戴維斯和她育有兩個孩子——蘇珊和克里斯托弗。為了養家糊口,科林·戴維斯不得不做幾份兼職,分別在格林德伯恩和新倫敦室內樂團擔任單簧管演奏員,并擔任了當地合唱團的指揮,同時還指揮著兩個成立不久的團體——主要由他和倫敦皇家音樂學院的畢業生共同組建的卡爾瑪交響樂團(Kalmar Orchestra)與半專業的切爾西劇團(Chelsea Opera Group)。
1949年到1957年的這段漂泊的日子,被他自己戲稱為“信馬由韁的業余荒原期”。當時,他的妻子艾普洛·坎泰羅到處演出,而科林·戴維斯的事業卻停滯不前,唯有靠在劍橋做家庭教師的酬金聊以謀生。但也就是從切爾西劇團開始,科林·戴維斯真正開始了他終身熱愛的對于莫扎特歌劇的研究與指揮嘗試。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切爾西劇團時期,他就已經指揮并上演過后來為他帶來無數榮耀的柏遼茲歌劇《特洛伊人》,只不過當時演出的是音樂會版而己。
1957年,科林·戴維斯終于迎來了事業的轉機,他被聘為BBC蘇格蘭交響樂團(BBC Scottish Symphony Orchestra)的助理指揮。1958年,科林·戴維斯首次出現在當時的英國一流樂團倫敦愛樂樂團和哈萊樂團(Halle Orchestra)的指揮臺上。同年,他在倫敦指揮上演了莫扎特歌劇《后宮誘逃》。
1959年秋天,科林·戴維斯迎來了他指揮生涯中最為夢幻般的時刻。那一天,他突然被制作人瓦爾特萊格告知,要頂替病倒的指揮大師奧托·克倫佩勒,與兩位超級歌唱家——伊麗莎白·施瓦茨科普夫和瓊·薩瑟蘭在皇家節日音樂廳合作,演出兩場音樂會版《唐喬瓦尼》。演出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歡呼與喝彩,科林·戴維斯卻把這次演出稱為“萊格的幽默感和惡作劇”,他覺得萊格的本意是要將他這個英格蘭的無名小卒弄進一座國際知名音樂廳,把大家嚇一大跳,然后,自己去偷偷地享受惡作劇的快感。然而,科林·戴維斯隨后便不可思議地發現,自己竟然在一夜之間就成了全英國最備受矚目的青年指揮家了。他的指揮事業開始有了巨大的起色,他的漫長的錄音生涯也由此開始。1960年至1965年,科林·戴維斯擔任了薩德勒的威爾斯歌劇院(Sadler'sWells Opera,即英國國家歌劇院的前身)音樂總監,并在1967年至1971年擔任了BBC交響樂團的首席指揮。
但是,成名后的科林·戴維斯并不受所有音樂家們的歡迎,因為他那易怒的脾氣,而他磨人脾性、不厭其煩的排練,也令一些樂團的演奏家們生厭。在后來的指揮生涯中,他的傲慢與缺乏經驗也再一次被印證。2007年,當科林·戴維斯回憶起這段時光時說:“當我和倫敦交響樂團第一次合作時,我還是一個初生牛犢不畏虎的年輕人,而他們卻像是一幫兇殘的海盜,除了一個叼著煙斗的豎琴演奏家,這個樂團里就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女性來了。我們之間發生過很多摩擦。當時的音樂標準是高的,但是也不像今天這么高,那時的演奏家們經常是帶著一身未散的酒氣,就匆匆忙忙趕來開音樂會。摩擦的起因,是因為我年輕,而他們則擺老資格,我不理解他們的信念,但是我能覺察出他們內心隱藏的小小不滿,如果你對待音樂就像打了雞血般過于狂熱,他們就會對此冷嘲熱諷,雖然我不覺得自己對此把控有度,但是,我還是挺了過來。”
隨著年齡的增長和歷練的豐富,科林·戴維斯逐漸改變了自己的做法,他說:“我不再過多地考慮雇傭和解雇樂手的事了,我不想再站在指揮或者是演奏者的任意一方的角度,這意味著我與樂隊都獲得了自由,因為我不打算解雇他們,我打算接納我所熱衷的一切,我打算視他們為音樂伙伴一起工作,讓我們來看看,我們在一起能做些什么,在我的生活中,沒有比這更快樂的事情了。不要告訴他們做什么,不要讓他們去做那些被迫接受的而又不理解的事情,作為一個指揮,你必須要幫助他們學會聆聽,那么一切都會變得自然而然,明白無誤。”從那以后,他開始變得寬容大度,由一個怒漢變成了一個紳士。一次排練時,科林·戴維斯被鐃錢樂手不能敲擊得足夠響亮而弄得火冒三丈。但是,他還是盡量壓抑著脾氣沒有發作。在經過幾次試驗后,雖然有所改觀,但還是達不到他的要求。這時,科林·戴維斯走下了指揮臺,丟下了面面相覷的樂隊樂手們,離開了排練大廳。正當樂手們驚訝錯愕不已,一聲鐃鈸巨響突然從樂隊的打擊器樂組傳來,大家扭回頭一看,只見科林·戴維斯就站在那兒,臉上樂開了花,笑著對他們說:“如果我能做到這一點,那么,你們也可以!”
幸福得之于失敗的婚姻
上個世紀60年代是科林·戴維斯指揮事業的上升期,然而事業得意的他在婚姻上卻慘遭觸礁,他和第一個妻子坎泰羅的婚姻解體了。
不久,科林·戴維斯愛上了自家的來自伊朗的,以幫做家務活而換取所寄宿家庭食宿的保姆阿什拉夫·奈尼(Ashraf Naini)。奈尼的工作就是在科林·戴維斯家里,幫忙照料他的兩個孩子。為了這一段婚姻,1954年,科林·戴維斯和阿什拉夫奈尼不得不在英國和伊朗辦理了3次結婚手續,一次在德黑蘭,另兩次在英國,以達到雙方國家的婚姻法規定。他們婚后育有三個男孩與兩個女孩,分別是庫羅什、卡弗斯、法赫德、沙伊達和雅爾達。他把自己和阿什拉夫·奈尼的新家安在了倫敦北部的海布里(Highbury)和薩福克郡(Suffolk)之間,而且他還在家里養了一只非常特殊的寵物南美鬣蜥,來訪的朋友們與同事們經常會被不知何時落到他們面前的鬣蜥給嚇一大跳。
科林·戴維斯生活中唯一做的與音樂無關的事情只有兩件,一件就是親手為他的家人做針織線衣——為他的兒子做毛衣套衫,為他的女兒做花式針織套衫。另一件事就是吸煙,他甚至因此而在1996年被評為當年的“煙斗客”(Pipe Smoker)。
他和阿什拉夫·奈尼的第二次婚姻非常幸福,奈尼一直以來都是他生命中的潛在推動力與情感的支柱,他們相互扶持的美滿婚姻一度成為英國樂壇的一時佳話。2010年,阿什拉夫·奈尼去世后,科林·戴維斯就一直沒有從悲痛中走出來,留給他的是無盡的沮喪和孤獨。
他的健康狀況也每況愈下,2012年5月,他暈倒在德累斯頓的-講臺上。雖然此后他試圖再度拿起指揮棒,為他化解這種痛苦,但是,晚年時他的全部愛和力量,都已經隨著他心愛的妻子奈尼一起逝去。此后直到他離世,不管有多少次數不勝數的懇請,他幾乎再也不接受任何的指揮邀約與合同。唯一的例外,是科林·戴維斯于2012年6月26日在倫敦宏偉壯觀的哥特式建筑圣·保羅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指揮倫敦交響樂團與合唱團合作柏遼茲的《安魂大彌撒》(Grande Messe des Morts),這是他指揮生涯中的絕唱,是他帶給世人的最后一場大型正式音樂會。其實他一生中曾多次在各地大教堂中指揮演奏過這部心愛的作品,如1989年在德國巴伐利亞州的雷根斯堡大教堂(Regensburg CathedrN),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Westminster Cathedral),以及此前于1966年和1976年在倫敦圣·保羅大教堂兩度指揮演奏的這部《安魂大彌撒》。而2012年的這一次,似乎是他在冥冥之中為自己奏響的安魂曲。
毀譽參半的“科文特時期”
除了家庭,站在指揮臺上的時刻,才是最讓科林·戴維斯享受的時光,他說:“每次指揮一場音樂會,時間仿佛暫時停擺了。你是時間的主宰,時間不是你的敵人,雖然它不能延緩死亡,但是,它能在你還活著的時候,讓你尋歡作樂。”
1971年,因為獲得科文特花園皇家歌劇院董事會和索爾蒂的欣賞,科林·戴維斯才從索爾蒂的手中接過了科文特花園皇家歌劇院的指揮棒,并擔任了音樂總監,一干就是16年。截止到1987年的這16年中,科林·戴維斯的觀眾永遠只有兩個——評論家和觀眾。他在科文特花園皇家歌劇院指揮上演的一些歌劇在評論家們和觀眾們中間產生了嚴重的分歧:評論家們贊美,觀眾們就喝倒彩;評論家們噓其下課,觀眾們就歡呼雷動。他曾在這里指揮上演的瓦格納的歌劇《湯豪舍》就曾遭遇到現場觀眾們的一片噓聲。但是,他毫無爭議的曲目是莫扎特、柏遼茲和蒂皮特的歌劇作品。其實早在他擔任科文特花園皇家歌劇院音樂總監之前,已于1965年在這里首次亮相,指揮上演了《費加羅的婚姻》等幾部成功的歌劇,包括他在1968年指揮首演的蒂皮特的歌劇《仲夏的婚姻》(The MidsummerMarriage),在1969年指揮首演的柏遼茲的歌劇《特洛伊人》,在1970年指揮首演的蒂皮特的歌劇《諾特花園》(The KnotGarden)等,最后都成了他的看家劇目。
但是,科林·戴維斯在科文特花園皇家歌劇院指揮上演的一批包括《仲夏的婚姻》在內的現代歌劇雖然在藝術水準上獲得了成功,卻并不叫座,幾乎與索爾蒂在任時指揮上演的布里頓歌劇《比利·巴德》一樣,遭遇票房慘敗。那時,蒂皮特的作品并不受人重視,雖然蒂皮特的對位法結構和名家風度的器樂寫作技巧其實早在1944年就已經趨于成熟,但也并沒有為他贏得多少喝彩。科林·戴維斯曾現場觀看過蒂皮特創作的清唱劇《我們時代的孩子》(A Child of Our Time)的首演,這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蒂皮特的音樂風格開始令他著迷。在當時,蒂皮特的作品幾乎遭到所有指揮家包括樂隊粗暴的拒絕,甚至在排練他的作品后,一些樂手竟公然肆意踐踏他的樂譜副本。而正是科林·戴維斯才讓這一切都成了過去式。他在觀看了清唱劇《我們時代的孩子》后不久,便開始涉足蒂皮特作品的指揮上演,并為這些作品灌錄唱片尋找著一切機會,以便讓更多的人聽到它們。值得一提的是,蒂皮特創作的最重要的一些作品恰恰都是由科林·戴維斯指揮首演的。1995年2月,為了慶祝蒂皮特90大壽,在巴比肯藝術中心上演了隆重的專門為蒂皮特慶生而舉辦的專場音樂會,科林·戴維斯成了當天指揮演出的不二人選。兩人惺惺相惜的深厚友情歷經多年風雨,始終牢不可破。
此外,科林·戴維斯在科文特花園的另一項驕人成就,就是他在1973年至1976年間聯袂德國杰出的歌劇與戲劇導演戈茨·弗雷德里希(Gotz Friedrich,1930-2000)這里指揮上演的瓦格納的《尼伯龍根的指環》全劇。在其任職音樂總監期間,科林·戴維斯一直擁護與支持的一批20世紀作曲家,如斯特拉文斯基、貝爾格、布里頓等人的作品在此上演,也受到了一致贊譽。
為了增強劇院的國際影響力,科林·戴維斯還分別于1979年和1984年,率領科文特花園皇家歌劇院的大隊人馬遠赴韓國、日本和美國等地進行了巡演。在任期內,他還在科文特花園皇家歌劇院指揮上演過《埃里克特拉》、《伊多梅紐》、《阿里阿德涅在納索斯》、《紐倫堡的名歌手》、《西蒙·波卡涅拉》、《法爾斯塔夫》、《奧賽羅》、《露露》及《西班牙公主的生日》(The Birthday of theInfanta)和拉威爾的《孩子與魔法》(L'Enfant et Sortileges)等歌劇。他直截了當的指揮手法與擅于制造音響效果的煽動樂隊的能力,曾經給這個劇院帶來了無數個不眠的夜晚。
然而,在科林·戴維斯的任期內,他和劇院董事會之間一直磕磕絆絆,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他所追求的更刺激、更具社會性的歌劇演出效果,遭到了董事會的反對。此外,他力主倡導的、以英語來演唱的《唐帕斯夸萊》、《特洛伊人》、《費加羅的婚姻》等幾部歌劇,也遭到了董事會的干涉甚至否決。對此,科林·戴維斯解釋說,之所以制作英語版的歌劇,是因為“不應該讓觀眾遠離劇情,如果能使用英語,與觀眾溝通起來,將會有更大收獲”。而當時的董事長德羅伊達卻把這個問題當作“權力斗爭”的一部分,拒絕妥協,并告訴其他董事會成員,如果最終決定用英語來唱,那么他將不會再留任董事長。在董事會上,德羅伊達甚至公開指責科林·戴維斯在董事們面前說話的語氣總是“相當放肆”。而科林·戴維斯則堅稱:“我沒有顯赫的背景,我是一個摳門的、子女盈屋的銀行職員的兒子,由于我是這樣的人,才會招致某些人的反對意見。”由于雙方溝通不暢,也不屬于同一利益陣營,最終導致了科林·戴維斯在1986年掛冠而去。
屬于世界的科林·戴維斯
科林·戴維斯屬于“墻內開花墻外香”的指揮家,在科文特花園皇家歌劇院雖然干得比較郁悶,然而他的國際性的指揮事業卻并未因此而受到絲毫影響,反而風生水起。1960年12月,科林·戴維斯身為明尼阿波利斯交響樂團的客座指揮,指揮該團作了美國首演;1972年至1984年,科林·戴維斯被任命為波士頓交響樂團的首席客座指揮;1983年至1993年,他被任命為巴伐利亞廣播交響樂團的音樂總監,曾經率領該樂團多次出訪演出;1995年至2006年,他被任命為倫敦交響樂團首席指揮;1990年,他成了德累斯頓國家管弦樂團的榮譽指揮,也曾率該團前往世界各地巡演;1998年至2003年間,他被任命為紐約愛樂樂團的首席客座指揮。此外,科林·戴維斯還與世界各大樂團如維也納愛樂樂團、柏林愛樂樂團、阿姆斯特丹皇家音樂廳管弦樂團、費城交響樂團、克利夫蘭交響樂團、波士頓交響樂團、洛杉磯愛樂樂團等一直保持著親密合作關系。
同時,科林·戴維斯忙碌的身影也經常穿梭于美國紐約大都會歌劇院中。1967年1月,科林·戴維斯在大都會歌劇院聯袂大導演泰隆格斯瑞(Tyrone Guthrie)和男高音榮·維克斯(Jon Vickers)組成了豪華的大制作班底,指揮首演了布里頓歌劇《彼得·格萊姆斯》(Peter Grimes),1969年,他在大都會歌劇院指揮上演了貝爾格歌劇《沃采克》(Wozzeck),1972年,他在大都會歌劇院指揮上演了德彪西歌劇《佩利亞斯與梅麗桑德》(Pelleas et Melisande),均獲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和影響。1977年,他成為第一個出現在拜羅伊特的英國指揮家,在瓦格納的音樂圣地,他應邀指揮上演了瓦格納的歌劇《湯豪舍》。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的目標是要成為一個優秀的歌劇指揮,在現階段的工作上堅定地錨固自己,而并非好高騖遠,身為一個指揮,做比懂得更加重要。趁著年輕,要盡力去做,否則,等你老了,到了足以洞悉世事的那一天,你卻因為年紀太大,而再也難以付諸行動了,這個道理有點像婚姻。”
由于在英國公眾音樂生活中的重要影響力和在世界古典樂壇取得的杰出成就,科林·戴維斯一生獲獎無數——1965年榮獲了大英帝國騎士勛章;1980年受封為爵士;1982年在法國獲封騎士勛位;1987年榮獲德國指揮官十字功勞勛章;1990年被授予法國藝術及文學司令勛位;1992年榮獲芬蘭指揮官雄獅功勞勛章;1993年榮獲巴伐利亞州功勞勛章;1995年獲得了皇家愛樂協會金獎;1999年榮獲法國榮譽軍團勛章;2000年榮獲巴伐利亞州馬克西姆利安功勞勛章;2001年被英國女王授予國家最高榮譽,獲封為榮譽勛爵;2009年獲得英國女王頒發的女王音樂勛章:2012年,丹麥女王為他頒發了丹尼布洛功勞勛章。
音樂的世界公民
科林·戴維斯在英國的公眾音樂生活中一直以來都扮演著難以替代的角色,他不僅指揮演奏、錄音,還以音樂教育者的身份在著名的皇家音樂學院(Royal Academy of Music)和市政廳音樂戲劇學校(Guildhall School of Music and Drama)擔任指揮教學工作,嘉惠后學,獎掖提攜著一批青年音樂家。
丹麥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尼古拉·齊奈德(Nikolai Znaider,1975~)在談起科林·戴維斯時,這樣說道:“他的謙恭、正直和寬宏大量是如此非凡地結合在一起,他讓我們所有站在舞臺上的人,包括獨奏家和樂團里的每一個音樂家,以我們自己想要表達的最好的方式來演奏音樂,他夾雜手勢的說話方式如此迷人,他能夠以簡單的手勢概括出一個樂句的精髓。我記得有一次在普羅旺斯的埃克斯觀看他和倫敦交響樂團一起排練《蒂托的仁慈》,在那個特殊樂句的尾聲處有3個音符,他給了樂隊中的木管樂手們3個蜻蜓點水般的輕吻,來形容他此時內心想要的效果。每次當我看到舞臺上奏響《蒂托的仁慈》時,我就仿佛看到了那3個輕吻。他能夠不費吹灰之力地讓奇跡發生。”
英國女高音約瑟芬·巴斯托(Josephine Barstow,1940~)曾回憶說:“我曾和科林一起工作過多年,第一次是在上世紀60年代末,我在科文特花園歌劇院上演的歌劇《彼得·格萊姆斯》中飾唱二侄女,還有就是1970年在科文特花園上演的歌劇《諾特花園》,我當時還很年輕,我最難忘的是,他是多么的寬宏大量。我當時并沒有唱過太多的現代音樂作品,要想唱好現代音樂作品并不容易,但他總是鼓勵我。我記得在演出《彼得格萊姆斯》時,他對我說‘我不想獨自馭使它,我希望大家一起來控制它。我有一份特殊的記憶,那是25年之后,我臨危受命,在科文特花園匆促接演歌劇《菲岱里奧》,在演唱詠嘆調時,我轉錯了調,瞬間即成災難:你不知道如何找回來,那么多指揮等著要宰了你,對待你就像你是一個白癡一樣。但是我記得,當時科林趁幕間休息時來到了我的更衣室,在我的身邊坐下來,只說了一句話:‘運氣不好。這句話是如此暖我心扉,讓我永生難忘。”
科林·戴維斯去世后,倫敦交響樂團發表聲明稱“科林爵士在英國音樂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難以估量的”。皇家歌劇院的音樂總監安東尼奧·帕帕諾則說:“我們和他還有很多未來的計劃,他的去世代表了一個時代的結束,意味著英國音樂生活中最悲傷的一刻。”
蘇格蘭歌劇大導演大衛·麥克維卡(David McVicar)回憶道:“我第一次聽歌劇是十幾歲時,當時我有科林指揮莫扎特歌劇的唱片。我曾經與他合作過3部莫扎特的歌劇:在皇家歌劇院上演的《費加羅的婚姻》和《魔笛》,在普羅旺斯的埃克斯音樂節上演的《蒂托的仁慈》。跟他在一起做莫扎特歌劇的經歷就是一個很好的學習過程,他給音樂注入了那么多的愛,但他從不追慕時尚,他只希望能夠找到自己的方式。他的方式是以對于音樂天生本能的理解作為前提的,他的學識與移情的深度都是非凡的。在排練中,他并不傾向于多說話,就是寬厚一笑,大多時間只是凝視著你。但是,他確定無疑地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如果他不喜歡,他就會提高調門,以你無可辯駁的簡潔的協商語氣表達自己的意見,使他們覺得言之有理。而對于歌唱家們則相反,他任由他們歌唱,他則成了一個想象力豐富的技術員,帶領著他的樂隊,他有那種別人無從洞悉的敏銳的觀察力與伴奏天賦,很少有指揮真的具備這種能力。”英國工黨副黨首哈里特·哈曼(Harriet Harman)評價說:“科林·戴維斯爵士在這個國家和全世界范圍內,為音樂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如果從世界指揮史的角度來考量的話,客觀地說,科林·戴維斯絕對不可能算得上是開宗立派的人物,因為他不像托斯卡尼尼、卡拉揚、小克萊伯等人那樣在指揮肢體語言上具備獨創的、系統化的而又具有審美意義的個人符號,他的指揮肢體語言沒有那些天才人物開天辟地的想象力作為支撐,他的功績與意義只能存在于對于特定曲目的詮釋角度范圍,比如柏遼茲、蒂皮特、卡爾·尼爾森、西貝柳斯、海頓、沃昂·威廉斯等。雖然科林·戴維斯并不是指揮史上的天才人物,但是,他良好的人文修養卻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和豐滿了他對作品的解讀與詮釋。大多數指揮家要么擅長歌劇指揮,要么擅長交響樂指揮,要么擅長合唱指揮,而科林·戴維斯在這三個指揮領域都堪稱當之無愧的大師。
正是在人文底蘊上的拓展與掘進,才使得科林·戴維斯最終成為科林·戴維斯,而不是其他什么人。音樂家如果缺少文化的滋養,那么無論他的技巧有多么卓絕,他依然是一個缺少境界的低級的手藝人,終難入得方家的法眼,更不要奢望會在歷史上留下坐標。這一點,科林·戴維斯想得很明白。他就像樹化石,經過漫長的化學交換與歲月變遷之后,方才顯露出他的價值。
科林戴維斯像一個作風老派的英國紳士,為人低調,從不涉及自己的隱私,從不愿多談有關于自己的細節,他更愿意把這些沉默化作指揮音樂的能量。即便談論起自己的本行,他也是惜字如金,他說:“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東西,在音樂中都能找到,因為音樂讓時間變得意味雋永。”
有人曾經問科林·戴維斯:“您到底愿意被人稱呼為‘大師還是‘科林爵士?”科林·戴維斯面帶溫和的笑容,回答說:“拜托!喊我‘科林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