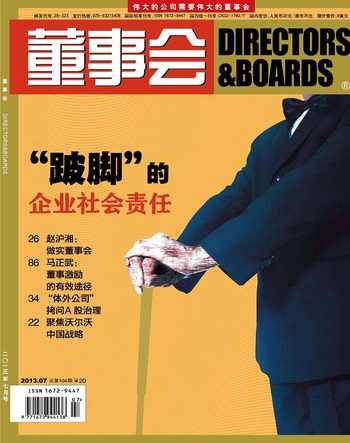拒絕常理
彭飛
僅上映一分鐘即被緊急叫停,在刪減掉一些裸露和血腥鏡頭后復映卻票房慘淡,草草收場——《被解救的姜戈》在內地的遭遇頗具昆汀式的荒誕意味,這樣一部風格之作商業企圖明顯,也不缺話題,其市場表現卻虎頭蛇尾,“莫名其妙”。如此黑色幽默,是對內地電影生態的絕妙諷喻。
事實上,此片在上映之前即有高清版本在網上流傳,這不僅使電影審查部門的“嚴謹”失去意義,還因此事迅即成為一樁飛速張揚的新聞事件,產生廣告效應,從而在更大范圍的觀眾群中普及了昆汀。
錄像帶租賃店小弟出身,卻橫空出世、一鳴驚人,僅憑前兩部作品《落水狗》和《低俗小說》便足以奠定其名垂影史的地位,繼而向好萊塢主流商業電影靠攏,在不失風格和水準的前提下拍出了《殺死比爾》、《無恥混蛋》等商業大片,這就是被譽為鬼才導演的昆汀。
此人路子野、口味重、熟諳影史,偏愛港式動作片、好萊塢B級片、法國黑色電影、意大利通心粉西部片等難登大雅之堂的老電影,津津樂道之余,還樂此不疲地將這些電影類型混搭、雜糅在一起,其亂燉的技藝可謂出神入化,爐火純青,各種橋段和場面經他轉手往往不露痕跡,自成一格,燴成屬于他個人的獨特風味。與正襟危坐、一臉嚴肅的學院派相比,昆汀更像是一位惡童,玩世不恭,一臉壞笑地玩電影。因此,其電影總是洋溢著一種狂放恣肆、舉重若輕的游戲精神,觀者只見粗口與血漿齊飛,調侃和戲謔紛紜,黑色幽默隨處可見,荒誕感直逼心頭。
如果將昆汀的風格納入到一種精神譜系中加以考察,那么我們可以把亨利?米勒和馮尼古特看作其文學上的遠親,而其影像中的近鄰則有蓋?里奇和寧浩。前者簡直是昆汀在英國的翻版,同樣憑借最初的兩部天才之作——《兩桿大煙槍》和《偷拐搶騙》揚名立萬,轉而嘗試商業大片《大偵探福爾摩斯》;后者則將這一風格移植到本土語境中,成功實現了嫁接。也有論者將姜文和昆汀聯系在一起,在我看來純屬誤讀。在狂歡化敘事方面兩人確有相通之處,但姜文的精英范兒和浪漫化傾向與昆汀純正的惡童氣質格格不入,即便再怎么裝流氓,我們也很難想象姜文會在電影中將自己炸得灰飛煙滅,正如昆汀在本片中所做的那樣。
在早期的兩部作品中,昆汀以結構拼貼、多線索敘事和塑造群像見長,此后的他似乎把這看家本領隨手丟棄了,轉而依托于他所鐘愛的各種電影類型,隨心所欲地戲仿、混搭和組合,竟也能玩出新意。《殺死比爾》脫胎于港式功夫片和日本武士片,《金剛不壞》刻意做舊畫面以營造早期B級片和邪典(cult)電影的氛圍,《無恥混蛋》則披了件二戰歷史片的外衣,到《被解救的姜戈》,昆汀再次別出心裁,在黑奴制盛行的美國南方莊園里上演通心粉西部片式的血腥暴力。
很多人會因為本片解放黑奴的主題而想到《林肯》,甚至格里菲斯的經典名作《一個國家的誕生》,我卻認為與本片形成最有趣對照的是李安被低估的電影《與魔鬼共騎》——講述一個白人少年和黑奴在美國南北戰爭中找到自我,實現自由的成長故事。兩片在表現黑奴自我覺醒、追求自由這一人文主義內涵上可謂如出一轍,甚至都借助白人伙伴的死來深化這一點,但在自由之后怎樣這一議題上,兩片的走向出現了分岔:前者順理成章地踏上事先鋪設的復仇之路,在觀眾期待之中的暴力大餐如約而至,而后者則讓主人公在與仇人狹路相逢時放下仇恨,選擇和解,因為“這沒什么對錯,就是這么回事”。
對暴力和戰爭的反思顯然不在昆汀的視野之內,甚至解放黑奴于他也只是一個“政治正確”的前提,有此前提方能心安理得地渲染、把玩暴力,對昆汀而言,暴力止于美學。我相信這既是昆汀的惡趣味,也是其深諳的商業規則,是不可逾越的生存之道。而在這約束之下迸發出來的創造力,不按常理出牌、率性而為的不羈氣質以及打破一切陳詞濫調的瘋勁兒,才是昆汀最大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