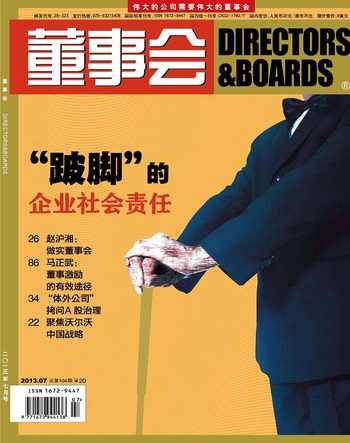重構機遇監督職能
Larry Bennigson and Frank S. Leonard
現如今,公司大多現金充裕。2013年年初,美國的非金融機構共持有超1.5萬億美元的現金及其等價物。然而,近期一項對50家標普500成分股企業的調查顯示,這些公司僅計劃增加2%左右的資本支出,預示著他們普遍缺乏大規模增長的機遇。
鑒于蕭條的經濟和如此高的現金持有量,很自然想到公司現在的優先選項是找到投資機遇、創造價值——管理層和董事會應共同關注這一緊迫挑戰。然而現狀是,董事會本應承擔的這一關鍵作用明顯缺失,因為一直以來,對董事會的職能定位就是履行“看家人”的作用,守住已形成的價值,而非創造新價值。
總的來說,董事會應該代表股東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履行兩大重要職責:監督對公司現有價值的保護以及監督新價值的創造。然而,即便大多數董事會都很重視公司的成長,但在實踐中,董事會的職能履行往往會向著一種不均衡的狀態演化:風險管理主導董事會議程。
雖然發現機遇對于價值創造的重要性,與風險識別對于價值保護的重要性相比不遑多讓,但很少有董事會關注公司的機遇生成能力。一家公司的機遇生成能力即其如何搜索、識別、建設和追求能夠創造價值的機會的能力。雖然在個別的機遇浮出水面時,董事會通常會給予關注,但在董事會會議上,鮮聞“機遇勘察”和“機遇生成能力”這樣主動態的詞匯。
對待風險和機遇的不平衡態度是一個潛在的嚴重問題,會對公司的長期競爭力和成長造成消極影響。董事會層面的這種不平衡將自上而下產生意想不到的結果:通過逐級下移,規避風險的情緒在組織內不斷放大,變成公司成長的剎車閘,造成事實上的機遇厭惡傾向。
雖然風險管理的擁護者們聲稱其管理框架能夠兼容風險和機遇,但這種說法值得懷疑。行為經濟學已經證明,人天生具有風險厭惡心理,在損失和收益概率相同的情況下,人們不由自主覺得損失會更大也更可能出現——這就會導致風險感知扭曲以及判斷失誤。因此,認識到當前工作中風險監督和機遇監督的不平衡,增強對機遇的發現;同時,不因這一調整削弱對風險管理的重視以及風險監督的效力,這是董事會不得不迎接的挑戰。
失衡的機遇監督職能
一直以來,量化機遇帶來的收益一直比量化風險損失更加困難。然而在過去的20年,立法機關、監管部門和股東們不厭其煩地要求董事會更多關注風險,在某種程度上,恨不得董事會能夠預測到全部的壞運勢、壞結果以及決策、管理失誤。董事會成員、高層管理者、會計人員、分析師以及學者都很依賴傳統的風險概念與框架,他們能夠用“同一種語言”進行溝通。但是,機遇方面至今仍沒有形成類似的“共同語言”和理解。
與管理層和董事會成員討論監督不平衡問題時,時常會得到兩種回復:“機遇管理是CEO的工作”;或者“董事會沒有經驗、時間和技能去管理機遇”。這兩種說法的確沒錯。構建、管理公司的機遇生成能力與構建、管理公司的風險管理能力一樣,都是CEO的關鍵職責。然而,公司的機遇生成能力卻沒有得到董事會足夠的重視與監督。考慮到機遇的重要性,這一點需要改變。同時,大多數董事會確實沒有足夠的專業能力與經驗來開展機遇監督,這一點也需要改變!
董事會應該像對待風險一樣,在機遇方面也投入同等的強調和關注。董事會若想履行監督價值創造的職能,應自問兩個問題:“對于公司當前戰略所指向的機遇,是否有能力理解通透?”;“公司是否有能力調整戰略適應重要的新興機遇?”。作為機遇的勘察者,董事會必須清楚四組信息:公司識別和獲取機遇的全盤方案;公司當前的機遇生成能力;這一能力如何與公司的戰略挑戰匹配;高層管理人員強化公司機遇生成能力的行動計劃。
培育機遇生成能力
所謂“培育強大的機遇生成能力以及董事會應該有效監督機遇”并非簡單指代公司要強調創新、加大對研發的投入或者積極開展收購活動;也不僅僅是指董事會每年對戰略和業務發展方案的評估;而是意味著公司需要培養“基于組織結構和管理流程的,能搜索、識別、發展和實現價值創造型機遇的復合能力”。
構建公司機遇生成能力的“積木”形形色色:與重要客戶的伙伴關系、參與行業組織或者咨詢委員會、充足的研發預算以及長期致力于市場研究。更加綜合的元素還包括:前瞻能力——能夠盡早識別大環境里的重要趨勢和轉變,管理創新的技能以及機遇敏感度高的企業文化等。
具體而言,若要形成有效的機遇生成能力、實現董事會的合理機遇監督,一則要求董事會與高層管理者之間形成活躍而有建設性的合作關系,二則要求董事會能夠理解機遇監督的內涵,監督公司實現和維持高水平的價值創造。
多元化的3M集團就是一家因良好的機遇生成能力而創造出長期價值的公司。“創新文化”是3M積極開展價值創造的標志,但讓3M真正引以為豪的是其機遇哲學。縱觀歷史長河,很多杰出的思想家都曾表達過這樣的理念:預測未來的最好方法就是創造未來。由此觀之,3M的商業模式應該是通過發明不曾存在過的新產品來推動公司的有機增長。
為了支持這一機遇哲學,3M有意識地管理著龐大而復雜的機遇生成能力,這一能力脫胎于40余個技術平臺、人力資源政策、各式各樣組織流程的相互協調,以及內部的思想交流平臺、支持探索性研究的投資、戰略伙伴關系和鼓勵分享想法、承擔風險、持之以恒的3M組織文化。
截至目前,很少有公司能夠復制3M的這一模式,但這不能成為止步不前的理由。一方面,公司可以嘗試從內部入手,逐步培養機遇生成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通過并購獲取機遇生成能力。不妨看看蘋果。如果史蒂夫?喬布斯及其管理團隊放棄構想巨大的市場機遇,也沒有培養必要的內部能力來抓住機遇,那么,蘋果的股東今日怎么可能獲得如此之高的價值?另一個生動的例子是孟山都,其在1985年收購了G.D.Searle& Co公司,成功由化工企業轉型進入生命科學行業,實現了后續發展。
與此相對,百思買、諾基亞和索尼的慘痛教訓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哪怕是風光一時的巨擘,如果沒能識別和搶占價值創造的機遇,也會跌落低谷。如此境況,何來所謂股東價值的保護?如果上述公司的董事會能夠對機遇生成能力足夠重視,如今恐怕會是另一種局面。
一些公司把機遇生成能力弱,錯認為是缺乏機遇。然而根據以往的經驗,只要公司能夠想象和預測可能的機遇并做出反應,就能夠獲取和抓住機遇。正如機遇生成能力的內涵一般,重要的是發現可能的機遇,努力使之成形;未來可以是公司自己創造出來的。
走好第一步
對組成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的30家公司進行分析可以發現,其中至少有7家——奧馳亞集團、美國運通、惠普、默克、輝瑞制造、寶潔和沃爾瑪都調整了董事會結構以服務機遇監督。這些公司都設立了專門的董事委員會,關注與機遇生成能力相關的戰略要素。
鑒于公司之間的差別,并不存在普適的機遇和風險平衡監督模式。董事們如果想要糾正風險與機遇監督的不平衡,以下建議或許可以幫助董事會走好第一步:
1.在下一次董事會會議上,納入對機遇監督的討論,同時,就接下來該怎么做達成一些共識;
2.鼓勵兩到三名董事請愿與CEO組建關注機遇的工作小組;
3.要求管理層對公司的“機遇生成流程”提供年度報告,并不斷改進方案;
4.組建機遇監督委員會,與負責風險管理工作的審計或風險委員會平行履職;
5.鼓勵董事會治理委員會重審董事會“基因庫”,確保董事會擁有足夠的經驗和資格來質疑、評估公司的機遇生成流程。
全球領先的動物飼料公司_荷蘭泰高(Nutreco)就完成了重要的機遇監督轉型。公司董事會特別設立了創新和可持續委員會,負責監督泰高的創新日程。2012年,該委員會發布了“可持續前景2020”,用以引導全公司上下的機遇生成工作。
必須再強調一次,只要對風險和機遇的監督存在不平衡,公司就會過度厭惡風險,錯失機遇。因此,平衡機遇和風險是董事會和管理層最重大的挑戰之一。董事會必須知道如何、何時以風險思維來考量機遇。太過強調風險管理會導致惰性、決策拖沓以及機會盲區。
(源于MIT Slo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