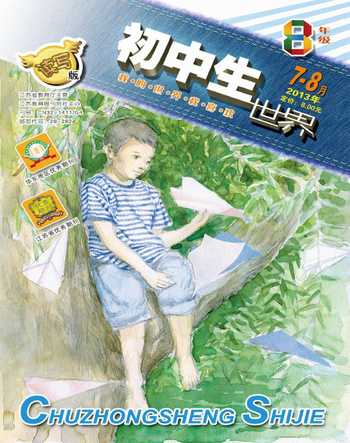文化習慣需要培養(yǎng)
我這一輩子是在“書”里面成長。小時候最大的夢想就是坐擁書城,等我終于能寫書、能夠去買書時,我就看中了墻上滿滿的書。現(xiàn)在雖然在網(wǎng)上能查到很多資料,但是坐擁書城這個夢想,還是我生命里踏實的事。如果不是紙質(zhì)文本捧在手里,沒有觸摸的質(zhì)地,我們怎么能有文本閱讀的快感?所以我查閱資料時使用電子的媒介,但在讀書時,一定是讀紙質(zhì)版本的。
紙質(zhì)閱讀關乎中國社會轉(zhuǎn)型時期民族文化習慣的養(yǎng)成。我的身份是一個老師,也是一個母親,面對我的學生和我的孩子,我不希望他們是只會看電腦、打游戲的一代人。社會轉(zhuǎn)型時期對書的信任是一個民族性的傳承,也是一個人理性的培養(yǎng)。因為書的閱讀過程比上網(wǎng)要寂寞,它沒有那么多人的觀點左右你,不會使人瞬間盲從,它會培養(yǎng)一個人的獨立性。讀書有著個人成長中一種寂寞的儀式感,比網(wǎng)絡、微博要寂寞得多。因為書籍是邏輯閱讀,它讓我們從碎片化信息的即時消費中解脫出來,進入一種深邃的、可以觸摸歷史、尊敬別人靈魂的邏輯閱讀。
今天的中國社會有著龐大的信息陣,人們在其中往往失去了對人的尊敬和信任。我們今天有多少不信,有多少懷疑,有多少抱怨,這一切僅僅是因為轉(zhuǎn)型時期社會矛盾沒有解決嗎?其實也關聯(lián)于很多習慣的養(yǎng)成。一個真正能夠深邃地在實體閱讀和紙質(zhì)文本閱讀中去觸摸別人靈魂的人,有的時候會油然而生內(nèi)心深深的敬意。
為什么說紙質(zhì)閱讀關乎轉(zhuǎn)型時期民族文化習慣的養(yǎng)成呢?整個20世紀我們完成了太多的價值顛覆,但沒有完成價值建立。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從封建體制的顛覆到傳統(tǒng)思想體系的坍塌,20世紀80年代剛要建立新價值的時候,拜金主義就進來了,消費時代猝不及防全面來臨。所以我們在多元的消費方式中好像進入了一個大游戲場,獲得了一種物質(zhì)文明的豐碩,但是人們內(nèi)心的空白處、用一個世紀完成顛覆的這個民族文化靈魂的空白處,卻沒有建立起新的價值體系。我們的未來交給年輕人,我真的希望他們熱愛閱讀。
文化習慣的培養(yǎng)是需要過程的,也需要載體。實體書店正在變成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有默契的文化場所、一個讀書人的圈子。這是一種養(yǎng)成,書店的功能絕不僅僅是賣書,它是一種生活方式的引領,是一個人價值觀判斷的提升。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確實需要更多的實體書店去引領紙質(zhì)閱讀。
(選自《光明日報》2013年2月28日,有刪改)
于丹,著名文化學者,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通過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等欄目普及、傳播傳統(tǒng)文化,在海內(nèi)外產(chǎn)生了廣泛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