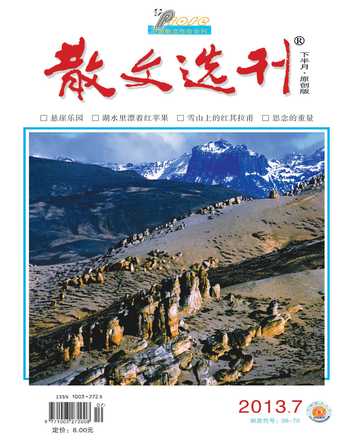姐
位娟
看著腳下的白云,時(shí)而悠閑地散步,時(shí)而匆忙地奔騰,就感覺融在了其中了。但,我能飄到哪里啊?
終于下飛機(jī)了,隨著人流我走出站臺(tái)。再也無意于周圍的風(fēng)景了,仿佛一切都不存在,仿佛空蕩蕩的大地就我一個(gè)人。
從機(jī)場(chǎng)到醫(yī)院不是很遠(yuǎn),步行就好了。這時(shí)天麻麻黑,下弦月像彎刀一樣跟隨著我。好像在收割著我身后的原野。太陽(yáng)的制造,月亮的收割,誰(shuí)也控制不了的啊!在我們的一生,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想想,哪一次淚水不是因?yàn)閻郏?/p>
我這次坐飛機(jī)回家,是去醫(yī)院看望我大姐的。姐姐得了肝癌。癌癥,我都不敢提這兩個(gè)字,就連別人說話的口型我都害怕。仿佛是怪獸,是魔鬼,正一口一口地撕咬著我的大姐。大姐比我大十好幾歲,我就是大姐哄大的,在我眼里,大姐比娘更像娘,比娘更親。小時(shí)候,農(nóng)活多,爹娘顧不上我,姐為了我只上了小學(xué)三年級(jí)。在姐花枝招展的時(shí)光,姐的身上散發(fā)的不是青春的香味,而是我的屎尿味兒。都是我拖累了大姐,如果不是我,姐會(huì)去讀書,會(huì)考大學(xué),也許會(huì)有個(gè)好工作,而不至于一輩子種地……
醫(yī)院就在眼前,之于當(dāng)時(shí)的我,是多么遙遠(yuǎn),恍若隔世之感,好像這個(gè)地方本不應(yīng)當(dāng)和我相干,本不應(yīng)當(dāng)和姐相干,姐不該在這里,姐不該離開我。姐依然是走在我身邊,走在我前面,為我遮擋陽(yáng)光,為我遮擋風(fēng)雨的那個(gè)小姑娘。就這樣,我不知不覺走到了醫(yī)院的花壇前,一位跪在月色下的背影讓我從幻想里警醒。她那么虔誠(chéng)地跪著,嘴里念念有詞。白色的上衣,黑色的褲子,長(zhǎng)長(zhǎng)的秀發(fā)披在腦后,讓我想起白娘子為夫跪求靈丹妙藥的情景來。我相信,她一定是為得了重病的親人求平安的,我相信月亮一定會(huì)看得到,我相信上帝也一定會(huì)看得到……我也不自覺地跪下來,祈禱神佑我姐能康復(fù)!突然,有人呵呵笑著朝這邊走來,嚇得我騰的一聲站起來,匆匆離開。而那位女子依然跪著,依然念念有詞。我的臉驀地發(fā)燙,慚愧啊!我竟然沒她虔誠(chéng)!我對(duì)不起你啊,姐!上帝,原諒我這一次吧。而此刻那個(gè)女子應(yīng)該充滿意希望的,她和我相較來說,比我幸福,因?yàn)樗粫?huì)為了今晚而愧疚。
拖著沉重的步子,來到姐的病房。在病房前,我的腳遲疑了好一陣才敢進(jìn)去,我控制住我自己,鼓勵(lì)著我自己,見到姐一定不能哭!姐看到了我,朝我伸手,顫顫地說一聲:“榮兒,來了。”然后,姐的眼圈紅了,抽搐地哭起來。手術(shù)后刀口因?yàn)檎痤澏罱愀纯啵n白的臉變得青紫起來。我拉著姐的手,把痛苦的淚水使勁壓回胸腔,擦干姐的淚說:“姐,我來看你了,你還不高興啊?你的病會(huì)好起來的!你說過我是個(gè)有福的人,會(huì)給你帶來好運(yùn)的,帶來奇跡的。還記不記得小時(shí)候我順著墻頭爬上屋頂,又從屋頂上摔下來。那一次,可把你嚇壞了,臉都白了,哭得聲音比狼都難聽。而我卻一點(diǎn)也沒傷著,倒是你把我揍了一頓!這一次,一定有奇跡發(fā)生在你身上!姐。”姐被我說得竟然又哭又笑,然后安定下來,給我講我小時(shí)候的事。
我們姐妹說笑著,姐夫遞給我一杯水。這時(shí),我才注意到姐夫。本來瘦弱身子,現(xiàn)在更瘦了,衣服有點(diǎn)大,空蕩蕩的,像一股風(fēng)就能吹跑。姐夫是建筑工人,和水泥,坯墻,壘墻,多重的體力活啊!姐夫這么瘦的身子,不知怎么挺過去的。現(xiàn)在城里一套房子就百幾十萬(wàn),而姐夫一月也就三千多,總覺得不平!但是,為了給姐看病,姐夫說,把瓦房賣了也愿意!姐,一個(gè)多月就不能自理了,是姐夫端屎端尿地精心伺候著,姐雖說很瘦,但很干凈,我真得感謝眼前的這個(gè)男人!我給了他三萬(wàn)塊錢,當(dāng)時(shí),我心里是慚愧的,我知道,這遠(yuǎn)遠(yuǎn)不夠,但我只有這些力量了。姐夫拼命不要,我說,你讓我少一些慚愧吧,要不,我一輩子都不會(huì)安心!他才接,還說,以后會(huì)還給我的,憨厚的姐夫,我能再要這個(gè)錢嗎?
姐夫給我買了晚飯,姐只能喝些稀湯。我來時(shí),給姐幾千塊錢買了幾盒燕窩,聽說很補(bǔ)身子。姐埋怨我,說,這么貴的東西,咋是咱吃的啊!我也不知怎么個(gè)吃法。姐夫說,燕子的窩,不都是草嗎?這能吃嗎?最后我們研究了半天,把瓶子取了出來,才知道,溫溫直接就能喝。姐喝了兩口,說,有個(gè)好味兒,不舍得喝,一天喝兩口就行了。是我硬逼著姐喝完的。我對(duì)姐說,喝吧,喝完我再給你買。姐拼命擺手,說一盒,夠她種一季地了!
兩天后,醫(yī)生給姐開了一大堆藥,讓姐回家打針,說,在這兒,在家都一樣,在家吃睡更方便些,而且這里消費(fèi)又高。我們費(fèi)力地把姐抬到車上,姐一路吐個(gè)不停,好像一只風(fēng)箏,要不是我們手中的那根線,早就輕飄飄地飛走了。姐靠著我,讓我感覺我和姐就像一棵不可分割的樹。姐每痛苦一下,我的枝葉也顫抖一下,心里一陣陣揪著疼。終于車行到姐的家鄉(xiāng)了。還是一望無際的麥田,只不過麥田里墳又多了些,而且大了些,好像大地上的一雙雙眼睛,一個(gè)個(gè)耳朵。本來墳上應(yīng)該長(zhǎng)有茂盛的青草,或者野花的,為什么沒有呢?我問姐夫。姐夫說,前一陣子平墳,上面下來平的,后來群眾不愿意,鬧了起來。最后,還是把平過的墳重新堆了起了!
終于到姐的村子了。以前是一些草房散落在田間地頭,現(xiàn)在仿佛還有茅草在陽(yáng)光下嘶鳴。草房都換成瓦房或平房了,冷冷的磚頭,少了些泥土的溫馨。走進(jìn)姐家,看四周,都是原野。讓人仿佛立于世外,不知生死。說起生死,此時(shí),疼痛中竟有幾分釋然了。死亡,是每個(gè)人必須的歸宿。我也會(huì)死的,死了后,去找姐,找大,找娘,找爺爺,奶奶,姥姥,姥爺……很多親人相聚在一起,我竟然升起了一點(diǎn)向往。生死界限突覺模糊起來。這時(shí),姐的大黃狗,搖著尾巴,蹭著我的腿,它可是第一次見我,一點(diǎn)對(duì)我不陌生,仿佛它早就知道我們的前世今生緣。看著它溫柔地舔著我的手,我一點(diǎn)也不感到臟,也許它的舔,永遠(yuǎn)留在我記憶里,也就是說,大黃狗走進(jìn)了我的生命。就像我和姐手挽手走進(jìn)了原野,大黃永遠(yuǎn)踽踽跟著。
我正在出神,口袋里的電話把我嚇了一跳,她像月光下突遇一條蛇,把我一下拽到現(xiàn)實(shí)的坑塘。
我的大地啊,都盼望我們好好活著。
責(zé)任編輯:子非
美術(shù)插圖:知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