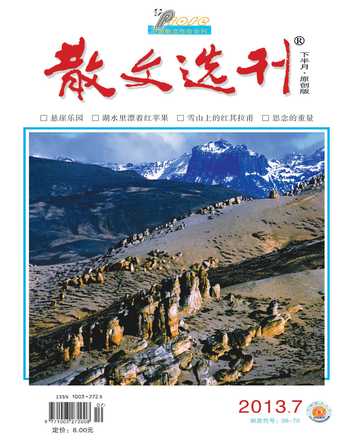“北大三老”的曠世愛情
焦紅軍
張中行、季羨林、任繼愈是新世紀中國文化進程中當之無愧的“北大三老”。他們無論是作為學子還是業師,他們的經歷、學識、思想、風范,在中國當代文化中,當之無愧,罕有其匹。
而“北大三老”的愛情,是其中尤為壯麗的華彩樂章。
張中行
“三老”中最受世間爭議的是張中行的愛情,而這一切,都和一個女人有關,這就是當代著名的女作家楊沫。
張中行與楊沫相識于1931年。那一年,張中行22歲,剛考入北大,在北大國文系讀書,恰是風華正茂,風流倜儻的年齡。而原名楊成業的楊沫,也是青春年少,在北京西山溫泉女中上高中,因家境衰落,為了減輕家庭負擔,楊沫的母親打算把她嫁給一個有錢的軍官,楊沫堅決不從,遂放棄學業,離家出走,尋找新的生活。有一個叫于大哥的因與張中行相識,便讓張中行為其表妹的同學(即楊沫)介紹一份小學教師的工作,于是二人相識了。“她十七歲,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豐滿,眼睛明亮有神……有理想、不世俗……”足以可見,楊沫在張中行一生情感中所占據的分量。
見面后張中行愉快地給在香河縣立小學當校長的兄長寫了一封推薦信,并且很快就得到回信,于是,楊沫去了香河當了一名小學教師。
張、楊一個郎才,一個女貌,加之二人在讀書和文學創作上,有著共同的語言,他們很快就掉進了愛河,在北大沙灘附近,租了間民房,過起了浪漫的生活。楊沫因為年輕,接受外界新思想較快,喜歡閱讀新文學運動一類的作品。張中行人則比較老成,愛鉆研古書和外國哲學原著,故兩人的興趣愛好與閱讀趣味呈現出距離與差別,正因為這距離與差別,為他們以后的離異埋下了分手的種子。兩人的熱戀持續了四年。1936年,意外的事情發生了。
1936年,正是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急時刻,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消極抗日”的政策,無疑加重了這種國難深仇。1936年發生的“西安事變”,更是將全民族的抗日浪潮推向一個新的高潮,這無疑對年輕的楊沫來說是一種強烈的震撼。她渴望與有為的社會青年一樣,在浴血的抗日戰場上,去接受人生的洗禮。而老成古板的張中行,還待在象牙塔里,一心一意地營造他自己的書齋生活,小資生活。這是與社會,與抗日背道而馳,并為時人所不齒的。在當時年輕的楊沫眼里,政治大于生活,政治也幾可等同于愛情。當循規蹈矩的張中行,再也罩不住楊沫思想的羽翼時,愛情的滑稽劇,就不可避免地又一次上演了。
但是事物的發展,不是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上世紀50年代,楊沫發表了長篇小說《青春之歌》,一舉走紅中國文壇。楊沫在書中虛構的以張中行為原型的余永澤成了廣大讀者一致聲討的對象。受此牽連和影響,張中行被遣返河北香河老家務農。對這一切的遭難,張中行都采取逆來順受,不置一詞的態度,始終隱忍不發。“文革”期間,有人讓張中行檢舉楊沫的言論,張中行也未跟著落井下石,說楊沫的壞話,而是說“她直爽、熱情,有濟世救難的理想,并且有求其實現的魄力”。再后來,楊沫在回憶錄《青藍園》中有對張中行不恰當的描述,張中行是抱著絕不發言的態度,一直沉默到底。到最后,楊沫去世,張中行拒絕了他與楊沫所生的親生女兒的請求,未去參加楊沫的遺體告別儀式。從這些情節上看來,張中行是很有骨頭和隱忍精神的。
我想,這是與他早年從事佛教的研究,并主編以佛教為主題的雜志《世間解》有關,甚至解放以后一段時間,張中行還在佛教協會兼職編輯《現代佛學》月刊。也許,張中行種種不平的遭際,他人生苦難的傷口,也因信奉了佛教,被博大精深的佛學緊緊地包住。
季羨林
要說季羨林的愛情,不能不追根溯源季羨林的家世。
季羨林祖籍山東臨清市大官莊,季羨林父親那一輩兒,只有他父親和叔叔兄弟二人,哥倆在老家實在混不下去了,跑到濟南城賣苦力。在最困難的時候,天上掉下了“餡餅”,季老的叔叔用兩塊大洋買了幾張彩票,結果中了頭獎,賺了四千塊明晃晃的“袁大頭”。據此,兄弟倆從赤貧變成了暴發戶,并由此完成了從無產者到有產者的轉變,蓋起了青磚瓦房,娶妻生子,過上了“貧民張大嘴”的幸福生活。舊社會,講究“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兄弟二人盼星星盼月亮,一生再生,結果他們這一輩只生養了季羨林這么一個男孩。老兄弟倆一合計,就讓六歲的季羨林到了省城濟南的叔叔家,過起了離家求學的生活。那么,季羨林屬于過繼,還是助養,老兄弟二人當時是怎么商量的,如今已無人知曉,就連季羨林自己也蒙在鼓里。反正季羨林在濟南,讀完了私塾,讀小學,初中考入正誼,高中轉入山東大學附中,又稱北園高中就讀。從初中到高中,季羨林的學習一路領先,國文習作很受老師推崇,古文功底尤甚,小小的年紀已經有了超群的寫作天賦。
但人生的不完美之處也在于此。種種人生遭際,讓季羨林幼小的心靈有異于常人,其孤獨之苦無法為外人道也。高中畢業,遵照叔父之命,季羨林報考濟南郵政局,也不知是季羨林有意考不中,還是老天爺成全,季羨林沒有考取。于是,再赴北京趕考,結果一鳴驚人,季羨林同時為北大、清華兩校錄取。從季羨林叔叔讓其報考濟南郵政局這一點看,其叔叔也沒有成全季羨林,助推其上學成長之意,至多就是把他當做一個傳宗接代的工具。
更重要的是,季羨林高中一畢業,即1929年18歲時,叔父就自代父命,親自為他選定了一門婚事,18歲上季羨林就結了婚。也許是叔父要用婚姻這條褲腿,縛住季羨林不知天高地厚,恃才傲物的青春性情,讓他從此熄火安身,順天認命,也未可知。
新娘是誰呢?為季羨林叔父同事的三女兒,名曰彭德華。季、彭兩家非常交好,交好到什么地步呢?彭德華的父親(即季羨林的岳父)之所以能夠得到當時濟南官場上的一大肥缺——黃河河務局的工作,就完全是拜其叔叔所賜。最有趣的是,季、彭兩家住的還是前后院,前院住的是季大科長,后院是彭德華一家。彭德華年長季羨林四歲,雖然算不上“青梅竹馬”、“一見鐘情”,但抬頭不見低頭見,東屋拿面,西屋借瓢,二人的接觸肯定也是有的。
但世間之事怪就怪在錯點了鴛鴦譜。季羨林看不中彭德華,他的丘比特之箭瞄準的卻是自己的小姨子——彭德華的四妹,小彭德華兩歲的“荷姐”。但時不我與,天不佑人,是季羨林自小就畏于叔父的嚴厲管教,不敢與命運抗爭?還是荷姐少不更事,畏于婦道尊嚴,不敢姐妹易嫁?到頭來二人的這段暗戀,都往事隨風,成為一場無言的結局。據說季羨林1946年留德歸來,在濟南宴請親朋好友,沒想到小姨子荷姐也在宴間,左一個“季大博士”,右一個“季大博士”,與季羨林說笑逗樂。“人欲愛,而時已移。”這種愛情的傷感,也唯有季羨林與荷姐二人,在心底深處細細體味了。
1936年,季羨林去德國,適逢“二戰”爆發,在德國一待就是十年。1946年歸國,即入北大,出任北大教授。他在德國期間是否遭遇過愛情?季羨林在《留德十年》中對此有所記錄,在離別的前一天,季一天之中,去了好幾次德國姑娘伊姆加德的老房子,那種離別前的悵惘、纏綿的感情,季羨林是有切膚之痛的。后來,他遵循了封建禮教的“父為子綱”的傳統,轉道回國了。
建國后,季羨林職場上是一路順風,他不僅是北大文科僅有的七個“正一級”教授之一,是教授中最為年輕的一個,而且是社科院學部委員,月工資400多元。按當時齊白石的畫價10元一張計算,季羨林一月可買40張,且贈品不算。這在當時已是巨富,足已養家糊口,買田置地了。按說,全家分別這么多年,也該家人團聚,安享和美的世俗生活了。但一直到1962年,季老夫人彭德華才遷來北京,全家得以團聚。這樣算來,從1936年季羨林去德至1962年全家團聚,夫妻分居長達26年。這段史實,直到2010年,季羨林的兒子季承在《我和父親季羨林》中才有所披露。原來是季承姐弟偷偷給北大校長陸平寫了一封信,北大上報北京市委書記彭真批準,彭德華才遷來北京的。“兒大不由爹”,季羨林知道,自己的兒女已經長大了。可家搬來了,兩顆不沾愛的心,卻始終彌合不到一起。季承寫道:“大床布置好以后,父親卻很不高興,他不愿意和母親睡在一起。
但季老就是季老,兩個人雖然沒有愛情,但是夫妻情分還是有的。季老還為妻子德華寫過一篇文章《寸草心》,文中這樣寫道:“德華長我四歲。對我們家來說,她真正做到‘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一輩子勤勤懇懇,有時候還要含辛茹苦。”
任繼愈
“三老”之中,任繼愈的年齡最小,愛情也是這三人中最為順暢,最為恩愛的一個。
任繼愈,原名任又之,1916年4月出生于山東平原縣的一個舊式軍官家庭。父親畢業于保定陸軍軍官學校,與國民黨高級將領劉峙、顧祝同為同窗,參加過抗日戰爭,后銜至國民黨少將,因不善拍馬奉迎,最后在參議員的位置上退下來。
1934年,年僅18歲的任繼愈,如愿以償地考入了北京大學哲學系,并受教于湯用彤、熊十力、錢穆等教授。在國難當頭,列強環伺的舊中國,學習一無用處的西方哲學,很多人不理解。因此三年下來,原來哲學系一同入學的十幾名同學,都紛紛走光,最后只剩下三人還在堅持,任繼愈便是其中之一。
1938年,任繼愈在隨校南遷的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1939年,他又一舉考取了西南聯合大學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研究中國哲學史和佛教史。1941年畢業后,即在西南聯大教書,當講師。生活對年輕的任繼愈來說,翻開了新的一頁,而愛情也在緊張的工作中不期而至。
任繼愈有一個北大哲學系畢業,后來留學英國的同學王維澄,他是湯用彤先生的研究生,以一篇《老子化胡考》的畢業論文,享譽學術界。王維澄回國以后,在師范學院教哲學史,業務很繁忙,王維澄的愛人則在西南聯大附中教語文。有一次,王維澄愛人生病,不能上課,學校又找不著合適的替代人手。王維澄便來找任繼愈商量,讓他這個大講師屈尊就駕,到附中代幾天語文課。這讓任繼愈很犯難,一個大學講師去給初中的小孩子授課,這是哪和哪的事啊!但任繼愈經不住王維澄的一說再說,便答應了去代幾天課。
不成想,這一答應,竟成就了一段美好姻緣。
當時,在西南聯大附中教另外一班語文課的,是剛剛大學畢業的年輕教師馮鐘蕓。因為是教同一年級的課,年輕人之間又沒有隔閡,一來二往,兩人就相熟了。馮鐘蕓出生于一個家世顯赫的知識分子家庭。她的父親馮景蘭是我國著名的地質學家,他的大伯馮友蘭是開宗立派的哲學家,姑姑馮沅君是知名的文學史家,更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位女教授。馮氏三兄妹以“三馮”名貫當時的學術界。他們的家鄉河南唐河更是以“三馮”為榮,在他們的影響下,整個唐河地區都形成了家家送子女上學讀書求知的教育氛圍。
也許老天爺要成心幫助這對人間男女。之后不久,馮鐘蕓就被聘到西南聯大中文系任助教,成為了西南聯大歷史上第一位女教師。按說這樣兩人更有了接觸的機會,但兩人作為大齡青年,同時又有學問在身,在男女情愫方面,并沒有什么太多的主動,盡管身在一個學校,作為同事,他們誰也沒有主動挑破愛情這層窗戶紙。
這時,任繼愈的導師和恩師湯用彤先生卻坐不住了。湯先生看到自己年輕的弟子,不事婚姻,心里很著急。終于有一天,他鄭重地打扮了一下行裝,親自跑到馮鐘蕓家里去,因為任繼愈孤身一人在外,且家人都在山東平原,所以,他自代家長,為弟子上門提親。“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恩師替弟子登門求婚,這在戰時不能說絕世少有,也是感人至深。
1946年,二人在北京舉行了婚禮。從那時起一直到晚年,二人相濡以沫,再也沒有分開過。他的女兒和兒子任遠和任重在緬懷任繼愈的紀念文章《永遠珍藏的記憶》中寫道:“2005年媽媽不幸去世。爸爸在送別卡上這樣寫:‘鐘蕓,你暫時離開了,可是我們永遠在一起,永不分離。媽媽告別儀式那天,爸爸早晨3點多就起來了,仔細地洗頭、洗澡、剃須、穿上干凈的白襯衫。在遺體告別儀式的兩個多小時內,他身后椅子也不曾坐一下。儀式結尾,家屬做最后的告別時,爸爸走到媽媽旁邊,伸出手去,輕輕地、輕輕地摸了一下她的頭發和臉龐,好像怕驚醒她的睡眠。眼淚順著爸爸的臉流下來。”
這就是一代大師任繼愈的感天動地、山高水長的芬芳愛情。
責任編輯:子非
美術插圖:段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