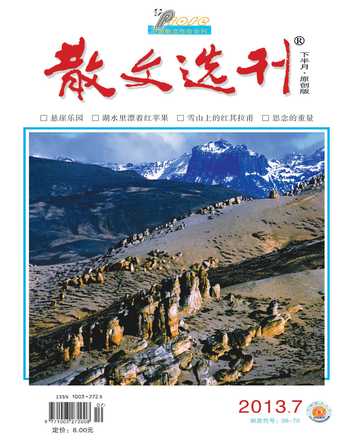書信背后的故事
黃紅衛
念書念到四五年級的時候,祖母叫我替她寫信,信是寫給祖母的女兒的。
祖母的女兒,我應該稱“姑媽”,但是我不認識姑媽,這姑媽是祖母與前夫所生,也就是說,當年祖母是以寡婦的身份與我鰥居的祖父結合的,是我父親及伯父的后娘。祖母嫁過來時,把唯一的女兒送給人家做了童養媳。那時,我父親4歲,伯父8歲,往后的日子里,祖母與祖父并沒有生下一兒半女。
祖母與我身邊所有的祖母一樣,勤勞、慈祥、仁厚,四個孫輩她親手帶大了兩個——大孫子及我這個小孫女。對于祖母的吩咐,我向來是言聽計從的。
常常是這樣開始寫信的,我準備好紙和筆坐在祖母的身旁,端坐著的祖母表情是莊重的,語速是緩慢的。通過祖母的講述,我了解到姑媽的生活非常不易,婆婆厲害,男人強勢,加之久不生育,姑媽處于仆人的地位。這也是姑媽不往親娘處走動的原因之一。另外,我了解到,姑媽好不容易生養的一女,那個我應該稱其“姐姐”的女孩兒,有個別致的名字——小農。因為小農,我陡然增加了寫信的興趣,甚至想象小農的長相、舉止、衣著打扮。有一次,我在信尾自作主張添加一句:希望小農姐姐來玩。
姑媽與小農終于出現在我們面前時,我在念高中,而小農早已輟學務農了。她們娘倆一副風塵仆仆的樣子,據說乘坐了半天的汽車,又步行了半天。我不知道小農是否沖我信中的“邀請”而來,她喊我“妹子”,拉過我的手翻來覆去地看,說這手又白又嫩,不是吃苦的相。小農屁股沒坐穩就開始幫祖母干活,自留地栽種,澆水,洗蚊帳、被子,動作之快令我汗顏。這是我們家與祖母至親唯一的一次友好交往。
不久,父親帶我們移居到了幾百里外的城市,伯父家搬到了幾十里外的縣城,曾經熱鬧的宅園僅剩祖父祖母枯守。在這段時間里,因婆婆離世開始當家做主的姑媽來往得很頻繁。祖父去世剛過“七七”,父親突然接到姑媽的通知,姑媽說她準備把祖母接到自己身邊去贍養,要這邊的兄弟倆一次性付清一筆贍養費,從此井水不犯河水,互不來往。待大家匆匆趕回老宅時,姑媽已替祖母打點好了行裝,任兄弟倆如何勸說,她們去意堅決。祖母走了,帶著“落葉歸根”之外諸多不可違逆的世俗。
祖母走后第二年,父親違背姑媽的約定動用單位的小車率我們去看望祖母。好不容易找到姑媽家,不冷不熱的姑媽指著堂屋里的一張床對我們說,外婆走親戚去了。我們問親戚家在哪?姑媽說遠哩,你們尋不到的。帶著種種疑問,我們無奈離開。望著祖母床上那條熟悉的藍印花老布被面,童年的記憶祖母的氣息撲面而來,我不禁淚水潸然。
后來,有曲里拐彎的消息傳來,說祖母其實不在姑媽家,而是與一老翁生活在一起。我不相信,80高齡的祖母,絕對不會另結姻緣的,何況,我們這邊已付足了生活費。
但很快,又有確鑿的消息傳來,祖母已經去世。果然,姑媽連憑吊的機會都沒給我們。
20年光陰,可以沖淡一切,比如恩愛,比如仇恨。
20年光陰,卻讓我把對祖母的懷念沉淀了下來。我清楚,這份日積月累的沉甸甸的沉淀需要釋放,我更清楚,釋放的最佳形式,只有寫信了。因為在過去的20年里,我與大阿哥偷偷尋找過祖母骨灰的下落,終因人生地不熟而不了了之。
我鼓足勇氣拿起筆,憑著記憶中的地址,給小農寫了一封信。為什么寫給小農,是經過權衡的:一則以我推測,作為當事人姑媽,恐已不在世間了;二則小農畢竟是同齡人,容易溝通。信是這樣開頭的:“小農姐姐,冒昧了。你還記得你外婆有個孫女嗎?我就是那個孫女。今天打擾你的目的是想知道我祖母的墓址,清明節快到了,我想去祖母的墓前祭掃,寄托這份無處安放的哀思,僅此而已。我一直沒忘記祖母,在我心目中,祖母就是我的親祖母。若把我倆放在天平的兩端稱,祖母的情感砝碼肯定偏向我這邊的。都說滴水之恩當以涌泉相報,遺憾的是我永遠沒有機會回報了。我想我此舉不會傷害到任何人,牽扯出任何事;我想我此舉祖母的在天之靈是愿意看到并樂意接受的。小農姐姐,請相信我。如方便的話,請幫助我……”
人心總是向善的。
今年清明節,在異鄉一座陌生姓氏的祠堂里,我與大阿哥雙雙跪拜在刻有祖母姓名的碑前。一旁小農姐的手心里,始終攥著那封我寫給她的信……
責任編輯:黃艷秋